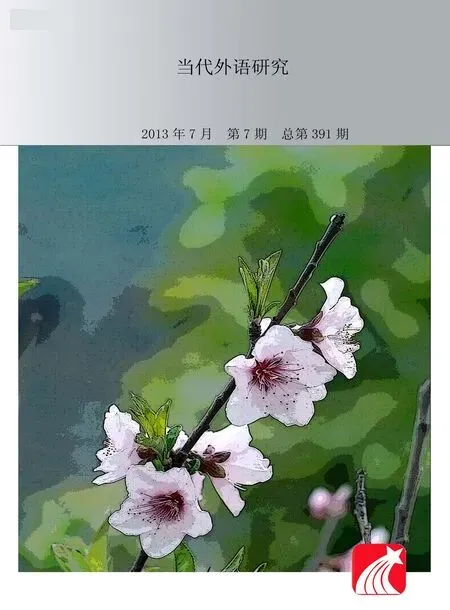《意义新论》
——第4章 意向敏感性表达式
(英)埃玛·博格 著 伍思静 译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吉林大学,长春,130012)
本章论述的问题涉及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强烈的直觉认为讲话者的意向至少在某些案例中同指称的决定相关;而另一方面,本书旨在捍卫一种语义理论化路径,该路径注定将当下讲话者意向看作同语义内容的确定无关。究竟为何最小语义学不认为讲话者意向具有语义相关性,这个问题将在第1节进行探讨。一旦阐明了这个问题,就会清楚理论家可能追循三条路径:其一,否认讲话者意向确实同指称确定相关这一假设(第2节的内容)。其二,否认最小语义学不接受指称性意向这一观点(第3节的内容)。其三,试图将指称确定的问题与语义内容的问题分开(第4节的论题)。头两个假设都面临若干显然很严重(并相联系)的问题。因此,最后这个方案为最小论者提供了可以择取的最佳解决方案。采用这一方案,理论家就可避开如下担忧,即掌握包含语境敏感表达式的合乎语法的句子之语义内容需要诉诸话语语境的丰富内涵方面。这样,最小论就可以保持其观点不受语用魔法的影响。
第1节语义相关的意向问题
文献中反复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语境敏感性表达式似乎会对语义学形式论路径造成困扰——用戴维森的话来说,它们“实在是令人扫兴的东西”。①这种表达式造成的部分问题(但不完全是戴维森本人所担忧的问题)涉及当前讲话者意向在确定至少某些此类表达式的语义内容时所起的表面作用。(下文将集中探讨指示词语,因为这些词语为那些语义贡献由讲话者意向确定的表达式提供了最强的直觉性案例。然而,假定意向敏感性词项的类型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至少包括指示语[见普雷德利1998ab]和名称[见克里普克1980])。下文指出,这种担忧在形式语义学更加极端的(最小)一端最为严重。然而,从一开始就应该清楚,为什么讲话者意向原则上对任何版本的形式语义学都具破坏性。这一担忧可以看作视角的冲突:形式语义学旨在进行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之间的类似比较,以阐释直接来自语言可编码形式特征的字面意义。其目的是揭示句子意义(无论某人说出特定句子处于何种动机,这种意义都成立),将其完全看作由句法形式与词汇意义决定。然而,如果语义理论总的目标是揭示可重复且可编码的特性,那么显然,认为自然语言中某类表达式的语义贡献由诸如当下讲话者意向这种模糊而又高度语境敏感的特性决定,就是成问题的。其语义贡献由当下讲话者想法决定的表达式,在将语义内容看作本质上不受具体讲话者的变化无常与奇异特性所影响这一路径中,处境尴尬。因此,从一开始,允许将当讲话者意向看作与语义相关就违反了形式语义学的精神特质,并(通过公开允许讲话者以言行事,生成意义而)冒了令立场滑向用法意义论的风险。
而且,这是形式语义理论的性质与目的同讲话者意向的性质之间的先验张力;如果出现更加严密的语义学方案,这种张力就会形成一种表面上非常有力的质疑。因为正如第1章所阐释的那样,最小语义学认为,通达意义的道路仅由演绎性推导过程铺就。②对最小论者而言,意义纯粹沿着句法的轨道行驶,从句法移向语义的过程是可以形式地表明的(如,通过真值条件的规范性推导)。③然而,在这种框架内,任何诉诸讲话者意向的行为似乎都是不当的。因为推论讲话者意向似乎显然不是演绎性的:为了推断某人在想什么,需要进行大量由内容驱动的推理以寻求最佳解释——这种推理是最小论者在复取语义内容过程中极力避免的。这一点已在别处(博格2004b)论辩过,其中心思想是,在归赋心理状态时,某人所知任何东西理论上都是相关的,尽管实践中人们仅仅利用所了解的各种内容中的极小部分。这种理论上的开放性与实践中的限制相结合,似乎表明归赋心理状态所用的推理并不仅仅是结构的作用,而且还受所包含信念内容的影响。
这样,最小论者面临的问题可以表述如下:
(P1) 至少某些表达式对句子所做的语义贡献依赖于说出这些表达式的讲话者的心理状态。
(P2) 关于他人心理状态的推理需要做出达致最佳解释的推论。
(P3) 根据最小论,复取语义内容过程中所涉及的只是易于做出推演处理的演绎过程。
(C) 最小论不能解释至少某些表达式的语义贡献。
将问题这样呈现出来之后,显然最小论者也许至少可以采取三种策略对此论争做出回应。最显见的策略是拒斥(P1):尽管乍看起来情况相反,但认为讲话者意向与指示词语或者其他表达式指称对象的确相关这一观点可能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可称为关于指称的“约定论”,将在第2节考察。另一方面,最小论者也许可以考虑反对(P2)。尽管依据上文所绘,讲话者意向看似并非易于进行形式处理的过程,但这种看法恐怕有误。提出这种想法的一个理由来自认知科学最近的研究成果。在认知科学中,有人提出某些心理状态(包括指称意向)与体现心理状态的行为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第3节将考察这些研究,看看它们可能如何解决最小论者的难题。最后,最小论者坚持认为,这一论证实际上是无效的,也就是说,最小论者可能接受(P1)-(P3),但却否认这几点合在一起蕴含着(C)。这一观点将在第4节探讨。
第2节拒斥(P1):关于指称的约定论
尽管指示词语表达式的指称对象由讲话者意向决定这一观点最初看来貌似合理,但是可以拒斥这一假设,转而认为,语境敏感词项具有约定的使用规则,该规则决定例型表达式的指称对象,无需诉诸讲话者意向。指示词语的约定规则要么诉诸指示动作(指向性手势,等等),要么诉诸指示动作伴随其他发挥指示作用的语境线索。例如,卡普兰首次引入纯指示语与真正指示词语的区别时提出,指示词语需要来自话语语境的附加特征以确定指称对象,即指示动作。与指示语不同,若没有指示动作,指示词语会被看作是语义不完整的。(至少卡普兰早期认为)正是这种附加指示动作,而非任何相关意向,决定了例型指示词语的指称对象。④显然,倘若结果证明指示负责确定指称对象,而且指示本身能够以非心理方式个体化(这一点下文将再作讨论),那么上一节的问题根本不复存在。因为结果会证明(至少从确定指示词语的指示对象这一视角而言)并不存在诸如具有语义相关性的讲话者意向这种东西。
然而,这种策略直接引发的担忧是,至少某些指示词语似乎无需伴随的指示动作就完全能够发挥作用。卡普兰自己举了一个例子,面对一排士兵,其中一个士兵突然晕倒。在这个场景中用不着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做手势指着那个士兵,就可能对该士兵实施指示性的指称行为。⑤同样,人们能够指称抽象客体或者处于直接感知环境之外的客体(例如,通过所谓“延迟指称”,指着一幅画而指称其作画者),尽管这种指称对象似乎不能作为指示手势的对象出现,等等。即使就指示词语而言,指示行为(的非意向性解释)能够有所帮助,这个解释也不容易扩展到诸如指示语的其他不需要指示动作相伴的表达式。正如本章开头所指,可能有理由认为,讲话者意向也同这些表达式语义内容的确定相关。
对这类担忧的一个明显回应是从集中诉诸身体姿势扩展到包括(话语语境之内或之外的)任何相关特征。⑥据此,虽然用手指明和头部姿势等可能有助于确定指称对象,但这些并不一定提供了确定指称对象的全部手段。也许可以将指示词语诉诸指示动作的约定性使用规则与其他语境线索结合起来。⑦约定论者可能诉诸的这类特征包括:凸显性、先指性、关联性、宽容性、指示动作、在序列中的位置,等等。⑧如果指称对象的确由这类特征而非由讲话者意向确定,那么第1节的论证看来就无法成立了:最小论不能在语义层面对讲话者意向作出阐释,这一点无关紧要,因为在语义层面无需诉诸讲话者意向。
而且,此处看来很有理由接受某种形式的约定论。(科拉扎等人强调过)理由之一源于对避免“汉普蒂-邓普蒂论”之需要的唐纳伦式关注。“汉普蒂-邓普蒂论”允许词语意谓讲话者想让其意谓的任何东西。⑨对于非语境敏感性词汇,这一方案显然不可接受:“红色”意谓红色,即使此时我意在用其指称蓝色。不过,这种词义的放任对于语境敏感性词汇同样是错误的。设想一个语境:一群讲话者站在一辆红色保时捷周围欣赏着这辆车。如果其中一人这时说“那是我最喜欢的车”,意在说她最喜欢的车是停在拐角的白色捷豹,那么,不管其没有公布的意向是什么,都有道理认为她语义地指称面前的保时捷。毕竟,在这个语境中,任何具备语言能力的听话者都会认为讲话者指称的是保时捷而非捷豹;而讲话者后来无论多么努力声称这并非她所说的意思,都可能不被理会。在这种情形下,讲话者意向被正常听话者事实上能够复取的内容因素遮蔽了;那些因素转而又由关于语境敏感性词汇如何确定指称对象的客观规约决定。看来,指示词语只能用于指称正常讲话者所能复取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地用于指称讲话者心中的任何想法。这类实例致使科拉扎、菲什与戈伟特(2002:17)提出:
我们不……必诉诸讲话者与/或听话者的个性化意向以阐释指示性表达式的指称。规约性地给定的语境参数是我们所需诉诸的一切。
假如这一点正确,那就提供了第一个最小论解决方案,用以解决指示词语与其他表面意向敏感性词汇所引起的问题。
然而,经过思考,并不那么清楚“汉普蒂-邓普蒂论”指控针对意向论者是否真正成立。究其原因,就在于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正确,即讲话者意向不受约束,无法确证指称性交际行为,但意向论者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如,要求指称意向为交际意向)对所感兴趣的一套意向加以限制。⑩或者,意向论者也可以接受以下观点:讲话者使用指示词语的方式不能为听话者理解(如,使用“那个”指称某个客体,但并不存在可用以帮助听话者识别这一意向的语境线索),则注定不能在所参与的任何交际活动中取得成功。然而,意向论者可能将此看作在交际层面的失败,并不影响意义层面:虽然讲话者使用的语言表达式其意义不能为听话者理解(因此根据格赖斯理论不是一个合作的讲话者),但这并不能阻止该表达式具有其固有的字面意义。
因此,约定论的动机有几分令人生疑。而这个解释本身也面临严重质疑,因为看来它所诉诸的那些旨在取代讲话者意向的概念本身就需要意向性输入。例如,使某个身体动作成为指向一条狗的动作(而不是指向狗的项圈、毛色或者位置,等等),并不只是动作的身体定向特征,而且涉及施事意欲用其手势指明什么。在指称确定的问题上,约定论似乎推迟而非真正消除了对讲话者意向的诉诸。雷卡纳蒂(2004:57)写道:
通常假定……指示词语指称在相关语境中碰巧所指示或最凸现的物体。但是,“指示”与“凸现”这些概念是伪装的语用概念……最终看来,指示词语所指称的是使用这些词语的讲话者用以指称的对象。
除非“指示”这一概念完全被理解为涉及身体的概念,否则就不会有助于对指称确定做出非意向性的解释。然而,以这种纯粹与身体相关的方式来理解指示,显然不能充分确定指称的归赋。这一质疑维特根斯坦(1981:81-2)注意到了,却并未被打动:
指向的不确定性……不能使[这样]诉诸指称意向成为必然……孤立地看,手势是不确定的。但,当存在另外的线索,如,谓词表明讲话者意在谈论某人,而在指示范围内又不存在其他任何人时,手势就能充分指明。
正如前面雷卡纳蒂的话所示,不确定性的问题不但可以针对指示,而且也可能针对约定论者想要诉诸的大部分其他因素(事实上,所有这些因素都阻碍特定表达式的语言意义)。以豪克尔(2008:365)“序列中位置”的标准为例。根据这一标准,说出“那个”也许可以认为指称序列中的下一个客体。可是,看来讲话者的心理状态必定起着某种作用,因为任何客体都出现在无数的不同序列中(例如,位于说话者左边的客体,在x/y轨线上离埃菲尔铁塔最远的客体,等等),而哪个序列相关似乎只能通过诉诸讲话者的意向状态确定或者同样,考虑一下在此诉诸凸显性(韦特施泰因也尝试性地采用了这一方式,参见1981:注31):认为在语境中凸显内容的确定总是无需诉诸意向状态这一观点根本就是错误的。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客体得到普遍性关注的实例,如卡普兰的晕倒的士兵,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语境中算作凸显的内容依赖于施事主体及其意向框架。依据身份的不同(受过训练的鸟观察员、花卉爱好者或昆虫学家),物理性描述的特定场景中什么东西是凸显的会有所不同。但是,假如是讲话者与听话者的兴趣决定凸显的内容,那么凸显就不能在对指称确定作出的非意向性简约阐释中发生作用。最后,即使在韦特施泰因的上述例子中,手势加上谓词能确定指称对象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考虑延迟指称的情况。在关于雇主的对话中,x指着某人说“那个人为种族关系做了很多事”可能成功地将x的雇主y而不是x作为指称对象,即使x是唯一处在指示范围内的人。(还要注意,正如斯特劳森[个人交流]所说,至少在某些场合,谓词非常笼统,对确定指称对象几乎没什么帮助,例如,“那不错”。)
为了确定指称对象,必须对约定论者诉诸的因素本身做出意向性的(心理)表述。这种认识显然只是奎因抱怨(即指称在性质上是确定的)的一种体现——仅凭可直接观察的身体动作,解释者不能对指称性表达式做出唯一性的解释。尽管约定论者的观点相反,但是看来意义并不只是在显性行为中表明的。而且,以话语语境的纯客观特征来取代讲话者意向的这一方法似乎削弱了指示词语存在的理由,使这些表达式的全部目的都在于令讲话者获得空前的自由,以对世界事物进行语言指称。通过延迟指称,指示词语可用以指称,如通过某人所写的书、拿着的书或者最近读过的书来指称某人。通过某人的胳膊肘、某人所处的位置,或者所犯的罪行,指示词语可用以指称某人。指着一幅画凸显作画者或者挂画的人;指着电视上人脸的图象帮助指称长着这张脸的人或指称拍摄这张图像的摄像师。这类能够佐证延迟指称行为的各种关系似乎无穷无尽。但是,这种创造性和新奇性似乎严重地削弱了如下观点,即可以在使用指示词语的约定规则中列出一系列(非意向性)因素,它们将始终正确地预测指称。事实上,即使能够以某种方式提出一个详尽的列表,列出所有延迟指称可能出现的方式,那似乎也只有诉诸讲话者意向才能确定在所指客体与实际指称对象之间的众多关系中,哪一个关系在“那”的某个特定延迟用法中是真正涉及的。
因此,直接从指称确定的问题中清除说话者意向这一做法看来是有问题的。这不仅有悖于我们强烈的直觉,即讲话者意向对于确定所说出的语境敏感性词汇的指称对象的确具有相关性,而且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循环论证的威胁就赫然而现:为了取代意向而诉诸的概念(指示或者那些集于约定性使用规则之下的概念)本身就偷偷采用了意向性概念。而且,如果试图从规约性特征中割除所有意向性内容,那这就会面临奎因式质疑,即无论多少身体行为本身也不能决定唯一的指称性解释。因此,摒弃(P1)的企图失败了,最小论者必须找到另一种方法以避免(至少在他们看来)不合意的结论,即最小论的学说无法充分阐释自然语言的语义内容。
第3节拒斥(P2):非推理说
避免意向与语义相关问题的第二个办法是质疑以下论点,即从形式语义学理论视角来看,当下讲话者意向是有问题的。虽然为了达致他人意向,就需要进行丰富的反绎推理,但这也许是错误的,至少对于关涉解释指示词语话语的那种指称性意向而言是这样。因此,预防第1节中问题的一个方法可能是缩小下面两者间的差距,即显然可以直接从话语语境中获得的特征与显然是隐含的且经过推理而复取的讲话者在该语境中的意向状态之间的差距。这样,听话者无需进行大量的推理也许就可能了解指称性意向。这一立场最为熟知地与维特根斯坦(1953)的理论相关联,但麦克道尔对此也有清晰的阐述,他(1978:304)写道:
在相关场合,断言他人疼痛的根据是,获得那个人疼痛的可察觉情况:那个人疼痛这种情况的例子本身就能为意识所察觉,而不只是通过行为表现才意识到。
这种办法相当于“非推理说”:对他人状态的开放性穷尽了赋予其(某种)心理状态的方法。因此,在看见甲以方式p做出行为与赋予甲以相关于p的心理状态m之间,没有推理性的步骤可以采取——只是从他人的行为中理解其心理状态。非推理性地直接达致(某些)心理状态这一观点也出现在近期关于心理解读研究的模拟论方法以及对立的理论-理论方法中。在模拟论方法中,诉诸非推理说与所谓“镜像神经元”提供了心理解读的神经学基础这一观点紧密相联。在理论-理论方法中,有关的观点是直接通过行为的意向派赋(有时称为“身体解读”)构成了完备的心理理论前身。既然这两种理论阐释都明显地可望通过非推理路径达致讲话者的指称性意向(从而为最小论者提供了一条路径,以避免第1节中的问题),所以下文将简要考察每一种方案。
3.1 模拟论和镜像神经元假说
根据模拟论,我们通过“设身处地”的移情过程,将心理状态派赋给他人:通过使用自己的意向性机制,在“假装”推理的过程中利用自认为他人很可能拥有的信念和意愿进行推理。然后,将这个意向性处理过程的结果派赋给他人。重要的是,这种“假装性”推理并不导致行动,而如果这是对相同机制真正的、第一人称的使用,就会导致行动:当我使用自己的推理系统推断时,若你因为相信自己正遭到熊的攻击而蜷成一团,这并不蕴含我也会蜷成一团。以其本来的形式,模拟论是可以(按照加拉格尔2006:4)称之为“显性”理论的东西:认为在心理活动某个相对较高层次的有意识阶段,人们是在模拟他人。不过显性模拟看来并不能为最小论者提供多少帮助,他们所需要的是对指称意向的复取作出阐释,这种阐释并不诉诸达致最佳解释推论的反绎推理。此处观点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将指称性意向看作由行为直接实现。然而,假如现在允许对指称性意向的掌握不是目睹行为的直接结果,而是利用了完整显性模拟过程的结果,似乎就再次回到对意向归赋做出大量推理的间接解释。正如加拉格尔(2001:93)所指出的那样,显性模拟论最终同替代性的理论-理论方法提出的心理解读具有同样的观点:
理论-理论说与模拟论都将两人之间的交际互动理解为发生在两个迪卡尔心灵之间的过程。这样的看法假定人们的理解包含了退回到理论或者拟像的领域,退回到一套内在心理操作,这些操作会在话语、手势和互动中得以表达(外化)。与此相反,如果将交际互动看作正是在交际行为中通过话语、手势或者交际本身完成,那么,对他人的理解涉及将看不见的信念做理论表述即心理解读这一观点就是成问题的。
加拉格尔在此指出:模拟论和理论说(以其通常的形式)保持了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距离,因而两者看来都坚持心理状态的复取必定是一个推理过程,该过程基于显性行为但并不完全由其体现。然而,模拟论似乎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
与显性模拟论相反,隐性模拟论认为模拟出现在亚个体层面,是对另一个施事者表现出的行为所作出的相对直接或自动的反应。这种隐性模拟论形式常常与人(及猴)脑中所谓“镜像神经元”的发现相关联。镜像神经元(MNs)是在两个不同条件下激活的神经元:
(ⅰ) 施事者发生具体的运动行为(例如,用手指抓住)。
(ⅱ) 观察同类实施(ⅰ)中的运动行为。
在(ⅱ)中,镜像神经元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离线的”,不能引起在(i)中所目睹的运动行为。人们发现当施事者做某事以及当施事者目睹其他某人正在做某事时,我们的大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一发现为心理解读的模拟论提供了佐证。加莱塞与戈德曼(1998:497)写道:
让我们将MNs里内部产生的激活理解为构成执行某一行为(例如,握住某一物体、抓住或把玩这个物体的行为)的计划。当相同的MNs——通过观察目标施事者实施行同样的行为——由外部激活,MN的激活仍然构成执行这个行为的计划。但是,在后一种情形下,MN活动的主体(视觉上)知道所观察的目标主体在同时实施这个行为。因此,我们假定他将有关的计划“标为”属于该目标主体。
可以将MN活动构成计划的观点称为“MN假说”,从而提出如下问题:“模拟论与MN假说一起能否为最小论者提供办法,解决第1节中针对最小论提出的问题?”
第1节所提质疑的基础是指称性意向的复取并非句法驱动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不只依赖于表达式的形式特征。因此,力图为语义内容提供一条纯形式句法路径的形式语义理论似乎不能阐释指示词语表达式,因为这些表达式的语义贡献由讲话者的指称性意向确定;然而,基于眼下的理论图景,至少将某些心理状态派赋给他人事实上并不是听话者这方进行丰富反绎推理的结果,因为这根本不是推理的结果。在此,将心理状态派赋给他人是目睹其行为的自动直接结果(这种行为在心中引发MN活动,相当于形成行为的具体计划)。这就规避了对最小论的挑战:形式论承认这些讲话者意向具有语义相关性,因为施事者得以掌握这些意向的途径,并不是通过某种复杂推理假设关于听话者整个信念集的相关成份是什么,只是通过讲话者行为导致听话者将具体意向状态派赋给讲话者。
3.2 理论-理论说与身体解读
非推理论在心智解读的某些理论-理论路径同样突显。这些理论路径通过将他人的行为归于十分普遍的心理学规则之下而对其加以理解。业已证明,理论-理论路径要陈述这些规则有些困难,但是可以假定这些规则具有某种如下形式:
如果A想要x,并相信做y是引起x的一种方式,那么,若其他情况不变,A将会做y。
理论-理论路径常常出于对经验性数据的考虑,这种数据表明,只有到了四岁左右,幼儿才能掌握类似于成人的心理解读技巧。具体说来,只有到了这个年龄,幼儿才开始认识到别人可能拥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或者具有与幼儿自己的世界看法不同的想法。解释这个令人惊讶之事实的一个方法就是假定存在不连续的心理学理论(关于心智的理论),处于这个发育阶段的儿童或者学会了这一理论,或者能够恰当地获取。而且,以这种方式理解心理解读能力似乎为理解某些类型的认知损伤(比如自闭症)提供了有用的途径(参见巴伦-科恩1995)。然而,还存在一些在理论-理论路径看来似乎是有问题的其他实验数据,因为看来显然前语言阶段的幼儿(即,在比四岁小得多的年龄)的确会做出至少某些类型的心理解读。也就是说,他们将他人看作意向性施事者,并能够认识并追踪其看护人的指称意向。事实上,后面这种技能作为语言发展的先导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理解对象词语的意思需要把握语言符号和外部客体的正确关系。只有当看护人引入一个生词时,能够认识看护人的意向,大概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布卢姆2000强调了这一点)。
由于需要对这些类型的原始心理解读技能作出阐释,理论-理论路径的某些倡导者因而假定了某种“心智第一阶段论”,作为习得完备理论的先导,也与行为追踪紧密相联。例如,巴伦-科恩假定,儿童通过使用两种先天机制获得某种非理性的意向归赋:其一,所谓“意向性探测器”(ID)令其将某行为看作意向性行为;其二,使用所谓“注视方向探测仪”(EDD)监控看护人的注视方向。巴伦-科恩(1995:32-3)认为:
ID是一个感知装置,它以目标和意愿的原初意志心理状态解释运动刺激。我将其看作原初心理状态,这是因为它们是最基本的心理状态;理解了这些心理状态才能够理解所有动物的普遍行动:接近与回避。
一旦存在适合于施事者的行动感知输入,ID就得以激活,因而可能生成过多的意向性归赋(并开始将目标和意愿派赋给机器人、各个移动点,等等),但是ID揭示了一个核心思想,即“目标探查是人类的固有特性,目标藉由某种行为感知而察觉”(34)。
ID和EDD,以及后来发展的能力,即巴伦-科恩所称的“共有注意机制”(SAM)一起,在发展出完备的心理认知之前,就构成了理解他人意向的早期(9-14个月)能力的基础。将不同的信念或者错误的信念归赋给他人需要完备的心理认知;但此处观点是ID、EDD和SAM足以使幼儿在通过错误信念检验之前,就能够进行相应的心理解读。具体而言,这三者足以将指称示意向归赋他人:ID与EDD结合,使幼儿可以将类似于“怀有鉴别出/指称x之目标”的心理状态加以归赋。显然,诉诸这类“身体解读”作为复取指称性意向的路径,规避了第1节中提出的问题:指称意向不需要通过丰富的推理过程复取,因为它们能径直在行为中看到。因此,指称意向在形式语义学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任何可视觉获及之话语语境特征可能发挥作用的方式完全相同。这样,身体解读产生了另一种假定的办法,以解决意向敏感性表达式对形式语义学造成的问题。
因此,(要么在模拟论中要么在理论-理论方法中)采用非推理论可能有助于规避免第1节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远不清楚这两种方法哪一个是实际可行的。对这两种理论阐释的担忧实质上还是奎因式不确定性担忧——认为无论多少行为证据也不能作出唯一的指称性解释。为弄清这一点,需再次简要考察一下这两种方案。
最小论的支持者(根据模拟论和MN假说)主张指称是由讲话者意向决定的,而听话者对这些意向的复取是一个由讲话者行为直接触发的自动过程。藉此,他们是否就能规避指示词语的假定问题呢?遗憾的是,似乎不能。问题在于,要帮助最小论者,MN活动似乎出现在了错误的描述层面上。MNs通过目睹某个行为促发,但是(从第2节已经熟悉的一点上)这样的身体姿势不能充分确定导致行为实施的确切意向。这就是说,喝水的意向和细看杯子图案的意向可能都会导致施事者A用手指准确把握住杯子。然而,目睹A动作的同类B激活MN的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是相同的。因此,就MN激活可以视为计划形成这一范围而言,它所的描述过于粗略:MN激活也许有助于将准确的抓握理解为意向性行为(与由外在于施事者的因素引起的行为相对);但这看来对诸如将某个抓握动作理解为抓住杯子喝水而不是抓住杯子观看没有帮助。同样,MN活动也许能帮助听话者H将讲话者S举起胳膊、伸出食指的动作理解为意向性动作本身,但是这并不有助于确定其独特的指称意向(即,指称狗而非狗项圈的意向),因为所目睹的行为(而使MN受到激活的方式)在这两种情形下是相同的。显然,为了确定指示性话语的指称,需要更加精细的意向归赋。因此,既然在掌握确定指称的意向之前,听话者这方还需要作出进一步推理,所以,MN假说不能为最小论者解决意向敏感性表达式的问题。
不过,MN假说的支持者也许不会接受这个观点,相反会提出MNs不只确实能够揭示行为的内容,而且能够揭示行为的原因(借用亚科博尼等人2005的术语)。最近,西尼加利亚(2008,回应博格2007b时)指出,镜像神经元不仅对物理描述的身体动作敏感,而且还根据下述因素区别性地作出反应:所实施的行为类型、行为对象的提供以及有关行为包孕其中的动作层级结构。他(2008:75)写道:
MNs以行为自身的运动目标相关性编码将要实施的行为。这种目标相关性确定运动行为,将其表征为具有自身运动关涉性的行为,以具体的方式(如,抓住、握住、摆弄,等等)指向(具有某种形状、某种尺寸等的)特定对象物体,而不只是“纯骨骼行为”或身体系列动作。
于是,这种运动目标相关性被认为是一种意向认识。在这方面,两个实验看来尤为重要:其一是乌米勒塔等人(2008)的“反向镊子”实验。实验中,下面两种条件下完全相同的神经元式样被激活:一是施事者使用/目睹使用一把普通镊子的行为(比如,用镊子夹起一粒坚果送到嘴里);二是实施/观察使用反向镊子做出相同的动作(这需要做出相反的身体动作以完成全部动作)。这些发现佐证了之前的发现(里佐拉蒂等人1988与里佐拉蒂等人2000),表明同一个身体可以为不同的神经元式样编码。这取决于该姿势包孕其中的上一级目标导向行动(因此,取决于是拿起食物去吃这一动作的一部分还是将食物放到别处这一动作的一部分,弯曲手指这一动作以不同神经元式样编码)。其二,卡塔内奥等人(2008)最近一项实验表明,在动作最初出现时,在MN层面会对按不同意向做出的相似动作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我们早在做出伸手动作的阶段,就认识到拿起食物吃的动作与将之拿起放到别处的动作是不同的)。在这些实验中,不管用于实现该意向的系列运动行为如何(如,在认识到主体的意向是捡起坚果来吃的过程中,一种MNs式样得到激活,不管在捡起的过程中包含了哪些具体的身体动作),MN激活式样既能对施事者意向作出不同反应,又能够在完成动作之前认识意向,因而可以在预测和解释他人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些结果假若证明可靠,那就的确表明MNs在将意向归赋给他人中起着有趣的作用(虽然这两组结果都是新近获得的,但所涉及的方法还有问题要探讨,如样本的大小)。然而,尚待考察的是,这种解释作用能否扩展到指称意向的认识(这是目前讨论的焦点)。问题在于,指称意向同行为的联系似乎逐渐减弱,因此旨在对他人行为作出反应而设计的方法看来不大可能独自揭示这种意向。譬如,虽然在运动行为系列的某一点上“拿起东西吃”和“拿起东西放置”必定体现出行为上的差异,但对指称意向而言情况却并不相同。如前所述,同一个指向手势可能构成指称一条狗、狗的项圈或者狗的毛色等意向。这种不同并不需要讲话者在任何总体运动行为中显现出来。基于MN理论框架,西尼加利亚对行为假定的那种“运动关涉性”似乎仍不能体现为指称意向归赋所需的那种关涉性。乍看起来,将某动作(如,指向的手势)认识为意在指称具体对象或性质而实施的行为,仍然需要高层次的意向性解释。这种解释是西尼加利亚自己所期待的,以抵制MNs层面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主张,因而可以做出经验性的反驳。也许最后会证明,MNs的确为归赋指称意向提供了基础,然而目前尚无实验证据佐证这一观点,也没有什么理由对其持乐观的态度。
如其不然,那么,以巴伦-科恩、加拉格尔和其他人的“身体解读”形式出现的非推理说是否能为最小论者应对第1节中提出的挑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呢?同样,似乎也不能。究其原因,即使我们将身体解读看作对所有外在证据都敏感(包括讲话者话语中任何语境敏感性表达式的字面意义,等等),看来依然或者指称意向不能完全在这个行为中表达(还需要某种推理行为),或者使该行为个性化本身就需要丰富的推理。指着一个女孩说“那是我最喜欢的”可能包含一种指称行为,指称她的衣服、发型或车。在指称对象的这些变化中,讲话者的身体行为不需要任何变化。而且,即使考虑到更广泛的语境特征(如会话主题)似乎也不会有所帮助,因为讲话者始终有可能打算改变会话的走向。正如鲍德温和贝尔德(像塞尔那样)所述:
在大多数若非全部情形下,人们做出动作的表面流向与意向的大量差异一致。因此,在观察他人行为时,需依赖其他的信息来源——关于人类一般行为的知识、关于特定个人的具体知识、关于场景的知识——才能消除歧义,确定在许多可供选择的意向中哪一个与特定情形相关……其要旨是,辨别意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植根于结构探察又由知识驱动。
如上所述,认为意向不完全由行为体现的观点重现了关于不确定性的老生常谈的奎因式关注。然而,这种关注已为某些认为行为体现原初意向的支持者所认识,如阿尔比布等(2005)。他们(2005:247)写道:
我们的方法将感知、行为构建和词义结合起来,尽管很多关于语言习得的研究假定手势蕴含指称歧义……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奎因的经典论著(1960),其中奎因讨论了人们在谈论并指向一只兔子时所蕴含的指称歧义。但是,孩子的看护人往往会准确地集中注意力,不会只是简单地一边指着某个东西一边说出某个不熟悉的词(诸如奎因的gavagaz)。相反,看护人会一边摩擦兔子的皮毛,一边说“皮毛”,手指一边沿着兔子耳朵的外廓移动一边说“耳朵”,一边抚摸整只兔子或者转动整只兔子一边说“兔子”,等等……成功的教学必然要求注意所说的内容与所发生的事情一致。
然而,很多哲学家都会怀疑,这低估了奎因挑战的力度:(阿尔比布等人设想的那种)白板式儿童面对看护人手指一边沿着兔子耳朵的外廓移动一边说“耳朵”,并不能确将这个词的意思理解为耳朵,而非将之理解为兔子耳朵的颞部或者兔耳的形状。(我们可能会认为,阿尔比布等人描绘的看护者/幼儿之间的互动只在显性教学场景中是正确的,但儿童的词汇习得显然超出了他们接触的显性学习场景。)复言之,只有增加某些背景信念(比如,就幼儿而言,关于讲话者往往会感兴趣的东西的一般信念;就成人而言,再结合关于具体讲话者的兴趣等更具体的信念)和基于这些背景信念与讲话者当前表现的反绎推理行为,才有望确定指称意向。
正像赫尔利(2006:222-3)所做的那样,也许还要指出,将意向确定看作与行为跟踪具有如此紧密的一致性,这一做法可能面临模糊这两种能力之间的真正差别的危险:
心理学家问:真正的心理解读与聪睿的行为解读之间有何功能性区别(怀滕1996)?动物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能够仅仅通过行为-环境的关联以及相应的行为预测解决,无需假定中介心理状态。也许可以说,我们所能“真正观察”的是环境中的行为:从行为推论心理状态。然而,心理解读者不仅跟踪其他施事者的行为,而且还通过他们的心理状态理解他们。心理解读者能够将意向归于他人,即使其行为不能实现其意向;他们能将信念归于他人,即使这些信念有误。
因此,这两个通过某种形式的非推理说缩小行为与意向之差距的假定方法看来都失败了。施事者在他人行为中“直接看到”其心理状态这一观点尽管不无魅力,但是似乎很有问题,至少就指称意向而言如此。因此,前提1(指称意向是确定指称的标准的观点)和前提2(讲话者意向的复取通过丰富的非推演性推理过程实现这一观点)得到了佐证。如果最小论者需要接受(P1)和(P2),而且既然(P3)只不过表述了最小论所坚持的核心观点之一,那么其最后选择看来就是否认这种论证的有效性——从而表明,也许与最初的印象相反,存在以下可能性,即三条前提都接受,但此处并未蕴含该结论。
第4节拒斥该论证:
区分指称确定、指称识别与语义内容
第一章说到,最小论旨在对语义内容做出一种倚重形式的阐释。也就是说,它希望使复取任何合乎语法之句子的语义内容所涉及的过程是演绎性的推理过程——这些过程着眼于表达式的形式特性而非着眼于其内容。这样,最小论想要得到的是对某个句子语义内容作出如下阐释:它无需真正探究言说该句子之人的心理,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偷偷诉诸语用学的神奇魔法。然而,这个愿望与将讲话者意向当作与语义相关的需求冲突(因为讲话者意向似乎负责确定指示词语的指称),讲话者意向的复取是神奇语用学魔法的最典型实例。但是,想避免这个问题的最小论者也许会质疑要求最小论将语义内容所有方面都看成可追溯到形式的做法。最小论者坚持语义内容本身是溯源于形式的,这可能会将与确定或识别语义内容相关的某些方面排除在外。正如形式论会告之“伦敦的公交车是红色的”这个句子的意思,但它不会告诉你为什么“红色”意谓红色,而非蓝色。因此,形式论会告之“那是红色的”这一话语的意谓,而不会告之“那”这个例型指的是客体x,而不是客体y。
作出这个区分之后,最小论者就会接受如下观点:使“那是F”例型话语指称甲而不是乙的是讲话者指称甲而不是乙的意向。然而,它们依然坚持,例型“那”的语义内容为客体甲所穷尽。因此,听话者为了理解这一话语所必须掌握的内容即是单称命题“那个甲是F”,此处命题内容中并未提及讲话者意向。最后最小论者还可能认为,讲话者能够心存这个内容,即使不能非语言地识别甲;也就是说,如果讲话者能够将甲理解为讲话者用例型“那个”指称的实际对象。这样,为了理解指示话语的语义内容,听话者需要做的就是引入句法生成的单称概念,这个概念以客体甲作为内容,但它可能以更为复杂的严格描述语表达(也就是说,即使在思想层面,也需要区分场合意义与系统意义)。甲是这一话语的指称对象,这是由超越语义学层面的特性决定的。而且,为了将此语义内容投入使用(即用以告知某人同世界的交往),听话者通常需要接着非语言地识别甲。但是,重要的一点仍然是,就语言意义或语义内容而言,实际对象客体的识别这种问题是不相干的。
因此,最小语义论可能会对“这是红色的”的语义内容按照以下路径作出真值条件分析(引自希金博特姆1994:92-3):
(1) 如果说出“这是红色的”的人用这句话中的“这”指代x,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那么在此语境中,当且仅当x是红色的时,说出这个句子是正确的。
理解了这个框架内例子的人可能将相关的语境参数看作“说出该话语的讲话者所指称的实际对象客体”,这并不保证他们能够进而确定到底哪一个客体满足这一描述。尽管如此,最小论者可以认为,(1)的实例穷尽了在这种场合说出的句子的语义内容,这一内容无需对指称对象进行非语言识别即可掌握。如果接受了这种语义理论化知识的观点,这就产生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假定的解决办法,可应对意向敏感性词汇对最小论的挑战:讲话者意向在确定指示词语的指称对象中确实发挥作用,而且只能通过丰富的反绎推理复取。但是,同指称确定相关的特征(正像同非语言指称确定相关的特征那样)并非语义本身的一部分。
根据这一办法,认为指示性话语表达单称命题是正确的(这需要拥有单称思想)。但是,听话者能够持有以下命题:即使只能以严格的例型自反描述语将“那个”的指称对象认作“使用例型‘那个’(即‘dthat’:讲话者使用‘that’[那]之例型的指称对象)的讲话者实际指称的对象。”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必须承认,即使听话者(在任何实体的、非语言的意义上)不知道正在思考的是哪个客体,仍然能够掌握一个单称命题,即具有单称思想。显然,如果将语义知识理解为构建了更宽广知识框架的一部分(即,看作如整个心智这一宽广认知系统的一部分),那就可以接受在很多情况下,听话者能够非语言地识别讲话者指称的对象客体,因为纯语义之外的信息会发挥作用。即使这类情况是一种常态,但根据眼下的阐释,即便理解了“那是F”这句话的语义内容,听话者也可能无法非语言地识别例型“那”的指称对象。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有问题的。
一个担忧是,基于当前理论框架,必须允许有时听话者可能认为自己抱有单称思想而事实上却没有,因为没有对象满足“讲话者用其例型‘那’指称的实际客体”这一描述语(比方说,在讲话者产生了幻觉时)。然而,这种第一人称无法获及自己心理内容的现象是任何关于语义内容的外在论的普遍特征,因此看来并不能构成具体针对这里关于语境敏感性词汇的最小论阐释的挑战。当施事者不能非语言地确定指称对象时,还承认其抱有单称思想,这似乎仍然有些同直觉相悖。这一点很关键。虽然下一章(表面上讨论关于真正涉及世界的内容之要求时)将重新展开,但要充分探究单称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必须满足的条件则超出了眼下的研究范围。
据笔者之见,将单称思想局限于施事者可以非语言地识别指称对象这一做法的基础看来极其不稳固。首先,似乎并不存在可以发挥此处要求发挥之作用的(即,用以区分语义指称性表达式与非指称性表达式)非语言识别的实质性原则概念。一旦认识到指示词语不仅能够用以指称共享经验环境中的具体客体,而且还用以指称抽象客体或概念,指称以某种方式与那些处于经验环境中的客体相联系(抽象或不抽象)的客体(比如,通过某人明天将坐的座位来指向某人),那么通过某种概念的非语言识别对这种用法在某一点作出区分看来是完全任意性的。其次,这一观点没有为指示词语表达式本身的行为所证实,这些表达式都表现得似乎属于单一语义范畴的指称性词项。当然,倘若允许对指示词语语义内容的把握并不必然意味着指称对象的非语言识别,那么,在此就只剩下一个关于语义内容的精细概念。实际情形不会是脱离了其他类型的知识,语义知识确保能在世界上生活或者以适当的方式与客体互动。可是,这与其说是对最小论方案的质疑,还不如说更像是声明了一种信条,因为最小论者业已坚信语义内容本质上是最小的,它不能单独担负起理论家有时置于语义学的所有任务(这是博格2004a的主要论题之一)。
在此应当考虑的最后一点质疑源于豪克尔(2008)。尽管他明确区分了指称确定与语义内容,但却辩称讲话者意向不可能与确定指示词语的语义内容相关。根据他的论述,讲话者意向的复取依赖于语言意义的掌握:人们需要懂得某人言说了什么,才能懂得他在思考什么。因此,事实并不是必须掌握讲话者意向才能理解语言意义;否则就会陷入循环论证。他(2008:363)写道:
我【对讲话者意向决定指称这一学说】的异议是,这种理论指示词语的指称对象无法为听话者所获及。为了确认指示词语的指称对象,听话者不得不弄清讲话者意欲指称的对象是什么。但是除了独立理解讲话者的话语之外,听话者通常无法做到这一点。
此处有两点相关:首先,正如刚才所指,根据最小论者的观点,指称对象的非语言识别并非掌握指称性语义内容的构成性特征。基于这种阐释,指称对象有时候对于听话者(从非语言角度)不可获及这一事实与此无关。所以,用豪克尔的挑战来反对关于单称内容的最小论者精细概念不能成立。另一方面,也不清楚豪克尔的总体质疑——如果接受讲话者意向具有语义相关性,那么主体就没有办法“打入内涵循环”——是否真正成立。这是因为讲话者意向之语义作用的(非最小论者)支持者在这种情形下会辩称,虽然掌握当前讲话者意向对于理解目前话语语境下某些表达式(如,说话者的例型“那”)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是很多其他表达式并不共有这个特征(即,任何具有“稳定”意义的表达式)。而且,关于这些意义的知识同听话者拥有的关涉典型讲话者(即,施事者在语境中通常发现凸显的东西,等等)以及这个特定的讲话者(即,她所感兴趣的东西,等等)的所有信息一起,使听话者能够弄清讲话者意欲指称的对象。当然,这是由内容驱动、以求得出最佳解释的非形式推理过程(因此这并不是形式理论能够直接阐释的那种内容)。但是,这种丰富的推理过程在很多情形下的确足以将讲话者意向、继而将讲话者意欲指称的对象置于听话者的认知范围中。
第5节结语
意向敏感性词汇表面上对各种形式语义学造成了问题,而且似乎对任何类型的形式语义学都具有根本破坏性。形式语义学寻求达致语义内容的纯形式可推演性路径(即完全摆脱语用学神奇魔法的路径),这正是语义最小论(至少按本书的理解)追循的路径。为了回应这个挑战,最小论者有三条路径可以追循:其一,否认指示词语等表达式事实上对当前讲话者意向具有敏感性;其二,主张指称意向在行为中显现,因此可用来以与任何其他语境性成分完全相同的方式发挥语义作用;其三,寻求将指称确定/识别同语义内容区分开来。倘若证明这些举措中的任何一个合理可行,那就能够表明形式语义学,特别是最小论,将如何规避假定由意向敏感性表达式所引起的问题。然而,前面两种方法都面临源于关于指称不确定性的奎因式关注的严重挑战,因为拒斥(P1)和拒斥(P2)的举措都力图将指称确定从讲话者的某种“隐性”心理状态转向在话语语境中外显的特征上(或者不再诉诸意向而是诉诸公众可观察特征,或是通过将诉诸意向看作等同于诉诸公众可观察特征)。然而,就诉诸话语语境中公众可观察的特征可到达意向性层面的程度而言,看来这只能获得关于意向归赋的相当笼统的概念,而且这也许对行为目标获得某种认识;而意向归赋即听话者将某个行为x识别为意向性行为(即,看作自我激发的、而非由施事者外部因素直接引起的行为)。此处显然需要一个更为精细的指称确定概念,但这种东西在施事者行为的任何一点上都没有充分体现。
因此,最后一个举措(即严格区分指称确定/指称识别与语义内容本身)为最小论者提供了最有吸引力的方案。这是博格以前(2004a:第3章)提出过的方案。本章旨在表明,即使还存在其他一些符合最小论总体事业的可能路径,这个方案依然是最小论者应当追循的最合理路线。这一路径必然意味着要采取关于语义内容的最小论观点。据此,对例型指示词语语义内容的理解并不必然意味着听话者能够非语言地识别指称对象。可是,既然存在独立的理由怀疑关于负载认识信息的单称内容概念,而且既然语义内容的“精瘦”特性就是最小论宣言的重要部分,那就完全应当接受这个结果。倘若关于单称内容的这一观点为最小论者采用(笔者认为应当为其采用),那继续向前就可能会出现麻烦,因为可能招致阴魂不散的命题论败局。
此刻面临的疑问如下:虽然本章提倡单称内容观以关涉客体的广泛内容,但人们也许要问,事实为何如此?既然最终获得的关于内容的最小论概念是如此精瘦、如此微不足道,那为什么不彻底放弃这一概念,而代之以如下观点,即语义学所关注的仅限于语言系统意义的问题。就字面意义而言,应该将诸如“那是我的”这类句子的内容看作在这个句子的所有例型话语中保持不变,语义学并不知道指称对象的本体以及事实上是否获得指称对象。这样,可能只在语用学——语言使用——层面上,世界才能涌现并提供成包含客体在内的完备内容。然而,如果指示词语语义学只提供系统意义的描述,而不能产生这些表达式的完备内容,那么包含这些表达式的句子语义内容就不能达致命题层面。诉诸词汇-句法特征只能产生命题干,即存在空缺需要语境补全的东西。而且,正如下面几章将示,存在一种十分真实的威胁,即这种思想会推而广之,从而不只针对直接指称性表达式。我们需要将其语义贡献理解为不充分确定的描述性内涵,而不理解为世界性外延;而且结果还可能证明这就是理解自然语言词汇意义的最普遍方式。例如,将诸如“书”等普通名词或者“红色的”等谓词的意义可能不被看作由世界上某种分离特征(即外延)提供,而相反被看作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世界的复杂结构性内容。这样,在某语境中说出“书”也许意谓某个具体客体(如在“她把书放在了桌子上”),在另一语境中它指称一个抽象概念(如在“伦敦每一家书店都有她的书”),而在其他语境中可能还表达别的意思。
假如最后这个普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问题就不是(如第三章中所述)某些句子可能无法表达命题,而是可能所有句子都无法表达命题。因为词汇对更大语言单位的真值条件作出的贡献在使用语境之外不能得到充分确定。在下面两章将转而详论词汇意义的最基本问题,探询以最小论所假定(甚至连雷卡纳蒂2004,2010那类语境论者也接受)的、最本原非语境敏感的方式看待词汇内容是否正确,或者探询此处指出的另一种理论构架(将词汇内容看作提供了意义的不确定片段,其不完整的意义部分需要通过实际加以应用)是否真的更加可取。
附注
① 见戴维森(1967:33)。他继续写道:“逻辑学家和那些形式方法的批评者似乎都很大程度上……同意,形式语义学和逻辑学无力解决由指示词语引起的烦恼。”
② 正如第1章和第2章中所指出的,并非所有最小论者都感到达致语义内容的纯推演路径有什么吸引力,参见卡珀朗和莱波雷(2005)以及博格(2007)的讨论。
③ 最小论者可能竭力坚持达致语义内容的纯句法形式路径的思想,一条理由源于最小论与心理组件论的联系;博格(2004a:第2章)突出强调了这一论点。
④ 见卡普兰(1977)。其他人也觉得指示动作确定指称对象这一观点具有吸引力;参见麦吉恩(1981)和瑞穆尔(1991)。卡普兰(1989)摒弃了其早期观点,将指示动作看作只是讲话者标准“指示意向”的外化。
⑤ 这是卡普兰(1977:490,注9)关于“适时指示”的概念。
⑥ 韦特施泰因(1981:78-9)强调,重要线索可能超出由话语语境提供的那些线索(当然这个观点取决于准备将话语语境具体确定为多宽或多窄)。
⑦ 这一立场(就笔者所知)源于韦特施泰因(1981)。他在那里称之为“指示语指称的语境阐释”。鉴于语境论在本书其他地方的使用方式,在此避免使用这个术语。科拉扎、菲什与戈伟特(2002)以及戈伟特(2005)也支持这一立场。他们强调与语境敏感性词汇用法相关的约定规则,允许不同的规约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法(据此,“现在”作为电话留言的一部分指称听到话语的时间,明信片上所写的“现在”指的是写明信片的时间);然而,他们并没详细地阐明这些规则可能具有的内容。豪克尔(2008)也赞同这一立场。
⑧ 这列内容引自豪克尔(2008)。韦特施泰因(1981:79)也强调,这些线索可能包括受话者对讲话人的兴趣、心愿和历史等情况的了解;这是否构成对指示词语指称的真正规约性阐释,因而并不显见(参见注14)。
⑨ 维特根斯坦(1981)阐述了类似的观点,约定论为讲话者指称与语义指称的分歧创造了空间,而意向论似乎瓦解了这两个概念。
⑩ 参见巴赫(1992a)。科拉扎等人(2002:16-17)简要回应了这一点,提出这使得对意向的依赖从属于对公众交际的依赖。基于这种理论阐释,正是规约性特征在真正发挥作用。然而,并不清楚这个回应是否足以表明意向在指称确定中并不能作为判别标准:诉诸于公众交际对于解释指称意向的本质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这一需要与讲话者意向确定指称对象的形而上学观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