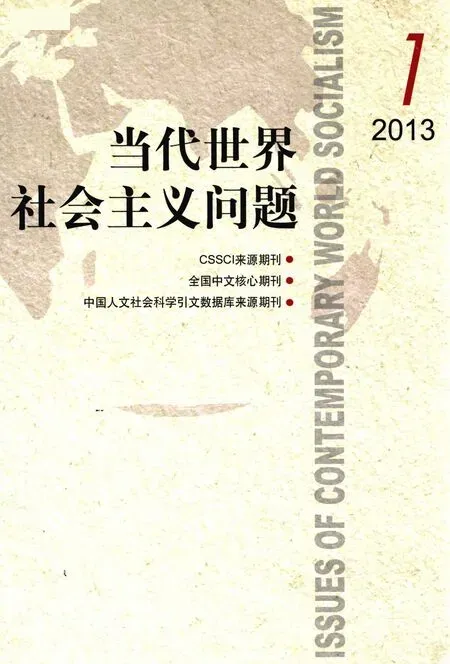20世纪上半期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在华传播及影响*
杨卫华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故乡在西方,一般认为兴起于1848年的英国,是受工运和世俗社会主义刺激而兴起的一股基督教思潮,其基本的理论倾向是致力于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调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约于20世纪初东来中国,但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的学者大都不太关注基督教界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关系,而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又难以进入社会主义史家的视野,这种双重忽略导致相关研究的薄弱。当然,这种情势除与它在两大思想阵营中的边缘化位置有关以外,也与其本身在近代中西历史中的影响大小相关。但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主义流派,它确曾进入中国教俗两界的言说,特别是在基督教界有较广泛的影响,且赢得了部分教徒的信仰并谋求其中国化,在调和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理论诉求下,成为他们应对世俗社会主义挑战和中国危机的一种资源。刘家峰曾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①刘家峰、刘莉:《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载《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中着重以贺川丰彦和张仕章为个案,对基督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非常好的讨论。但拓展的空间仍然很大。本文将在其基础上,详其所略,略其所详,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东传及中国基督徒的回应给予更全面的探讨。
一、基督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关于基督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两段当事人的回忆值得一提。一是著名教会报人沈嗣庄的回忆,他1934年在《社会主义新史》中提到了该书以基督教为出发点谈社会主义的原因:“这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我忝主中华基督教文社,因为要使基督教适合于现代生活的缘故,于不知不觉间,我便为基督教社会主义所迷住了,并且纠集了许多同志,作有统系之研究,如是有一年之久。”后来文社解体,研究材料被束之高阁,过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成立,我得参加末意,当然,我又在提倡我以前醉心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了。运动中明达者,早已先我而见,以故一经倡导,响应者颇不乏人,结果,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精神便钻到运动的宗旨中去了”②沈嗣庄:《社会主义新史〈自序〉》,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版,第2页。。一是基督教青年会文字干事张仕章1939年回忆:“著者所提倡的‘耶稣主义’也就是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它在中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然仅在文字上鼓吹彻底的社会革命,或在口头上宣传宗教的社会主义,却并无组织政党的企图,也从未参加政治的活动。一九二八年的夏天,有些耶稣主义的信者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新文社’,发行了一种野声月刊,出版了几种小丛书。到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就无形停顿了!”③张仕章:《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序〉》,青年协会书局1939年版,第2-3页。二人都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积极宣传者,从这两段文字中可知它在教会中的大致历史与位置,但其影响所覆盖的范围更深更广。
张氏云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华已有十多年历史,应是以他1922年10月发表《中国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④见《青年进步》第56册,1922年10月。为开端,而沈氏所说则是以他在主持中华基督教文社的1926年前后对该主义兴趣激涨为坐标。但教会接触它却远在这之前。最早的接触自然应属传教士。不过,从各传教士报刊来看(如传教士机关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相关谈论并不多。1913年在江阴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李德里(L.Little)提到一位对英国社会和工业问题颇有研究的朋友的信,信中表示“他相信基督教社会主义是解决目前冲突的最后方案”。李德里认为在赞同其结论之前期待听到更清晰的界定,因为他对任何认为社会主义与基督教关系亲密的观点都较为警惕①Missionary news,“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Kiangyin”,The Chinese Recorder,April.1913,p.255。该杂志较多提到英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主要介绍其诗歌小说②Arthur.H.Smith,“The Provers and Common Sayings of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1882,p.114。美教会领袖华德(H.F.Ward)的在华演讲中也曾提及:天主教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是阻止经济根本变革的手段,引起无产阶级与圣经教训的仇离,而欧陆真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则在化解二者仇恨,但效果有限③[美]华德:《革命的基督教》,简又文译,上海中华基督教文社1926年版,第139-140页。。不过,在华传教士中也不乏认同其理论取向者。如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Bates)曾自称尽管其观点与德国宗教社会主义者蒂利希(Paul Tillich)不完全相同,但很喜欢其立场: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已到了激变阶段而趋于没落了,宗教的社会主义将采取社会主义的方式。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蒂利希和英国麦墨累(John Macmurray)等已试图在基督教和马克思的观念中提炼出综合的原则。许多国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及不自觉为社会主义者的基督徒已准备与社会主义者合作,以对付目前的政治运动和劳工问题④[美]贝德士:《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张仕章译,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9年版,第1、2、7页。。
教内中文文本最早提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可能是1912年基督教青年会文字干事胡贻谷译的《泰西民法志》,译自克卡朴(T.Kirkup)的《社会主义史》。胡氏将社会主义译为“民法”,称之为“基督教博爱之支派”,是“民法学之伦理,虽非适合乎基督教法,然殊途同归,不能离而而之也”。作者介绍了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鄂温学说既衰,接武而兴者,有基督教之民法家。自四十八年至五十二年,为其风行之时,金司勒、马立司、罗特禄,皆其中之矫矫者,当时激进党挟持之名义,固执鲜通,顾马立司辈闻通相感,恻然动悲悯之心,著伦敦苦民一书,刊布于四十九年,是书穷形尽相,笔墨酸辛,而罗特禄固飫闻傅理雅之绪论,而定同心者,乃倡立通功营业会,借为补牢之策”,“金司勒复手编寓言小说数种,厯抉争竞弊习,不遗余力。且别具高屋建瓴之识解,谓民法窾要不外基督教之博爱,行诸民间,斯真度世金针也。夫伦理与民德为巩固民会之金汤,持此理以激励之,裨益世道人心,功在不朽,故虽疏于计学,非殖产家之指南,而重视民艰,实均财派之左券也”⑤[英]甘格士:《泰西民法志》,胡贻谷译,上海广学会1912年版,第8、53页。。该译并非原文照录,间有删改,但大致道出了英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概况,只因其译文与寻常所译差异较大,且为文言,似未引起大的影响。
其后钱泰基在介绍克鲁泡特金学说时,提到了盛行于19世纪中叶的“基督教社会派”(Christian Socialist)⑥钱泰基:《倡互助论者苦鲁伯金之生平》,载《青年进步》第27册,1919年11月。。1921年顾彭年译《社会哲学的略史》中介绍了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领袖金斯利和莫利斯“反抗绝对放任主义,主张发展社会化的基督教生活”,将经济和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置于基督教哲学之下的主张。作者认为他们的社会观念或不大确切,但动机是好的。“他们所建议有意识的和为大众福利的社会活动,慈善事业的创举,得以产生”①[美]F.Blackmar,J.Gillin:《社会哲学的略史》,载《青年进步》第42册,1921年4月。。当时的一份杂志《唯爱》介绍了1930年代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宣言,“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团契深信如果用社会主义者的条件去应付基督教的伦理,定能使这种伦理得到最适当的表显,并能在社会当中很有效率地运用起来。他们相信,基督教会应承认基督教和资本的个人主义伦理间有了基本的冲突”。他们承认阶级斗争的事实,认为实现社会正义不能单靠特权阶级的伦理眼光与智识,用非武力的方式去实现正义看不到多大的希望,所以他们赞同武力②《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团契的宣言》,远涛译,载《唯爱》第14期,1934年5月。。中华圣公会恭思道(T.Gaunt)的《基督教会史纲》用一章介绍了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对他们在工人的住屋、工资及改良公众卫生上的贡献给与肯定③[英]恭思道编著:《基督教会史纲》,中华圣公会书籍委员会1939年版,第319页。。
广学会《道声》刊载冯雪冰译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施》(译自1908年The Expository Times)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译介更详细。该文首先介绍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分裂:一派认为耶稣并未让其使徒去筹设社会经济计划,另一派则认为,如果福音除去了社会的因素,那就只剩下僵硬的仪式和无生气的教义。文章认为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可将宗教和社会两个维度合二为一,“基督教社会主义是趋重于灵质的”,它对今日的社会主义“唯物的倾向常深为疑虑,对于它的方法亦抱重忧,而对于它最后的目标,与其伦理的标准,却非常致其同情与钦佩”;基督教社会主义“包含一切教会组织对于改进社会的努力,和一切因受基督的感动,而谋发展基督徒社会生活的企图,由此将现社会人的关系和物的条件完全改变”;基督教社会主义不像一般社会主义那样依靠物质的力量,忽略人格的培养,而是基督对于人良知的权力,而诉之于人内心道德的力量;基督教具备社会主义的特性,尽管它不反对改善人生须先谋灵魂改善的说法,但却坚持只有改善人生物质的环境,才能使灵魂有至高的改善。文章作者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基督化的社会秩序比较经济化社会主义的理想有更高的观念,它包含社会主义的美质,却更容纳社会主义现在所否认的要点。将来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成功,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上帝的国实现的成功”④[英]D.Macfadyen,M.A.Highgate:《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施》,冯雪冰节译,载《道声》第3卷第2期,1932年。。
更多将基督教社会主义带到中国的是石川三四郎和贺川丰彦。石川三四郎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基督徒,以倡导无政府主义闻名,曾信奉基督教社会主义,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史》等作品被译成中文,颇有影响。1929年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的李博将《基督教社会主义》翻译出版;1930年出版的《社会运动史》则用一章介绍基督教社会主义,内容差不多,只是详略有异。两书都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名词为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金斯利、莫利斯等首创,但以基督教的精神而作社会主义运动的应是圣西门。两书末尾都引用了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布利斯(W.D.P.Bliss)的话:“基督教社会主义是把基督教的道理用于社会上……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个人的基督教。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最初所应做的事,当然是个人的接受基督。基督教社会主义并不把悔改、信仰、洗礼、圣餐等个人的精神的生活,也取而代之。基督教的救济不能专靠组织或境遇的力量一举来实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固然是由于个人的服从基督而起,但是在现代,却不能单以个人的服从为一切的服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通乎人情,以完成其社会法。”①[日]石川三四郎:《基督教社会主义》,李博译,上海华通书局1929年版,第48页;石川三四郎:《社会运动史》,北平青春书店1930年版。
影响更大的是贺川丰彦,有传记《日本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贺川丰彦评传》在华出版,他本人也多次来华。贺川自称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自述“最初我是一个抱社会主义的人,不是物质的是灵性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要改造社会必须有社会的原则,那就是社会主义。我是一个基督徒社会主义者,虽然,在日本,他们很不喜欢这名称的”②《贺川丰彦生平事业的自述》,载《工业改造》第15期,1927年12月。。贺川在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作品的译介。1928年时在日本求学的阮有秋将其《基督教社会主义论》翻译出版,同年基督教青年会机关刊物《青年进步》也节译了该书③[日]贺川丰彦:《基督教社会主义》,张民节译,载《青年进步》第115期,1928年9月。。
贺川在《基督教社会主义论》中讨论了广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基督教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无论哪一个时代事实上都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生活,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光荣的历史自身便是基督教社会主义之本质。基督教之运动,根本上已不是个人主义的运动,这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爱之运动,我们不能说它单是一种经济的运动,它同时是生命之运动或到自由之运动。换言之,基督教从开始便是一种社会运动”。以这种认识为框架,该书将基督教历史中的社会主义挖掘出来。贺川式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一种以基督爱为基础的渐进的社会改良学说。他在“社会革命乎?社会进化乎?”一节中说道,“耶稣决未曾叫我们妥协,他说我们为了主义,有时候竟不得不舍弃家庭,舍弃民族。但是他却不以为理想的社会组织是可以一瞬间构成的”;天国是渐渐成长进步的,“耶稣始终主张社会运动应以道德的内部改造为基础,并且相信另有超越的上帝之力来参加这种改造的工作”④[日]贺川丰彦:《基督教社会主义论》,阮有秋译,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3、45-46页。。
该书引起教会人士广泛注意。时任《华北公理会联合月刊》编辑的霍希三就属其教友注意该书,公理会信徒金受申读后认为,贺川将基督教的共同生活说成是共产生活,是“不敢尽信的,因为共产主义,是唯物史观的,基督主义,是唯神的。基督教的流血,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不得行而失败的,是因为团契精神——唯神——而成功的”①金受申:《读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论后》,载《华北公理会联合月刊》卷3第3-4期,1929年4月。。曾与贺川晤谈过的张仕章读后表示,它是“初研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最好门径。可惜作者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界说看得太广泛了,以致他把‘基督教共产主义’连在一起讲了。我以为这是不太妥当的。因为‘基督教社会主义’已经在历史上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名词——正如他自己说是‘限于特殊时代中的特殊地方之运动’”,并认为他大半讲的是“基督教共产主义”②张仕章:《介绍〈基督教社会主义论〉》,载《野声》第3期,1928年11月。。贺川氏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各类基督教刊物上,对中国基督教社会意识的塑造颇多影响。
在中国推行基督教社会主义最力者是前面提到的沈嗣庄和张仕章。沈嗣庄,浙江嘉兴人,生卒不详,1916年毕业于金陵神学院,1919年毕业于美国乔治省以马利大学,获神学学士学位,1920年入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获神学硕士学位,返国后任教于金陵神学院,1924年入东吴大学宗教科任教,1925年主掌中华基督教文社,后入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回沪。张仕章(1896-?),浙江海宁人,与徐志摩中学同学,后同入沪江大学,1917年受洗,1921年沪江大学宗教科首届硕士班毕业,后在广学会担任编译员,1927年被聘为文社编辑干事,1934年入青年会全国协会出任文字干事。共同的信仰将沈张二氏的事业也连在一起。1925年3月文社试办,沈嗣庄主其事,发行《文社月刊》,1926年8月聘王治心长编务,1927年夏增聘张仕章为编辑干事,1928年6月因教会内指斥月刊思想过激,美国方面停止津贴,三人同时辞职③王成勉:《文社的盛衰》,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观传播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7页。,旋组建新文社,出版《野声》杂志(1928年9月创刊,1931年10月出版完第2卷第2期后结束),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新文社结束。三人合作共事的这段时间正是他们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高峰期。三人算得上基督教激进派,其言论相较于世俗革命有距离,但超过了部分教会人士特别是传教士所能接受的范围。他们是基督教的少数派。
沈张二人在1930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关系及提倡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作品。沈的贡献更多聚集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研究与介绍,而真正对之做出中国化理论建树的是张仕章。张自述,俄革命后他开始关注国际社会主义的书籍,对马列学说特别注意。1922年独自竖起耶稣主义旗帜,做信仰的目标和宣传的张本。以后对耶稣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加以综合分析,对比研究,更感觉耶稣主义在中国有提倡的必要和实现的可能。“我确信只有耶稣主义才能纠正马克思与列宁的机械主义的宇宙观和经济定命的人生观。所以我现在还是一个耶稣主义者”④张仕章:《我现在为什么还是一个耶稣主义者》,载《野声》第2卷第1期,1931年9月。。前面提到的1922年10月发表的《中国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主要是应对非基督教运动及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冲突而写。他写道:“近三四年来,我常常想做一篇关于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文字,好使中国的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家都明白他们的冲突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因为这种冲突无非处于成见、误会、猜疑或忌妒罢了”。可见张氏重在应对马列主义的挑战,其中充斥着浓厚的调和味道。
沈张二氏注重西方相关理论及实践的研究介绍,但他们主张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并非西方的简单翻版。沈曾谈到“对于那些像我一样醉心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人,更有一言,非声明不可。我之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断断不是历史中陈列着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比如使徒时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它们统统失败了。二十世纪与科学社会主义昌明的我们,又何必蹈它的覆辙呢?它们所主张的原则可与天地同其不朽,它们的方案与手段却有修正之必要”①沈嗣庄:《社会主义新史〈自序〉》,第3页。。张仕章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别当他是从前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或现在美国的社会的基督教,因为他是在中国产生的化合物”②张仕章:《中国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载《青年进步》第56册,1922年10月。。因此,张力图结合中国实际致力于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同化,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宣扬其中国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③其中张认为其《耶稣主义讲话》(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为其代表作,他自言耶稣主义是其二十年来的信仰基础和目标,也是其著作的核心和革命思想的结晶,此书一出,就死而无憾了。见该书序言。关于张理论的内核,可参刘家峰、刘莉《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载《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
张氏坚持几十年宣传耶稣主义。即使在抗日胜利后的国共内战期间,张仍在宣扬中国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耶稣主义。他曾致全国基督徒一封公开信,呼吁建立“耶稣主义学会”,有组织的推行耶稣主义,以完成改造新中国的使命。学会定性为纯学术的研究传播团体,但并不排除将来组党走向实践政治的可能。张为学会起草了章程及组织程序④张仕章:《敬告全国基督徒书——为发起“耶稣主义学会”而作》,载《基督教丛刊》第16期,1946年12月1日。,但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回响。
二、基督教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努力
欲使基督教社会主义走向基督教的中心而被更多的人接受,首先要应对一些占据思想中心地位的主义或思潮。当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在中国实际上面临的是三面作战:基督教保守派、资本主义、世俗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基督教在中国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对手首先是教内保守派,即只讲个人灵魂得救不问世事的基要派或纯福音派。基督教社会主义认为,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处境中,基督教不能只顾个人得救不顾社会的得救;基督教不能满足于小修小补的改良主义,必须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以基督教革命的方式实现上帝的天国。1939年基督教领袖江文汉倡议中国宜仿效欧美建立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他提出六点基本主张:团结;抗战到底;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国民工人生活彻底的改造;联络国家间一切维护正义的力量。他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不是政党,目的不在夺取政权,而在教育基督徒;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也不代表教会,而是集合基督徒个人,使其信仰在集体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为社会改造提供一种路径①。在急剧变动中的中国,各地基督教人士也感觉到需要成立美国那样的团契,以集合力量,推进社会②。
基督教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应对劳工问题而起,它的一个诉求就是不满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企图改变劳资冲突、贫富悬殊的恶劣现象。针对教外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狼狈为奸的攻击,基督教社会主义成为抵御这种攻击的挡箭牌。简又文曾在反驳此类攻击的文章中写道:“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发生,而‘基督教社会主义’亦应时势之要求而崛起,其在英国所成就的事业实在不少”③。梁均默在反驳中共刊物《先驱》呼吁反资本主义就要推翻基督教时,曾力陈基督教是平民的宗教,历史上挺身做社会主义、实行共产制度的不知道有多少,而不见逢迎资本主义的。“基督教实是社会主义的来源,基督教只能替社会主义张目帮手,而绝非社会主义的仇敌”;不能因“我们温和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发源于爱的——不和你们发源于妒恨的社会主义者同暴烈的举动,就诬蔑我们和资本主义同声一气”④。徐庆誉也争辩道:从基督教义上看它并不拥护资本主义的,可能存在资本化的教会,你可反对这样的教会,但不可因此牵连基督教。基督教是平民的福音,没有拥护特殊阶级的臭味。今日提倡社会主义的人多反对基督教,殊不知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并不背驰,基督教社会主义就是证据,若研究社会主义来源,就应知晓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亲密⑤。
基督教社会主义最为关注的是与世俗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掌握话语权时,基督教不能缺席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反教资源时,必须化解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芥蒂。1934年沈嗣庄《社会主义新史》出版,蔡元培在序中说该书较注重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沈自序也明言是以基督教为出发点来谈论社会主义,其理论归宿仍在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调和。他认为1848年同起两件大事: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兴起,“历史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后者因为要直接应付前者而起,而其适足以使前者知道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本不是两件不同的事,这是无可疑义的。所以研究社会主义的人,非同时研究基督教不可。这和研究基督教的人,非同时研究社会主义不可一样。批评基督教为反社会反革命的人,读了本书,或者可以知所反矣”①沈嗣庄:《社会主义新史》,“自序”,第2-3页。。沈也曾翻译列德莱(H.W.Laidler)《社会主义史》,该书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拥有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忠诚,许多人加入它,是因为感到“基督教是需要社会主义的哲学的,同时,社会主义的运动也是需要着基督教的关于精神的能力”,“他们所主张的大概是资本制度下生活情形的改良,而不是这制度的推翻”。该书认为,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正是应对世俗社会主义而起,其历史意义在于:鼓励了合作运动;丰富了经济学家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使人们明了放任竞争制度的流弊;增强了人们对劳工运动的同情。更重要的是消解了英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间的仇恨,这种仇恨在欧陆很普遍,足以危及任何一方,他们的努力使英国更多的基督徒得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②[英]列德莱:《社会主义史》,沈嗣庄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69-870、877页。。谢扶雅也认为基督教不但不与社会主义冲突,且是牖发社会主义的功臣,“基督教是人的宗教,所以也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宗教。它绝不能容忍机器把生命吞没了去,金钱把性灵侵蚀了去,资本制度把劳工神圣的血都吮吸了去。读过教会史的人,都会明白基督教在最初——以后各代也有——便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运动”。接着谢介绍了英基督教社会主义及其对工业制度的痛斥与活动,他认为它最特殊的一点即“必以‘人的价值’为基本条件”,认为“基督教对现代社会革命家大无畏地进攻资本主义制度,表示无限感动,并愿执鞭先驱,同时对他们的缺乏更透彻的理论与更宏实的信仰,不能不有所诤告。因此,在最近将来,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依然会有它的地位与应付的使命”③谢扶雅:《基督教与现代思想》,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版,第71-73、210-211页。。
当然,除了证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不矛盾,基督教有自己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更要证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19年冬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开演讲会,由副总干事何丽臣讲基督教社会主义。他认为基督教的真意在知事上帝,爱邻如己,社会主义的真谛也在此,而“今之提倡社会主义者,苟不得其真际,反以制造社会纷乱之阶,盖爱力不足,空言改造。难收实效也”。而基督教不仅能去有形之罪恶,且能去心中之罪恶,故“惟基督教乃有真社会主义”④《演讲基督教社会主义》,载《青年进步》30册,1920年2月。。这番议论明显含有以基督教社会主义匡正世俗社会主义之使命感。张仕章也认为它所提倡的耶稣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⑤张仕章:《耶稣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载《天风》第7期,1945年5月4日。。王治心也强调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关系密切,当下各派社会主义流行,但基督教社会主义与普通社会主义不同,后者以社会为单位,往往从社会制度做起,以经济-物质为中心,而前者以个人为单位,看重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不否认经济物质,但其之外有更重要的精神,以爱为中心;它与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工团主义的抵抗政府、国家社会主义的改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自固、三民主义的党治不同,与无政府主义的互助有点相似,其社会政策的要点在:消灭一切阶级,提倡绝对平等,反对财主,消灭贫富阶级,同情弱者,消灭人我界限;人人努力工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王治心在对基督教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同时也不乐观,他认为“我们如能尽力去成立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将来总有世界成为一家的可能”,但并非短期可实现。他套用吴稚晖的说法:三民主义十年、共产主义三十年、无政府主义三百年、基督教社会主义一千年①王治心:《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载《动声》第3、4期,1931年7月。。基督教知识分子多对世俗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列主义表示不满,企图通过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提倡,将社会主义置于基督教的规范之下,以达到超越其他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列主义的目的,从而为基督教获取文化领导权提供一种可能。
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声誉的跌落升降,近代中国渐趋厌恶资本主义而向往社会主义的时代氛围,都驱使基督教一步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使基督教人士不得不从基督教中挖掘社会主义的资源。无疑,基督教社会主义与世俗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分享部分共同的理论诉求,这在有限的范围内为基督徒化解与共产主义的隔阂甚至走向后者提供了铺垫,但更多的是试图对后者进行纠偏,并企图以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取代世俗社会主义。他们的基本策略是认基督教为共产主义的理论来源,认为原始基督教已有某种共产生活,历代基督教都不乏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督教同样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且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较世俗的社会主义更为完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还试图结合中国实际,谋求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而非简单延续西方,为基督教的现实适应提供某种可能。但这些努力因其激进化趋向而超出了教内所能接受的范围,在教外更难见成效,故其影响十分有限,终至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