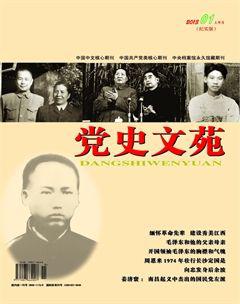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诞生记
张小芳
1997年5月9日,对76岁的姚筱舟老人来说是一个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前去参加第十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晚上8点在上海电视广播大厦四楼演播厅舞台上,导演与主持人精心策划,安排了这样一个温馨时刻,带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现场他第一次见到了作曲家朱践耳和已成为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玛。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三人忘情拥抱,紧紧地握手。一家报社记者意味深长地说:“这一天是一支歌中成名的三个人共同的节日。”这支歌就是由姚筱舟作词、朱践耳谱曲、才旦卓玛唱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劫后余生颂党恩
姚筱舟老人是来自陕西省铜川矿务局《铜川矿工报》的一位老编辑,是位军人出身、对矿工有着深厚感情的词作家。1949年只有16岁的姚筱舟正在家乡江西省铅山县中学读书,被五星红旗所召唤,投笔从戎,成为第二野战军某师政治部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1951年冬,又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朝鲜战场。停战后凯旋归来,转业到陕西省,后调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了一名采矿技术工。从此,与“蕉萍”相依相随,与矿工亲如兄弟,用“蕉萍”作笔名写矿工、赞矿工。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煤矿设施还很落后。寒冬腊月,煤矿竖井口结冰,影响了工作,消冰还是用的最原始的办法,直接生一堆明火烧烤。1957年1月8日这天,一不小心,火堆引燃竖井中的木柱,最后酿成14名井下矿工死亡惨剧。姚筱舟虽然当天恰好生病休息在家,但身为矿区技术员,当年8月还是受到“撤职下放,管制劳动”的处分。从此,他成为一名井下采煤工。
姚筱舟一直追求进步,突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不再被信任,这使他对前途变得心灰意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神思恍惚。一次,煤矿剥离土层放炮,瞬间井下地面开始摇晃,岩石、土块往下倾泻,若不是班长跑来一个翻身把他压趴下,可能就没命了。又一次,一辆装满煤的矿车脱钩飞驰而下,人们又喊又叫,但走在轨道边的姚筱舟竟然毫无知觉,没有一点反应,幸亏一位老矿工一把揪住他的领子,甩到一边,才保全了性命。两次死里逃生,都是党员矿工救了他,给他内心很大的震动,使他对党、对工人产生了无比感激的心情。从此,姚筱舟常常主动走到矿工圈里和矿工们一起喝大碗茶、拉家常,倾听老矿工们直起嗓子喊高亢的陕北独有的秦腔。矿工们也不再把他当外人,生活里的喜、怒、哀、愁也都愿意与姚筱舟拉呱拉呱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矿工说起往昔的窑主不把矿工当人看待,矿工受的磨难那是苦到了黄连,讲到共产党的恩情是赞不绝口。他还记录下许多矿工编的顺口溜和歌谣:“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窑工的棺(材)板子”;等等。因为旧社会矿工一下井,每天都有出不来的可能。姚筱舟每天都被感动着,渐渐认识到“煤矿工人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部分阳光,把脏、苦、累留给自己,把光、热、笑贡献给人民”。听多了,记多了,姚筱舟不自觉地有了写诗的冲动。1958年初春一个风雪交加之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灯下,一口气写了三首小诗,其中就包括《唱支山歌给党听》。姚筱舟后来回忆说,这首诗的其他部分都写得比较“顺手”,只有第二段中“鞭子”这个词,难为了他个把钟头。初稿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但他反复斟酌,总觉得不够理想,又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句替换。心烦意乱中,他随手翻阅一本小人书,偶然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抽打几个长工,顿生灵感,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三座大山”更形象化,于是马上提笔改成“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揍敌人!”
他用“蕉萍”为笔名,把三首小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被刊发在“诗传单”专栏内,后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汇编在《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
雷锋看到了姚筱舟的诗,觉得写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就把姚筱舟的诗记到日记本里,并且做了两处改动:“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样更精炼,更有节奏感,也更适宜谱曲,表达对党的热爱之情。
“是雷锋、作曲家朱践耳、歌唱家才旦卓玛三个大月亮照亮了我。”多年后姚筱舟动情地说,“当初我写诗时,没有想要它成为歌词,功劳是他们三个人的。曲谱是翅膀,有了好的曲谱,歌词才能成为美丽的天鹅,飞向远方。”
给“雷锋遗作”谱曲
朱践耳是我国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原名朱荣实,少年时代就喜欢音乐,关心国事,思想进步,深受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影响,改名为“朱践耳”。他后来回忆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向聂耳学习,为人民大众创造优美动听的音乐。
1962年,雷锋不幸牺牲。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雷锋”的活动便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雷锋日记》出版了。朱践耳在读到《雷锋日记》时,以一个作曲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他兴奋地给它谱了曲,为它加了一个标题《雷锋之歌》,并标注歌词节录自《雷锋日记》。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
这首诗表达了对党的无比热爱之情,对旧社会的深刻仇恨,这完全吻合雷锋的身世和感情,他写出这样一首诗歌是情理中的事。朱践耳把这首诗歌理解为是“雷锋遗作”,这样标注,也就是说,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大家也都觉得没有什么疑问。
1963年7月,姚筱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他既惊讶又激动,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首小诗竟然会成为广为传唱的动人歌曲。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试着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雷锋日记》的歌词是摘抄自他所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正好,中国音协的刊物《歌曲》要转载《雷锋之歌》,征求朱践耳的意见,朱践耳就将姚筱舟写给他的信转寄给中国音协。中国音协通过组织渠道向陕西省焦坪煤矿党委了解此事,证明情况属实。于是《歌曲》编辑部发表时就用诗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作为标题,词作者署名为“蕉萍”。从那以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得以正名。《唱支山歌给党听》把朱践耳和姚筱舟历史性地定格在一起。
才旦卓玛“抢”歌
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一天清晨,她在去教室的林阴路上,听到喇叭里正在播放歌唱家任桂珍主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一字字,一句句,农奴出身的才旦卓玛觉得这首歌就是为她写的:西藏的农奴居住在世界的最高处,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是共产党来了,西藏农奴才翻了身,才有了自己的今天。在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幸福,才旦卓玛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一股歌唱的激情在她胸中迸发。她立刻转身,一口气跑到她的主课老师王品素那里,结结巴巴地告诉王老师她的请求。王品素担心地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吗?不要丢了风格。”才旦卓玛语不成调哽咽地说:“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才旦卓玛为什么要唱一首汉语歌曲,但王老师最懂她的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才旦卓玛找到了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汉语歌词,纠正她的发音和咬字,到了音乐学院月度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后来朱践耳在听了才旦卓玛的演唱后,就主动提出让才旦卓玛唱这首歌参加1964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之后,电台把录制的歌曲播放出去后,才旦卓玛和这首歌一起变得家喻户晓。
当回忆起最早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时的情景时,才旦卓玛真诚地说:“这支歌的原唱不是我,是我努力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仅是雷锋的心声,更是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写照。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唱支山歌给党听》永远是人民群众对党发自内心世界的真挚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