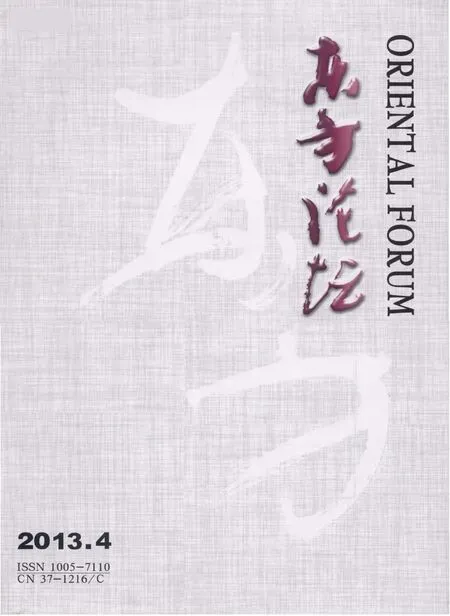新写实:现实主义文艺的新拓展 ——兼论30年来中国文艺创作的演变轨迹与审美转向
徐 良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表现形态,在我国现代文艺史上展现了它极其辉煌的历史成就和纷繁多变的表现形态,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它已远远超出了自身固有的意义,衍变构建了深厚的美学原则,体现了特有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指向。尽管它那几乎无所不包的涵盖性、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使其成为一种近乎全息性的多载概念,由一种文艺表现形态、创作方式上升到审美意识形态,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历史的必然,并且又一次回归主流位置,统率、决定、导引着整个文艺创作活动,但是它也并非一成不变。与任何审美形态一样,它总是流转变易、更替发展的,它那潜在的生命力量总是涌动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之中,展现着现实生活的脉搏与律动,生活永远是它的根基与土壤,现实存在永远是它的意义世界,这是它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量。新写实主义文艺,正是现实主义文艺的新拓展,是现实主义文艺在新的历史文化视野、新的现实存在和生活世界中新的展现形态。审视和分析新写实主义文艺,对于我们整体地把握和理解近30年中国文艺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历史的轨迹──现实转向与文艺转型
尽管对新写实主义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对它的理论指称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艺创作方法和表现形态,在近30年文艺实践中显示出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形成了中国当代文艺史上一种特有的文艺现象。很明显,创作实践的推动,使得它的美学内涵越来越清晰,审美价值越来越有影响。众多理论工作者的不断争鸣探索,使得它的外在轮廓、哲学基础、文化背景、本质特征和存在形式逐渐得到廓清,这种实践和理论的双重作用,使得新写实主义文艺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并成为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内容。
所以把它称作为新写实主义,一是它没有和现实主义发生断裂,是现实主义的新拓展;二是它没有和现实生活发生断裂,它就是现实存在的新展示,现实生活的再表达。但是,它又有着自身特有的美学品格,显示着自身独具的审美力量和审美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的美学原则,以展现和揭示人的存在状况为目的,关注人的生存、命运和情感乃至潜意识世界,把人性的本质、本能以新的视角,从多个领域,多个方面,多种取向加以观照、审视和把握;另一方面由于现实存在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叙述方法和表现角度已根本无法和这种新的现实存在相适应,这就使得它不能不对原有的美学原则实行新的变革。因此,新写实主义既是继承发展,又是变革推进。事实上,任何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审美形态的孕育和诞生,总是在一定的审美土壤中进行的,它有着各个方面的前准备,如果没有这种前准备、前基础,任何一种新的变革、新的发展都将是不可能的。
新写实主义的孕育和诞生、变易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现实基础和审美意识前提。理解和把握新写实主义应该把它置放于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整体框架中,置放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汇的复合体系和整体中国的历史演变与生活进程,才能得到清晰而确切的把握。新写实主义绝不像某些人指责的那祥,是故意标新立异、玩弄时髦,相反它真切地传导了当代中国文化选择与个体生存、社会价值与伦理情感、现实存在与精神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付诸于文艺的表达,形成一种新的创作原则,体现了强烈的“新写实美学倾向”。
新写实主义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逻辑必然,是中西文化交流和融汇、对峙和衍转在文艺实践中的具体体现。30年来,中国文艺走过了这样三个阶段,并呈现出明显的转折性,展示出深厚的生活底蕴,折射出强烈现实精神,并且无可替代地反映了整体中国的时代变迁和民族的心灵历程。
第一阶段(1976—1986年),第一个十年阶段。这十年以“反思文艺”为主导,中国文艺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它是人们从恶梦般的文革中苏醒过来后形成的一种文艺洪流,配合着对那惨绝人寰、艰难困苦岁月的全面否定,发自内心深处地传导了全社会的心声,上升到美学高度以文艺的形式给予震撼人心、痛彻心肺的表达,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效应。
第二阶段(1986—1996年),第二个十年阶段。这十年以“寻根文艺”为主导,体现了浓厚的文化色彩。寻根文艺是在反思文艺的基础上,在新的中西文化剧烈冲撞、裂变、融汇的背景下,力图从更深的文化根源中解答当代中国人的困境和出路,因此它也是对反思文艺的突破和超越,并实行了新的转向。这一阶段西方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它深刻地影响了文艺主体的哲学观念、审美倾向、价值判断和思想内蕴。“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人不断解放自己的历程”。[1](P288)当代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对人的一种重新认识、重新反思和重新解放,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汇通给它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换句话说,这场对人的重新认识、重新反思和重新解放运动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提下进行的,寻根文化就是对此的审美表达。
第三阶段(1996—至今),第三个十年阶段。这十年以“新写实文艺”为主导,体现出强烈的回归生活,回归现实,直面世俗生存状态的倾向。新写实文艺是寻根文艺的深层递进,并直接深入到人的存在本质和心理困境中,直接表述新的社会变迁来临之际人们无所适从的生活本质和生命欲求。它超越了一切形形色色的外在限制和理性规范,剥离了所有的理想光环和追求渴望,将人投放到繁琐的世俗困惑和复杂体验中,让每一个个体直面世俗生活的本质,直面生存的艰辛与复杂,还原本能的欲求和无奈。也就是说它已超越了寻根文艺,拓展形成了一种新的文艺创作倾向。可以这样总结,从反思文艺→寻根文艺→新写实文艺,呈现出三度递进的层次,每一个层次都以前一个层次为基础,而每一个层次又是对前一个层次的突破和超越,每一个层次又有着各自独立的审美特征。
二、理论的蜕变──外来影响与本土呼应
问题是如何才能厘清新写实文艺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如果新写实文艺得不到定位,那么新写实主义美学倾向也就难以定位。有人担心如果把新写实和现实主义连接在一起就会把新写实混淆于现实主义;把新写实和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就会取消新写实主义。实际上,新写实恰恰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混合交媾的产物,不能说婴儿来源于母亲就等同于母亲。新写实是现实主义的新拓展,新写实也是现代主义的新变易。我们从现实主义来把握新写实,就是为了在其母体的文艺传统内,更准确地把握新写实文艺的审美特征。
解析任何一种文艺现象都不可能脱离它的现实基础,把握任何一种文艺潮流都不可能远离它的现实土壤,脱离现实的文艺是不存在的。但是对现实的审美处理、艺术表达却不仅仅是一种,因此才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这样或那样的表现方法。有人厌恶新写实,觉得把新写实冠之以主义实在是不能接受的,而新写实作为一种客观的文艺现象在当代中国已成为基本的事实。实际上,新写实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一种文艺处理、文艺表达,至于叫不叫新写实那倒可以另当别论,我们要紧的是梳理出它的基本美学原则、审美倾向和价值尺度。时至现在,新写实这一称谓,确实是比较贴切和恰当的。
新写实是现实主义的新拓展,但新写实确实不同于现实主义,它有着独特的美学品格。要阐明新写实的美学品格,必得阐明现实主义。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在我国一直是最有权威性的文艺概念,但它也是最为困惑的文艺概念。一方面,不论什么文艺都是对现实或这样或那样的观照、揭示和表达,以至于一些人想用现实主义规定、概括一切文艺创作方法和流派;另一方面,由于忘却或者根本不管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表达手段,硬把它上升到一定的意识形态高度来支配一切文艺活动,从而使现实主义彻底地不再是现实主义,变成了伪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一种创作方法,它有着基本的审美倾向和基本的美学原则,一旦背离了这些审美倾向和美学原则,它就不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了。诚然,现实主义要发展、要变革,但如果现实主义成为无边的现实主义只能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能称之为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流派和文艺思潮是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掀起的,自从法国文艺家尚弗勒里首次用“现实主义”一词为标志来表达这一新的文艺流派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都取得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现实主义为人类贡献了世界第一流的文学艺术大师,而文艺实践的推动,使得它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它的基本的美学原则和审美倾向得到了完美的确立。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而“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表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乃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因为我们认为,探索那些所谓原始因和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亦是毫无意义的”。[2](P30)现实主义的形成和确立亦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原始的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使大陆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它却“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3](P26)现实主义面对的整体文化背景是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全面胜利。科学文化的进步,近代宇宙观的形成,使得人类的理性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类对自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笛卡尔以哲学的形式对此给予了最高的概括,他的理论成了近代哲学文化的方向。黑格尔则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全面奠定了近代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基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成了近代欧洲文艺实践的最高准则。在思想上,现实主义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主义运动的光荣传统,把人道主义推向新的高度,要求自由和平等,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作为人的一切权力,反对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并形成了它基本的审美倾向。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那就是注重对社会本质和人性本质的探讨,通过对客观现实生活准确、真实的描绘,通过对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塑造,完美地概括出社会和人性的本质。因此,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在文艺性质方面发生了一次彻底的革命”。[4](P556)
历史步入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推动,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彻底击碎了近代宇宙观的神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量子理论使得牛顿力学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才成立,无边的微观和客观世界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有效的本质规律,一切永恒不变的真理只能是人们的虚构。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打破了人类对社会理性的无限崇拜,也使得人类从理性的迷梦中苏醒过来,重新考虑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相比于冷冰冰的外部自然世界,人类还有一个比外在可见世界更深的层次和领域,然而靠纯粹的理性是根本无法窥其堂奥的。面对这个世界,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在哲学上作了全新的反应,通过这些天才性的研究发现,支配人类现实生活的客观理性、客观真理已根本不能概括人的全面本质,根本不能代替社会的本质意义,一个比理性本质更为重要的存在意义将成为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因此,20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艺面临着全面挑战,一场新的文艺革命势必到来,其标志就是现代主义的崛起和兴盛。
然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不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现实主义作为对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是一种强烈的理性表达,它是在近代哲学美学前提下产生的;而现代主义所关心的仍然是人类命运和人的存在意义,它只是作为一种非理性的表达,同样也是在现代哲学美学的前提下产生的。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只是一个意义的两个方面,两种不同的文艺表达。现实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温床、土壤,如果没有现实主义这种前准备、前基础,现代主义根本不可能产生和形成。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如易卜生、斯特林堡、陀斯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同时又是现代主义的鼻祖。因此在20世纪,现实主义美学本身也产生了巨大的转折。它彻底抛弃了凌驾于人们头上的理性本质,不再以反映客观现实和人性固有的本质为前提,不再以塑造典型性格为基本的表现方法,不再而且也无力给人生寻找最终的答案。相反,它认为现实世界根本没有不变的本质,现实世界是需要改变的,现存世界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流动的、变化的、向前发展的,它根本没有一个确知的答案和确定的结果,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现代文艺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意义。现代文艺家不给人提供答案,它只是提出问题”。[5](P524)现实主义的真实已不再是普遍的共相、类型和相关概念,作家的任务不再是真实地解释这个世界、揭示这个本质,相反真实性的概念是与不可解释的东西相联系的,“真实性不再是已经完成的,不变的,而是未完成的,可变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主义文艺是通过作品本身来实现这种变革的”。[5](P531)所以,作家作为理性本质的代言人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文艺家再也不能作为局外人在说话,谈论先于文艺家自己的那个世界,充当上帝的身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地进行判断。在现代,文艺家没有什么要说的,一切都发生在作品里边,在写作之前,不存在一个预定的思想意义世界,是写作本身成为创造世界的实验,文艺的意义在于文本本身,“作品成立之前,什么也没有,没有肯定,没有主题,没有信息。”[5](P525)作家并不提出什么现成的意义,作家唯一的介入形式就是文本本身,它不再关心人和所有世界的本质而是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对于寻求人生答案的人来说,“现代作品是令人失望的。”在巴尔特看来,“文艺行为……是完全不及物的行为,对作家来说写作乃是一个不及物的动词”。[6](P64)对此,当代西班牙著名文艺家M·德利维斯给予精辟的概括,他指出“现代文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趋向客观,越来越掩饰作者的存在。”[5](P874)正因为如此,“现代文艺家创造文艺,文艺也要创造自己的读者,读者跟作品的关系不是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而是读者参加创作实验的关系”。[5](P525)这就向读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读现代文艺的困难正在于真实性概念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读者完全陷入一个意义变化无穷、方向莫测、时隐时显、随时发生问题的世界中,如果读者认为世界是固定不变的,认为当今世界有一个确定的本质意义,人的责任只不过是试图如何理解再现这个世界,“这样必然是新文艺的坏读者,也必然是当代的坏读者”(巴尔特语)传统文艺要求被动的读者,现代文艺则要求积极的读者,他要不断地参加创造世界,创造他在阅读的文艺,要在作品的空白、遗漏、无穷变化、游移歧路中间留下自己的踪迹。这样,现代文艺美学所关注的重心已不再是作家、不再是客观现实世界,而是注重文本本身和读者作为接受主体之接受性的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一个无穷的存在意义世界,要求人们去经历、去体验、去补充。法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美学家、新文艺的代表人物阿兰·罗布·格里耶1984年来我国访问时曾指出:“到了现代,现实主义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含义完全颠倒过来了;以前的现实主义旨在找到那些不可接近的普遍概念(本质),通过文艺把这些概念带给人,而且人是得不到这种概念的,今后的现实主义旨在再现这个世界并且把它看作是真实的,尤其要再现这个真实世界各方面的特征。”[5](P528)
新写实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这个特有的文化环境中交媾的产物,它既有着现代主义的倾向,又有着现实主义的倾向。在哲学文化上它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存在主义文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艺对它的产生和形成起了很大影响。在1986年前后的文化热潮中,新写实虽然姗姗来迟,但由于准备充分,基础深刻,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并逐渐走出文艺领域,成为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普遍现象。事实上,新写实已经在文艺以外的美术、电影、电视、戏剧等许多领域出现,并大有席卷之势。我们从现实主义出发观照新写实,是因为它确实和现实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它已超越了现实主义,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文艺风格,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一个时期文艺发展的主要表现形态。
三、文艺的实践──生活回归与创作表现
探索现实主义的演变轨迹,站在中西文艺比较的角度上,更能比较准确地整理出新写实主义的趋向,梳理出新写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审美倾向。新写实主义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创作原则,有鉴于西方现实主义的发展,针对着中国现实主义的传统,新写实主义文艺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发生了新的变革,从而构成了它自身独有的审美特征和美学品格。
(一)美学基础的变革。由传统现实主义的本质反映论、伪现实主义的唯意志论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存在实践论。普遍的理性本质概念不再是社会和人性的全部,生存境况和本能体验成为人生世界的主要内容,成为新写实的现实基础,因此不再以探求客观本质为最高的美学追求,而以存在状况的真实揭示为基本的美学原则,这是新写实主义的根本特征。如电视剧《空镜子》、《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金婚》、《双面胶》、《亲兄热弟》、《家有九凤》、《大姐》、《我们俩的婚姻》、《马文的战争》、《王贵与安娜》、《蜗居》等,越来越趋向于表现家长里短的琐碎与平常,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细腻和庸俗,并以此作为叙事的主体内容,也成为构建戏剧冲突、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表现手段,以最贴近百姓的情感脉搏回应着人们繁琐辛苦的生活,也揭示着中国家庭伦理的价值转换和存在意义。
(二)价值观念的变革。由注重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把握社会历史的动向转变为注重个体价值指向和把握个体存在意义,从传统现实主义的历史、社会、群体的文艺结构中,转变深入到个体的现实生活感受、生命情感体验、潜意识世界乃至本能直觉领域,从而使价值脱离了本质概念,消失了历史的纵深感和厚度,直接进入生存领域,不受限制地作出自由的、本能的判断和选择,自然自在地体悟现实世界的本真意义,进而直面人性和社会的真实存在。作家基本上放弃了价值判断,“中止判断”成为普遍的倾向,让读者通过作品自己去把握。电视剧《渴望》首先引发了这种转变,贾平凹的《废都》全景式地展示了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刘震云的小说《塔铺》冷静、客观、有点辛酸味儿地描绘了几个补习生的高考经历,让人们切实理解高考的意义。高考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只是人生的一种艰难选择,高考选择人,人们也通过高考得到了重新选择。
(三)表现方式的变革。由传统的忠实于客观对象的纯粹反映转变为主体对客体对象的纯粹体验,换句话说,客观现实不再是和主体相分离的,而是和主体溶为一体的。因此,生理和心理的活动过程、生命感受和本能体验成为新写实文艺的主要对象,它的普遍性和真实性不再是外在客体对象的本质概括,而是生命体验和生存过程中的普遍感受。在刘震云的《单位》 和《一地鸡毛》中是寻找不到生活理想的,生活体验和生活本身是密不可分的,主客体的对立得到了最大的消解,体验就是生活,生活就在于体验,那种纯粹客观的生活,已经被溶化在生活体验之中了。电视剧《婆婆、媳妇、小姑》、《娘家婆家》、《麻辣婆媳》、《双面胶》、《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完全是以婆媳矛盾作为主要叙事内容,人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完全隐没在这纯粹而简单、繁琐而无尽的世俗体验和生活纠葛之中,此外再无任何追求。
(四)塑造形象方法的变革。由传统的塑造典型人物、表达社会人生理想转变为平铺直叙小人物(小女人和小男人)的普通生活。新写实主义崇拜现实生活本身,相信现实生活本身的真实,它认为典型人物是作家拔高生活的产物,处处透出人工的匠迹,是与芸芸众生相脱离的,所以新写实主义作家往往致力于写普通的小人物、写普通生活,从琐细而平庸的生活中咀嚼人生的酸甜苦辣,使人感受真实的生活意义。池莉认为“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力量”,她的《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一天到晚承受着多重的肉体和精神烦恼,然而正是这很累、很烦恼的平庸生活渗透了人生基本的存在意义,蕴藏着异常亲切、深厚的感染力。而《牵手》、《来来往往》、《结婚十年》、《蜗居》、《接触》、《爱了,散了》、《错爱》等电视剧,多领域、多视角地反映出当代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纠葛和情感冲突,并对此进行了全景式的再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无可奈何的生活状态。人们没有理想,理想就是生存,生存往往既简单又世俗。
(五)作家和艺术家主体地位的消失。由传统的创作主体充当全知全能角色转变为创作主体的全面消失。在传统现实主义创作中。作者以万能的上帝君临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作家不仅写出了广阔的时代背景,而且可以深知人物最隐秘的内心活动,作者可以随意调动一切力量和一切情节、一切人物。但是,新写实主义则与之不同,它是一种零度创作,创作以前什么也没有,创作以后什么也没说,作家唯一能作的只是客观地写作,只是写作本身,是写作本身成为创造世界的实验,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意义空白,让读者对作品进行二度创作,去填充、去增补,去体验,在作品的空白、遗漏中留下了自己的踪迹,使读者的地位得到了强烈的凸现。这一点明显地借鉴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新上门女婿》、《大女当嫁》、《李春天的春天》、《老牛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客观再现,没有高度与深度的一种冷处理,什么也不告诉你,但又明白地展现了一切,告诉你的远不如自身体会到得有味。
(六)叙事角度的转换。由传统的全知全能叙事角度转变为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两种基本方式。前者,叙事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事,叙事者也能叙述。叙述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轮流充当;可采用第一人称,也可采用第三人称。后者,叙事者只描写人物看到的和听到的,不作主观评价,也不分析人物心理。显然,这是作家主体地位消失后所造成的结果。在范小青的创作中,人物根本拒绝思考,他们总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栀子花开六瓣头》中的金志豪总以叹一口气或不再说话来代替思考,或者在要问为什么时突然转移话题。人物都不知道、不思想,叙述者还知道什么?实质上这是一种不思的思,不说的说。
(七)历史背景和历史传统的淡化。传统的现实主义文艺往往有典型的人物场所和活动背景,甚至以宏大的历史时代背景规范人物命运,而人物也总要体现时代的基本倾向和规律,典型人物的理想往往是时代的理想,人物的结局也反映着时局动荡的结果。但新写实主义却极力淡化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描写极左路线盛行几十年时间,但作品绝对没有把意义指向对准这时代背景,只是模糊地论述这年没粮了、那年又遭灾了等。在刘震云的小说《单位》中甚至连单位名称也没有,人物姓名也不清楚,哪还有时代倾向和人物理想。电视剧《媳妇的眼泪》、《张小五的春天》、《老大的幸福》、《金太狼的幸福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人物完全没有理想。只有一个法则,就是生活与生存,存在决定选择,而不是根据理想选择生活。
(八)主题的消解。传统现实主义把作品的主题视为作品的主干和灵魂,作品题材必须充分地、突出地为主题服务,甚至为了某一主题刻意去搜集题材。在传统文艺看来,没有主题的作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新写实主义却使主题明显地模糊乃至消失,作品常常没有意义指向。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等作品把主题本身消解在题材中,通过本能的欲望与渴求体现出深层的生命意蕴和文化意蕴,这里不存在任何超出生存本身的意义。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题目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无主题的人生态度,正是这种无主题的人生却反映了基本的人生状态。王朔的许多作品,充满了玩世不恭的味儿,但正是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嘲弄了机械、麻木、僵死、乏味的生活,实际上这是一种无主题的主题。电影《本命年》、《北京杂种》、《甲方乙方》、《有话好好说》等都从不同的艺术路径体现了这种新写实主义风格。事实上这种无主题的作品远比那些为解决某一问题而写的作品的生命力要长久的多。因为问题可能过时,生存却是永久的,生活的脉动是不息的。
由此可以看出,新写实主义虽然根源于现实主义,但它已经彻底超越、摆脱了现实主义,它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原则,它的基本美学风格已经形成。我们应该尊重这个基本事实,绝不能把现实主义看作全部文艺创作的阿基米德点和普罗克路斯忒斯的床,如果是这样,在中国就不可能出现文艺的繁荣。但是,新写实主义文艺也隐含着巨大的危险,过分描绘人性中猥琐、低级、原始的冲动,过多展示日益弥漫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及其所裹挟而来的道德危机与情感荒漠,完全沉迷于小男人与小女人的繁琐生活,即使是为了真实地表现人性的复杂性,表现人性中的弱点,表现性欲望的自然属性与合理性,也不应忘却呼唤美好的人性与道德良知,不应放却生活的理想与希望,不应或略文艺的升华功能和审美追求。时代要发展,历史要进步,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崛起,文艺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洪谦.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M].北京: 商务出版社,1964.
[3]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49.
[4] 恩格斯.大陆的巨动[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5] 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 对话与潜对话(下册)[M].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
[6] 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M].北京: 三联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