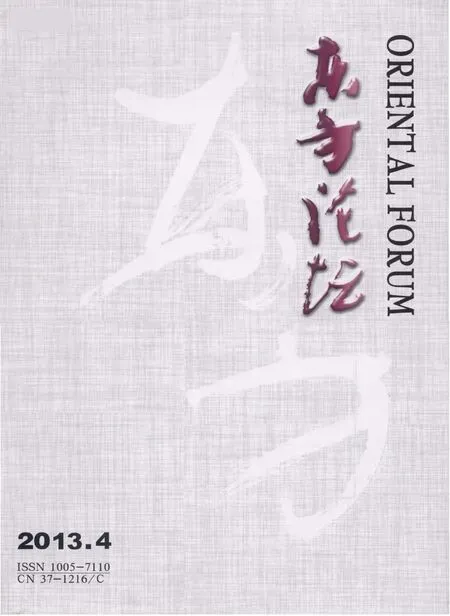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化观
孙旭红
(江苏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江苏 镇江 202013)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化观
孙旭红
(江苏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江苏 镇江 202013)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政策的指引下,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讨论中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他们的探讨结合了自身对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事业,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和学术进程,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总结也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文化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曾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P663)这里的“文化”主要是与经济、政治相对意义上的概念,是为了强调其与经济、政治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据此,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文化观必然以反映抗战、服务抗战为主题,也同时是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特殊时期的重要外在表征。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族文化”观点为“最高典范”[2],高举抗战文化旗帜,科学地回答了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超越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内涵。它不仅在文化领域内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一战线政策相适应,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概括,还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转型的雏形和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飞跃。
一、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配合对中国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日本军国主义宣扬中国社会“停滞论”、鼓噪中国文化“外铄论”等谬说,妄图以此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日信念,进而从文化与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在国内,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刻意在公民文化教育中再次扯起“尊孔复古”的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儒家宣扬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战国策派鼓吹法西斯主义文化观,“新生命派”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号召,“动力派”极力鼓吹和宣传“中国国情特殊论”,反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还存在照搬西方文化的机械效仿的偏向,当时的辩证法、唯物论“忽略了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太没有认清中国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而只知抄袭外来的教条”[3](P79)。这一缺陷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斗争中必然不能占据明显优势。再次,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影响还没有彻底清除,他倡导并推行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与此前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原则有本质区别,也严重干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可见,这时的法西斯御用文人、投降分子和抗战派都十分注重中国历史上可资借鉴的史迹问题或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法西斯御用文人妄图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并企图以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证明其侵略行为的合理及有利于其对中国的侵略”;投降分子是“为着准备投降的宣传,并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以证明其投降理论的正确”,抗战派的目的则是“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从历史的规律中证明中国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可见,“各种不同观点,不同使命的人们对历史学不同的活动,以及相互间展开的激烈斗争”[4](P663)。
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迫切需要有一支拿枪战胜敌人的军队,还要有一支“文化的军队”[1](P847)。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文化运动与之相配合”[5](P617),这种“配合”主要是指抗战文化要具有民族性、战斗性、大众化等特征,他在会上还对抗战时期的文化发展方向进行了概括,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1](P706-708)。而就其时局势而言,抗战文化的任务是要针锋相对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复古主义文化思潮做斗争,同时不断发展壮大进步文化力量,团结、培养和爱护文化干部,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推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等。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P663)这种对抗战文化“中国化”的强调,既适应了当时民族救亡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对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和激励全中国人民英勇献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起到了巨大作用。”[6]
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下制定抗战文化政策的同时,还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号召。而要实现“学术中国化”,首先要将中国的国情研究清楚,然后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对接[7],这就必须要扎实地进行史学研究。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情况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1](P797)。显然,毛泽东对许多党员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未充分挖掘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现实表示不满。因此,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号召全党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这一号召发出后,马克思主义史家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文化抗战的历史洪流中。
而经历过中国社会史论战洗礼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方面在面对中国近代以来最迫切的民族危机及其所引发的民族文化生存危机时,便自觉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共识;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提出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逐步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紧密联系,才能正确对待古今中西的历史文化问题,也才能深化唯物史观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此外,中国史学本身便是一座蕴藏丰富的文化宝库,要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史学进行一个系统的检视,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既体现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又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杨松曾对此概括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学术中国化的核心,而学术中国化的本质是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要在学术思想领域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要“彻底批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历史学上、政治经济学上和哲学上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8]。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就为强化历史研究提供了直接契机,马克思主义史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
二、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创造新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两种文化多持泾渭分明的态度,这种观点在实践中便体现为对新、旧文化或扬或弃而罕有持中之论。但抗战爆发前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主导的抗战文化运动逐渐“改正了过去文化运动中抹煞民族特征的错误,人们学会了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传统”[9](P306)。为此,毛泽东首先向全党提出要求:“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P534)而且,“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P707-708)。而其中的“民族性精华”主要指“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1](P245),这都意味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选择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其原因正如张闻天所概括:“旧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10](P663)同时他还指出要通过“批判的接受旧文化”来处理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必须全力扫除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文化。这一种扫除工作,应该愈彻底愈好”,而且,“新文化就是对这种文化的彻底的否定”[11](P41)。
实际上,对待旧文化遗产的讨论,归根结底还是在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这也是“学术中国化”的题中之义。因为“学术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在贯通现代世界性的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之间的必由之路,其途径在张闻天看来是“接受、改造与发展”。吕振羽1940年在重庆撰文指出:我们的文化战士要“从全部民族文化史中进行科学地深入地探究,去发掘其优良成果和进步因素。从而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才有实践的内容。”[12](P137)嵇文甫认为涉及“如何接受民族传统”的因素“参互错综,变动不居,决不能机械地看”,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因此,若简单地说“批判地接受”、继承改造一类是不够的,因为批判何者、接受何者实在难以判断。鉴于此,他主张将“可接受的传统文化”区分为以下四种情况:第一,带有一般性或共同性的文化,和现代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这很容易接受;第二,旧文化在经历时代转变后留给我们的只是它的某些精神或远景,这些在现代生活中又能发生某种有益的作用或暗示,这也可以接受;第三,善于从旧文化的神秘外衣中,剥取其合理的核心;第四,尊重文化的时代意义,不妨舍其本身,而单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阐扬其进步性[13](P663)。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学术的中国化”是对外来先进学术文化的一种“民族性”消化[14](P238)。
当然这种对文化遗产民族性的讨论,最终还是要为其赋予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使其具有时代性的内涵。如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生,郭沫若主张综合创造。他认为中华民族要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就必须创造新文化,因此高喊“我崇拜创造的精神”,“要自己种棉,自己开花,自己结絮。”[15](P4)吕振羽谈及创造民族新文化与继承文化遗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民族新文化“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所以说,我们要珍重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优良传统,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16](P124)范文澜在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中,认为封建时代的“嘉言懿行”、“节烈”等行为观念,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资料,无产阶级也可以拿来用作反抗敌人暴行的训诫[17](P300)。嵇文甫强调外来学术文化与本民族优秀学术文化传统、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形相结合之间的融合,才能发展出既具有民族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先进性的那样一种学术文化[14](P238)。侯外庐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学术的具体内容提出建议是:“中国学术史的特点,一方面保持历史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18]。延安学者何干之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指出:孙中山提出用新方法总结民族文化遗产问题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我们应当重视这个提出,应当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用人类最高的思维方法,来重新估量我们祖先给我们的遗产,拿这些遗产来作我们建国运动的武器”[19](P302)。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家已经自觉地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以及创造新文化与创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最终“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20](P298)
三、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民族化”,这还涉及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打到孔家店”到保存“国粹”,从“东方文化派”到中国教条主义的“欧化”倾向和洋八股,中国近代以来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多次反复,在犹疑中徘徊辗转,其纠结的症结便在于“民族的”和“西化的”文化如何调适的问题。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对待西方文化时则已经注意规避闭关主义、排外主义的态度,而是“赞成把中国的东西与外国的东西均衡地结合起来的主张,特别反对过分强调西方因素的倾向。”[21](P244)而且,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本质上并不是排他的。艾思奇在《五四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一文中谈及五四以后西洋学术文化的引介时指出,一个民族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新文化,单纯依赖外来文化或模仿外来文化都不能成功,但外来文化却可以刺激和促进民族文化的生长。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等论著中,立场鲜明地批评了闭关锁国、拒绝一切外来文化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全盘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文化教条主义和所谓“全盘西化”论。在此基础上,他主张鲁迅的“拿来主义”[1](P706-707)。这个方向是要在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的前提下,对中国古代以及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和吸收,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P707)
此外,张闻天也认为新文化需要大胆地批判和接收外国文化,并最终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未来文化的需要[11](P42-43)。郭沫若对西方文化持开放的态度,认为中国不仅要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还要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22](P157)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他就希望中国人“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23](P90)这里所说的“新的文化”,就是要批判接受“既成文化”,所谓“既成文化”自然包含了中外优秀文化遗产。1940年代,他更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凡是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都应当赶快设法接受”[24](P250),要“并蓄兼收”,“一炉共冶”。嵇文甫认为中国文化“始终吸收着世界各方面的文化,而又时时把自己贡献给世界,它和世界文化始终是起着交流作用的”[25]。
这里,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所持的开放态度,实际上也就承认任何文化都有一般性和特殊性,这一观念的产生应该说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家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相一致。在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关系问题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1930年代中后期以前偏重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忽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探讨,那么从193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4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继续强调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一致性的同时,突出对中国历史个性的研究,强调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指出:历史研究要将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的历史之具体内容”。吕振羽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史的发展过程之一般的合法则性的规律的发现已经是“铁则”,“这种一般性的规律,虽不能排除个别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但却是最基本的决定的法则”[26](P663)。华岗指出:“历史或历史科学本身,是有其一定的发展变化的普遍的特殊的规律,是即历史的发展规律……我们如能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还是可以研究出历史内在的发展规律来。”[27](P32-33)另外,侯外庐提出的“特殊的民主制度”和不同的民主道路;何干之认为“中国自己的道路”和不同的民主运动形式;胡绳提出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法等[21](P244),都表明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历史规律的认识逐渐摆脱了早期“公式主义”的倾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该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与文化继承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认识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四、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批判
日寇入侵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潮,大后方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形成了新的民族觉醒,但其中难免良莠杂陈,而且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和妥协投降文化也潜滋暗长。例如,一个为国民党独裁反动推波助澜、宣传法西斯文艺思想的“战国策”派应运而生。战国策派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攻击马列主义是“舶来的衣钵”、“时代没有需要”,进而借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将争取个人自由民主权利与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截然对立起来,这种观点由于暗合了国民党当局的所谓精神动员运动,因此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严厉批判。胡绳在《论英雄和英雄主义》、《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等文中指出,战国策派是法西斯毒素在中国蔓延;郭沫若在重庆文化界第七次座谈会上对林同济进行了“点名批评”,指出他们的历史文化观是一种“玄学的研究方法,将使中国学术思想倒退。”[28]他在创办的学术刊物《中原》创刊号上明确提出,对那种“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或“带有些那样气息的”文章,“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此外,郭沫若这时期不少张扬民主精神、反抗法西斯统治的文章言论中,以及他所倡导、率领的进步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讲座、历史研究中,也都体现出对这股法西斯主义思潮的抵制和批判。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发表了如《“战国”派文艺的改装》、《“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等文章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集体批判下,“战国策派”从此被定性为“宣扬法西斯主义”和“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的“反动思潮”[29]。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非难的还有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均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们在民族主义情绪、救亡图存、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主旨上是相近的,但这些共同性的背后也有诸多差异,仅就双方文化观的差异而言,归根结底在于文化哲学的不同。前者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后者基本上采用的文化形态史观。这种差异使得现代新儒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抱持拒斥态度,其实质是期望“复兴儒学”以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仍然不脱“中体西用”的基本框架。抱着复兴中国传统儒学的目的,他们相继发展了“新儒学”,如梁漱溟的新孔学,张君励的新玄学,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等,这些都是在西方文化的某些长处的基础上,赋予传统儒学以“现代化”的内涵。
面对新儒家的文化观,胡绳运用唯物史观撰写了《评冯友兰著〈新世训〉》、《评冯友兰著〈新事论〉》、《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等论著,批评现代新儒家的“非理性主义”谬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30](P24)。大后方文化主将郭沫若明确反对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现代化,“本是粪土之墙而涂上的廉价油漆,本是枯枝槁木贴上些洋纸剪花,那自然也可以算是‘新’,但和我们是同姓不同宗的。”[31](P254)他自己对文化进行思考的工具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历时性与共时性两大特征,且两类特征具有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而且文化的时代性要优于民族性。对于如何处理文化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郭沫若仍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文化路径:“等质的文化容易溶洽,如清水之与浊水。异质的文化不易溶洽。如水之与油。”“然油与水并不是完全不能溶洽,用高度的压力可以使它们生出Emulsion(乳融)。这高度的压力便是Revolutionl(革命)。”[23](P98)这是主张以革命的方式通过主体的综合创造来实现,这对新儒家文化史观的缺陷进行了揭露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新文化的主观条件。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其它各种唯心史观或庸俗史观也进行了批判。如胡绳认为“复古主义”的见解“在根本上是复古也是排外,因为它是把一切外国的东西,从中国旧文化传统的立场上看去是新的,不适宜中国的东西都加以排斥,它排斥一切西洋文化中对于当前中国的现实具有进步意义的东西。”[32](P203)身在重庆的吴泽撰文集中对中国人种和文化外来说进行了驳斥,此外,他还批判了地理环境史观、人口史观、英雄史观、历史唯心论等错误历史观,指出诸如地理环境、人口因素、英雄等只是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但并不是社会发展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及其面貌的主要力量。此外,杜国庠、周谷城、蔡尚思、胡绳等学者都利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对冯友兰、贺麟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批评。
五、申论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学术中国化”的理念得到加强和深化,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中共领导的抗战文化事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都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就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新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胡绳的《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等论文对民族形式以及“学术中国化”发表了看法。重庆的《读书月报》更是开辟了“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潘菽的《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柳湜的《论中国化》围绕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以及根据自己民族特点创造新文化等方面展开研究。《理论与现实》(季刊)以“学术中国化”和“理论现实化”为办刊宗旨,侯外庐的《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嵇文甫的《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等都对“学术中国化”发表了见解。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积极在《新建设》、《新文化半月刊》、《理论与实践》等刊物上撰文,不仅使得“学术中国化”的观点得到迅速传播,还突出了“学术中国化更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造新的中国文化之行动的口号和前提”[33]。这些讨论对于克服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封建复古主义等消极影响,均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的推动下,延安与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都开始在史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贯彻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如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华岗的《中国近代史》(上)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吴玉章的《中国最近50年民族与民主运动简史》、李平心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胡华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吴泽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等,这些论著都十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展现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而阐明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郭沫若的《屈原思想》、《韩非子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的《屈原思想的秘密》、《颜习斋反玄学的基本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等论著,纷纷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或历史,对传统思想中的民主性、科学性精华和唯物论思想有比较正确的总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利于抗战的思想文化资源。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继承,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具体契合点,从而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批判了抗日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有害倾向,他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与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论著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论著高扬的“人民本位”价值观,“歌颂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赞美那些有卓越贡献的民族英雄,提倡爱国爱乡、自立自尊的民族精神,鞭挞对外投降、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34]。一言以蔽之,“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文化观的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文化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史学属于文化形态的一个方面,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影响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答和分析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因此,中国抗战时期两大文化中心延安和重庆都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史,充分体现了革命文化为抗战服务的要求。为了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现这一要求,史学普及与大众化被摆在重要位置。1940年张闻天就指出,“真正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新文化”;限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定要坚持通俗化的方向。同时,“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为大众所了解。”[10]抗战时期的进步学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便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知识和通俗化的语言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念。
首先,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通俗化,使之方便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如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艾思奇与吴黎平的《唯物史观》、侯外庐与罗克汀合著的《新哲学教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等论著,对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撰写了一批通俗性与学术性兼顾的史学作品。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杨松、邓力群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等,还有延安出版的《革命岁月丛书》等革命历史普及读物,吕振羽还在《解放日报》“常识讲话”专栏上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历史常识的专栏文章等,都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35](序)。这些著述在内容上或直接取材于前线抗敌故事,或讴歌历史上抵御外侮的英雄,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体裁上则尽可能采取平话、传奇等编写简明历史课本,编撰历史人物传记,并广泛运用小调诗歌、旧戏、大鼓、鼓词等形式,这些史学论著语言上易懂,减少了普通读者在阅读时的困难,也易于普及历史知识。最后,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也被用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念。如抗战初期延安上演的革命历史话剧《广州暴动》、《血祭上海》、《血祭九一八》、《九一八以来》,任桂林的《卢俊义》、卜三的《江油关》、李纶的《秦桧》、孙震的《瓦岗山》、魏静生的《河伯娶妇》、秦腔剧《人心归闯》、《洪承畴》、《民族魂》等,国统区的郭沫若先后编写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多幕大型历史剧。这些历史剧以贴近群众的表现形式,宣传了中国历史上抵御外族入侵的英雄,以艺术的形式更有效地给人们以历史教育,使群众在了解基本的历史知识的同时,更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表现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大众化的进程中所展现的强烈的实践性、革命性的突出特征。
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文化的继承与思想的启蒙等还缺乏长期性与艰巨性的认识,对于文化在政治与经济等关系中所具有的相对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概念运用、逻辑推理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等方面阐述不足,以及在刻意的文化“致用”观念下进行的史学研究而损害了学术“求真”的旨趣等,这些现象都是需要今天所正视的,但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文化观及其史学研究实践,对于今天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学术中国化的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 吕振羽. 国共两党[N]. 解放日报, 1943-08-07.
[3] 贺麟. 当代中国哲学[M]. 北京: 胜利出版公司, 1945.
[4] 叶蠖生. 抗战以来的历史学[J]. 中国文化, 1941,(2、3).
[5]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6] 郭伟伟.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政策及其启示[J]. 党的文献, 2003,(5).
[7] 李方祥.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互动[J]. 中共党史研究, 2008,(2).
[8] 杨松.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J]. 中国文化, 1940,(5).
[9] 胡绳. 文化的方向和前途[A]. 胡绳全书: 第1卷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0] 张闻天. 抗战以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J].中国文化, 1940,(2).
[11] 张闻天. 张闻天文集[M]. 北京: 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0.
[12] 吕振羽.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13] 嵇文甫. 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J]. 理论与现实, 1940,(4).
[14] 北京市档案馆编. 北京档案史料(第一辑)[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15]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1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16] 吕振羽.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17] 范文澜.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A].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18] 侯外庐. 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J]. 理论与现实, 1940,(2).
[19] 何干之. 三民主义研究[A]. 何干之文集(第2卷)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20] 范文澜.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21] (德)罗梅君. 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 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M]. 孙立新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22]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1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23]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1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24]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1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25] 嵇文甫.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J]. 时代中国, 1944,(1).
[26] 吕振羽. 本国史研究提纲[J]. 读书月报, 1940,(4~5).
[27] 华岗. 中国历史的翻案[M]. 北京: 作家书屋, 1946.
[28] 龙显球. 抗战时期对“战国策派”及〈野玫瑰〉演出的斗争在昆明[J]. 云南文史丛刊, 1987,(3).
[29] 李琼. 林同济传略[M]. 世纪中国, 2004-8-13.
[30] 胡绳. 胡绳全书: 第1卷(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31]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2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32] 胡绳. 胡绳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33] 柳湜. 柳湜文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34] 马宝珠等.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N]. 光明日报, 1998-01-20.
[35] 吕振羽. 简明中国通史[M]. 香港: 生活书店, 1941.
责任编辑:侯德彤
Marxist Historians' Cultural Concept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SUN Xu-hong
(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uzho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times, Marxist historians enriched new-democratic cultural concept in their historical resea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nti-war cultural policy by considering how they should trea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disputing against the anti-Marxist cultural concepts. Their approach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not only developed the anti-war cultural policy,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t also has its significance in summing up the experience of Marxism in China.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Marxist historian; cultural concept;Marxism in China
G112
A
1005-7110(2013)04-0046-07
2013-05-1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ZX01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2013SJD710004)、江苏大学高级人才引进项目(11JDG174)阶段成果之一。
孙旭红(1982年- ),男,安徽庐江人,江苏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