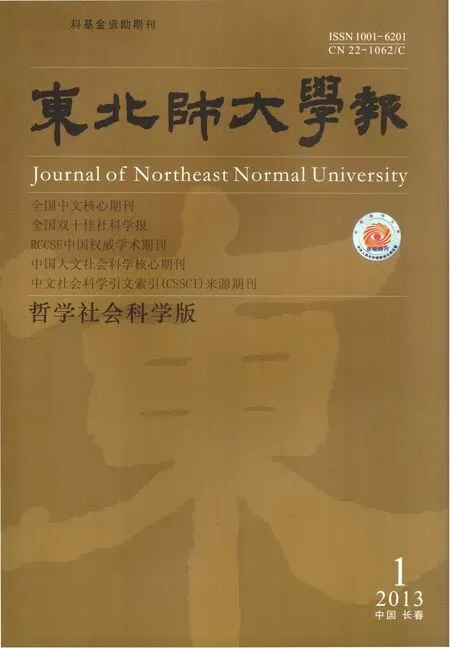从户的相关立法谈秦汉政府对人口的控制
王彦辉,薛洪波
(1.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2.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国家强弱的决定性标识,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把掌控人口视为国家兴亡的军国大政。但帝制农本社会与宗法封建社会在人口控制方式上有所不同,宗法时代是通过“宗族”血缘纽带实现对人口的凝聚,帝制时代则是通过户籍编制将人口固着于乡里体系之中。尽管不同时期基层政权组织形式略有变化,作为私权力的“宗族”也不断与公权力的“国”反复争夺对人口的控制,但国家掌控人口的本质并无不同。因此,历代政府都极其重视户籍编制工作,恰如徐干在《中论》中指出的那样:“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1]580以往,人们在解析“民数”与人口控制问题时主要是从编户的义务即国家剥削与奴役方面展开讨论,所谓“以令贡赋”、“以作军旅”云尔,却无视百姓被编入版籍后所享有的权利,所谓“以分田里”是也,而这两者原本就是相辅相成的。
一、“户”:合法占有田宅的前提
在秦汉时期的法律术语中,“户”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并非单纯的姻亲血缘单元,还包括非血亲的奴婢在内,故睡虎地秦律《法律答问》解释说,“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即同户籍者为同居①关于奴婢登入户籍的问题,笔者在《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一文已有申论,今据里耶秦简可证当时的推论是成立的,如《里耶发掘报告》公布之户籍简K27第五栏录为“臣曰聚”;K30/45第二栏录为“妾曰□”;K2/23第五栏录为“臣曰”等。。而在表示亲缘关系时“同居”又可称之为“室”,所谓“‘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室人’者,一室”[2]238。就是说“室”侧重于家庭的社会学属性,“户”侧重于家庭的法学属性。由于在帝制时代,作为主权意义上的国家疆域治权同土地所有权往往是混同的,私人的土地权利从来没有达到超越政治法权而“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所以对土地资源的获得必须经由国家的认可才属合法。秦汉国家正是利用了两者之间的模糊性,排除了法律政策许可范围以外的“先占取得”的原则,规定立户才是占有土地的法律前提,这在秦及汉初律中体现的尤其鲜明。
秦自商鞅变法实行国家授田制,按《二年律令·户律》的内容可证汉初亦然。在国家授田制体制下,“户”是授田的前提,所谓“未受田宅者,乡部以其为户先后次次编之,久为右。久等,以爵先后。有籍县官田宅,上其廷,令辄以次行之”[3]52。简文中的“为户先后”是说授田的先决条件是立户,无户籍者不得“受田宅”。应当指出的是,汉初的国家授田并非在吏民占有田宅的基础上打乱重分,而是在沿袭战国、秦朝国家授田以及田地占有的既有事实的基础上,对返乡之复员的军吏卒及新立户者实行的授田。但无论是国家所授之田抑或通过继承、买卖等渠道占有田宅,“户”才是法律预设的终极前提,故《户律》324简规定:“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也就是说,只有到官府登记户口成为国家的编户,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才能占有和利用法律赋予的生产资源,否则就属违法。只有在民间通过遗嘱的形式处分家庭财产时,未立户者才可以临时占有田宅,但需要在国家恒定的户籍登记日履行立户手续才属合法,所以《户律》在规定遗嘱订立程序时指出:“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3]53-54所谓“八月书户”即在每年八月的“案比”之日,“不为户”者要立户并把所分田宅登记在户籍之上。
西汉中期以后,大规模的国家授田行为废止,转而实行“名田”,即“以名占田”。“名”者有名于户籍也,“名田”就是根据户籍占有田,户籍作为占有土地的合法前提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改变。换言之,随着土地私有权的确立,民间处分田产的自由度扩大,但田产的归属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户”,政府的“计赀”也是以“户”为最小单位。就是说,国家始终也没有放松对治下人户拥有田宅、奴婢等家庭财产的掌控。
李振宏在详实考察汉代地价的基础上,曾经指出:“在汉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值远远高于土地的价值,只有劳动力才是最重要的东西。”[5]275国家之所以把“户”作为占有田宅的前提,正是要通过“户”来掌控支配“劳动力的手段”,即国家把治权范围内的一切资源都视为国有,并通过立法获得法理上的公权,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支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和占有,最终达到对域内人户的有效控制。
二、“邑”:合法居住空间的限定
以往论及中国古代对人口的控制更多关注于户籍编制与管理制度,很少注意到国家对百姓居住环境的限制。实际上户籍只是人口控制的一种手段,而把人户限定在乡里体系下的“邑”也是人口控制的有效方式。
“邑”是指先民定居以后经过人为规划而建筑起来的大小不等的且有墙垣或城郭围护的居住空间,与自然形成的“聚”相对应,故先秦文献经常可以看到“营邑”、“作邑”、“制邑”等提法,其义无非营建新的聚居点而已。秦汉时期,“邑”又与各种行政建制名称结合起来使用,诸如郡邑、县邑、乡邑、里邑(或邑里)等。在宗法封建社会,“邑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同宗族成员的保护,而在帝制社会,“邑居”更主要的目的是对国民的限制,尽管不排除防盗、防敌对势力侵扰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国家往往把“野处”视为违法的表现,《魏户律》就声称:“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2]292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必然需要在原有城邑之外兴建新的居住区,或自然聚居,或人为规划,其形成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二大类型:一是民间自发聚居而成新的聚落。这种“聚落”或是城居的农民利用在田间已有的“庐舍”或“田舍”发展而来,或是百姓脱离原住地而在交通便利或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自然聚居,或是豪族在城外广建田庄,吸纳流民而形成的新的聚邑。二是国家为安置流民或移民实边而营建的邑里城郭。此即晁错所言:“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6]2233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聚邑,都不可能逸出国家编制的乡里体系,“聚”虽然是生生不息的,但经过国家的整合,在自然聚落置乡建里,从吏民的居住空间上实现对人口的实际管辖。
作为政府行为的城邑也好,依地理条件形成的聚邑也罢,居住区内部的构造未必都规划有致,但乡里建制却是整齐划一的。无论是国都、郡府、县廷所在地,还是离乡、聚邑等都按制划分出独立的“里”,若干“里”统属于一个“乡”。每里辖几十户到百户不等的“户”。里有墙垣与外界隔绝,依其方位的不同设有二到四个里门,有专人负责开闭。对此,我们以往只能在一些礼书及《汉书·地理志》中略知大概,且无法判断其是否现实存在的制度,今则有法律文献为证,《二年律令·户律》明确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里典更挟里门籥(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
律文中“比地为伍”一句,是说在里中以五家为单位将比邻编制为什伍组织,所谓“可(何)谓‘四邻’?‘四邻’即伍人谓殹(也)。”[2]194其主要功能是“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此即商鞅变法所规定之“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7]2230。而儒家所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8]119之类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法家的改造在法律文献中已经荡然无存。
“比地为伍”不仅体现在城邑乡聚之中,而且也反映在邑外的田庐之处。当时,人们除了在邑中有自己的居室即“宅”,在阡陌田间还有供临时休息的“庐舍”或曰“田舍”。在国家推行授田之初,授田的次序是“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9]。这个“以地次”就是孟子所谓“乡田同井”[8]119,正如张金光所论“在乡居民行政编组与在野之受田耕垦秩序是一致的”[10]301。授田如此,庐舍的排列同样遵循这个原则,此即“田有封恤,庐井有伍”[11]之谓也。如此,百姓无论是在邑中居处还是在田间生产劳作,都处于无数双眼睛的时刻监视之下,一旦发生为盗、逃亡等现象,就会有人立刻“谒吏、典”。随着土地买卖的经常化和地权转移,“庐井有伍”的编制自然随之淆乱,邑庐的分别也会随着居住空间由中心城邑向郊野的辐射而发生变动,但乡里体制是不断复制的,这就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正常情况下都无法规避国家的监管。
三、“籍”:身份证明和财产的法律认定
国家通过对生产资源和居住空间的有效掌控,使每一社会成员轻易脱离国家的管制都很难生存,而这两种主要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取得又是以“户”为根据的,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帝制社会早期的特征。不唯如此,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和财产的监管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堪称严密,这主要体现在户籍登记、变动和财产登记、转移的法律认定等方面。
秦国的户籍制度草创于秦献公十年(前375)的“为户籍相伍”,至商鞅变法始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就一般编户的户籍而论,又可称之为“名数”,而各类人名册则称为“名籍”,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户籍”。
关于户籍登记的内容,学界已讨论多年,无非《商君书·境内》篇的“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12]146。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初令男子书年”以后,男子以及家口的年龄始书于户籍以外的“年籍”,即张家山汉简《户律》的“年细籍”。户籍在登记“民众口数”[12]48之外,秦及汉初还需要登记家庭财产,《户律》所说的“宅园户籍”,登录的内容就当包括户主及家庭人口、奴婢以及房屋、家畜等,属于家口与财产的合籍。但不包括田地,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土地在法律规范上还不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汉中期以后,宅园户籍与年细籍合并,田地也有录入户籍的迹象,但是否存在户籍以外的“户赀簿”,时下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户籍是社会成员的身份证明,擅自脱离原住地属于违法行为,称为“亡命”即“无名”。民户迁移要履行法定手续,户籍所在地的乡部要把户籍及年籍一并送至迁徙地,里耶一号古井出土的县廷文书中就保存了一份有关文书,简JI(16)9A面载:
(二)劾等十七户徙都乡,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问之劾等徙□
(三)书,告都乡曰:“启陵乡未有枼(牒),毋以智(知)劾等初产至今年数。□”
(四)□□□,谒令都乡具问劾等年数,敢言之[13]137。
简文的大意是说,启陵乡所辖渚里十七户徙居都乡,未按规定移送年籍,都乡呈请县廷过问;县廷询问情况后回复说,启陵乡没有年籍,也不知这些居民的年龄,请都乡自行查问劾等的年龄。从“皆不移年籍”的问询口气来看,户籍已经随人移送,否则都乡不会单独索要年籍。按秦汉制度,百姓从甲地迁往乙地,必须把户籍等档案材料同时移送到迁居地,秦律《法律答问》设问云:“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2]213-214即百姓徙居,必需移送百姓的“数”,“数”即“名数”,亦即户籍。睡虎地秦律的形成时间跨度很大,我们很难判断这段简文的时代,但《二年律令·户律》中已明确规定:“有移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3]54即要求把户籍及“年籍爵细”一并移送到迁居地。
百姓迁徙要有户籍证明,平时游学、出仕、经营、更戍,以及追捕盗贼等官差同样要有官府开具的“符”或“传”。如终军以“辩博能属文”选为博士弟子,从济南西入函谷关时,“关吏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6]2819-2820。肩水金关汉简73EJT9:104记载了一件由居延县发放的逐捕亡命者的“传”,内容如下:
五凤四年八月己亥朔己亥,守令史安世敢言之:遣行左尉事亭长安世,逐命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金城郡中,与从者阳里郑长富具乘占用马、轺车一乘,谒移过所县道毋苛留。敢言之。八月己亥,居延令弘、丞江移过所县道如律令/掾忠、守令史安世。[14]108
文中的“逐命”即逐捕亡命的略写,“占用马”即汉武帝行算缗令之后的“各以其物自占”之义。73EJT9:55记载了一份居延令发放给返乡戍卒的“传”,简文曰:
和平四年二月甲申朔丙午,仓啬夫望敢言之:故魏郡原城阳宜里王禁自言:“二年戍属居延,犯法论,会正月甲子赦令,免为庶人,愿归故县。”谨案律曰:“徒事已,毋粮,谨故官为封偃检,县次续食给。”法所当得,谒移过所津关毋苛留止,原城收事。敢言之。
二月丙午,居令博移过所如律令掾宣、啬夫望、佐忠。[14]33
简中的“居令”,应是居延令,漏脱一个“延”字。但“误,其事可行者,勿论”[3]33,所以该“传”的底本才得以保留下来。
此外,居延汉简、金关汉简中还保留了许多申请从事商贾活动而由乡部出具的证明及县廷发放的“传”,如金关汉简73EJT10:120A就是一件完整的“传”:
甘露四年正月庚辰朔乙酉,南乡啬夫胡敢告尉史:“临利里大夫陈同,自言为家私市张掖、居延界中。谨案:同毋官狱征事,当得传,可期言廷。敢言之。”正月乙酉,尉史赣敢言之:“谨案同年爵如书,毋官狱征事,当传,移过所县侯国勿苛留。敢言之。”正月乙酉,西鄂守丞乐成、侯国尉如昌移过所如律令/掾干将、令史章。
简的B面署有“西鄂守丞印”[14]136。其中的“谨案”,在其他残损的过所文书中一般称“谨案户籍臧乡官者”[14]104、“谨案户籍在官者”[15]349等,是“谨案”乃前引文的略写。“谨案”的事项包括“年爵”及是否有“官狱征事”,其中,“年爵”指年龄和爵位;“官狱”云云,是看申请人有否犯罪记录;“征事”即本年度是否已服事更徭之类。由此可知,户籍中不仅要详细登录户人的姓名、籍贯、年龄、爵位等,还要记录已事、未事等项内容。
编户平民不仅没有流动的自由,而且财产的转移也需要经过法定程序才属合法。张家山汉简公布后,经过学者的不懈探讨,有关财产继承问题已经大体清晰。即秦汉的继承制度包括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两大类,身份继承由法律予以规范,分为爵位继承和户主继承;财产继承附属于身份继承,又可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形式。我们要讨论的是,从财产转移的角度来说,不论是身份继承抑或财产继承都是对被继承人死后财产归属的法律规范,并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日常“析产”行为。就经常性的民间处分家庭财产而论,我们可以将之细化为不同的类型,笔者在《论汉代的分户析产》一文中曾概括为家富子壮出分型、先令券书型、户后推财型、兄弟分财异居型、妇女为户析产型等[16],但这是把两汉作为一个时间单元给出的结论,并没有考虑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变化。随着里耶秦简的陆续刊布,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其实,张金光在论证普遍授田制的终结问题时就注意到《二年律令·户律》有关“先令”析产的法律规定与江苏胥浦汉墓所见遗嘱之间的截然分别,指出《户律》中的先令析分需经官府许可才属合法,胥浦先令则属民间的自主行为;《户律》先令是官办,要以“券书从事”,胥浦先令属民间契约,只需以民间先令“从事”,表示民间具有田地的处分权;《户律》先令“乃是国家授田制下为土地转移配置所制作的官文书”,胥浦先令则是“私田分析之民契”[17]。应当说,张金光的卓见是有启发意义的。据此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说在推行国家授田制的前提下,民间日常的析产不得涉及田地,只有通过遗嘱形式才有处分田地的权益。比如《户律》规定“先令”可以包括田宅、奴婢、财物等,而平时的析产则不包括田产。337简就规定:“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3]55如果这个假定条件可以成立,那么民间自主处分家庭财产时是否包括田产就可以作为判断一些简牍簿书性质的依据之一。
已公布的《里耶秦简(壹)》中保留了二份完整的有关析产的“爰书”,其中,简8:1443载《都乡守武爰书》:
卅二年六月乙巳朔壬申,都乡守武爰书:高里士五武自言以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产。典私占。初手。
简8:1554载《都乡守沈爰书》:
卅五年七月戊子朔己酉,都乡守沈爰书:高里士五广自言:谒以大奴良、完,小奴嚋、饶,大婢阑、愿、多、□,禾稼、衣器、钱六万,尽以予子大女子阳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齿。典弘占。[18]
对于这两份簿书的性质,陈伟在主持校注时是持以非常谨慎的态度的,仅注引《二年律令·户律》的内容参见之,唯张朝阳在简帛网发文“将其称为民间遗嘱”。根据之一是引居延简202.8—202.15所见“知之当以父先令户律从。父病临之县南见啬……”云云,认为里耶爰书也“提及一位父亲谒见了乡官,留下财产转移的安排”。二是《都乡守沈爰书》中财产赠与对象是已出嫁的女儿,财产比较庞大,“为何一位父亲如此大规模地把财产转移给予已出嫁的女儿?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是在安排遗产。”[19]
我们认为,仅凭这两点还不能简单地将之定性为遗嘱,理由是:
一,按法律规定,先令要由乡部“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即把副本上报县廷。如果这两份文书属于遗嘱副本,其中必然涉及“爰书”的题名,立遗嘱的理由以及遗嘱生效的日期等。江苏胥浦先令明言朱凌“甚接其死”,而且写明将“稻田二处、桑田二处”分予公文的时间是“于至十二月十一日”;居延简所见先令也是由于“父病”,才于神爵元年“二月卅日”到县南乡见啬夫,且有“到二年三月癸丑”的字样。而里耶“爰书”既不见“先令”一类的题名,也没有立遗嘱的缘由,更不见遗嘱生效的日期,足见此二物并非正规的遗嘱书写格式。
二,如上所分析,在秦朝继续推行国家授田制的前提下,百姓是无权自主处分田产的,只有通过遗嘱形式才能转移田地。里耶“爰书”若是遗嘱,自当包括田产在内。“高里士五武”分予“子小男子产”的财产包括两个成年男奴、一个大婢和一个小奴,以及牝马一匹;“高里士五广”分予“子大女子阳里胡”的财产“凡十一物”,其中还有“钱六万”。如此富足的家庭不可能没有田宅,何以在遗嘱中只字不提呢?唯一的解释是这种析产行为非先令券书型,而是一般性的分户析产。
三,至于“为何一位父亲如此大规模地把财产转移给与已出嫁的女儿”,甚至可以进一步怀疑一个父亲何以把财产分给身为“小男子”的儿子,仅从简文揭示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不排除我们可以做出多种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析分财产遵循的是“中分”原则,而“爰书”只分予给一个女儿或一个小男,这本身就有悖于传统乡俗。或以为析产的对象都是孤子,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禁止分异的。《户律》规定:“寡夫、寡妇毋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毋异其子。”[3]55按,“小男”一般指7—14岁,据彭卫统计,秦汉时期男子的初婚年龄一般在14—20岁之间[20]89,是“小男子产”可能已成婚别居,但若是“寡子”则不能分异,这都反证了《都乡守武爰书》提到的户主不可能只有一个小男。如果假定“爰书”是遗嘱,而“子小男”又不能在户主生前别居,其按法定继承制度代户继承即可,根本不需要立遗嘱。至于户主“高里士五广”因何把大量的财产给予出嫁的女儿,那是他的合法权利,或者将之看作陪嫁的奁产亦无不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卓王孙起初不肯分一钱,及司马相如以中郎将出使西南夷,卓王孙以为荣,乃“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7]3047。高里士五广未必如卓王孙一般富足,但分予其女丰厚的资财亦在情理之中。
按秦汉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的正本藏乡部,副本上报县廷。民间发生先令析产或“生分”行为,乡部则要“参辨券书”或“辄为定籍”,先令的副本要及时上报,“生分”造成的财产转移也要将“定籍”后的簿书上报。里耶秦简中的“爰书”未必非要作“司法文书”解,亦可以按“具有法律公证意义的笔录文书”[21]183的义项来理解,即把民间自言之析产内容笔录之后上报县廷,正如颜师古在《汉书·张汤传》注“爰书”所云:“爰,换也,以文书代换其口辞也。”[6]2637因此,我们认为把里耶秦简的两份析产“爰书”定性为“生分”或许更为准确。这种“生分”即《户律》337简规定的“相分予”一类的内容,而“爰书”未涉及田宅也与法律相符。
如果我们的推测可以大体成立,从中就不难发现在秦代即使是私人的财产,在让渡给他人时也要谒报官府,经过乡官里吏的“任占”才属合法,由此可见国家对“户”的监管是极为严密的。
四、谨防“户”的残破和人口流亡
家庭是实现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社会细胞。因此,扩大在籍户数和严防人户的脱籍流亡就成为帝制国家的不二选择。秦汉政府一方面强制将大家庭拆分为个体核心家庭,并通过立法鼓励分户析产,另一方面以法律手段谨防“户”的残破以期稳定在籍户数,其核心价值正在于“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
秦代“异子之科”直到曹魏才正式废除,尽管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6号木牍和11号木牍所载两份家书也揭示了商鞅变法后兄弟同居的现象,但商鞅的“分异令”在秦国造就的个体核心家庭的汪洋大海却是公认的事实。实际上,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宗法家族的瓦解,其他各国的家庭结构也在不断趋向微小化,银雀山汉简《田法》概述齐国的家庭人口构成就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9],这种5—7口人的家庭应是当时典型的自耕农之家。目前所见汉初律虽然没有执行“分异令”的痕迹,但鼓励民间分户析产的倾向却是明显的,如《户律》340简规定:
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叚(假)母,及主母、叚(假)母欲分孽子、叚(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3]55
具体言之,不仅子男可以别户析产,尚未立户的子男也可以通过遗嘱形式占有田宅,甚者按继承制度不具有代户资格的寡妻只要有另立户籍的意愿,就可以分割家庭财产。此即《置后律》386简所谓:“其(指寡妻)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予田宅。”此外,女为“户后”一旦出嫁,还允许其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3]61总之,汉政府为鼓励立户可谓不遗余力,当然,诸种另立户者都需要在每年八月履行法定程序,所谓“民欲别为户者,皆以八月户时,非户时勿许。”[3]56
与此同时,秦汉国家还制定了详尽的法令法规谨防“户”的残破。以往,我们只是根据汉人的说辞把秦代非常态的举措作为批判秦政暴烈的口实,其实嬴秦能从列国中脱颖而出必然有其制度上的优势。据云梦秦简可知,秦律中有许多防止因劳动力缺乏而影响农副业生产进而造成民失作业的法令。比如在征发兵役时,一户之中尽管有两个以上的成丁,但严禁同时征调。故《戍律》云:“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2]147就是有罪赀赎或欠官府债而“居赀赎债”,也要轮流服役,所谓“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责(债)而莫见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2]85。这些法令显然都是为了保证家庭生产和“户”的延续而制定的。汉初律虽然对秦律有所调整,但这一立法精神却被继承下来,《户律》就针对一些特殊家庭立法禁止“分异”。
被禁止“分异”的家庭背景涉及四种状况:一是单亲家庭(分为寡夫、寡妇)在没有成年子女与之同居的情况下,“子年未盈十四”;二是在相同背景下,“寡子年未盈十八”;三是“夫妻皆(癃)病”;四是“年老七十以上”,都不允许“分异”。反之,一旦出现以上家庭景象,家长可以要求已经分户的子男“归户入养”,出居之子也可以谒官“归户”[3]55-56。汉律之所以禁止各类残破家庭分户析产,除了伦理因素之外,无非是为了保护个体小农家庭不至于“户绝”,以期最大限度地稳定在籍户数。但“户绝”的现象因战乱、饥荒、瘟疫等又是无法杜绝的。因此,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权时性的补救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许可奴婢代户继承主人的财产,《置后律》382-383简规定:
死毋后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为庶人,以庶人律□之其主田宅及余财。奴婢多,代户者毋过一人,先用劳久、有□□子若主所言吏者。
对上文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一,户绝者的奴婢一律免为庶人,但继承户主身份的只能是其中之一,即奴婢继承的前提是首先取得庶人的身份,优先条件是“先用劳久”或“主所言吏者”。二,无论男奴或女婢都有代户的资格,这和“女为户后”在立法原则上是相通的。三,代户者直接继承其主人的田宅及余财,文中“以庶人律□之其主田宅及余财”的缺字□依前后文义应是“予”字,句意为按《庶人律》给予其主人的田宅和余财[22]。这种做法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物权的体现,其维系“户”的延续才是立法的宗旨。
由此可见,秦汉国家稳定“户”的生生不息的意愿是迫切的,但天灾人祸又总是把无辜的百姓推向流亡的险途,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就有3件涉及平民与奴婢逃亡的案例。在秦汉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民流亡”、民“来去城郭流亡”、“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等更是不绝于书。为此,政府尽管鼓励流民“自占”,把“获流”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同时制定严格的法令强迫流民“自占”,所谓“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3]97。《二年律令·亡律》也针对“吏民亡”、刑徒亡、“奴婢亡”以及“匿罪人”、“取(娶)亡人为妻”、“取亡罪人为庸”等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条例,后世还有“流民法”、“舍匿法”、“通行饮食法”、“沉命法”等,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论构筑起看似如何严密的禁令法网,也无法阻止无以为生的百姓铤而走险。
作为国家的自觉行为,秦汉政府以“户”为统治终端,把百姓编制到乡里体系之中,“户”是合法获取生产资源的前提,也是获取居住空间的依据,“户”的传承由法律来规范,“户”与“户”之间的财产转移也需要经过法定程序才属合法。这种通过对“户”的立法建立起来的乡里秩序,是秦汉时期实现人口控制的依托。乡里体系在后代虽然几经变异,但户籍制度作为帝制国家治理社会的成功经验却一直沿袭下来。
然则,这种基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政治理念和屡试不爽的以剥夺人的自由选择为代价的乡里秩序,不过是专制体制下的强权产物,即使在歌舞升平的年代也不能保证百姓安其田里。其最大的风险在于体制的本质重在压制而不是管理,“可(何)为‘(率)敖’?‘(率)敖’当里典谓殹(也)”,这种缺少道德感召力的刚性化的秩序及其传统惯性造成的官民对立的不断积累,终将由于特大水旱之灾,急征暴赋而引发百姓的群起抗争,表面上固若金汤的网络体系就将被群体暴乱所冲毁,帝制国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会随之一夜土崩。
[1]徐干.中论.汉魏丛书[Z].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2]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3]张家山汉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释文修订本.
[4]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60,高亨译注本.
[9]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J].文物,1985(4).
[10]张金光.秦制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春秋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0,杨伯峻注本.
[12]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高亨注译本.
[13]马怡.里耶秦简选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4]肩水金关汉简(壹):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2011.
[15]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6]王彦辉.论汉代的分户析产[J].中国史研究,2006(4).
[17]张金光.普遍授田制的终极与私有地权的形成[J].历史研究,2007(5).
[18]陈伟.里耶秦简校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9]武汉大学简帛中心.张朝阳.里耶秦简所见中国最早民间遗 嘱 考 略 [EB/OL].http://www.bsm.org.cn/index.php,2012-06-01.
[20]彭卫.汉代婚姻形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21]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2]王彦辉.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