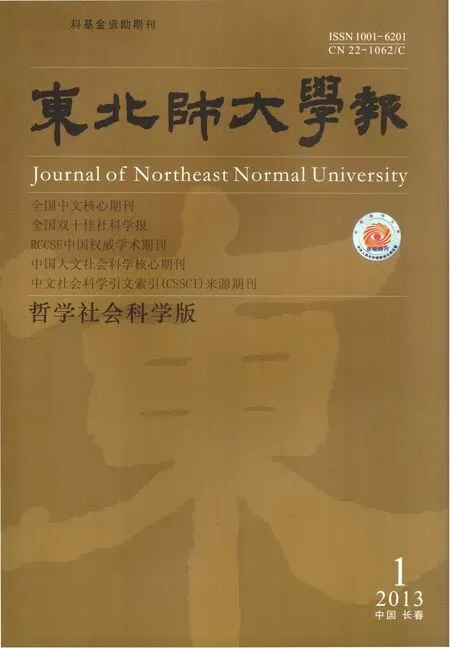先秦两汉宫廷傩礼世俗化演变探析
刘振华
傩,是一种产生于史前的,具有宗教性与艺术性的古老、奇异而又神秘的社会文化现象。“傩”,意为“驱疫”,也即“驱赶鬼疫”。但傩并不是最早的驱疫本字。从夏、商、周到秦汉时期作为驱疫本字,经历了“禓”、“宄”、“难”、“傩”的过程。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将“难”写作“傩”的是《吕氏春秋》:“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1]所以说,傩(难)的本义是“发难”、“责难”之义,胡新生指出它表示的“是一种驱除疫鬼的攻击性行为”[2],引申为“驱疫”。
傩起源于原始的狩猎活动,而后逐渐演变为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正如曲六乙所说:“原始狩猎活动是驱疫之傩一类礼俗得以发生的本源,是由狩猎活动中的驱赶行为逐渐发展演变成为驱疫之傩。驱疫之傩的根就在原始狩猎驱赶行为之中。”[3]至周,傩礼被列入五礼中的军礼,是聚集大众的礼典。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礼崩乐坏”,及至秦汉时期,傩礼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向世俗化方向演变和发展,并最终促成了傩戏的产生。
一、有关史前傩的神话传说
度朔神话,也称黄帝时傩。《论衡·订鬼》:“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4]。王充认为是黄帝创建了傩礼,而《后汉书·礼仪志》中却认为黄帝只是根据度朔桃树的传说,“法而象之,驱除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画郁垒持苇索,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5]3129。这个传说中度朔山上大桃树的内容,后来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富的重要傩俗——桃傩俗。
嫫母护尸。《云笈七签》卷一百:“帝周游间,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祖神。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因以嫫母为方相氏。”[6]宋高承在《事物纪原·方相》中说“嫘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监护,因置方相,亦曰防丧”[7]342。唐代《琱玉集·丑人篇》说嫫母为“黄帝时极丑女也。锤额顣頞,形簏色黑,今之魌头是其遗像。而但有德,黄帝纳之,使训后宫”[8]。以极丑嫫母为方相氏,可以想像方相氏的形象也必定十分丑陋。
颛顼时傩。这个故事《论衡》、《独断》、《搜神记》、《文选》等文献均有记载。《独断》“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为瘧鬼;其一者,居若水,是为魍魉;其一者,居人宫室区隅,善惊小儿。于是命方相氏黄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常以岁竟十二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9]。颛顼发现了小儿鬼作恶,于是命方相氏“索室”时傩。
以上三个神话传说,流露出史前傩仪的几个特点:有相对固定的程序;驱傩的主角是方相氏,且“黄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装扮;其职责是出现在“时傩”和葬礼中。这些特点已具备了周代傩仪的雏形。
二、周代傩礼——古傩的样板
先秦傩仪中最为完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周傩,被称为古傩的样板,而且由于被列入五礼中的军礼,所以作为中国傩礼的源头,其所确立的一系列形式对后世影响极大。宋高承《事物纪原·驱傩》中说,“周礼有大傩,汉仪有侲子。要之,虽原始于黄帝,而大抵周之旧制”[7]310。
(一)三时之傩
虽然傩礼是周代官方烦琐礼典制度中的一个很小的项目,但由于其是严冬腊月中的两大岁时礼典——大蜡和大傩之一,所以备受朝廷重视。《礼记·月令》中记载了国难(傩,下同)、天子难和大难三种傩礼。“国傩”也称“国人难”,是指季春之月以天子和诸侯为主体的王城周族设置的傩礼,“命国难九门磔禳,以毕春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命方相氏帅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之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天子难”是指在仲秋之月天子举行的傩礼,“天子乃难,以达秋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阳气也”;“大难”是指在季冬之月有民众参与的规模最大的傩礼,“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阴气也”[10]。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三种傩仪的规格是有所不同的。《周礼注疏》中贾公彦疏曰:“季春之月,命国难。按彼郑注,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行而出,故难之。……云‘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者,按彼郑注,阳气左行,此月宿直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行,故难之,以通达秋气,此月难阳气,故惟天子得难。云‘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者,按彼郑注,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故难之。”[11]381
(二)周代傩礼的基本形式
《周礼·夏官》中记载:“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圹,以戈击隅,驱方良”。郑玄注曰:“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贾公彦疏:“郑云‘方相’犹言‘放想’,汉时有此语,是可畏怖之貌,故云方相也”[11]431,474。
周代傩礼中方相氏已是四人,且“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形象,其职责是“时傩,以索室驱疫”和“大丧,先柩,及圹,以戈击隅,驱方良”。王国维说:“面具之兴古矣,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似以为面具之始。”[12]王氏说法虽值得商榷,但可以看出方相氏的“装扮”和“表演”色彩。“执戈扬盾”虽是“时傩”之道具,但在“狂夫四人”手中定是动作剧烈的舞蹈动作,而且是“帅百隶”的群舞。同样在“大丧”时,到了墓地要“以戈击隅,驱方良”,一定也是以狂热的舞蹈动作,砍杀各种疫鬼(方良即魍魉),以免它们惊扰了亡灵。
三、秦汉宫傩三制的世俗化
秦汉时期,由于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使傩礼也冲破了周代礼制的束缚,第一次在政治性宗教礼典的基础上,加入了鲜活的世俗成分,初步向世俗化演变,创造出了新的格局。
(一)秉承周制的秦——西汉傩礼
秦傩在史料上几乎没有记载,但秦时应该有傩。《史记》卷121《儒林外传》唐张守节正义曰:“颜云: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传以秦坑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13]
西汉的傩礼,《汉旧仪》中记载:“方相率百隶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撒之。”[14]《礼纬斗威仪》中记载:“(西汉)以正岁十二月命祀官持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15]
西汉傩制与周制已大不相同:一年中只有“正岁十二月”一次傩礼,即周之大傩。没有了春傩和秋傩,而春傩和秋傩分别是“国傩”和“天子傩”。此二傩的取消,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傩礼的逐渐大众化。方相只有一人,百隶还在,但增加了童男童女;增加了乐器—土鼓,以及以“桃弧、棘矢”射杀疫鬼,以“赤丸、五谷”驱鬼(或慰鬼)的傩俗。由此可见,西汉的傩制的确比“周之旧制”相对要复杂些。
(二)“驱鬼咒词”——东汉前期傩礼在世俗化方面的突破
张衡在《东京赋》中所描写的大傩场景,真实地记录了东汉早期的宫廷傩礼:“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氏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必毙。熄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绝飞梁。捎魑魅,斫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象,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魃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于是,阴阳交和,庶物时育。”[16]
与秦—西汉傩礼相比,东汉前期傩礼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程序上复杂了很多,内容也更加丰富了。方相还是一人,但手执斧钺。没有了百隶,童男童女只剩下了童男——“侲子”。他们身着黑衣,头戴红巾,用桃弓苇矢射鬼,用石头瓦砾打鬼,用水泼鬼。增加了巫觋,且手持桃枝扫把打鬼。而且有骑兵加入,他们举着火把将恶鬼赶往四方荒凉之地。然后方相把天池上的桥梁拆掉,使恶鬼再也不能回来了。最后,在大门上立起郁垒和神荼二神的桃偶,他们监视着各个角落,捉拿漏网之鬼。这样,宫廷里就干净了,没有了不好的东西了。于是,阴阳调和了,风调雨顺了,来年一定万物丰产。
东汉前期傩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驱鬼咒词的出现。根据意思,“捎魑魅……况魃蜮与毕方”应该是一段驱鬼咒词。驱鬼咒词的出现,是傩史上的一大突破。因为从史前到先秦,在傩礼上虽一定有呼喊之声,但驱鬼咒词就不仅仅是呼喊了,而是有具体内容的说唱了,东汉前期的傩礼在世俗化方面较之此前更进了一步,更具有观赏性了。
(三)“方相与十二兽舞”——东汉末期傩礼在世俗化方面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末期的傩礼: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天子)乘輿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汝)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三省过,持矩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5]3127-3128。
东汉末期傩礼时间上有了变化,是“先蜡一日大傩”,在蜡日的前一天进行大傩,这和其他朝代的驱傩时间都不相同。人员上有变化,增加了中黄门、冗从仆射和黄门令,最为重要的是增加了“有衣、毛、角”的十二兽。程序上更为复杂,驱傩人员准备就绪后,“夜漏上水”精确计时,文武百官各就各位,皇帝乘龙舆来到前殿坐定,黄门令向皇帝报告:侲子等已准备就绪,请批准逐疫!傩礼开始,由中黄门领倡“十二兽吃鬼歌”,侲子们和,然后跳“方相与十二兽舞”。再由方相率领十二兽和侲子们欢呼着索室逐疫,一共要进行三遍。然后手持火炬把疫鬼驱赶到端门外,端门外骑兵将火炬传给宫门外骑兵,宫门外骑兵又将火炬传给城门外骑兵,最后将火炬弃入洛水,表示将疫鬼赶下了水。仪式结束后,皇帝向百官赏赐苇戟和桃仗。
东汉末期傩礼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十二兽”的出现,这是傩礼在世俗化方面的里程碑式的标志。在傩礼的开始阶段,中黄门领倡、侲子们附和“十二兽吃鬼歌”。“倡”其实就是一种似唱非唱、似说非说的“艺术形式”。“倡”过之后,就是舞——“方相与十二兽舞”。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说,“汉制大傩,以方相四,斗十二兽,兽各有衣、毛、角,由中黄门行之,以斗始却以舞终”[17]。这一“倡”一“舞”,实际上标志着傩礼中已出现具有情节的艺术形式,这和先秦原始的傩仪已有本质上的区别,也显露出些许傩戏的端倪。
从史前有关傩的神话传说,到周代的傩礼和秦汉的宫傩三制,我们不难发现,傩这一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到了秦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时期,在其仪式上的显著变化—开始有了世俗化元素。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傩仪的世俗化又前进了一大步,及到隋唐时期成为主流,最终促成了傩戏的产生,从而也验证了中国戏剧的起源同宗教祭祀仪式间的密切关系。
[1]吕氏春秋·仲秋纪[M].上海:上海书店,1986:76.
[2]胡新生.周代傩礼考述[J].史学月刊,1996(4):8.
[3]曲六乙,钱茀.东方傩文化概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221.
[4]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书店,1986:221.
[5]司马彪撰.刘昭注.后汉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张君房纂辑.蒋力生等校注.云笈七签[M].北京:华厦出版社,1996:611.
[7]高承.事物纪原[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8]佚名.琱玉集[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73.
[9]蔡邕.独断[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10]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04,325,346.
[11]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2]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197.
[13]司马迁著,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17.
[14]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104.
[15]宋均.礼纬斗威仪[M].马国翰.玉函山房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055.
[1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63-64.
[17]任半塘.唐戏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