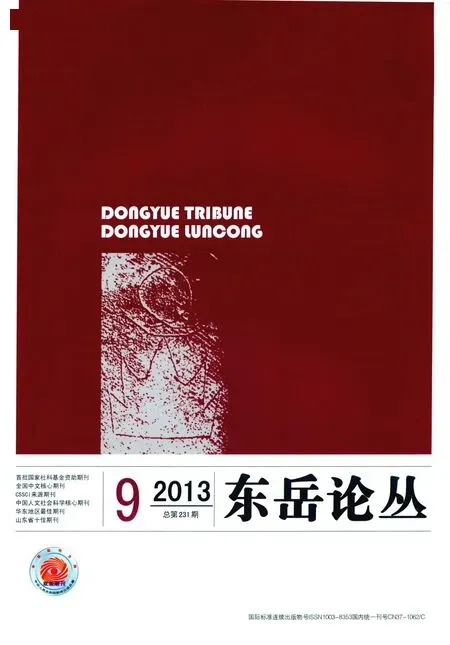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传播策略的当代转型
贾磊磊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毋庸置疑,全球化为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对话平台。文化交流的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特别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信息交流方式越来越普遍。可是,在一个大众普遍参与的文化交流模式中,在一种海量的信息交流活动中,要想实现文化交流、尤其是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我们还有诸多尚需努力的工作,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进行中国文化传播策略的时代转型。我们不仅应当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建立通畅的文化交流渠道,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寻找一种能够保障不同文化相互认知、相互理解的有效方式,以确保文化意义的迅速、有效、准确的传播,而且还应当有效地抵制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话语霸权与文化霸权,保持多样性的文化生态,促进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
一、将中国文化的本土化表达转化为国际化表达
目前,人们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动力、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现象视为全球化的开端,特别是以苏联、东欧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当作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起点①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0页。。可是,由于各国所介入的全球化程度并不相同,进入全球化的历史时段也并非一致。世界各国不是站在同一个文化历史的起点上,尤其是由于各个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不同,尊奉的文化信仰不同,践行的政治理念不同,依循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势必造成在文化理念与文化传播方式上的对立与差异。在人类社会还不可能弥合这种“文化分野”的情况下,对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会显得极其重要,基于这种情况对本土文化的国际化表达也显得越来越紧迫。
那么,什么才是一种本土文化的国际化表达呢?如果,有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那么,我们就要用这种语言来讲述我们的历史故事;如果,有一种国际共有的传播工具,我们就要使用这种工具来传播我们的文化思想;如果,有一种国际共享的信息载体,我们就要用这种载体来传输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不能够期望外国人都去学会了汉语再传播我们的文化,在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多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需要进行升级换代,我们需要用活动影像替代(不是取代)书刊杂志,用彩色影像替代黑白文字,用交互式的互联网替代单向度的印刷品。虽然,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传统文化资源都转化为能够在新媒介上进行传播的文化形态,我们毕竟能够改变“用传统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的陈旧模式,最起码能够让我们的文化产品在格式上,在制作品质上要与国际通行的文化产品相一致。在“传播系统成为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变化的晴雨表和推进器”的时代①丹尼尔·勒纳:《传播体系与社会体系》,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传播话语的国际化转型,是当今社会结构现代性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其转型的现实动因。
目前,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韩国的世宗学院、中国的孔子学院都把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尽管这些机构也举办了许多其他的文化活动,但是,对语言的教学与推广依然是他们的工作重点。这种建立在印刷时代的文化传播理念并没有随着影像时代的来临而相应地有所改变。我们对于文字语言的过度依赖,使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不能够满足现实的迫切需求。跨文化研究的成果表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动时,最明显的差异,乃在于无法共享符号系统(shared symbol system),甚至还会赋予相同的符号不同的意义。这种符号的异质性是跨文化沟通的最大障碍”②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所以,如何利用相同的文化符号系统,实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认同,克服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偏颇与认同误差,是实现不同跨文化沟通的必要前提。
其实,相对于复杂的文字语言符号系统,非文字类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往往能起到更直接、更便捷、更迅速的作用。这类国际共享、通用的文化符号,主要指的是那些依靠视觉图像及其听觉符号进行表述的意义载体。如一幅意境深远的绘画,一支舒缓悠扬的乐曲,一场激情奔放的舞蹈,一段生动幽默的视频,亦或一座气势恢弘的建筑,以及一部流光溢彩的纪录片。这些直接诉诸于人们感觉系统的文化符号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乃至不同信仰的人都能够产生直观的、生动的印象,有时它们甚至比文字语言具有更真切、更直接的传播效应。
总之,传播媒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主流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对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传达中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路径。为此,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实现文化意义的准确互译,防止由于传播方式与传播路径的不当所产生的文化理解的歧义与错位,是实现文化有效传播极其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二、用多向共享的文化传播理念取代单一呆板的文化宣传模式
事实证明,宣传策略并不是最佳的文化传播策略——最起码不是对外文化交流唯一有效的策略。在汉语中,“宣传”这个词十分常用,通常是指对大众颁布政令、政策时所采用的一种公共传播行为。但是,汉语的宣传译成英文时总存在着被曲解甚至被误用的情况。汉语的“宣传”,在英语中一般用propaganda或publicity来表示,前者的含意是指散布某种论点或见解,它最常见的是被放在政治环境中使用,特别是指政府或政治团体支持的政治活动,有时是指那些可能采取虚构或夸张的、引人注意的方法,以及用来为某个政治领导人或政党获取支持或影响民意的做法。在大众传播学中它通常会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例如,对商业广告,人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宣传或说教(propaganda)而已③《“宣传”的各种英语表达方式》,资料来源http://www.tesoon.com/english/htm/07/34937.htm。在《纽约时报》的官方网页中,检索propaganda出现的,几乎都是关于政治宣传的文章。可见,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个词的用法一般还是有保留的。对宣传较为中性的表达是publicity,这个词的使用更为普遍。尽管由于语言的用法会赋予同一个词汇以不同的意义,但是,在关键词语的选取上,依然还是能够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图所在。在新世纪出版的汉英大辞典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改译成了the Publicity Department,CCCPC①吴 景荣,程镇球主编:《新时代汉英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策划、外交部、外文局、新华社、中国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等单位编译的《汉英外事工作常用词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一词由原来的“propaganda”改译为“publicity”②张明权《“宣传”到底该怎么翻译?》中国日报中文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trans/2009-10/27/content_8856201.htm),对此,有关专家曾指出,“这是解放思想、锐意革新的一个具体成果。”③张明 权 《“ 宣 传” 到 底 该怎 么 翻译?》中 国 日报 中 文 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trans/2009-10/27/content_8856201.htm)通过检索《中国日报》的网页,我们发现了793个包含“publicity department”的网页,而包含“propaganda department”的网页只有24个。这已经看出我们对外宣传策略上越来越采取一种中性的词语来表达我们的意图,而不再刻意地将宣传的理念植入到对外文化活动中。然而,在《纽约时报》网站检索中输入“propaganda department”,得到的有两个结果,依然都是关于中国的报道。由此可见,西方传播媒介对中国宣传机构还是存在着固有的偏见,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宣传部门似乎就该叫做“propaganda department”。在我们自己的新华网上,“中共中央宣传部”仍然翻译成“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网页中,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则已经被译成“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按照这个英文词的本义,宣传的概念已经被传播的概念置换。长期从事新闻翻译研究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健教授主张“外宣翻译”一词译为“transl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在以上两个表述中都引入了“communication”(传播)的理念,”来取代“propaganda”(宣传)的理念,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在对外文化传播策略方面,不论是国家的新闻媒介还是主管的中央机关乃至于学术领域大家都对同一个问题越来越形成基本的共识。我们深知,对外文化交流乃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是靠一两个概念的置换就能够实现的。我们在此所强调的主要问题尽管限定在核心概念的使用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视野仅仅局限在单一的语言范围内。
英语中的“传播”(Communication),原意中包含着通讯、通知、信息、传达、传授、交通、联络、共享等多重意思。1945年11月16日,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宪章中,曾经这样写道“为用一切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手段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协同努力。”其中的mass communication被翻译为“大众传播”(专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而言),所以,这些媒体也就被统称为“大众传播媒体”。由此可见,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相互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交互运行。传播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单向的宣传诉求,而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机构与机构、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系统进行的信息传递、接受或反馈活动。采取这样一种建立在双向互惠基础上的文化传播策略,无疑比那种单向度的文化宣传模式更容易使对方接受,进而也会更为有效。
传播学巨匠麦克卢汉在1964年就提出了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地球村”概念。他认为,电子媒介在传播重大事件与各种信息的同步化,使地球在时空范围内“缩小”为一个人类共同居住的村落,进而人类进入了“重新部落化”的时代。这种“重新部落化”导致人们需要大众传媒提供一个可以通过想像认同的文化空间。在传播媒介疾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必须考虑到我们的任何文化表达都是一种面对全球媒体的文化宣言——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它都必将是一种即时性的、外向性的、世界性的表述。正像安东尼·吉登斯所强调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秩序之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影响他人而同时被他人所影响。”④“Anthony Giddens and Will Hutton in Conversation,”in:On the Edge: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ed.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London:Jonathan Cape,2000,pp.1.所以,我们要用多向共享的文化传播理念取代单一呆板的文化宣传模式。这就是说,我们在传播一种文化理念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能否为对方提供一种艺术享受与审美体验,抑或是一种资讯服务,进而达到心灵层面的相互沟通。
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曾经发表了针对孔子学院的批评性文章。其中核心的观点,就是批评孔子学院并不是一个文化的传播机构,而是一个文化的宣传机构。因为宣传的主导动机与文化的传播效应并不能够相提并论,最起码与人们所期望的文化交流并非一致。孔子学院在西方某些著名高校受到抵制,也是基于他们对孔子学院宣传职能的误解,因为这种带有政府宣传职能的运作模式与他们想象的学术理念相互抵牾,进而造成了文化传播上的深度隔阂。所以,在文化艺术领域,官方的、政府的角色在国际交流、特别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应当“后置”,推到前台的应当是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艺术院团以及民间文化艺术团体。这样反而能够达到更有效、更广泛的传播效果。
三、实现文化产品在文化取向上的通约整合
目前,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型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犹如巨流奔涌,引起泥沙俱下。在我们面前,不同文化时代的各种角色同时登场。现实的生活几乎能够为各种不同的价值判断提供事实依据。恰恰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的社会现在越来越缺少普遍的集体共识,越来越难于确立共同的价值标准,以至于在我们的社会中显露出前所未有的价值裂变。处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产品应当对这个社会的精神走向起到一种引领与导航的作用。而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需要对文化产品形态中所表达的价值观进行通约与整合,而不能将文化产品的经济、社会以及艺术职能肢解开来,好像艺术电影就是浑身的个性,可以完全不顾及观众的感受;商业电影好像就是一脑门子金钱,可以放弃任何的文化责任;主旋律电影就是满腔的时事政策,根本无须考虑观众的审美要求。我们要在文化产业的生产机制中寻找最大的通约性,来整合文化产品的审美、娱乐与教育功能,来实现文化产业在艺术、商业与思想维度的相互统一,而不是将它们相互对立起来。在世界电影史上有许多主流商业电影,在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与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要实现文化产品在价值理念上的通约整合,就要求我们的文化作品不论讲述的是什么时代的历史故事,选择的是什么类型的叙事形态,都应当体现出中国文化共同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风格影片中各说各话。中国文化产业所承传的价值观不是一个艺术风格的展现问题,而是一种叙事艺术的表达策略问题。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在文化产业领域,我们任何文化价值的表达,其实都是建立在观众对作品的总体认同的基础上。观众不可能接受一部在审美的感觉上被拒绝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他们也不可能将一部作品的人物先推出银幕,然后再来接受它留下来的文化思想。美国戏剧理论家阿诺尔德·阿隆森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戏剧可以没有剧本,没有舞台,没有布景,没有灯光,没有道具,没有服装,甚至可以没有演员,那么,剩下的什么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呢?是观众①汉 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李亦男译,译者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ⅱ。。所以,“观众”在二十一世纪将成为当代戏剧的本质。在相同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现在的电影什么都有,有编剧,有导演,有资金,有特技,当然还有明星,那么,我们没有的是什么是呢?依然是观众——或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观众。一部没有人观看的电影,所有的价值诉求都等于零。只有观众存在,其他的所有价值才有可能一一兑现。
面对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国不可能将文化体系封闭起来进行自我表达,势必要与不同的文化资源进行通约整合。所谓通约,在人文科学领域,通常是指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同构、相互重合的部分。如精神分析学与心理学、符号学与语言学、美学与艺术哲学都是具有通约性的学科。科学哲学家库恩曾经用“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②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来表示新、旧两种科学研究范式之间质的差别。在他看来这种不可通约性近似于两种语言的“不可翻译”。在数学领域的涵义是,假如两个不等于零的实数a与b相除,商是一个有理数,则意味着它们之间可以进行通约。数字中的这种特性称之为可通约性。例如,8除以4等于2,那么,8与4这两个数就具有可通约性。如果8除以3,两数不可以除尽,商不是有理数,而是无限循环的小数,这两个数即不具有通约性。在天文学里,两个公转于运行轨道的天体,如果它们的公转周期的比例是有理数,那么,它们相互就会呈现出可通约性。例如,海王星与冥王星的轨道周期的比例是2:3,这两个恒星天体就具有通约性。
固然,在文化领域寻求通约性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我们知道,与物质的价值不同的是,文化的价值具有相对性。凡是物质性的东西,在世界上一般都具有统一的认定标准。珠宝在任何民族都是拥有财富的标志,黄金在所有国家都是经济实力的体现。可是,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对某个民族来讲可能被奉为金科玉律,可是,对另一个民族来讲也许并不为惜。所以,在文化领域寻求通约性首先会受到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反对,在“那些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看来每种文化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和伦理,不能以一种文化的目标和伦理为尺度来衡量和要求另一种文化。”①劳伦斯·哈里森:《文化为什么重要》,载塞缪尔·亨廷顿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第14页。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者还会以殉夫自焚、甚至奴隶制度来为自己寻找事实依据来抵制文化的交融与整合。美国人类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1947年还不赞成联合国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由此可见,在世界上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共享的价值观,面临着诸多障碍。在物质领域,尽管一桶石油的价格也会随着市场的波动时起时伏,可是石油的物质属性和实用价值并不会改变,它永远都是驱动汽车奔跑的能源。可是,一种文化价值,有时会在并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在“十年动乱”时期举国信奉的价值观今天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文化价值的这种相对性与易变性使人们对于文化价值的确认,难以建立一种恒久的历史共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共同的文化价值开始持有信心。比如,人们现在都会认可文明比愚昧好,光明比黑暗好,和平比战乱好,正义比邪恶好,富裕比贫困好②劳伦斯·哈里森:《文化为什么重要》,载塞缪尔·亨廷顿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第14页。。这些被世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使不同文化之间具有了某种可通约性。在文化产业领域、尤其对于那些对海外的文化市场有依赖的行业,更要寻找这种可通约性的切入点,这是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被他人接受的心理基础。
如果,我们将文化产业的空间视为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对弈舞台的话,那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我们不能够采取一种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零和”思维来建构我们的价值体系。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在价值观上都是相通的。举例来说,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叙事主题是为了让一个普通的士兵在惨烈的战争中活下来,那么,中国电影《集结号》的叙事主题则是为了让那些死去的普通士兵能够永生;如果说,美国电影关注的是普通人存在的生命价值,中国电影关注的则是普通人牺牲后的生命意义;美国电影是通过防止人的自然死亡来强调生命的意义,中国电影拒绝的是人的“符号性死亡”来强调人的精神价值;在人类价值观的天枰上,中国电影讲述的价值观同样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旷世情怀。为此,对任何一部电影、电视剧,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它在叙事情节上的合理性、人物性格上的合理性,美学风格上的合理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它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够将影片情节的可信、性格的鲜明、艺术的完美作为创作的全部要求,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在作品中所传播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理念,体现的是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塑造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形象。
四、改变厚古薄今的文化传播策略
中国在迈向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将一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现实的文化形象,“植入”到我们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表达方式之中。我们不能再以封建社会旧中国的文化遗产、民国时代旧社会的文化符号作为我们当代国家的文化标志。我们现在需要建构与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而不仅是那些深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静卧在博物馆里的古董,沉睡在古籍中的文字。我们能够将它们作为文化遗产予以保护,能够作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予以承传,但不能够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来推广。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能够进入市场具有竞争实力与博弈能力的文化产品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抗衡。有些传统文化遗产只能够作为珍品予以收藏,而并不能进入文化产业的流通市场进行推广,而一种不能够进入流通市场的文化产品,无论它过去怎样辉煌,都不能够承担当代中国文化形象建构的时代使命。进而言之,当代中国期望别人认同的并不应当只是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还是那些能够体现我们时代特征的、绚丽多姿的当代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都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被建构、被塑造的。为此,我们应当按照当代文化的市场需求来配置文化产品的构成元素,根据流行文化的交流方式来搭建文化产业的交易平台,根据当代中国的现实地位来铸造我们的文化形象,根据国家发展的未来需求来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固然,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有长城、十三陵、故宫、颐和园,同样我们当代文化的典范也有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国家数字化影视制作基地;我们的传统艺术形式有京剧、昆曲、琵琶、古琴,我们当代文化形式还有流行音乐、3D电影、网络游戏。我们的国产影片曾经屡次超过好莱坞进口影片夺取年度单片票房冠军;我们有些娱乐性的电视节目尽管创意取自欧美电视市场,可是现在反过来却在节目形态上影响到海外同类的电视节目的设计;我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所创作的令世人瞩目的小说,我们流行音乐的组合还登上了欢迎外国总统的演出晚会;我们的表演艺术团体(残疾人艺术团)曾经作为联合国的和平特使出访世界各国……这些都是能够体现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文化产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能够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代言人。如果我们总是年复一年地让外国游客上长城,游故宫,听京剧,看陵墓,这样不仅会强化他们对一个旧中国的历史记忆,而且还有可能会消解他们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印象。总而言之,文化的力量不是靠自我命名、自我确认来实现的,我们的文化只有得到他者的认同,只有赢得他者的肯定,才能够兑现我们文化的价值,才能够实现我们的文化影响力。
我们还应当看到的是,全球化的进程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建构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同质化,使得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模糊了那些国家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特征。这就是说,掌握了新媒体核心技术的国家,利用强势的科技力量,可以对其特有的文化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传播,而在新媒体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自身的文化难以通过有效的技术平台进行传播,而且其自身的文化还面临着一种被覆盖、被取代、被压制的境遇。发达国家还利用政治与经济的优势,在双边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交易中制造文化上的不平等,致使文化多样化的合理诉求在无形之中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抑制。
在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上,尽管我们不赞成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但是,不管我们借鉴的是哪种文化类型的衣钵,最终连接的都是我们本土文化的“地气”。这个本土化,即指的是我们的作品对自己脚下谋生图存的这片土地的关注,也指的是对我们自己头顶上魂牵梦系的文化天空的认同。美国电影可以利用它覆盖全球的发行放映网络,传播它的商业影片及其文化价值观,可是,发展中国家的电影要想进入美国的电影院线,首先遇到的就是难以支付的高额发行费用。在这种窘境中,所有建立在商业平台上的文化交流诉求,都有可能付之东流。事实上,文化多样性的愿景,在这种看似平等的市场逻辑中,正陷入一种更深的不平等。可是,我们的有些电影作者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文化的现实处境,致使我们在经贸领域通过艰难谈判争得的本土电影市场,却在心理上远离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一位远在美国留学的北大学子在看过影片《中国合伙人》后说,“我承认在这部电影中有很多正面的能量和信息,比如说在困境中背水一战的精神,在创业中愈挫愈奋的勇气,还有兄弟之间的真情等等。可是,在人生轨迹中,从始至终,成冬青们的梦想都是以美国为轴心在疯狂地运转。一个迟迟未被实现,因而显得更加急迫的美国梦始终是成冬青们走不出来的阴影和怪圈。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成冬青们‘新梦想’的内容始终被美国所定义。在‘新梦想’占领华尔街的那一刻,不知道是成冬青们征服了美国,还是华尔街征服了燕大的湖光塔影?”也许,有人会说,一个被美国定义的梦想有什么不好?然而,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罢,如果我们永远捆绑在他者的轮子上,我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论呢?我们不否认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与美国人有类似的地方。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可以以别人的目标为基准来校正我们的方向;在物质世界中,我们也可以以他者的标准为尺度来衡量我们的高度。唯独在文化精神与理想境界上,我们不能够自我泯灭我们的民族个性,不能够丧失我们的文化品格。也只有这种多元文化的世界远景,才是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