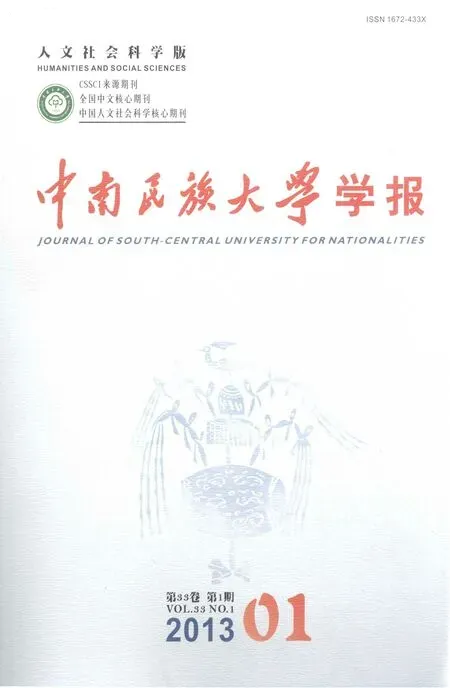西汉社会转型对王褒文学创作新变的影响
龙文玲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530001)
前人对王褒文学成就曾有精辟评价,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比较先秦两汉十大赋家特点时指出,“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1]135,特别拈出了王褒赋“穷变”的特点。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王褒在两汉之交的文学史进程中有开导先风的作用:“西京之流而东也,其王褒为之导乎!”[2]6667而王褒创作之所以有如此鲜明的新变特点,并在西汉走向东汉的文学史进程中起到开导风气的作用,不仅与其本人的个性、才学和创作理念有关,更跟其所处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一、社会转型对王褒文学内容新变的影响
据笔者考察,王褒文学活动大致在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至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间,正处西汉社会在宣帝统治下,变武帝的武力扩张为偃武兴文的转型期。社会转型的时代特色,对王褒文学创作的新变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1.变抨击武帝弊政为讴歌国泰民安、外患平息的时代新貌。汉武帝变汉初无为政治为有为政治,师旅连出,虽迫使匈奴远遁漠北,但也使汉帝国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4]233的惨重代价。为奉征伐,他实施了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并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以维护其政令推行,导致民怨沸腾。对此,司马迁《史记》就有深刻揭露。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也对其弊政给予了猛烈批判。对武帝政治的反思与批判,使昭宣时期形成了“崇文过武”文学主题。
武帝死后,霍光辅佐昭帝,调整政策,根据武帝晚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4]3914的轮台诏精神,变多欲扩张为备边养民,终于使汉帝国平稳度过危机。宣帝即位,外交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友好与控制,对势衰的匈奴重德义而慎出兵。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型获得了巨大成功,除巩固了西域诸国的友好,还极大改善了汉匈关系,使日逐王来归,呼遬累单于称臣朝贺,呼韩邪单于奉国珍来朝,西北边境得到安定。《汉书·匈奴传下》就描述了单于来朝后的太平景况:“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菞庶亡干戈之役。”[4]3832-3833《汉书·食货志上》也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情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4]1141宣帝时期在休息养民、兴文偃武政策下出现的这些社会新貌,在王褒作品中得到及时反映,由此前作家侧重批判武帝弊政,转向了讴歌宣帝时期国泰民安、外患平息的时代新貌。这以《四子讲德论》为代表。此论开篇即借微斯文学之语,“盖闻国有道,贫且贱焉,耻也”[5]711,表达了对宣帝治世的肯定。论中还借浮游先生之口:“太上圣明,股肱竭力,德泽洪茂,黎庶和睦,天人并应,屡降瑞福。”[5]712颂扬了宣帝时明君贤臣治世,使百姓获得安居的业绩。参以《汉书·循吏传》载宣帝亲政,“历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4]3624《宣帝纪》载:“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4]275可知宣帝不独勤于政事,而且注重整顿吏治,推动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4]275中兴局面的形成。由此亦可见王褒的颂扬不为虚美。
除颂扬君明臣贤、百姓安居,《四子讲德论》还讴歌了宣帝的惠民政策:“举孝以笃行,崇能以招贤,去烦蠲苛以绥百姓,禄勤增奉以厉贞廉。减膳食,卑宫观,省田官,损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灾害,不遑游宴。闵耄老之逢辜,怜缞绖之服事,恻隐身死之腐人,凄怆子弟之缧匿。恩及飞鸟,惠加走兽,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5]715据《汉书·宣帝纪》,这里列举的惠民政策皆本于宣帝诏令。由此可知,汉宣在革除武帝重徭役、严刑法、兴宫室等弊政方面发布了一系列改良政令。而这些都给王褒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四子讲德论》还颂扬了外患平息的历史新貌:“夫匈奴者,百蛮之最强者也。……三王不能怀,五伯不能绥,惊边扤士,屡犯刍荛,诗人所歌,自古患之。今圣德隆盛,威灵外覆,日逐举国而归德,单于称臣而朝贺。”[5]716在唐前游牧民族政权中,匈奴最强大,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亦最持久。《诗经》就有部分反映周王室抵御匈奴侵掠的诗篇。汉宣帝之前,先有秦始皇举全国财力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后有汉武帝举汉兴六十余年积蓄征伐,使单于远遁漠北,但都未曾使单于臣服。因此,宣帝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促成了单于称臣朝贺的重大历史事件,消除了周代以来中原政权面临的北方边患,确为历史的重大转折。《四子讲德论》及时表现了这一内容。同样内容在汉《鼓吹铙歌·远如期》中也有反映:“单于自归,动如惊心。虞心大佳,万人还来,谒者引,乡殿陈,累世未尝闻之。”[6]643新时期的政治军事胜利,给王褒等作家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作品呈现出新的气象。
2.变借颂瑞肯定征伐为颂扬统治者兴文偃武、修政固权。王褒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正逢汉宣帝亲政固权。《汉书》多次提到宣帝“修武帝故事”,然而,宣帝并非简单模仿武帝修郊祀,兴礼乐,而是通过此举宣扬其继统的合理性,神化皇权统治,巩固政权。在自我神化时,宣帝和武帝一样重视称颂天命符瑞。不同的是,武帝注重借祥瑞为大一统和武力扩张造舆论,而宣帝则侧重宣扬自身继位合理性,及其休息养民、兴文偃武措施获得上天肯定。在此可以《汉书》本纪载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郊祠泰畤诏》和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匈奴来降赦诏》对比说明。武帝诏追述获宝鼎与渥洼天马,由此引逸《诗》“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表示当趁此祥瑞“亲省边垂,用事所极”[4]185。这显然是借祥瑞宣扬征伐匈奴的合理性。宣帝《匈奴来降赦诏》则先指责匈奴曾“数为边寇”,然后提到虚闾权渠单于请和亲、呼遫累单于来降归义、单于称臣朝贺,使“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4]266-267等系列事件,接着自称因匈奴称臣而亲行郊祀,获天降神光、甘露、神爵、凤皇等祥瑞。这就将消除边患的宏伟业绩跟天降祥瑞联系起来了。在此,宣帝宣扬因消除北方边患而获祥瑞,跟武帝强调因武力征伐而获嘉祥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据《汉书》记载,宣帝时所获祥瑞以凤皇最多,而武帝时祥瑞虽多却无凤皇。据《汉书·宣帝纪》,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宣帝诏称凤皇集泰山、陈留时引《尚书》:“凤皇来仪,庶尹允谐。”颜师古注:“《虞书·益稷》之篇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言奏乐之和,凤皇以其容仪来下,百兽相率舞蹈。是乃众官之长,信皆和辑,故神人交畅。”[4]254在先秦两汉时人看来,凤皇出现,预示着神人交畅、上下和谐。歌颂这样的瑞应物,也可见宣帝对政治和谐稳定的追求。
宣帝时期颂瑞内涵呈现的这些变化,在王褒作品中也有突出反映。如同是颂麟,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因获白麟作歌,“图匈虐,熏鬻殛。辟流离,抑不详,宾百僚,山河飨”[4]1968,借颂麟为征伐匈奴张目;终军在武帝“博谋群臣”时作《白麟奇木对》,颂扬“大将军秉钺,单于犇幕;票骑抗旌,昆邪右衽。是泽南洽而威北畅”[4]2815,借颂麟为武力征伐推波助澜。王褒《四子讲德论》也颂麟:“今海内乐业,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灵。神光燿晖,洪洞朗天。凤皇来仪,翼翼邕邕。群鸟并从,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栉比。大化隆洽,男女条畅。家给年丰,咸则三壤。岂不盛哉!”[5]716这显然是借宣扬神雀、麒麟等祥瑞赞颂朝廷施行仁政的效果,从而与武帝、终军颂麟目的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凤皇来仪,翼翼邕邕。群鸟并从,舞德垂容”,实受宣帝诏影响,以“凤皇来仪”象征政治和谐清明。由此可见,在历经武帝战争和扰民政治的痛苦后,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文人,都企盼能施德政,致和平。
此外,王褒《甘泉宫颂》:“窃想圣主之优游,时娱神而款纵。坐凤皇之堂,听和鸾之弄。临麒麟之域,验符瑞之贡。咏中和之歌,读太平之颂。”[7]1115想象宣帝在甘泉宫校验符瑞,欣赏中和太平的歌颂。《文选》李善注引王褒《碧鸡颂》“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5]757,以黄龙、白虎之瑞呼唤金马碧鸡神归来,都体现了宣帝时期歌颂偃武兴文、仁德和谐的颂瑞特征给王褒创作带来的影响。
3.变抒写不遇感伤为纵论新形势下君臣遇合的理想。自屈原《离骚》后,反映君臣遇合问题的作品就不绝如缕。汉武帝时期,由于皇权专制的弊端及武帝视人才为有用之器的人才观,导致这类作品多倾诉不遇感伤,追问不遇根源。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均哀叹生不逢时,有能不陈;东方朔《答客难》揭露皇权专制下帝王凭一己好恶决定臣民升迁的不合理用人制度。昭帝时期盐铁会上的贤良、文学还认为文人不遇的重要原因在于武帝将儒臣变成缘饰政治的工具①参见拙文《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载《学术论坛》2012年第1期。。盐铁会后,为稳定政权,统治者霸王道杂用,在重用文法吏士的同时,也任用魏相、萧望之等通达儒士。只要将《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所列名臣的教育背景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宣帝时期修习儒学的名臣较武帝时明显增多。另外,宣帝勤政,除诏举贤士,还重视考察、擢升地方官吏,使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吏治改良,一定程度改善了人才进用的环境,也给王褒等文人带来了君臣遇合的希望,并使他们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以往作家更全面而深刻的思考。
王褒对君臣遇合问题的思考,首先在于给贤才做了一个明确定位,即《圣主得贤臣颂》所云:“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4]2823此定位与汉武帝“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8]638的表述相似,但内涵不同。武帝从专制帝王角度出发视人才为“有用之器”,认为只要帝王能识才,就不愁无才;人才若不为所用,就该杀掉。王褒则从维护士人利益角度出发,把贤才提升为治国利器,认为贤才在治世中当积极求仕显才,帝王亦应改善用人渠道,“以延天下英俊”,依靠贤者“建仁策”、“树伯迹”。[4]2823
其次,指出君臣遇合乃千载一遇,士人当积极开拓求遇渠道,如《四子讲德论》所云:“夫特达而相知者,千载之一遇也;招贤而处友者,众士之常路也。”[5]712这种积极求遇的态度与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感伤显然不同,与东方朔和盐铁会上的贤良、文学的愤激也不一样。它反映了在用人渠道改善的社会里,文人对入仕显才充满了渴望与信心。
再次,在治国问题上,认为明君贤臣共治方能获致功德弘业,如《圣主得贤臣颂》所云:“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4]2827把君臣关系视为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难能可贵。这种认识也跟当时统治者相对开明分不开。《汉书·循吏传》载宣帝语:“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4]3624正是受统治者相对尊重人才的时代精神感发,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才得出这样的认识。
本着对君臣遇合的理想,王褒《四子讲德论》还称颂宣帝勤于求贤获致群贤毕集:“屡下明诏,举贤良,求术士,招异伦,拔俊茂。是以海内欢慕,莫不风驰雨集,袭杂并至,填庭溢阙。”《圣主得贤臣颂》还展望了君臣相得共建功业的盛世前景:“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4]2827由这些深情讴歌与展望,足见宣帝时期仕进环境改善给文人立德立功的昂扬奋发心态带来的影响。
4.将文学书写的笔触由上层社会拓展到底层社会。王褒创作内容相对前代作家视野阔大,突出表现在他将文学表现的笔触由上层社会延伸到社会底层。其《僮约》通过买僮券契中对奴仆劳动内容的详细罗列,客观反映了农庄奴仆一年四季每天从早到晚的艰辛劳作和困苦生活。《责须髯奴辞》通过对髯奴面容清瘦“常如死灰”、须髯肮脏零乱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悬殊、阶级尖锐对立的现实。这样的内容在此前文人作品中未曾有过。武帝时期虽作家众多,文学成就巨大,但他们多关注帝王与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反映普通百姓生活者鲜有。盐铁会上的贤良、文学在反思武帝政治时,关注到弊政下普通百姓的艰难困苦,但因其目的是通过反映民间疾苦来指陈时弊、改良政治,故未具体描述百姓的生活样态。因此,王褒这两篇作品的出现,无疑丰富了西汉文学的表现内容。
此外,王褒《洞箫赋》描绘了洞箫制作过程,是今存最早的乐器赋。《甘泉宫颂》描写了甘泉宫的壮美,是今存较早的宫殿赋。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宣帝时代新的物质文明,表现了宣帝中兴期乐器制作与宫殿建筑的高超技艺。
二、社会转型对王褒文学艺术新变的影响
王褒文学艺术的新变,同样跟其所受时代风气的熏染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声偶渐谐,声貌穷变,推助了两汉之交文章渐重声律骈偶的风气。张溥评王褒:“奏御天子,不外《中和》诸体,然辞长于理,声偶渐谐,固西京之一变也”[3]153,还指出了王褒作品的新变特点跟其主要为“奏御天子”而创作有关,可谓知言。据《汉书·王褒传》:“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4]2829说明王褒待诏后的创作主要是在与张子侨等宫廷文学侍从竞技逞才的氛围中写成的。奏御天子、竞技逞才的创作目的,必然促使王褒勤于艺术探索,从而形成了“辞长于理,声偶渐谐”的艺术特点。
应该说,王褒之前的作家在声韵和谐、整齐对偶的语言艺术美方面已有关注,如李斯《谏逐客书》、贾谊《过秦论》、枚乘《七发》,就运用了对偶句式。司马相如还强调赋之迹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9]12。“一宫一商”,就蕴含着对汉赋声韵和谐美的追求。王褒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吸取前代作家的艺术经验,在这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
如《四子讲德论》多由声韵和谐、对偶整齐的句式组成,其中,“夫特达而相知者,千载之一遇也。招贤而处友者,众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无刃,公输不能以斲;但悬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腾撇波而济水,不如乘舟之逸也;冲蒙涉田而能致远,未若遵涂之疾也。”[5]713用了四个语气词“也”,四个连接词“而”,读来朗朗上口。而“空柯无刃,公输不能以斲”与“但悬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膺腾撇波而济水,不如乘舟之逸也”与“冲蒙涉田而能致远,未若遵涂之疾也”则构成了两两相对的骈偶句。《洞箫赋》以骚体句式为主,较《四子讲德论》声韵更和谐,对偶更精巧。如赋开头描写箫干生长环境:“翔风萧萧而迳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磕磕而澍渊。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5]244不独运用“兮”字造成音韵和谐的效果,而且“山”、“渊”、“颠”、“间”几字还互相押韵,构成韵脚。在偶句的运用上,除“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磕磕而澍渊”,其它均整齐相对。《甘泉宫颂》基本由四六句式组成,其结尾“坐凤皇之堂,听和鸾之弄。临麒麟之域,验符瑞之贡。咏中和之歌,读太平之颂。”[8]1115用“坐”、“听”、“临”、“验”、“咏”、“读”等六个动词,将六个整齐的四言句串联起来。这种句式结构,更见王褒创作的独运匠心。
王褒在文学语言艺术上的这些探索,使其作品更宜诵读。《汉书·王褒传》即载:太子体不安,“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萧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4]2829诵读王褒赋可以治病,这可能有夸大,但足以证明其赋骈偶整齐、音韵谐美所别具的艺术感染力。正因如此,其作品在当时宫廷中已广为传诵,并对东汉骈偶渐行起到了有力推助作用。
2.雅俗兼综,推进了汉代文章风格的多样化。王褒创作的这一新变亦跟时代影响密切相关。为巩固政权,宣帝讲论六艺,兴礼乐,任用雅琴乐师赵定、龚德为歌诗协律,促使此期乐府乐曲较武帝时多雅声。汉《鼓吹铙歌·远如期》描写接待单于时的乐舞场面即云:“雅乐陈,佳哉纷。”[6]643并且,宣帝不仅欣赏典雅艺术,也喜好愉悦耳目的音乐和辨丽可喜的辞赋,曾宣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4]2829这种对文学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包容态度,必会引导一时风气。
受此影响,王褒初出茅庐就步追《雅》、《颂》。他创作的《中和》、《乐职》、《宣布》三首诗被王襄令人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被宣帝赞为“盛德之事”。其《四子讲德论》还解释作诗意图:“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吉甫叹宣王穆如清风,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伪臣虚称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5]713表明了对周公、尹吉甫颂德事迹的追慕,强调了在世平道明之时歌颂统治者业绩的必要性。论中还描述微斯文学和虚仪夫子听浮游先生、陈丘子歌咏《中和》等三首诗的感受:“咏叹中雅,转运中律,啴缓舒绎,曲折不失节。”由《中和》等诗的传播方式、读者解读和作者的自我阐释,足见颇有《雅》、《颂》遗风。步追《雅》、《颂》,力主颂德的创作理念,促使王褒艺术风格呈现出典雅雍容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重视引用儒家典籍,使作品典雅醇厚。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汉代文人引用儒家典籍日渐增多。相比而言,武帝时期像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这类坐而论道、典雅醇厚的文章并非主流,更多还是司马相如式的宏伟壮丽和司马迁式的雄深雅健。宣帝时期,随着社会矛盾趋向缓和,王褒延续了董仲舒的典雅醇厚之风。如《四子讲德论》虽以四人对话形式展开,但没有针锋相对的辩驳,而是通过对话引出干禄的愿望,解释《中和》等诗的意旨。其中多次化用了儒家经典,如“盖闻国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出自《论语·泰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10]2487。又如《圣主得贤臣颂》开头:“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借《公羊春秋》义,引出圣主得贤臣的最终目的:正统,稳定政权。这些儒家典籍的引用富于理智,有力营造了作品的典雅醇厚之气。
二是注意使用舒缓的语气词和节奏平缓的句式,使辞气舒缓雍容。如《四子讲德论》歌颂宣帝正统固权、兴文偃武之功:“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获白虎,亦偃武兴文之应也。获之者张武,武张而猛服也。是以北狄宾洽,边不恤寇,甲士寝而旌旗仆也。”[5]716连用四个语气词“也”,辞气徐舒。三个连词“而”的使用,更加强了文章的和缓语势。《四子讲德论》、《洞箫赋》还大量运用节奏平缓的四言句,颇具《雅》、《颂》遗风。
在追寻典雅雍容艺术的同时,王褒还创作了《僮约》、《责须髯奴辞》等诙谐通俗作品。《僮约》开头与结尾都用简明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对话书写。如开头一段写狂奴便了拒绝为王褒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但约守冢,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子泉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奴父许人,人无欲者。’子即决卖劵云。奴复曰:‘欲使皆上劵,不上劵,便了不能为也。’”[11]466通过富于个性化的语言,把便了桀骜不逊而又刁钻狂傲的形象栩栩如生描画出来。文章结尾:“读劵文徧讫,词穷咋索,仡仡扣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11]467又活灵活现勾勒出便了面对券文无缝可钻的劳作规定恐惧痛悔的狼狈情态。两段文字,对比鲜明,勾勒出便了前傲后卑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责须髯奴辞》以须髯为描写对象,将贵族跟髯奴之须髯进行对比,刻意突出髯奴胡须“既乱且赭,枯槁秃瘁,劬劳辛苦,汗垢流离,汚秽泥土,伧嗫穰擩,与尘为侣”[11]466,从而使其卑贱困苦形象如在目前。无论是《僮约》还是《责须髯奴辞》,都营造出轻松诙谐、生动活泼的喜剧氛围。作品将处在社会底层的奴婢作为挖苦对象,其轻视体力劳动者的世界观应当批判。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褒以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充分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和鲜明对比的手法,获得了“辞浅会俗,皆悦笑也”[1]270的艺术效果,亦给后世以人物为题材的俳谐作品如蔡邕《短人赋》等提供了艺术借鉴。
3.开创了新的九体辞赋形式,在七言诗发展进程中进行了有益尝试。王褒《九怀》是一篇拟骚赋。在内容上虽无明显创新,但艺术形式上开创了新的九体辞赋形式。王逸《九辩章句序》评:“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12]182认为《九怀》源自《九辩》,不无道理,但《九怀》采九立义,为每一义立一小标题,不仅使这一篇幅甚长的作品眉目清晰,而且便于诵读。汉人拟骚赋立小标题,始于《七谏》,而运用到九体中,则始于王褒。此后的九体作品就基本沿着王褒开创的这一形式创作了。
《九怀》篇末的乱辞是一首七言系诗:“皇门开兮照下土,株秽除兮兰芷睹。四佞放兮後得禹,圣舜摄兮昭尧绪,孰能若兮愿为辅。”[12]280每句押韵,用韵虽稚拙,但运用比兴手法颂扬宣帝治世,表达了积极求仕之情,是今存最早附在辞赋后的七言诗。班固《竹扇赋》、马融《长笛赋》、张衡《思玄赋》均有七言系诗,溯其源,恐怕与王褒等西汉作家的艺术形式探索有关。由此可见,王褒在七言诗发展史上所作的有益尝试。
总之,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王褒在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上都做出了可贵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褒文学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其本人的俊才,而且也得益于汉宣帝时期社会转型的时代之助。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王世贞.弇州四部稿[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6667.
[3]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欧阳询.艺文类聚[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15.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葛洪.西京杂记[M]//燕丹子 西京杂记(合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12.
[10]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87.
[11]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