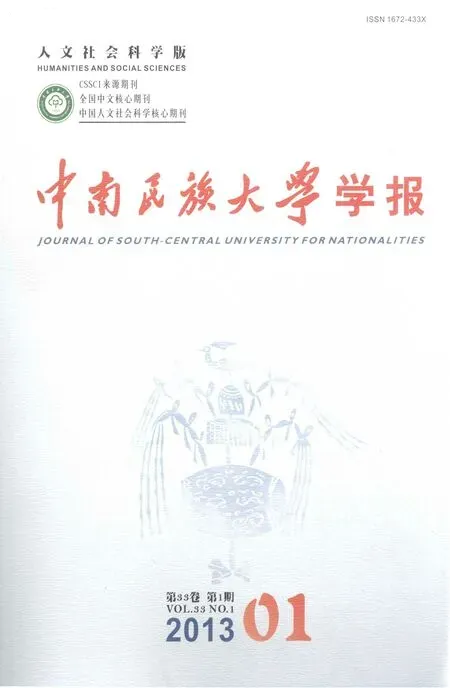刘纲纪教授有关《周易》生命论美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曾繁仁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现代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古代美学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定位与评价问题。黑格尔将包括中国美学在内的东方艺术定位于前艺术时期的象征型美学,鲍桑葵则将其定位于“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1]。由此导致中国学术界在中国古代美学的定位与评价上缺乏自信并长期摇摆不定。长时期以来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一种“以西释中”的路径,以西方“感性认识的完善”或者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等。再就是在中国古代美学的性质定位上莫衷一是,有“意象论”、“意境论”与“滋味论”等说法,均有一定道理。刘纲纪教授另辟蹊径,在宗白华研究的基础上以《周易》为切入点①宗白华1928—1929在《形而上学》中提出“中国生命哲学之真理惟以乐示之”,并有“中国八卦:‘四时自成岁’之历律哲学”专章。《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04、624页。宗白华又在《论中国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中写道:“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周易’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将中国古代美学定位于东方生命论美学。刘纲纪教授的贡献是在宗白华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挖掘《周易》所包含生命论美学的丰富内涵与重大影响,并从中西美学对比的视角深刻阐释了它的特有价值意义,他所著《“周易”美学》一书,内涵丰富深刻,可以说是一部准中国古代美学史,意义非凡。事实证明,将中国古代美学定位于生命论美学更加符合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的实际,具有更强的阐释力量,并为更好地参加国际美学对话提供了前提。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美学本来就是在“天人合一”哲学思维基础上的一种主客不分的混沌的以生命力量为特点的美学形态,这正是区别于西方现代“思辨美学”的特点与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应该充满自信的地方。下面笔者对刘先生《周易》生命论美学研究的价值意义作一个具体的阐发。
一、刘纲纪的周易美学研究的切入点和内涵挖掘
刘纲纪教授准确地以《周易》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切入点,挖掘其生命论美学的内涵,为中国古代美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找到了一条好的路径。
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到底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这是颇费思量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似乎应该从原始艺术或者先秦文献入手,但这种描述性的研究往往缺乏准确性,而选择从《周易》入手则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切入点。刘先生深刻论述了这种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切入点确定的必要性。首先,在刘先生看来,《周易》具有某种原初性。也就说,《周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的原始思维与原始艺术形态,因而从《周易》入手能够准确地抓住中国古代先民审美的基本特征。他说:尽管《周易》之中的“周代的占筮已不同于远古时代的巫术,不再具有原始巫术那种极为神秘的色彩。但它终究是从远古巫术活动发展而来,而且去古未远,所以仍然保持着巫术特有的准艺术思维方式,并且由筮辞的遗留而保存和记录下来了”[2]5。其次是从《周易》入手具有某种综合性。刘先生在书中分析了《周易》赖以产生的秦末汉初的特定时代,那时刚刚结束战乱纷争,“历史期待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出现,以结束纷争的局面。在思想上,则期待着一种批判地综合各家,能够普遍认同,以为某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建立论证的理论出现”[2]2。而“‘易传’的作者是明显站在儒家立场上的,但又大量吸取了道家思想,并且可以说是巧妙地吸收、消化了道家的思想,并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世界模式,把儒家思想历来较为忽视的有关天地、自然界方面的问题纳入了儒家思想体系之中”[2]3。这就揭示了《周易》,特别是《易传》融汇儒道的基本特点,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儒道互补的基本特点。使得《周易》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的奠基之作。再次是刘先生揭示了《周易》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成为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古代美学呈现东方生命观的根本原因。刘先生以点睛之笔指出了中国古代长期农业文明成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的根本经济社会原因。他说:“这和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对生命现象的规律比对力学、物理学规律更为重视有关。而古希腊则由于航海、造船的发达而大大推动了对力学物理学的研究。”[2]174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长期以农业为主的特点,所以对于“天人”关系,对于气候气象特别关注。从而使得中国古代哲学成为一种“天人之际”的宏观的人文的哲学。正是在这种“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基础上才产生了“生生之为易”的生命之观。最后是刘先生集中论述了《周易》所包含的东方生命论哲学与美学的内涵。他说:“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生命即美’。”[2]57他又说:“就美学而论,生命之美的观念在‘周易’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是‘周易’美学最重要的特色,也是它的最重要的贡献。”[2]115而且,刘先生进一步指出了这种生命之美的“有机性”。他说:“‘周易’的生命观是把有机生命和有机生命得以存在、发展的种种自然条件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的整体的生命观。”[2]有机的生命论哲学和美学恰恰点到了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最基本的特征。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本源属于有机唯物主义哲学。从每一时代的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发表的声明都可以找到例证。中国哲学思想从不以超自然的理想主义为主,至于机械主义世界观甚至从未存在。中国的思想家普遍赞同机体论观点,即每一现象都遵循其等级次序与其它现象互相关联。可能正是这种自然哲学的某些论点推动了中国科学思考的进步。”[3]非常可贵的是刘先生深刻论述了这种东方式的生命之美的特殊价值意义,使得在许多表面看来没有“美”字的地方却存在着“美”。他说:“讲到‘周易’对于美的观念,一般可能会到‘周易’中去寻找那些有‘美’这个字出现,直接提到美的地方。实际上,在没有‘美’这个字出现的许多地方,同样是与美相关的,而且常常更为重要。”[2]16这里所说没有“美”字的地方就是《周易》中对于有机生命的论述。这恰是中国包括《周易》在内的古代美学的特有内涵,是长期以来外国人与后人不解或误读中国古代美学之处。
西方古代以“和谐比例对称为美”,以“感性认识的完善为美”,这样的“美”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反而是有机的生命之美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美学形态在工业革命时代难以被理性主义美学所容纳,但在后工业的生态文明时代却闪现出特有的光彩,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全面研究、甚至是重新研究与发掘中国古代美学的精华。这就是宗白华先生与刘纲纪先生的重要贡献所在。刘先生在《周易美学》之中从实证与理论结合的角度,深入而全面地论述了《周易》所包含的生命美学的深刻内涵。诸如“元亨利贞”、“保合太和”、“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男女构精化生万物”、“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天文与人文、饮食宴乐、阳刚与阴柔、象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等所包含的重要的并特有的美学思想,发人深省。另外,刘先生还从《周易》生命论美学与古代绘画、音乐、书法与建筑等艺术门类的密切关系论证了生命论美学的生命活力,特别是从中国古代绘画“气韵生动”之中所体现的特有生命活力,说明生命论美学的价值意义。刘先生还从中国美学史的角度论证了《文心雕龙》之后所有的美学与文艺论著对于《周易》生命论美学的继承与发展。正是从这一点来说,《周易美学》可以说是一部“准美学史”。
二、刘纲纪的周易美学研究的比较视野和阐释深度
刘先生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进一步阐发了《周易》生命论美学的特殊内涵与价值意义。他首先将《周易》的生命论哲学美学与法国的生命论哲学家柏格森进行比较,阐发了《周易》的生命论是“天人合一”背景下人与自然一体的东方生命理论,它相异于柏格森的“意识至上”的人与自然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哲学。柏格森是活跃于20世纪前期的著名法国生命论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刘先生通过将柏格森的论著与《周易》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尽管相差了两千多年,但在生命的变化运动以及这种变化运动在时间中的呈现等方面却是非常一致的。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周易》力主“天人合一”与“天地人一体”,而柏格森则力主“意识至上”,从而堕入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刘先生指出:“柏格森又把人类生命的创造、自由完全归之于‘意识’。柏格森有相当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不可能完全看不到生命是要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定、制约的。但他又认为生命的‘意识’的发展完全可以打破自然规律的限制、束缚。”[2]53刘先生还指出,《周易》的生命论是广义的,包括无机物在内的天地人万物,而柏格森的生命论则是狭义的,认为生命的基本特征就是意识,只包括人、动物与植物,其他均为“堕性物质”。刘先生在这里没有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词句,但“意识的发展完全可以打破自然规律的限制、束缚”,不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吗?而《周易》是“在一种素朴的思想形态之中……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并且主张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效法自然,其行动须与自然的变化符合、一致。‘周易’不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不认为人可以任意左右、支配自然。”[2]54这不仅将《周易》的生命论与现代欧洲的生命论划清了界限,而且为《周易》生命论纠正当代“意识决定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作了深刻的阐发。诚如刘先生所言:“‘周易’的生命观是把有机生命和有机生命得以存在、发展的种种自然条件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的整体的生命观。整个宇宙万物被看做是一个不断在运动变化着的生命整体。从而,一切与有机生命的存在、发展相关的自然想象都是生命的表现,宇宙间不存在柏格森所说的那种与有机生命截然对立的所谓‘堕性的物质’。这样一种生命观,从美学上看,极大地扩展了审美的范围。即使是没有生命的山石,也会因它的坚硬、陡峭而显出刚健之美。‘周易’能达到这样一种整体生命观,又是因为如我们已指出过的,‘周易’把人的生命看作与整个自然界(包括有机界与无机界)不能分离的。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深刻的思想。”[2]115这是刘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生命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与阐发。
其次,刘先生将《周易》的生命论与古代希腊的和谐论进行比较,发掘了中国古代生命论哲学美学的特殊的生存论内涵,论证了中国古代的“中和”相异于古希腊的“和谐”。刘先生认为,《周易》中的“中和”的核心乃是“生命”,是包括人在内的生命万物的兴旺发达。他说:“‘周易’认为美在生命之中,生命即美,而这种美的最高表现即是‘大和’。因为只有在‘大和’的状态下,生命才能获得最顺畅、最理想的发展。”[2]69这实际上是一种东方式的生存之美,因为在“天人合一”的背景下万物一体,只有万物均获得兴旺发展,人的生命生活才可能获得美好的生存发展。在这里,人的生命和生存发展与万物是一体的。而西方的“和谐论”哲学美学却更加重视一种与生命分离的形式的数的和谐与比例对称。刘先生指出:“毕达哥拉斯则忽视了生命问题,他虽然也讲到由宇宙和谐而来的音乐的和谐与社会生活的和谐的关系,但就他整个思想而论,毕达哥拉斯所了解的宇宙的和谐是一种由数所决定的形式的秩序,具有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性质,并且没有同宇宙生命及人类社会的和谐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神秘的、抽象的、形式上的和谐。”[2]99这就划清了中国古代的“中和”与古代希腊的“和谐”之间的界线,揭示了中国古代“中和论”论美学的生命论与生存论的内涵。
再者,刘先生还分析了《周易》生命论美学的“交感论”与古希腊美学“模仿论”的区别,在文学艺术本性问题上厘清了中国古代“生命论”美学的人文性质与“模仿论”美学的科学性质的差异。“交感论”是《周易》的必有之义。因为所谓“生命”就是天地、阴阳交感化生的结果,这就是“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而作为文化的审美现象也是一种天人的交感。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文言》)。可见,所谓“交感”就是君子(即“大人”)从天地自然现象所获得的道德启示。而“模仿说”则是古希腊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理论家所确立的以“认识”客观事物为旨归的一种文艺创作活动。因此,刘先生指出:“将古希腊美学的模仿论与中国古代美学的交感论两相比较,我们可以说模仿论是与科学密切相关的认识性美学系统,而交感论则是与道德密切联系的情感性美学系统。”[2]190而“交感论”也优于现代西方以克罗齐为代表的非理性纯直觉的“表现论”美学。刘先生认为:交感论美学“将会在人类当代艺术发展中保持和发展其固有的生命力,并与西方近现代被异化了的人的美学——‘表现论’的美学作强有力的抗争。”[2]200
刘先生还论述了《周易》之中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认为前者是一种“刚健中正”之美,后者则是一种“厚德载物”之美。实际上两者都是生命之美的不同形态,是生命之美的呈现。特别对于“阳刚之美”作了深入地分析与辨别。他认为,这种刚健中正的阳刚之美就是中国古代的“崇高”,区别于西方的“崇高”。他说,这种阳刚之美“始终保持着积极入世的精神,不到现实人生之外,也不到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中去寻求‘崇高’,这是中国式的‘崇高’即阳刚之美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而且这是中国式的“崇高”,不同于郎吉弩斯的“华丽的外表”、古罗马的“更神圣的事物”、柏克的“独立的个人为前提的崇高”以及康德的“超感性”的理性力量。这种“中国式的‘崇高’经常表现为肯定性的雄伟、壮丽,与西方式的那种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对抗的‘崇高’不同。”[2]53
三、刘纲纪的周易美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美学如何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的问题。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白话文运动与破除封建旧文化的过程,中国新旧文化之间存在一个程度不同的断裂,加上长期以来文化建设中的“以西释中”,学术界一直在讨论我们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失语症”问题。刘先生继承宗白华先生的前期工作,在《周易》生命论美学问题上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其最重要的价值意义在于这是一种富有成效的中国古代文化与美学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的有益尝试,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的意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入侵,我国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当时我国不仅武器落后与经济落后,而且在文化上也丧失了自信心,包括许多前辈学者都有“中不如西”之论。20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近30多年以来,整个国力与经济发展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文化上的“失语”状态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文化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费孝通先生很适时地提出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学领域同样存在。美学是一定地理环境、民族生活方式、审美精神与文化艺术的集中反映。中华民族绵延5000年,有着自己特有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审美精神与文化艺术,必然有其特有的区别于西方的美学精神。尽管在19世纪初期以降有一个新旧隔离问题,但民族的文化血脉与审美精神没有也不可能中断,特别是这种文化血脉和审美精神顽强地生存于民间的文化与生活之中。刘先生的《周易》美学研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充满着一种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刘先生在《周易美学》一书的结语中指出:“我们完全可以说属于儒家系统的‘周易’的美学是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美学”,“‘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美学永远不会磨灭的伟大精神。它自商、周以来到现在,以至未来,将永远活在中国文艺中的魂魄。”[2]299-300
当然,《周易》生命论美学研究还在于它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抓住了“天人合一”背景下的生命论美学精神。这是一种中国古代特有的区别于古代希腊科学思维之下的“和谐论”的“中和论”美学精神,而且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综合儒道阴阳、贯穿各个艺术门类与民族生活的特殊位置。特别可贵的是这种生命论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普世价值与现代意义,可以说,这就是一种东方古典形态的强调天地人一体的生态美学智慧,完全可以补正理性主义美学的种种不足。而且,在当代生命论美学已经被西方当代环境美学家充分肯定,将其看作是高于传统形式之美的更深层的美学形态[4]。总之,刘先生《周易》生命论美学的阐发提出了一条富有成效的中国古代美学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之路。当然,我们从不排除还存在别的途径与探讨模式,完全可以在学术对话中推动中国美学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之路。
刘先生在《周易》生命论美学研究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必要的批判分析。因为,《周易》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一部以占筮形式出现的论著,其中的落后迷信的成分自难避免。刘先生均以适当篇幅予以厘清。
[1]鲍桑葵.美学史:前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刘纲纪.周易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3]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M].李彦,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1.
[4]卡尔松.环境美学[M].杨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