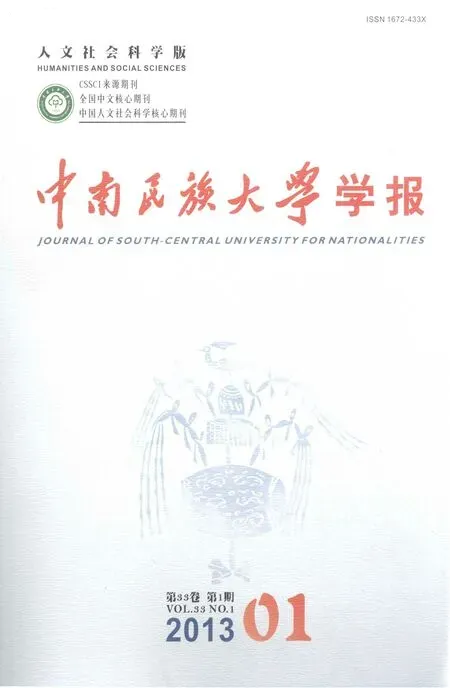关注人的发展:马克思科技伦理思想及当代中国现实考察
操菊华,田辉玉,吴秋凤
(1.华中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2.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205)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专门论述科技和科技伦理。马克思的科技伦理思想是从属于他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不是其研究的终极问题[1]。但是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生活,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异化劳动、工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在三部著名的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出发,以当时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的发展为背景,在论述大工业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关系的影响的过程中,阐发了他的科技伦理观[2]。在研究中,马克思抛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把科技同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同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相结合,提出了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马克思的科技伦理思想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伦理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马克思科技伦理思想的解读
通过梳理马克思的有关著作,我们发现,马克思是以揭示“科技的本质”为出发点、以“科技与人的关系”为基本点,以“人的发展”为落脚点来阐述科技伦理思想的。其思想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科技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18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其著作中,实践、劳动和生产属于多词一义,都表示人对自然的能动的改造作用。科技活动属于人的实践活动,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其结果是人的器官的延长与功能的扩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4]88,这里的“工业”是科学技术的下位概念,实际上就是科技。马克思反对仅仅从外在有用性和工具这些方面来理解科技,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自我生成与完善[5]。
在马克思看来,科技的发展与人本质力量的显现是同一过程,是具体历史条件下、具体社会发展阶段中人的发展过程。
2.科技是生产力,实质上与道德一致。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科学技术必将转变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6],“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108蒸汽磨和手推磨分别代表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技术工具。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才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256。
邓小平正是在总结马克思科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他不仅把科学技术直接地看成是生产力,而且看成是比生产力中其它要素更为重要的首要因素[7]。
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科学技术作用下形成的“人化自然”正不断拓展人的生存空间,优化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25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推动的。同时道德水平的提升又反作用于科学技术,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与道德是辩证统一的,在实质上是一致的[8]。
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成为异化的力量。科技异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科技活动及其成果背离主体——人的需要和目的,成为人难以驾驭的力量,并反过来控制人、统治人和危害人的特殊现象[9]。
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是西欧的工业化时期,科学技术成为社会建制,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日益广泛地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形成了以机器为主导的机械化劳动方式,工人日益沦为车间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人的自由和全面性。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已完完全全成为工人异己的力量,一种不道德的力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正如人用脑创造了上帝而受上帝支配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创造了财富,而财富却为资本家所占有并用来支配和奴役工人,这种财富的占有以至于劳动本身和人的本质都异化为与工人相敌对的异己的力量。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52
马克思在其文本中深刻地剖析了异化的根源。他指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以及对人的影响,揭露出科技与资本的联姻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马克思不禁感叹:“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0]
由此可见,马克思始终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来分析科学技术的影响。一方面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另一方面,他指出异化现象并不是科技本身造成的,其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在于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成为异化的力量,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解决矛盾唯有进行社会制度变革,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二、科技发展现实中的三大伦理困境
在当前“大科技”时代,科技迅速地向各个领域扩张,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等的联系日益紧密,彰显着强大的社会功能。但同时,科技发展产生的“双刃剑”效应引发人们对科技伦理的深刻思考。
困境一:科技发展与人的自由相对受限的矛盾。当今社会是技术化生存社会。在“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下,人们的衣食住行与精神生活无不受到科技的影响。科技模式已经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并外化为他们的行为方式。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一方面,科技成果更加智能化、人性化,人们能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社会服务和质优价廉的产品。借助科技手段,人们的生存空间大大拓展,其实践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人们对科技成果又爱又恨。因为人们一离开科技成果所构造的现代文明,就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这种科技依赖综合症使人的自由受限制,人的心灵被压抑。这与科技发展的终极意义是相违背的。
人们不禁要追问:科技究竟是为什么服务的?其终极意义与现实目标是否存在矛盾?这是否是“技术控制人”、“技术统治人”?如何认识这种现象?
困境二:科技与传统伦理的冲突。科技在给人们带来福音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水土流失、大气污染、资源枯竭、极端天气等问题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太多的不和谐之音,“天人合一”的图景似乎已成为历史。
现代高科技更是严重挑战着传统的伦理观念。人工授精、体外授精等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可能淡化了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网络技术打造的虚拟空间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安乐死技术似乎降低了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克隆人技术更引发了传统伦理观念的革命,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同时高科技的风险更大,不确定性、未知因素较多,高科技产品的安全性、负面效应仍是饱受争议的问题。
科技发展、特别是高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道德危机迫使人们思考,这些伦理问题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是科技本身的原因,还是科技的使用引发的?
困境三:科技与人文的割裂。在我国社会,发展是硬道理,科教兴国是国家发展战略。重视科学,尊重科学早已是国人的共识。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科学技术的贡献率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但同时,人们在快节奏的技术化生存的社会中常常在内心拷问生命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一面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创造的高度繁荣的物质生活,另一面却是信仰模糊、道德滑坡与精神空虚现象,科技与人文被割裂了。
1923年发生“科玄之争”是一场关于科技功能的辩论[11]。论战以“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为核心命题,涉及到科学与人生观、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等。如今,这一话题穿越时空的变迁重新摆在人们面前。人们仍在追问:为何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却似乎迷失了自我,找不到精神的家园了?人们甚至开始怀念农耕社会里,没有了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在保守、温和的儒家文化普照下,人们过着简单的生活。
那么,科技与道德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大力发展科技的同时,国家应如何实现为大众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
三、关注人的命运,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观
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一路高歌猛进,强力彰显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强烈地作用于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科技为人们打造了日趋优化的物质环境和不断进步的精神文明。另一方面,这种技术化的生存状态却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如何认识科技的本质,如何看待科技的负面效应,如何理解科技与人的目的、意志与自由的关系,这些由于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伦理问题正在困扰着人类。马克思的科技伦理思想对于走出当今社会的科技伦理困境、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观具有重要意义。
1.着眼人的发展,树立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对于科技的价值观,历来有两种观点。一是科技价值中立说,一是科技负荷价值说。科技价值中立说强调科技的自然属性,认为科技是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运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工具理性。科研人员是出于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爱好,在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从事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他们不关心、也不过问科学技术应用的后果。科技负荷价值说则强调科技的社会属性,突出人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意义,认为主体总是带着明确的目的去从事科研活动。科技活动是一种有动机、有目的、有建制、有价值选择的理性活动。科研人员应主动关心科技成果的运用,规避风险,趋利避害,实现科技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综合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但又失之偏颇。
按照马克思的科技伦理思想,科学技术发展的终极意义是人,它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满足社会的价值需求。因此科学技术的价值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的自然属性,社会要满足科研人员探求真理的内在需求,要鼓励科研人员按照科技自身的范式,“为科学而科学”,反对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的束缚。这也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关键。二是科技的社会属性,科技成果要促进社会的发展,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在这里,科技不再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服务大众的公共产品,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受到社会的监督与约束。
2.从科技大国到科技、文化强国的战略转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增强综合国力,建设科技大国,这是我国的发展战略。
科技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挖掘科技内在的文化内涵、理性之光,提高科研人员的职业修养,提升大众的科学素养,在发挥科技巨大能量的过程中展示人的本质力量。
科技与人文犹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杨叔子院士说:“人文素养与科学教育,相通相融则利,相隔相离则弊;相通相融则育人,相隔相离则制器。”[12]
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主旨专题研究文化建设。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会议将文化建设置于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文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化热”的兴起反映出我国正由建设科技大国到建设科技、文化强国的战略转移。
随着我国以科技为基础的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文化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与繁荣,科技与人文的冲突也将逐步弱化,代之以科技与人文的和谐共促,整合成新的精神力量,成为大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3.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科技伦理思想,科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一种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在于促进人的发展,推动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技与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科技异化与科技负面效应的出现并不是科技本身使然,而是科技的运用失当,其主体没有全面把握科技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没有对后果作科学评估,在根本上是没有关注人,没有把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从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述等,都始终着眼于人的发展,都始终强调科技要为人的发展服务,不能去危害人类自身。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论断与马克思科技伦理思想是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如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把科技作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维护人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长远发展的重要手段,把握宏观、驾驭大局,规避负面效应,真正关注人,关心人,以人为本,这是马克思科技伦理思想的精髓。这一思想对我们走出当前伦理困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王伯鲁.马克思技术思想纲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4-15.
[2]陈爱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技伦理观[J].东南大学学报,2006(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王丁龙.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5.
[7]林剑.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意义的多维思考[J].福建论坛,1992(6).
[8]胡东原,李冲.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及其理论主要来源[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0(6).
[9]陈翠芳.科技异化问题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9.
[11]操菊华,康存辉.对科学主义的再认识——兼论中西方科学主义[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2).
[12]杨叔子.“育人”非“制器”——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J].高等教育研究,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