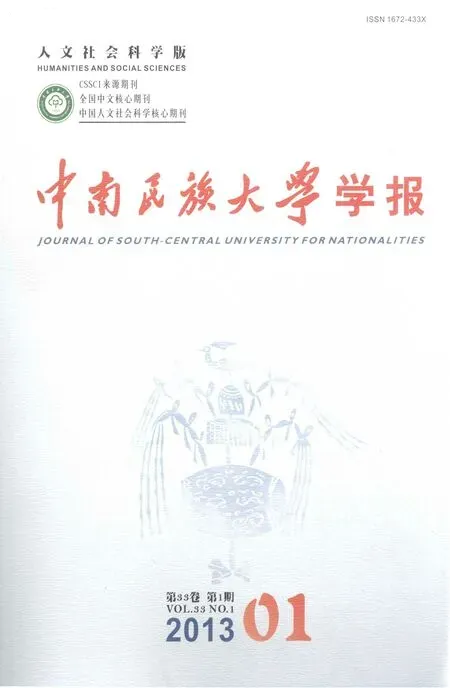在野的全球化:旅行、迁徙、旅游
范 可
(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93)
目前,对全球化的思考大体上都涉及到这么几个因素与现象,即资本全球性流动;高科技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相对于以往低廉得多的通讯与旅行成本;文化混生、分化,以及与地方主义兴起不无关联的文化和地方多样性的重新建构,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在冷战结束之后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令人目眩的变化。我们很难说全球化究竟由谁所主导,尽管,资本在此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它的作用下,今天的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甚至出现了“主权缺失”的现象。我们很难预测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最终结局是什么,但种种事实说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此保持乐观。它既不可能导致某种同质性文化的出现,也不可能导致人类彼此间构筑壁垒固步自封。它在推动多样化的文化繁荣的同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将更能彼此间宽容并相互理解——它完全可能是令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催化剂。
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传播扩散的过程与结果,那么我们也许要问,究竟是什么的传播与扩散可以标志着全球化的进程?现代性,可能是许多人的回答。那么,何谓现代性即刻成为问题。我们无需理会那些因为表达政治正确立场所虚构出来的所谓非西方的现代性。西方虽然是个大而无当的建构性术语与区隔,但在学理上,它所涵盖的内容与外延不言自明。它首先是一个地理区域,在那里资本主义率先发展起来,它又是一个文明区域,其间的文化多样性虽然复杂但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基督教世界的烙印。在人类学的意义上,这个术语自然遮蔽了该地区的文化复杂与分化,但也没有人否认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内涵。这些基本内涵中的一些主要价值,如科学与理性,构成了所谓现代性的基本象征。吉登斯认为,它们在世界范围的扩散开始于17世纪[1]。换句话说,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
但是,把制度性因素或者某些价值的传导作为历史过程的展演,对人类学者而言,难以令人满意。毫无疑问,制度观念等,在漫长人类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必须通过人与人的接触来传播。也就是说,人,是传播的主体。广义而言,人类迁徙的起点其实也就是全球化的开始。换言之,全球化如同在野而无法控制。民族国家的发展流布其实也是全球化的过程。然而,民族国家对主权归属的强调却又在许多方面对全球化有遏制作用;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却也因为霸权的崛起对全球化推波助澜。曾几何时,却又因为全球化又日益失去其内在的能动性。
旅行、迁徙、旅游,一般说来,都是人类有目的的“移动”。但是彼此间却不能相互取代。旅行与移民之间的不同很容易区分,而与旅游之间有什么区别?从逻辑上说,旅游是一种旅行,这是没有错的。但反过来说则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可能不好说旅行是一种旅游。因为后者是指通过旅行的休闲游玩,而前者的内涵却宽泛得多。一般说来,这两种移动都有一定的目的。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我们知道,确有人漫无目的地旅行或者旅游,但这毕竟不是常态。迁徙则目的明确,对于当事人而言,旅行只不过是指抵达目的地的过程与手段。从情感的角度言之,旅游令人产生愉快之感,而旅行未必全然如此。人类历史上的许多迁徙就经常伴随着痛苦的经历。它虽然也是一种旅行,但有时却不见得知道哪里才是终点。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离散”(diaspora)之说。“离散”是希腊语中专指历史上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失去家园、流离失所的状况,渗透着一种背井离乡、何以为家的感伤、沉郁与悲凉[2]。人类的迁徙有自愿的,但也有许多是被迫的。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轻易不离开家园。但近几个世纪以来,却不断有人离乡出洋。福建与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历史上出洋者似乎是自愿的,但如果仔细想来,也有某种“被迫”的成分。换言之,如果家乡能为他们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们断不会历尽艰辛出洋谋生。所以,如果把旅行、迁徙、旅游三者并置,我们便可以看到它们在人类活动中所产生的不同意涵。如果将这三种“移动”置于全球化的语境里,那么,权力和资本与这些不同“移动”形式的相关性如何,关系如何,而这些不同的“移动”之于人类历史过程的重要意义又是如何,是很值得考虑的。
一、旅行与人类历史进程
旅行在人类演化与发展的时间长河里,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不同文化、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交往,人类文明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成就。除了极个别的区域之外,不同地区人类之间的交往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尽管交往的范围与速率受到了技术发展的制约。在人类学里,文化之间的接触被认为是文化创新的动力。而传播、采借则是重要途径之一。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历史上绝大部分重要的发明与发现之所以能在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主要是通过传播而达到的。地球上同纬度的地区有着大体相同的驯化物种说明了这一点。而美洲与欧亚大陆由于大洋阻隔,故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这两大地域的人类所种植的作物和养育的牲口驯化自不同的野生物种。对于为什么同一纬度地带的人们有着相同的驯化物种,戴蒙德有着自己的解释[3]。乍看起来,他的解释似乎与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传播学派中的某些说法有些类似。但并非如此。按他的逻辑,人类早期的许多发明和发现不太可能在不同的人类群体里都独立发生。它们可能在某一特定的地区首先出现,而后,扩散到其他地区。例如农业的发明与人类定居,最初可能是地理环境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地区,如两河流域,最初可能因为偶然的原因使得驯化在人类社会中得以发生并由此奠定了文明的基础。而驯化的物种则传播到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模仿和学习的过程。
但与人类学史上的传播论者不同的是,在戴蒙德看来,传播的前提并非是传播论者所言的那样——绝大部分早期人类心智低下,故而发明与发现只能发生于特定的地区,以后再渐渐地传播到世界的其它地区①传播论有数种不同学说。这里所提及的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史密斯(Elliot Smith)。。恰恰相反。传播的过程也是人类模仿的过程,而人类之所以模仿是因为它更具实效。这说明早期人类是很聪明的。而传播如何才能实现?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惟有通过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实际接触。不同地区的人们如何能相遇?这就得通过旅行。如此说来,旅行在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演化发展的历程中居功至伟。人类学认为,在现代科技传递信息手段出现之前的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人类信息的获得更多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尤其在人类的早期更是如此。通过接触,人们之间便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可以想见,人类早期的文化传播就是这样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旅行,人类社会就不会有今天。当然,旅行也并不总是具有积极的意义。战争同样也与旅行脱离不了关系。在世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之前,不同地区的王权与帝国为了经济上和人口上的掠夺,经常进行远距离征战。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一种“旅行”,它持续了两个世纪有余,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灾难。但客观地讲,十字军东征却也在沟通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实,人类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旅行史。当今有关人类的起源主要有两种假设。其一是建立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的单元说,也就是所谓“走出非洲说”(out of Africa hypothesis);其二为“多元说”(multiregional hypothesis)。前者主张今天所有人类的祖先在十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大陆,渐次散布到各大洲。人类之所以有着不同的体质表型,是人类祖先对不同地理和气候环境适应的结果。而多元说主要是建立在古猿和古人类化石的证据之上。地球上除了美洲和大洋洲之外,都发现有古人类化石。它们的存在表明,这些大陆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年前便有古人类居住。这样一来,如果接受“单元说”的话,那又如何解释这些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化石证据呢?这是有些学者不愿放弃“多元说”的主要理由。当然,不能否认,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已经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一些学者的认知。在他们看来,民族(nation)就应当是一个共享血脉的群体,于是——以国内的一些学者为例——很自然地把诸如北京猿人之类的古人类与今天的中国人甚或中华民族联系起来。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与本文无关。但是,无论是“单元说”或者“多元说”都与旅行脱离不了关系。由于到目前为止,唯有非洲才有古猿化石出土,所以,即便力主“多元说”者也承认,人类祖先最早确乎来自非洲。但他们早在一百多万年前就已经走出非洲。也就是说,“多元说”的“走出非洲”发生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直立人”(homo erectus)阶段。而按“单元说”,人类祖先甚至在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经是现代人了(homo sapiens)。
人类为什么会走出非洲?人类学研究证明,迄今为止,人类在自己历史上的90%以上的时间里,都是食物拾取者(food collector)。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常常追寻可以裹腹的动植物。早期人类的生活由是而不断迁徙,是名副其实的“旅居”(dwelling in travel)①借用自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1997:2)。、[4]2。可能就是因为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的一部分祖先最终离开了非洲大陆,并渐渐地分布到了旧大陆的许多地域。
因此,如果我们同意戴蒙德的说法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旅行在人类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既然动植物驯化之后即在同纬度地带的人群中通过“拿来主义”得以迅速传播,那么,这不啻意味着,人类中的绝大部分能够从食物拾取者转变成为食物生产者(food producer),更多地还是得拜旅行之赐。驯化的滥觞无疑是偶发的,一旦驯化成功之后,也就对人类文明的演化产生了革命性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那些决定文明进程的发现与发明,如动植物的驯化、制陶和后来出现的金属冶炼等,虽然并未在所有的社会里起着相同的作用——如最终出现了国家组织等,但是,绝大部分人类都因此而成为了食物生产者。
现在通常认为,大概在一万多年前,在两河流域出现了植物如小麦等的驯化,人类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Golden Childe)称之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其标志为农业、定居和制陶[5]。但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阶段是不同步的。在中国,中原地区已经有了中央集权的强大王朝之时,东南地区还在流行着印纹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样。直到与殖民主义者有所接触之前,有些族群还停留在这一时期,有的甚至还以狩猎采集为生计,连定居都谈不上。但人类学者注意到,这些族群大多生活在地理学意义上的“死胡同”(cul-de-sacs)。我们可以由此体会到与外界的接触有多么的重要。当然,有些研究者可能会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食物生产者,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足以使他们的族群繁衍生息的动植物资源②对于有些族群来说是有道理的,如生活在美国西北的海达印第安人和生活在极地地区的因纽特人。传统上,海达人是定居的,但依然被归于“食物拾取者”,他们所处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赖以为生的各种鱼类和海洋哺乳类。因此,在与外界接触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他们的生产方式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在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已经“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样也得考虑到,生活在地理学上的“死胡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在这样的地理位置里,他们失去了与外界接触的大量机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一直处于“旅居”之中,但始终在十分有限的地理环境里转悠。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的确,他们所处的环境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活条件。但由于所处地区的特殊性,其他人类也少有进入者,致使他们能将传统的生活方式保持下来。所以,“旅居”范围之有限也决定了他们成为人类社会最晚被“现代性”感染的一群。
人们定居之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着“旅居”方式。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旅行无法、也没必要成为大部分人的日常行为。从这个时候起,人类的旅行多是为了交换和征战。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说明人类欲求的满足必须通过贸易来补充。丝绸之路的存在说明了旅行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卷入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的人数量一定不少。而这一交流也经历了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使得东西方往来在海面上首次贯通。海上丝绸之路其实主要进行的是香料、茶叶,以及瓷器等货物的交换贸易。战争也是旅行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战争或者交换贸易,承载的主体都是人,交换或者战争都是人类接触的结果。在现代科技发展起来之前,同外界接触唯有通过旅行。要么自己外出,要么在家乡遇见外来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旅行在人类历史上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旅行的密集化肇始于殖民主义的兴起。最初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的殖民扩张,多少带有点探险求宝的卡通色彩。其驱动力并非由资本而起,而是来自王室贵族对海外珍宝和奢侈品之贪得无厌的欲求。但是,“地理大发现”直接导致了疯狂的殖民掠夺,并间接地成了爆发工业革命的前奏。分别发生于16和17世纪的尼德兰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化,转而又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各种“探险”和贸易船队飘扬过海,为了海外殖民地和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资本,俨然成为驱动海外探险航行的直接动力。随着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建立,人类旅行的网络进一步扩张。至此,凡是这个网络触角所及之处,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最初因殖民地贸易而逐渐成形的世界体系。整个世界就此日益“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6]。人们的生活日益地与地球上的其他区域联系起来。
克里福德(Clifford,1997)提到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用来说明世界的“克里奥尔化”。印度人类学家古许(Amitav Ghosh)到埃及一个想象中应该是十分偏僻闭塞的村子里做研究。但他很快就惊讶地发现,当地人的生活已经与整个中东地区联系在一起。大多数年富力强的村民们忙于穿梭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不同国家之间,他们的生活已经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旅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古许所设想的那种古老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7]。人类学家已经不再是传统上的那样,来自某一个都市中心到边远的乡下。相反,他那“古老和定居”的田野点已然开启了居住和旅行的复杂过程。换言之,用“当地生活”(localized dwelling)这样的话来概括人类学家和当地人的生活已经很不精确。“旅居”可能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好说明[4]1-2。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旅行其实对人类历史过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费孝通[8]和沃尔夫[9]都认为,全球化始于“地理大发现”,因为紧接着的就是几个世界霸权对海外市场与殖民地的争夺。而“地理大发现”则是航海旅行的结果。旅行因此与工业革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旅行既推动了殖民扩张,也导致了去殖民化[10]。
二、迁徙与治理术
任何迁徙——无论是自愿或者是被迫——都得通过旅行才能达到。但与一般的旅行不同,自发的迁徙往往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因此,自发的迁徙者离开了出发地之后,多半不会再选择回来长期居住。移民是一种迁徙。移民可以简单地分为国际移民与国内移民。国际移民大多为自发的,国内移民则未必。比如我国常见的因为工程而有计划的移民,这样的移民就不是自发的,而是政府所要求的。这类移民在其他国家也有。有时,国家政府主导下的移民很是残酷。苏联的斯大林政权就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它曾根据莫须有的罪名和所谓“国家任务”把一些民族驱逐到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其中,日耳曼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巴尔卡人等11个民族被全部迁移,达数百万之众[11]。所以,有许多移民实际上是被迫的。
不少英美学者把中国的“农民工”称为migrant worker。而这一名词在联合国给出的定义里,指的是在另一个国家靠劳动换取酬劳者①英文原文为:The term"migrantworker"refers to a person who is to be engaged,is engaged or has been engaged in a remunerated activity in a State of which he or she is not a national.(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cmw.htm)。回到中文的语境里,“外劳”可能是最好的翻译。可能是由于备受诟病的户口制度,导致了农民工在自己的国家内竟然身份如同外劳。“农民工”的生活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他们的居住仿佛都是暂时性的,处于不断的搬迁之中。正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基本上没有权利在他们所工作的城市里定居,他们不得不在每年的年关岁末踏上返乡之旅,“春运”由是成为铁路部门的“生意旺季”。试想,如果他们与他们所工作的城市里的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有谁还会想去插足于连脚都难以迈入的列车车厢里。如果说移民意味着寻找新的家园,那么中国的农民工绝对不是移民。在基本的社会公义落实到他们身上之前,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扎在故乡的泥土里,要么就是漂泊者。
移民的迁徙与以上所谈的旅行很不相同。当然了,迁徙本身也是一种旅行,它的不同之处是单向的。虽然移民当中有些人最终可能返回故里,但是从法的意义上来讲,他们的方向是最终“归化”为“旅居国”或者所在国家的公民。从联合国和移民接受国的法律来看,移民种类繁多。冷战之后,跨国移民日益增多,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成为移民输出国,或者输入国,或者二者兼具。而且在国际性流动的移民潮当中,也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现象。许多人只是不停地穿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因此,很难定义他们是否侨居于某国。于是,当今联合国对移民的定义也就有了新的内容。它似乎已经不再根据移民主体本身意愿来进行定义。而且也不再以是否拥有所居国的永久居住权来作为标准。换言之,有些人在所居国并不拥有永久居留的身份,甚至没有合法身份,但由于他们在所居国有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被考虑为移民[1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代表所在国政府的意愿,而且对所居国政府本身如何定义移民也没有什么约束作用。
移民们背井离乡到异乡寻求发展,其后的心理机制是“工作”与“爱”;工作寻求的是挣更多的钱,而挣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①当然,许多国家的富人由于各种原因,也通过各种途径移民到国外。例如中国不少贪官污吏及其家人为了逃避罪责或者其他担心,也移民到了海外。这类移民能否用跨国移民称之尚有待进一步商榷。至少到目前为止,文献上所谓的跨国移民基本上都没把这部分人包括在内。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类人移民国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为恐惧所迫。二是这部分人在海外大都十分低调,身份很难确认。因此,在对移民的研究中,他们尚未成为一种特定的类别被区别对待。到目前为止,他们基本上只是未加区别地被包括在移民的基本数据里。。所以,移民往往是踏上旅途便义无反顾。从长远看,国际移民经常会对他们的出发地或者移出国有积极的影响。譬如在欧洲的浙江人无论在各方面都对他们的家乡有着积极的贡献。到东南亚的闽南移民也是如此。福建侨乡经济的繁荣自有他们的功劳。广东经济的发展除了港澳之外,北美的广东裔华人也有巨大的贡献。吸纳移民的国家也必定从移民中受惠。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球上南北半球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国际移民在移动的方向上,呈现出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动和由南向北移动的基本态势。尤其在冷战之后的近一二十年来,全球化挟高科技和信息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比之于以往大大降低的旅行和通讯费用,移民潮日益汹涌。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有了更多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人口。这种状况引起了这些国家中低层劳工阶层和保守人士的不安,生怕移民抢本国公民的饭碗和分享社会福利。而因应大量的外来移民进入,一些国家也制定了门槛,公民权因此再度成为论题[2]。有些国家通过细化或者重新制定一些公民方能享有的权利,把本国公民同外来移民进一步区分开来。具体的做法很多,此处无法细究。
面对汹涌的移民潮,有关国家都出台相关治理术,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对之加以“完善”。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在历史上对待移民的政策不断变化。以对待华人为例,美国政府曾经在19世纪下半叶推出“排华法案”,大量的华工迅即沦为法定的社会排斥对象,他们无法“归化”为美国公民,他们的配偶子女无法来美团聚。这些限制直到“二战”才因中国是美国的盟国才予以废除。但是,直到去年,美国政府才对当年颁布“排华法案”表示歉意。
为了便于控制,所有国家都对国内人口进行分类。这些分类的标准并不相同。除了根据文化与族群(包括“种族”)的分类之外,还有其他。有些国家的人口分类不只一种,例如我国的分类除了民族之外,还有户口。户口制度把人口分为两种类别,即“农”与“非农”。这一分类与民族分类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更具治理术上的意义。民族分类,我们称为“民族识别”,它主要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与执政党所宣称的国家的政权性质有关系。既然这个政权是人民政权,就必须要有所有民众的代表,于是需要有各个民族的代表。这样就需要知道有多少民族,于是,就有了民族识别。我国政府在民族识别的同时,还进行了历时8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该调查的直接后果便是将少数民族作了另一种分门别类,即根据所谓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他们定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并据此决定相应的扶持力度,制定不同的发展规划[13]。在治理术的意义上,民族识别自是有助于国家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同时,这也是国家同当地民众之间的某种“社会契约”,通过提供较为优惠的政策来换取当地民族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民族识别政策虽然与这里所谈的迁徙没有关系,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直接给以下将要讨论的旅游打下了烙印。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与之直接相关的有关少数民族知识的系统性生产,为地方上的民族旅游、文化旅游等提供了某种似是而非的资源。
与民族识别不同,同样是治理术的户口制度,其外显之功能就是表现为对人口迁徙的限制。可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户口制度扼制了人口流动。建立户口制度显然具有政治意义。它的确立与政府对粮食安全的关注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方针之后,工业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吸收了许多农民进入工业生产。许多农民也就因此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由于找不到工作,有不少人始终流离于城市与城市周边地区,“盲流”一词由是而生①其实“盲流”的说法甚至在新中国刚成立的1950年就出现了。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于1950年11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告——《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收入于建嵘主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二卷下册)。该文列举了当时农民进城找工作的现象后,指出“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的情绪”。至于必须劝阻农民进城的理由,文告点到:“浪费国家许多钱财,影响社会秩序,而且给各地人民政府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并指出:“对于农民来说也很不利,因为他们盲目跑到城市,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只好卖掉衣服被褥等物,走上流浪的道路”。全文最可圈可点之处,是下面这句话:“目前的劳动就业主要是解决失业问题,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不是失业者,他们有地种,有饭吃。”(参见周其仁撰:《限制迁徙自由的理由》一文,载《经济观察报》2012-05-25。)。农民离开土地自然影响到了农业生产,而在当时,由于缺乏外汇储备,国家必须通过输出农产品来换取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与工业产品。因此,粮食安全主要考虑的并不仅仅是吃饱饭的问题,它同时是国家在发展方略上的决策,然而,这一发展决策却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14][15]。
户口制度的出台与1953年开始实施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在这一政策制度下,农民完全失去市场,国家掌控了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而且还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保证足够的农业人口和进行有效的政治管理,国家在1958年正式确立了户口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限制了广大人口的空间与社会流动——不仅人们不能随意迁徙移动,更为重要的是,身份的变动,亦即“农”转为“非农”,在大部分情况下也不可能。这种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改善。但是,户口制度下所形成的区隔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普通民众心理上,影响依然深远。“农民工”这一称谓直接表白了这样的一群人必然的命运:他们在走出家乡之后,无论在何处——在旅途上或在他乡的工作中——都会遭到制度性的刁难和众多当地人的排斥。
综上,可以明确,迁徙是一种旅行,但旅行并不意味着迁徙。移民是一种迁徙,但并非所有的移民都是自发的。作为自发移民的迁徙,其后的动力是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认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生存条件的未来之预估远低于对迁徙目的国所具机会之预估的话,他们将宁愿承担风险远走他乡寻求机会。因此,自发的移民是一种决策和投资。这样的迁徙尽管可能充满艰辛,但却阻碍不了前进的脚步,所谓用脚投票以及大量的非法移民即为其例。这种迁徙看似为了更有保障的生活,其终极驱动的力量却可能是政治的。首先,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霸权强化了南北半球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其次,国家制度导致的政治经济腐败——这样的国家缺乏公平与正义,理所当然地成为移民输出国。通过对迁徙的分析,可知人类历史上有大量的迁徙与移民是被迫的。除了不同的国家政权所为之外,国家所计划的一些项目也在客观上迫使人们迁徙或者移民。例如大量的水利工程建设都有这样的举措。自由迁徙的反面是强迫迁徙,移民的反面是强迫移民与禁止移民。大部分国家除非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才会制定这样的强迫性政策,但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曾经是一种常态。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就是通过户口制度来对民众的流动进行限制。这种在空间上对人民的控制可以内化成为阻遏社会流动的壁垒,从而成为社会分裂的催化剂。因此,比之于旅行,迁徙更为具体,从而也就更多地携带了政治意涵。
三、旅游的透镜
旅游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充满愉悦的,这构成了旅游与其他旅行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旅游出现得并不算太早。过去,西方殖民当局官员的旅游可能是因为他们职业的关系顺势而为。后来,大英帝国善待其在海外殖民地的“公务员”,让他们有若干年一次的环球旅行。这种形式的旅游自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抛开物质的因素,作为游客的殖民地官员与一般游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他们喜欢看的可能与今天的许多游客——尤其是新兴的中国游客,有颇为相似的地方。比如喜欢看些比自己的“文明程度”低的群体及其文化,这种猎奇趣味的后面,是某种妄自尊大的心理机制。对此,笔者将在后面讨论。
旅游业成为常人的一种娱乐和消费风尚无疑拜全球化之赐。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随意浏览各种信息,从中筛选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各地如何吸引人的信息,而通讯费用与交通费用的大幅降低也为一般人出行提供了方便与可能性。除却各种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外,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冷战结束,使得人们更容易在地球上往来。世界政局的变动也会多方面影响到旅游产业和人们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甚至影响到人们旅行的欲望。地球上不同区域的每一次动乱对旅游业产生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可能导致游客数量锐减,更可能影响人们的消费决策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关于旅游,笔者的问题是,为什么它会成为一种消费时尚?人们选择这一消费方式时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受到自我认定的所处阶层价值观的影响?旅游产业的存在与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等等?当然,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旅游业的从业者与游客的互动,游客如何看目的地文化,如何与当地人互动,当地人又是如何看游客,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四、旅游与当代生活
我们知道,在过去只有少数相当富裕的人才消费得起旅游。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富裕的西方社会里,也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到国外渡假。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跨国流动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密集接触。跨国旅行者除了政要、商务人士之外,还有大量的“外劳”、学生和难民。这些人并非都是游客,甚至政要和商务人士大部分出行也非旅游。可是,关键在于这种流动现象给不同的社会都带来了许多异邦的元素。在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里,来自其他社会的象征与文化元素随处可见;到处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所经营的餐馆,而不同国家的移民在欧美许多国家的大都市里所形成的具有异国色彩的聚居区或者邻里社区,更是使人感受到世界的“混杂交错”。这些,都可以激发人们的猎奇心态,以及了解或者“玩赏”“他者”的欲望。另一方面,商家也在这一文化驳杂的时代推出了各种促销措施,敦促人们走出去看世界。对于商家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吸引游客。他们深谙一般人心理,理解游客的“凝视”所在,因此也就能为之树立起“靶子”。从旅游目的地经营者和旅游从业者所策划的角度来看,如何迎合游客的“凝视”以便兜售是最重要的。于是就有了所谓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的兴起。
由于旅游变得如此普遍,对旅游的研究自然增多。根据旅游的性质和目的,学界通常把它分为这么几个类别:休闲旅游、文化旅游(含民族旅游)、医疗旅游、情感旅游、黑暗旅游,等等。这些旅游虽然目的有所不同,但是,除了医疗旅游之外,大多数还是与休闲娱乐有关,尽管其中不乏艰苦甚至是痛苦的历练。医疗旅游虽然不算休闲,但还是有不少是人们出于健康的需要,遵医嘱到一些自然条件宜人的地方旅游疗养。但是,医疗旅游更多的是指这么一种情况,游客/患者通过国际旅行以便在国外进行治疗。所以,经济是推动医疗旅游的因素。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士选择到一些经济上相对落后、消费水平较低,却又能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国家进行治疗。有些案例则是因为患者/游客所希望获得的治疗,可能在他们的国家属于被禁止,或者必须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例如小布什当政时,就有一些美国人到国外寻求干细胞治疗。由是观之,医疗旅游其实更多地与健康或者公共卫生相关联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相关,称之“旅游”实在有些不妥①感谢我过去的学生,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地理系博士候选人柯明节(Travis Klingberg)对此所提供的解释。。所谓的黑暗旅游(dark tourism)则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历史、集体记忆和各种社会与个人的创伤密不可分。换言之,黑暗旅游犹如朝圣之旅。人们通过寻访、凭吊灾难遗址、大屠杀所在地或纪念馆,以及各种与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家族有关的纪念和记忆场所来铭记过去。这种旅游的政治含义自不待言。由是,黑暗旅游往往被更多地用来指新纳粹分子的活动,他们到对纳粹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或者纳粹头目葬身之所进行凭吊。这类活动的用意与精神昭然若揭,这样的旅游并非为了休闲而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
与黑色旅游意义相似的则是所谓的“红色旅游”。在极权和威权官僚政体的国家,权力机关也会组织类似的旅游,然而却“功夫在诗外”——这类旅游实质上是社会动员和宣传的组成部分。有些人的旅游与宗教信仰有关,但不能否认其中有些与社会创伤有关,例如到耶路撒冷哭墙的旅游就是如此。世界各地犹太人到欧洲各地的排犹遗址或者纪念馆的凭吊之旅则完全是为了铭记整个群体所经受的痛苦,具有建构认同的强大力量。用意相同,却有着参拜和朝圣意义的所谓“红色旅游”,在客观上却也为旅游从业者开辟了新的资源。我们不妨把这种具有凭吊或者“朝圣”意义的旅行称之为“颜色旅游”(colored tourism),把所有具有政治意涵的旅行活动都包括在此类别之内,以便更好地探索和诠释这类活动的多方面意涵。这一类别的好处,是在一定程度上摒除了价值判断,从而有助于理解“左”和“右”的极权体制在本质上的某种一致性。
典型的休闲旅游与文化旅游有所不同。不管是为了“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或者纯粹为了猎奇,文化旅游无论如何都带有一种了解未知的目的,奢侈消费不会在计划中占据首位。休闲旅游毕竟是为了休闲(可谓是消费的代名词),虽然每个游客都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来决定如何消费。除了到胜地景区或者其他更贴近自然的地方小住之外,休闲旅游的内容经常是游山玩水。随着旅游业的开发,休闲旅游现在也往往增加了许多有文化含量的内容。但是,严格地说,休闲旅游应当是地点相对固定,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想远离都市的喧嚣让身心极度放松的活动。经济能力决定这种旅游的奢侈程度,因此,休闲旅游的品位和档次体现了游客的社会身份,也因此成为了某种极具意义的符号。
但是,一旦旅游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与需求之后,各种涉及旅游的服务业应运而生,这些从业者的目的自然是商业性的。一旦商业的动机瞄准了游客的猎奇心,那必然会导致旅游产业泥沙俱下。因此,旅游在带给人们享受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可以成为人们的噩梦。我们经常听到不少人抱怨在旅游过程中“挨宰”的经历。境外的许多旅游团体和中介机构往往刻意将赌城安排在旅游线路上,有些旅行社甚至大量开办这种赌博旅游(为了好听一点,可以冠之“博彩旅游”)。北美的华人旅行社经营这种旅游可谓行家里手。华人好赌也因此名满世界。当然,这样的旅游不会要求游客到了赌场之后都必须参赌,所以,如此旅游完全是揪住了人类的弱点来开发商机,瞄准的其实是人类的愚蠢性(stupidity)和其他弱点。故而,许多旅游开发必然会把重点放在如何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之上,我国众多游客的境外表现在证明这一点上居功至伟。他们一定会被当地的旅游中介(针对华人游客的中介机构基本上都是华人经营,或者由华人专事服务华人事宜。)带到奢侈品商店。应当说,满足人类自然欲望是旅游从业者的不二法门。因此,食色赌必然成为旅游产业的赚钱之道。这种情形给我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问题——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问题。
五、内部东方主义的幽灵
游客在旅游中都抱有猎奇心态,这种心态与好奇有所不同,后者多少带有某种探究的心理,而前者未必有。如何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态便成为旅游策划者和从业者的重要任务。在许多国家,国内文化多样性和历史通常都成为旅游开发的资源。通过展示不同的文化来招徕游客是最常见的方式。但是,如何展现文化,尤其是展现非主流的文化或者展示非主体民族的文化?这是经常受到挑战的问题。在我国,许多民族地区都充分利用本地区丰富的族群多样性的资源来进行旅游开发。然而,在展示民族文化的方式上,援用的却是一些看起来在政治上不是那么正确的方式。换言之,在许多旅游景点里,少数民族之“异”往往是重点展示的对象。而且对所谓“异”的解释往往又有本质化之嫌,似乎他们因“异”而与主流社会或者主流文化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很明显,旅游目的地的许多景点在与旅游的“凝视”对接上,都有这么一种本质主义取向。换言之,景点的策划者都试图迎合游客的猎奇心。因此,原先可能可以发挥博物馆社会功能的教育功用的景点,遂在某种程度上与此背道而驰。它们所展示给游客的并非当地人今天的社会生活,而是不恰当地对当地的传统进行夸张。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教育和主流媒体的宣传,许多景点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描写与介绍完全与国家对民族的分类的解读如出一辙[13]48-66。比如民族村的解说员会介绍说某民族处于某阶段,信仰“原始宗教”,“文化落后”等等。这种似是而非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进步与落后甚至在一些策划和设计中成为某种元素,而这些元素一定与自然的风光山水搭配。为此,设计者可以将与当地无关的族群或者民族置放在山水之中来娱乐游客。譬如广西阳朔有一处利用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山形岩洞与水流构建起来的景点,名“世外桃源”。游客们泛舟水面,穿行岩洞。在水路的两边山坡和崖面台地上,不时出现载歌载舞的佤族男女青年。佤族是生活在云南的山地民族,为什么要把他们安排到广西来?同在一条船上的导游姑娘的解释是,“因为他们最原始,也就最快乐”,于是与美丽的山水最为协调。这真是个奇怪的逻辑!按照这位导游的话,岂不越“原始落后”也就意味着越快乐,越幸福?这种逻辑的背后其实就是越“原始落后”,头脑也就越简单;头脑越简单也就越无忧无虑。如果卢梭“高尚的野蛮人”之说尚可以考虑为对“文明”的失望,那么“原始落后”与“快乐”成正比,则表现了“现代文明人”的无知与妄自尊大。其实,我们在众多的民族旅游目的地景点所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他者”建构;而且还可能是一种“自我”的“他者化”——如果我们考虑到许多当地人也参与了这样的建构的话。
上述所提及的情形在中国许多民族旅游场合都可以听到,这绝非偶然。除了今天可以见到的各种涉及少数民族的古代文献都充斥着荒诞不经和歧视性的记载之外,当代国家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的分类和与此分类直接相关的有关知识,也将少数民族嵌顿在一种“落后-进步”或者“野蛮-文明”的线性演化的梯度解释模式上。这种貌似理性分析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解读,无疑给一般主流民众甚至少数民族民众自身建立起一种有关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另类的刻板印象。因为它貌似理性,与一般意义上的刻板印象有所不同。
有学者将这种建立在对“他者”或者对外族的想像之上的演绎和表现称为“内部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从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发展而来。1978年,萨伊德出版了《东方主义》一书,该书对人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认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导致了西方人的政治与文化霸权。这对西方学者如何看待“东方”的影响不可低估。西方学者把欧洲的文化与发展作为标准,而“东方”的异族情调不符合这些标准[16]38-41。依据萨伊德所揭露的一些偏见,西方学者所描写的东方是一个缺乏理性、软弱和女性化的“他者”[16]65-67。换言之,在萨伊德所批评的西方学者的眼里,东方与西方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各自的“素质”绝然不同。受到萨伊德的影响,匹兹堡大学的宗教学家贝科奇-海登(Bakic-Hayden)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内部东方主义”,认为东方人里也有把其它不同的东方人看作一种原始或者落后的“他者”[17]。
旅游不是简单的旅行,它包含了诸多的意涵。旅游中,游客必然要“看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看似如其所愿,但却未必是全然真实的。它,多少有了虚饰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游客所期待看到的,亦即游客的目光,是可以被支配和引导的,聚焦所致是为“凝视”。社会学家尤里(John Urry)认为,“游客的凝视”(tourist gaze)是一种建构性的目光,它取决于那些与游客所熟悉的事项相反或者矛盾的形式[18]。换言之,游客都会有猎奇的心态,总是期望所看到的是与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完全不同。而从业者便是抓住这种心理为游客建构他们的“凝视”。换言之,如何对接游客内在的好奇心和猎奇的愿望,便是旅游市场策划者的任务。因此,游客从旅行社、各类媒体、旅行广告、旅游小册子等所得到的,往往是一些鼓吹旅游是一种脱离平庸生活方式之类的说辞。而游客到旅游景点之后购买纪念品、拍照,以及与当地人的互动,便被宣传为满足“脱离平庸生活”的主要方式。建构“游客的凝视”的同时,也就是在建构“他者”。通过与他者的接触,游客们有了不同的体验与经历。在国内,绝大多数的游客接触“他者”的方式之一,就是去民族园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有众多的民族村可满足游客对“他者”的各种好奇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主题公园有不少冠名为“民族园”、“民族村”,或者包括展现少数民族的“锦绣中华”等等。在此,不妨笼统地把这些都称为民族园。从深圳到北京,从青岛到桂林,形形色色的民族园引来众多的游客。这些展现民族文化的主题公园虽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在如何表现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则有相同的原则——以展现少数民族的“奇”与“异”来招徕游客。有些学者认为,将少数民族村与周围代表现代的东西摆在一起,有意地强调了少数民族的落后[19]。这样来比附尽管可能不准确,但是符合游客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期待。长期以来,国家有关少数民族的系统知识已经使民众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强烈的刻板印象。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汉族相比,一定处于落后的阶段上,他们必须依靠国家和主体民族的支持才有可能走向现代化。同时,在国家所认可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叙事上,少数民族又被描写为有着诗意的浪漫风情并能歌善舞。许多民族旅游景点的策划,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与游客的期待与凝视对接。
这种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展示,在多大程度上能真实地反映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状况?非常值得怀疑。王富文(Nicholas Tapp)曾在深圳一个主题公园里访谈一位布依族姑娘,得知她的“老家水电都有”,生活条件远比主题公园里所表现的要好些。但主题公园所表现的布依族生活,得符合游客对少数民族的想像[20]。杜磊(DruGladney)在北京也发现,中华民族园所展示的少数民族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比较“现代化”的民族,比如朝鲜族和满族。这些民族“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文化“发达”,因此,也就没有那种“异域风情感”。第二组则是那些比较“淳朴”的民族,如傣族、哈尼族、黎族,他们主要进行的任务是唱歌跳舞和泼水节表演。如此安排,反映了一般民众对少数民族的看法[21]。
上述案例提及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展示或者再表现(representation),是长期以来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教育体系和主流媒体所传导的有关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知识的结果。正如笔者在其他地方所批评的那样,这样的知识体系首先建立在完善和建设国家权力机构之一环的人口分类的基础上,而为了使这样的分类具有合法性,就需要能够支持这一分类之思想、历史、文化的各类知识建构[22]。贯穿在这一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说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提出“五阶段”说。该说最早见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参见联共(布)特设委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49年版,第122-165页。。通过如此似是而非的所谓社会发展史分类将少数民族结构到整体的中华民族叙事当中,于是不同的少数民族根据其所处的所谓“社会发展阶段”,遂在发展的图腾柱上垫底或者处于低端的位置[13]76。
许多有着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省份,都发展了民族旅游。旅游民族村的存在使游客得以直接进入少数民族村落,这无形之中提高了游客直接接触少数民族文化的期待。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有些地区,发展民族旅游似乎有利于地方民众福祉的提高。例如贵州黔东南的千户苗寨。但是,在许多方面,当地对民族文化的表达,还是难以摆脱内部东方主义。游客们离开之后大概不会对当地的男性留有印象,仿佛只有女性才能代表不同的民族文化。如此的少数民族展示给一些西方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此看来,无论是以民族文化为主的主题公园,还是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其设计与策划都是以对接主要是国内的“游客的凝视”为目的。它们都符合游客们所特有的那种内部东方主义的异地感,都给予游客以某种“异族情调”氛围。游客们在接触少数民族民众之前,实际上已经对少数民族有了某种刻板印象或者概念。而为了吸引游客,一些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甚至将特定节日和特定场合才举行的仪式活动挪到成为旅游点之后的“日常生活”中来。旅游成为一种商业运作之后,不少少数民族村寨刻意地突出自己的“异”,这是一种“自我的他者化过程”——通过兜售刻意建构的“落后”的“传统文化”来与游客的凝视对接,由此寻求经济的发展。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长此以往,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互动与关系究竟何时才能摆脱内部东方主义式的不平等框架。
六、结语
全球化已经是无法扭转的潮流。全球化最主要的特质就是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它通过人类的旅行开始,随着走出非洲,人类开始向全球辐射。人类在分别进入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后,形成了各种地区性的差异,并在各自所在区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与文明。这些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又由于人类各种形式的旅行而相互接触与传播,由此推动人类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互渗。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旅行都对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人类的旅行和迁徙在国家出现之后多少都有了不同的限制。即便如此,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旅行从未变得如此艰难。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同,它夯实了传统国家那种松软的社会边际[23];或者出于主权的考虑,将“边疆”变成“边界”[24]。主权成为国家首先考虑的问题之后,人类旅行遂有了限制。护照的需要其实是民族国家暴力的折射。但在任何现代国家内部,人口的迁徙从未停止。于是许多国家便有了相对的政治治理术来对付版图之内的民众迁徙,以维护其制度性需要。历史上曾有极权国家将迁徙视为国家的惩戒方式,竟可以将整个不被政府所信任的族群从他们的土地上连根拔起,迁徙到其他地区以抵消那些当政者想像出来的潜在的威胁。
虽说殖民主义列强对世界的争斗与征服的起因与民族国家的政体形式扯不上关系,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形式在欧洲和日本崛起之后,无疑推动了列强瓜分世界与全球性资源和市场的争夺。但它也因为这种争斗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长时间的殖民地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争夺导致了在经济上形成世界体系——诚如马克思所言,帝国主义把全世界归并到资本主义体系。这一体系的最大“成就”就是造就南北半球巨大的经济落差。然而,也正因为这个落差,人口的跨国迁徙才成为战后、尤其是冷战以后的世界性现象。于是,“跨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面向。迁徙因此在今天对学术界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国家治理术的有效性问题。
旅游无疑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情调。无论是跨国旅游或者境内旅游,都与此脱离不了关系。除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因素,全球化之所以可能,最重要的要素就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包括各种人工智能和通讯的发展)和交通费用的大幅度降低。而旅游之所以能在中等发展水平以上国家百姓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也是主要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旅游有着各种形式,这些也都在中国的百姓生活中出现。由于现代经济的提升与发展都把消费视为重要的途径,如何促使人们消费遂成为各行各业孜孜以求的事情。因此,如何激发人们内在的各种欲望也就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旅游虽说也是这样的一种产业,但应当看到,如果对旅游开发进行有良知的策划的话,这一产业无疑可以造福生活在旅游目的地的民众。
然而,正因为旅游也是针对人们的某种来自“天然”的需求,旅游从业者自然懂得如何打造“游客的凝视”。我们看到,在我国的许多主题公园和旅游文化村或者民族村,内部东方主义往往是那些打造和对接游客的凝视的策划者之不自觉的视角,它下意识地把少数民族置于一种不平等的被“打量”和凝视的位置上。而如何展现少数民族则是根据国家在进行人口分类——民族识别之后所渐次建立起来的有关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知识来打造的。也就是说,国家的少数民族叙事是这些展现的主要话语体系。换言之,少数民族被当作“他者”,通过突出他们的“异”来招揽游客。少数民族文化在这些展示里被突出的是其传统性,亦即他们的“落后”成为了卖点。这是当今旅游产业存在的一大问题。
[1]Giddens Anthony.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J].思想战线,2012(1).
[3]Diamond Jare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1999:83-113.
[4]Clifford James.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5]Childe Golden.Man Makes Himself[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
[6]Hannerz Ulf.The world in Creolization[J].Afric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1987,57(40):546 -599.
[7]Ghosh Amitav.The Imam and the Indian[J].Granta,1986,20(Winter):135-146.
[8]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M]//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387-400.
[9]Wolf Eric.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10]Anderson 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of Nationalism[M].London:Verso,1991.
[11]乌布沙耶夫.卡尔梅克1943-1957——一个民族被驱逐与回归的真相[M].何俊芳,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1-8.
[12]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4.
[13]范可.他我之间——人类学语境里的“异”与“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4]Chan Kam Wing.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50[J].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9,50(2):197 -221.
[15]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J].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9(September):644 -668.
[16]Said Edward. Orientalism[M]. New York:Random House,1978.
[17]Bakic-Hayden,Milica.Nesting Orientalisms:The Case of Former Yugoslavia[J].Slavic Review,1995,54(4):917-931.
[18]Urry John.The Tourist Gaz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1990].
[19]Picard Michel,Robert EverettWood.Tourism,Ethnicity,and the State in Asian and Pacific Societie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
[20]Tapp Nicholas.Romanticism in China?Its Implications for Minority Images and Aspirations[J].Asian Studies Review,2008,32(4):457 -474.
[21]Gladney Dru.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y[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4,53(1):92-123.
[22]Fan Ke.Ethnic Configuration and State-Making:A Fujian Case[J].Modern Asian Studies,2012,42(4):919 -945.
[23]Duara Prasenjit.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History of Modern Chin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65 -69.
[24]Giddens Anthony.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M].Cambridge:Polity,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