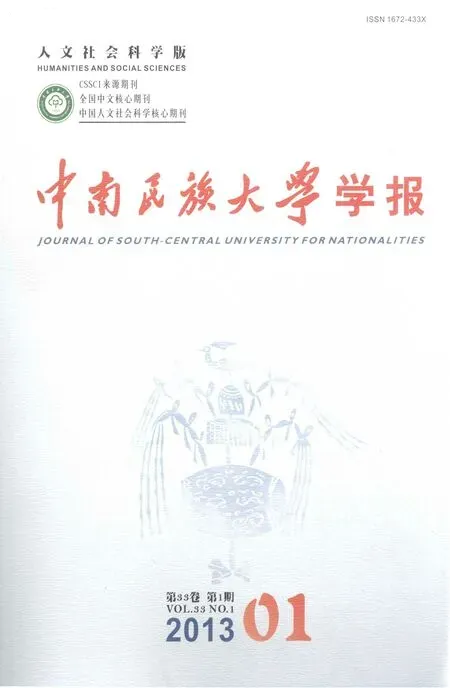“工具”与“价值”:基于诉求回应视角透视佤族的国家认同
袁 娥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阿佤山与内地的地理距离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内地与佤族地区的互动,滇缅在地理距离上的相近使得中国佤族与境外佤邦同族居民形成了相似的社会文化网络,使以地缘为基础、以族缘为纽带的跨国流动便利而频繁,致使佤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其国家认同具有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如纳日碧力戈所言:“中国的诸多‘跨界民族’,它们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属于同一个群体,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国民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被政治疆界分离出来,在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也逐渐发生差异,在认同上也有复杂的变化(有时认同,有时不认同)……”[1]
一、当前佤族的国家认同状况
佤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经历了从初步形成到完善,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佤族的国家认同意识较为模糊。随着佤族的中国少数民族身份被确立,其国家认同意识也随之逐渐清晰起来,但还很难说这种国家认同意识具有鲜明性和稳定性。1965年7月,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沧源视察,当问到许多佤族群众属于哪个国家的人时,有的回答是中国人,有的回答是佤族人,有的回答是缅甸人,有的回答是佤国人,还有的说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为此,阎红彦书记在沧源召开的有关干部会议上,强调“沧源的学校教育要结合边疆民族实际,要帮助当地民族培养‘三员’、‘五匠’,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边疆各族人民都知道‘我是中国人’。”①资料来源:陈荣华主编《中共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党史大事记》(中共沧源县委党史研究室内部资料)。“三员”“五匠”专指科技人员、医务人员、管理人员和各种能工巧匠。“文革”的到来,破坏了这种认同感的培育。特别是“文革”期间佤族中的很多人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等帽子,遭到迫害,从而形成了佤族对国家的疏离感和对主体民族文化的排斥感。随着我国拨乱反正、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以及改革开放至今,佤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归属感己经走出模糊,越来越鲜明。这种国家认同感的确立与国家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国民认同教育的强化作用是分不开的。此外,中国经济的崛起无疑也进一步提升了佤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佤族在与缅甸佤邦的交往中真切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差异,“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在佤族群众中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缅甸佤邦马落村与中国马落村仅一条宽约3米的土路相隔。2004年,为了发展南邓街区,佤邦政府要求村民搬走并破坏了现有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加之2009年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战事发生时到这里暂避的群众也离开了简易棚,村寨只剩下空空的房屋架子,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又搬了回来。2010年2月笔者在此调查走访时,整个村寨显得十分冷清。幸运的是,与中国马落村为邻,缅甸的孩子可以到中国马落小学读书,通过架接电线杆,就能用上中国的电。缅甸马落村村民龙新介绍:
佤邦的行政机构设置是按照中央总部—县—区(注:相当于我国的镇)—乡(注:相当于我国的行政村)—村(注:相当于我国的小组)。我们要按等级上税,第一等级每年要交386斤大米,第二等级每年要交260斤大米给芒坝乡,由乡里又交给南邓区。佤邦的义务工干也干不完,不仅要修路,还要干很多事,比如区上要柴火,每户要有1人去参加,要砍柴给他们,上山砍柴还要自己带饭吃,不去出义务工的人要按照每天30元的标准收费留作村上的集体经济收入。仅2009年,我出的义务工就数不清,当时果敢打仗,我到芒坝乡出义务工守营盘,我们自己在山上盖房子,20-30人合住,一去就是5个多月。每月才给100元,还要交小菜钱,每月从我们100元的津贴里扣,最后拿到手的就是50元。我只认佤邦,不认老缅。我的很多亲戚就在隔壁中国马落村,在中国不上税,没有义务工,政策真是太好了。
田野调查发现,许多缅甸佤族人自然流露出对中国佤族的羡慕之情。从帮康到南帕冷,从当阳到腊戌,电视里播出的节目大多是中国电视台的节目。在腊戌的一个佤族人家,主人介绍:
在腊戌可收看到中国电视台的40个频道。缅甸和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好,但是没有中国的好,中国的电视节目内容丰富健康,我们看得懂,听了很亲切,这是大家的共同感受。要是我们也能生活在中国就更好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卫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包括佤族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国家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这更加坚定了佤族的爱国之心,增强了他们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尤其是在与缅甸佤族群众生活实实在在的对比中,中国佤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不言而喻的。
2003年,中国实施民房改造,把茅草房改成石棉瓦房。2009年,国家实施民房加固工程,国家提供水泥、砖瓦、沙子、门、窗,村民自己挖地基,准备石头、木料来建盖房子。每家建房面积为70平方米。国家补助2.5万元,村民自筹 1万多元。2009年1月,国家免费提供核桃树苗和塑料薄膜给老百姓,帮助佤族村民发展经济,而且沧源县烟草办还推广烟叶种植,建盖烤烟厂。现在种烤烟、种茶叶、种核桃,村民的收入也增多了。生活困难的家庭还享有农村低保。一类低保是每月55元,二类是每月50元,三类是每月45元。中国这边关心老百姓,关心我们佤族。佤邦那边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也有,但是不多。有的人做毒品生意发了大财,房子住得很好,有的人家甚至还雇佣了丫鬟,但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很穷,贫富差距非常大!相比佤邦,我们这边佤族的日子太好过了。(访谈人:男,佤族,47 岁)
不过,尽管中国佤族的国家认同感日益增强,但现状仍不容乐观。除了在民族国家基础上构建国家认同的时间不长,面临着多样性的民族认同等结构性制约等问题外,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也对佤族的国家认同状况造成了不利影响。
二、佤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民族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对国家认同意识的影响,不仅源于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而且也广泛存在于一国内部不同民族群体的比较中。认同感作为民族共同体成员普遍持有的心理状态,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可变的量。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后,国家认同得到有效提升,总体上达到较高的程度。但是,国家利益与民族自治地方利益的矛盾、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所办企业利益与当地少数民族利益的矛盾仍时有存在。2010年2月,笔者调查的班洪乡富公村共有61户人家,全部为佤族,信仰小乘佛教。村民们对当地铅锌矿藏资源的开发给其生产生活带来的恶劣影响表示了不满:
1996年就有一家公司来开采,2000年后以70万的价格卖给了另一家公司,2007年又以2000万的价格卖给了新公司来开发。虽然矿藏是国家的,但毕竟是属于富公村的土地,村民没有享受到任何资源费。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村民要求给200万元的资源费未果,后来几经讨论,公司每年给村里1万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但是几年下来,他们开矿的碎石、矿渣掉进河里,造成污染,谷子减产,草果也无法生长。不仅是富公村,而且南板村、班洪村都受到影响。直到2009年,国家才同意采矿占用林地的,每亩补助村民1400元,无法恢复生产庄稼的每亩补助3000元。(访谈人:男,佤族,41岁)
根据我国1982年宪法和我国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然而,实际上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并没有因为当地资源的开发而得到很好的照顾,国家与民族自治地方在资源开发问题上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有的是因为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兴办的企业未能与当地的经济融为一体,未能很好的起到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有的是未能充分地顾及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补偿金没有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有的是没有解决好污物排放的净化处理,给当地造成了环境污染,引发多起群众纠纷,损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2]。在阿佤山,除了矿藏资源的开发引发不小的争议外,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动植物的保护与当地佤族利益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自1980年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热带植被恢复较快,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增加,为许多濒临灭绝的国家级保护动植物提供了最后的栖息地。但随着野生动物种类数量的不断攀升,保护区内的栖息地容量逐渐出现饱和状态,野生动物食源匮乏,许多野生动物走出保护区觅食,给保护区周边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从大局上来讲,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进行资源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域,利国利民,但在局部上又确实与当地群众眼前、近期的经济利益发生矛盾。班洪乡村民岩惹(男,佤族,43岁)表示:
2008年保护区粮食赔偿按照亩产估计产量来进行。每亩产粮900市斤,每公斤补助1角3分8,2009年有所增加,每公斤补助4角。但是在市场上,大米至少卖每市斤1元4角。保护区扩大,粮食不够吃,但是补助又少,还得用钱去买粮。勐永村48户人家,也属于芒库,水田300亩全部被划入保护区范围,每亩才补助300元。芒库村没有更多的经济来源,虽然种植西楠桦、沙松树,但要七八年后才可以用作木料。村里也没有更多的地来种植,村民的柴火只能靠自留山上的2-3亩土地。因此,国家说要发展,但无处发展。
极个别偏激的佤族村民甚至抗议说:“佤族就是太乖了,乖的反倒得不到关心。那些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乖的民族,国家还随时关照着。”
可以看到,佤族在遭遇各种现实利益冲突时,少数人会有意无意地将一般性利益冲突与民族关系纠结起来,使问题的处理变得盘根错节,极大地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可能直接威胁到边疆的稳定。虽然当前佤族地区并不缺乏对国家的认同,但在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得不到国家的回应时,部分佤族群众就会认定国家“故意忽略”了佤族的利益,此时,在与民族认同的对比中,国家认同的主导地位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动摇。
2003年,自然保护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野生动植物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却影响了当地佤族群众的生活,割断了其祖祖辈辈生活上对于大山的依赖,这使得原本经济就不发达的佤族人更是焦虑不安。这种焦虑,在野生动物肇事长期得不到合理补偿的情况下,加剧了佤族村民的痛苦心理,成为民族与国家冲突的导火线,严重影响到边境地区的安宁。因此,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不仅是佤族与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问题,也关乎佤族对国家的认同问题。
访谈中,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表现出极大的烦恼: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的保护区,但是保护的压力和责任全部由保护区周边群众与当地政府来承担。象征性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经费已无法再取得当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如果不重新制定合理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佤族与国家政府的对立情绪将可能愈演愈烈。为了缓解这一矛盾,2008年,沧源县克服重重困难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标准提高,非试点村赔偿费谷子从0.2元/公斤提高到1元/公斤 ,玉米从0.2元/公斤提高到0.8元/公斤 ;黄牛从160元/头提高为3岁以下500元/头、3岁以上1500元/头,水牛从200元/头提高为3岁以下1000元/头、3岁以上 2000元/头;橡胶苗由 0.35元/株提高为0.6元/株。试点村补偿经费更高一些:谷子2元/公斤 ,玉米2元/公斤 ;黄牛2500元/头;水牛3000元/头;橡胶树34.83元/株。为使佤族群众利益得到最大的保护,沧源县提出了将以往由政府单一补偿转化为以商业化运作模式进行补偿的全新补偿思路。2009年3月23日,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沧源管理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沧源分公司签订中国野生动物肇事理赔第一保单。按照县委、县政府确立的“由主管部门出资统一投保,群众不出一分保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专业保险服务、按市场化进行运作的原则”,沧源管理局一次性向保险公司交纳了7.8万元的保险费,保护区周边5个乡镇6万多群众因此获得了全年60万元金额的保险。按照双方签订的保险赔偿协议,在伤亡责任限额内,受伤人员医疗费用若已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含工医保险)的,在扣除合作医疗报销部分外,剩余的由保险公司给予赔偿;若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含工医保险)的,则由保险公司全额进行赔偿。
补偿保险机制的建立,缓解了保护区周边群众对政府的抵触情绪,但仍不能完全解决补偿标准低的问题,尚需更多的筹资渠道。当地财政的紧张迫使政府寻求更多的方式来解决佤族的利益诉求问题,而目前酝酿的“野生动物救助补偿基金会”便是补偿保险机制的有益补充,但这需要得到热心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各界支持才能较好发挥作用[3]。
三、民族文化价值的坚守
经济的发展与保障是增强佤族的国家认同感的“工具”手段,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佤族对国家的认同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还与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情感因素有关。2008年,在佤山发生的“岩帅事件”就是最好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前夕,岩帅是个与周边部落乃至缅甸、泰国、老挝等国有着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山镇。李培伦等共产党员受指派来到岩帅,经过做工作,以田兴武、田兴文为首的民族上层欣然接受了和平解放的倡议。但由于国民党李弥残部的顽抗,在解放岩帅的战斗中有11名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岩帅的赵们茸和田三木拉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岩帅从此享有了革命老区的美誉。岩帅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团结乡全部和勐省镇的下班奈、和平、农口等办事处。而当时的沧源还属于思茅地区,沧源县政府设在岩帅。1952年底沧源划归临沧后,县政府迁往勐董镇,而岩帅仍然保留了自己的辖区,也是区政府所在地。20世纪70年代初人民公社化时期,团结、下班奈、和平、农口被划分出去。团结作为一个乡,岩帅作为一个镇一直独立存在。及至2006年3月,政府把团结乡并入岩帅镇作为其下辖的一个区域。2008年,沧源县政府决定把岩帅镇政府由目前岩帅大寨的住址,搬迁至原被撤并的团结乡政府原址,并在团结挂牌岩帅镇。政府搬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口逐渐增多,岩帅较为拥挤,且雨季自来水浑浊。另据镇政府办事员小田向笔者透露:“团结那边地势比较平坦,岩帅地势狭长,扩不开。”由于在决定之前没有广泛征求各方的意见,在2008年沧源县两会期间,县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做好岩帅镇的搬迁工作”,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觉得镇政府搬迁一事太突然,对此议论纷纷,特别是岩帅镇当地广大佤族群众更是难以接受,坚决不答应镇政府搬迁出去。2008年4月21日,岩帅大寨头人及村干部在岩帅村村委会召开了会议,就搬迁一事进行讨论并形成《关于反对将岩帅镇政府迁往团结乡的报告》,希望岩帅镇政府继续留在岩帅,提出的理由主要包括:
一是岩帅自明、清时代就是佤族地区名扬滇西南乃至缅甸佤邦地区的一个部落首领驻地,……岩帅是佤族地区接受共产党领导最早的部落。1949年岩帅产生了沧源县人民政府和第一任县长,岩帅名副其实地成了佤山的革命老区,至今这个政治中心的作用仍不褪色。
二是岩帅是佤山地区最早建立集市(1941年建立)贸易的地方,岩帅街一直是县内外、国内外客商云集的地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经济中心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是岩帅是一个文化中心。沧源第一所学校,佤族第一个县长,佤族第一个初中生(肖子生,现在沧源)都产生在岩帅,现在佤族通用的语言和文字都是岩帅语,岩帅在佤族地区是不可替代的文化地域,佤文化的打造仍需要地道的岩帅人唱主角。
鉴于上述情况,报告中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维持现在岩帅镇政府所在地不变。第二,对于拥挤问题可以通过部分农户搬迁的办法解决。第三,自来水雨季浑浊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处理办法解决。第四,倘若要搬迁,绝不允许使用在岩帅人民心中庄严、神圣的名字——岩帅,就应该改为团结镇。
报告内容不仅体现了岩帅佤族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一种博弈,更重要的是显示出岩帅佤族人捍卫其民族文化阵地的决心。因此,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国家既要重视边疆民族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也要重视其民族文化价值的满足。只满足其中之一是远远不够的。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实现的基础和条件,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目的,二者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统一体。
由于政府没有较好地处理岩帅佤族群众的意见,导致在团结乡举行挂牌岩帅镇仪式当天(2008年5月21日)发生了冲突事件。当笔者在调查中问及岩帅镇政府搬迁一事,很多村民还是义愤填膺。
2008年5月21日,团结举行挂牌岩帅镇仪式,在这之前,群众向上面反映情况,但没有任何回应。挂牌前几天,老百姓在街上贴标语,要求尊重历史。当天,老百姓各家各户共600多人,坐着拖拉机去抢牌子。老百姓9点钟到达团结,政府说会给牌子,结果等到11点,愤怒的老百姓砸团结镇办公楼的玻璃,牌子才得以拿回。(访谈人:男,佤族,63 岁)
5月21日在团结举行挂牌岩帅的仪式,刚好在汶川大地震默哀日的那三天,想想地震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让人心酸,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给国家添乱,否则我们岩帅就会约上几个人到北京上访。(访谈人:男,佤族,37 岁)
挂牌引发的冲突只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忽视佤族群众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岩帅一位退休老人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1949年5月6日,岩帅人参加革命到沧源活捉了匪首,解放了沧源,2009年5月6日,县政府、镇政府在岩帅举行沧源解放60周年庆祝分会。这么重要的会议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让老百姓来参加,可是他们只召集了一小部分人,根本就没要其他的老百姓来参加。说到这些事情,我的心很凉。说不定以后我们还是只能靠我们佤族。佤邦是我们的篱笆,我们和他们是不可分开的。
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是这个国家的最后防线,公民的内心哪怕是出现一点点缺口,都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内心的国家认同感尤其需要巩固。虽然佤族有着明确的国家归属意识,但由于与境外佤邦民族属性上的同宗同源,使得大多数佤族内心深处存在着对国家和对民族的二元身份认同。一旦在现实利益中受到挫折,佤族的民族认同就会增强,而国家认同则会弱化。“在社会转型中体会到‘失落’的民族成员,当正式的国家制度不能或不能充分地提供利益保障时,人们会倾向于向民族寻找安慰和力量,这使得民族的重要性增强,民族利益的一致性被强调和放大,人们通过民族被重新非正式的组织起来,利用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感受,组织起以宗教、地缘或精英人物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并能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4]如果民族认同过于强势,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
政治精英们追求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力和影响力,普通民众更看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福利和经济前景及实际感受。当国家和政府不能尊重民意诉求而与当地佤族群众产生矛盾时,佤族就会到佤邦去寻求心理上的归属,他们经常用“佤邦是我们的同胞”这样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即使在平时,中国的佤族也会经常关注缅甸佤邦的发展。如果佤邦的发展比中国的发展较快时,佤族的民族认同会更为强烈。要增强佤族的国家认同,不仅要满足佤族群众物质上的“工具”需求,更要对其“价值”上的文化诉求表示尊重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满足,这样才能促进佤族群众的中国公民自豪感,增强佤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1]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38 -39.
[2]唐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矛盾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5.
[3]袁智中.中国野生动物肇事理赔第一保单始末[N].云南经济日报,2010-01-05.
[4]解志苹,吴开松.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的重塑——基于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J].青海民族研究,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