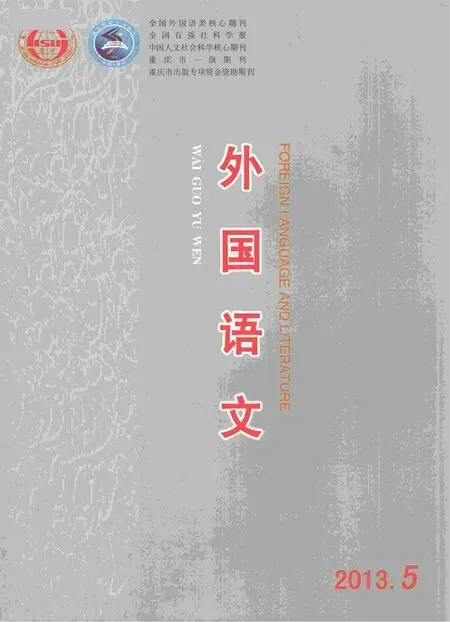界面研究的涵义、学科意义及认知诗学的界面性质
熊沐清
(四川外国语大学 期刊社,重庆 400031)
1.引言
近年来,“界面”及“界面研究”已越来越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四川外国语大学已于2012年牵头成立了全国性学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并且主办了多次不同规模的全国性界面研究学术会议,来自国内外语界文学、语言学、翻译、外语教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和教师、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从界面研究的涵义、学科意义、方法论特征和实际应用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也毋庸讳言,由于资料匮乏或视野有限,国内不少人对界面研究依然不甚了了,且不乏误解和偏见。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国外界面研究动态的基础上,综合各家之言,尤其是结合“界面”在国外学界的实际用例,对界面研究的涵义和学科意义作一概括性探析,力求正本清源,有助于界面研究在国内的深入和健康发展。本文同时指出:认知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界面特征。这一特征使它具有开放性,蕴涵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2.“界面”及“界面研究”的涵义
界面(interface)也译为“接口”或“接面”,在各个不同学科中广泛使用。在物理学中,它指两个或多个不同物相之间的分界面,如气/水界面;在地质学中指“不连续面”,即地球内部不同圈层的分界面;作为设计用语,界面是人与物体互动的媒介;作为电脑用语,界面是呈现在用户面前的显示器屏幕上的图形状态,等等。它还可以是“无形”的,用以指学科间的交叉,比如“物理、化学的界面彼此频繁交叉,以至于其确切的界线模糊难辨。其界线与其说是由于任何内容方面的明确划分,不如说更多地是由语言和方法的逐渐变化来标志的,它已成为整个分子与原子、表面与界面、液体与固体科学在理论、应用上的不断进步之源”(克莱恩,2005:8)。
Routledge出版社于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一套界面研究丛书——The Interface Series。该套丛书有如下书目:Narrative: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Language,Literature and Critical Practice:Ways of Analysing Text;Literature,Language and Change;Literary Studies in Action;Feminist Stylistics;Language in Popular Fiction;Language,Text and Context:Essays in Stylistics;The Language of Jokes:Analysing Verbal Play;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A Linguistic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Literature about Language;Textual Intervention:Critical and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Literary Studies等等。
从以上用例可以看出,“界面”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指不同学科间的交融交汇,如语言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文学与教育、语言与性别、生命与哲学、生命与政治、生命与语言、生命(生物学)与社会学、生物学与认知(认知生物学)、生物学与伦理等等。
概言之,根据用例可以得知,“界面”大致指三种研究类型:其一是学科之间整体性的互涉(interdisciplinary),比如上述Routledge出版社推出的那一套丛书的绝大部分;其二是借鉴性的或是派生性的学科互涉,产生出新的边缘学科,比如Feminist Stylistics(Mills,1995)。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一个现象是:受认知科学影响,衍生出许多基于“认知”的边缘学科,比如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文化学、认知教育学、认知文化学、认知人类学、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诗学等等,不胜枚举,其中一些算是“二次派生”的边缘学科;其三则是学科分支之间的互涉,如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界面研究。这一方面国外的著述颇多,如Cognitive Interfaces:Constraints on Linking Cognitive Information(Zee& Nikanne,2000);Academic Writing at the Interface of Corpus and Discourse(Charles,Pecorari& Hunston,2009);Exploring the Lexis-Grammar Interface(Rmer & Schulze,2009);Interfaces-Recursion=Language?Chomsky’s Minimalism and the View from Syntax-Semantics(Riemsdijk,Koster &Hulst,2007);Exploring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Valin,2005)等。值得注意的是:牛津出版社还曾推出过一本通览性的语言界面研究文集: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nterfaces(Ramchand & Reiss,2007)
以上三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跨越了单一学科的边界,是一种“边界作业”(boundary work),是内容、方法或概念等的融合、交汇或借鉴,人们打破并重构知识单元之间的界线,通过形成某种惯例来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或研究范式。前两种类型都可以视为广义的界面研究。其中,第一种类型因为涉及学科之间交叉、交汇,可称之为“平行型”界面研究;第二种是以某一学科为基础,吸收、借鉴了另一学科的学理、方法或概念体系,可称之为“衍生型界面研究”,比如feminist stylistics(女性主义文体学),即是以stylistics(文体学)为本体和基础,吸收、借鉴了女性主义研究成果,产生了新的边缘学科。又如cognitive poetics(认知诗学),则以poetics(诗学)为本体和基础,吸收、借鉴了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新的边缘学科。“借鉴”是这一类型的方法论突出特征,而“衍生”则是其典型性结果。第三种是狭义的界面研究,特指学科分支之间的交接和交织,可称之为“交织型界面研究”,比如语言学中句法与语义之间的交织而形成的界面。
当interface用来指称学科间的关系时,它与inter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以及 cross-disciplinary有密切联系,且经常互换使用,许多人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微妙区别的。尽管它们的涵义与interface非常接近,但inter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以及 cross-disciplinary这些词一般指学科之间的比照、借鉴或交叉,却不能用来指学科分支(如语义—句法、音位—句法、语音—音位等界面)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考虑到这种区别,所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采用了interface,学会也命名为“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简称“外语界面研究会”)。我们以“界面研究”统称这些涉及两种及两种以上学科或学科分支的跨界研究。我们之所以使用 interface而不是cross-disciplinary或interdisciplinary是因为interface不仅可以指称学科间的互涉,还用以指称学科分支之间的交叉,如语言学各分支之间的界面研究;而interdisciplinary等词通常不用来指称学科分支之间的交叉。
综合各种用例,笔者认为,学科意义上“界面”的基本涵义指不同学科或学科分支的相交处,其延伸义指不同学科或学科分支的交融交汇。这种“交融交汇”可能是研究对象(内容)方面的,也可能是研究方法方面的,还可能是研究工具或概念、话语方面的。概言之,不同学科或学科分支之间的某种结合、融汇和交汇即是“界面”,界面研究则是内容、方法或概念等的融合、交汇或借鉴;从宽泛的意义说,“界面研究”就是跨学科的研究。但是,它与以“比较”为主要特征的跨学科研究(如比较文学、比较法学、比较教育学等)有所不同,它并不在意于两者之间的对比而在于两者之间的交融交汇或借鉴。
近年来还很活跃的另一表述:crossing boundaries,也是指的跨学科的研究。比如下面这些著作,饶有意味的是,它们并不是出自同一家出版社,各家不约而同,这表明已形成普遍共识:Crossing Boundaries:Thinking through Literature(Sheffield Academic Press,2001)、Crossing Boundaries:Postmodern Travel Literature(Palgrave Macmillan,2000)、Crossing Boundaries:Knowledge,Disciplinarities,and Interdisciplinarities(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6)、Crossing Boundaries:African American Inner City&European Migrant Youth(LIT Verlag Münster,2004)、Crossing Boundaries:Advances in the Theor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Languages(John Benjamins,1999)、Crossing Boundaries in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Waxmann Verlag,2012)等。
事实上,界面及界面研究无处不在,界面研究已经成为研究常态。所以,虽然有许多界面研究的成果冠有 interdisciplinary、interface或 cross-这些字眼,但也有更多的成果没有贴上这些标签,我们在其著述的标题上看不到interface或interdisciplinary这类字眼,它们却可能是不折不扣的界面研究成果,比如Gibbons(Routledge,2012)的著作Multimodality,Cognition,and Experimental Literature。又如:A.Clark(2004)所著的 History,Theory,Text: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一书,在“语言转向”的背景下借助了语言学、结构主义、叙事研究等理论来研究历史和史学;Vyvyan Evans(2005)所著的The Structure of Time:Language,meaning and temporal cognition一书,则从现象学哲学角度讨论了时间概念,并且从概念隐喻、时态等表现形式探讨了诸如延续性、瞬间性、事件等各种时间涵义和时间结构,堪称时间研究的典型性界面范例;Jane Duran(2007)的专著 Women,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试图弥合文学研究、哲学和思想研究领域各自为战、不相往来而形成的鸿沟,整合了多个学科的成果,探讨了女性写作中的哲学和女性主义元素;G.Binder&R.Weisberg(2000)合著的 Literary Criticisms of Law一书,别出心裁地把法律视为一种文学的和文化的活动,其开篇即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作为文学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接着作者分别对法律作了解释学的、叙事的、修辞学的、解构主义的和文化的批评,无论就理论基础还是方法论而言,该书都是一部典型的界面研究之作。
三、认知诗学的界面性质
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是典型的衍生型界面研究类型,其主要来源明确揭示了这一点。Stockwell(2002:4)指出:“认知诗学是直接基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建立起来的,它们都是认知科学的组成部分。”在《认知诗学导论》的最后一章,Stockwell(2002:166)更明确地指出认知诗学的跨学科性质:认知诗学的疆界变化很快,它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门能够衍生出许多新的交叉联系的边缘学科。
认知诗学的界面性质,或者说它的跨学科性,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认知诗学的主要学科基础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它所使用的主要理论和概念包括来自语言学的隐喻、概念及概念整合、脚本、原型、心智空间、指示语、话语、语境、认知语法等,也有来自心理学的情感、想像、注意、移情、图式、图形—背景等。
其次,认知诗学还广泛借用、整合了包括传统文学批评和文体学、修辞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及概念体系,比如来自逻辑和哲学的可能世界理论、来自文体学的前景化以及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本肌理、共鸣、声音、风格、心理分析、读者反应理论等等。
第三,认知诗学的哲学和认识论基础也是多元的。Stockwell在其新著Texture: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中曾经专辟一节讨论认知诗学的原则(principles of cognitive poetics)。在讨论这些原则之前,Stockwell(2009:2)坦承:认知诗学从认知科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中借用了许多模式、方法、假设和合法性依据,而认知科学通常包含了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心智哲学和神经科学的某些方面。他分别概述了六条原则,即: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普遍化(Generalisation)、文体学(Stylistics)、连续性(Continuity)、体验(Embodiment)和生态(Ecology)。这些论题可以视为认知诗学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
不过,认知诗学并不是上述理论和方法的简单聚合,它们或者经过了修订,或者被重新界定和阐发,都指向和服务于文学分析,因此,它们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这一点,从Stockwell对这六条原则的论述可以看出。Stockwell(2009)认为,认知诗学的各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验性实在论(experiential realism)。该观点主张:身体之外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种实在论观点),我们接近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我们对它的感知和认知的经验。美国学者克莱恩在谈到修辞学转向时也这样评价认知与经验主义的关系,她(克莱恩2005:85-86)说:“认知方法植根于有丰富理论的经验主义传统,靠的是阅读、记忆、语言处理与语言习得、人类发展、洞察力和独创性。”经验主义的观点引出认知科学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存在着人性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因此,如果某些断言对某一人群和他们的认知能力来说是真实的,那么对所有人来说也同样为真。当然,这并不否定文化的、种族的、性别的、地理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差异,但是人类的种种可能性的宽大窗口是以同样的方式受制约的,这方式就是我们大脑的工作和我们身体与现实世界的互动。(Stockwell,2009:2-3)也就是说,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和人类依靠身体与外界的互动方式,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这就是Stockwell描述的第二个原则:普遍化。
Stockwell的第三个原则是文体学。他主张,研究文学的最好方法是专注于文本性和文本对读者的效果。因此,他认为,认知诗学最好是依循文体学传统,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批评理论。关于第四个原则“连续性”,Stockwell的主要观点是:文学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两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的大脑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学模块”;文学,尽管它会很特别很神奇,但它没有超越人类的能力,文学不过是把语言艺术发挥到极致罢了。(Stockwell,2009:3-4)这就是说,文学和文学接受/阅读是可以理解、可以解释的。“体验”是第五个原则,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物质的、感性的世界和抽象的、概念的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心—身二元对立应予否定;其二,自然与艺术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都是自然的过程,都需要利用我们的认知能力。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和生态学的观点。由此,引出了第六个原则,即生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不要把一个文学文本仅仅看作是一个物体、一个印刷品,也不要孤立地谈论读者,而是要把作品看作是文本与读者合作的物化产品,这样,就不应该仅仅关注文本或者仅仅关注读者,要做的是对文学阅读的整合性研究。(Stockwell,2009:2 -6)
事实上,认知诗学与现象学也有密切的关系,虽然Stockwell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我们从认知诗学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可以意识到现象学的影响。现象学把审美活动看作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意向性活动,强调主体应当排除尚未验证的假设和先入之见,而要具体体验和直观呈现在面前的审美客体,认为主体的能动参与和审美对象的重建是审美对象存在和“具体化”的基础与前提,研究者就是要从这里出发去阐述诸如审美对象、审美感知、审美享受、审美价值等一系列具体的美学问题,而且要求对审美主体具体体验到的现象进行尽可能直接、忠实的描述和研究。罗曼·英加登在谈到文学作品的界定时指出:“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的构成,它包括:(a)语词声音和语音构成以及一个更高级现象的层次;(b)意群层次:句子意义和全部句群意义的层次;(c)图式化外观层次,作品描绘的各种对象通过这些外观呈现出来;(d)在句子投射的意向事态中描绘的客体层次。”“文学的艺术作品(一般地说指每一部文学作品)必须同它的具体化相区别,后者产生于个别的阅读(或者打个比方说,产生于一出戏剧的演出和观众对它的理解)”。“同它的具体化相对照,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图式化构成 (a schematic formation)。这就是说,它的某些层次,特别是被再现的客体层次和外观层次,包含着若干‘不定点’(place of indeterminacy)。这些不定点在具体化中部分地消除了”。“文学作品是一个纯粹意向性构成(a purely intentional formation),它存在的根源是作家意识的创造活动,它存在的物理基础是以书面形式记录的本文或通过其他可能的物理复制手段(例如录音磁带)。由于它的语言具有双重层次,它既是主体间际可接近的又是可以复制的,所以作品成为主体间际的意向客体(an intersubjective intentional object),同一个读者社会相联系。这样它就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超越了所有的意识经验,既包括作家的也包括读者的”。(英加登,1988:11-12)这些观点与认知诗学的观点十分吻合。美国学者Margaret H.Freeman——认知诗学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曾多次提到现象学,她推崇现象学的一位主要人物梅劳-庞蒂,引用他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诗学象似性”理论,认为诗学象似性创造了一种“现象的真”(phenomenally real);因为诗学象似性的作用,读者得以“从符号的诗歌世界进入现象学的诗人世界”(原文:causes us as readers to move from the semiotic poem-world to the phenomenological poet-world)(Brne& Vandaele,2009:189)。
4.界面研究的意义
关于界面研究的学科意义,不妨先看一个有关的背景材料:
目前,关于知识有两种说法广为人知,第一种说法是知识日益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引证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但结果相似。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学术研究的突破,新的奖学金的提供、以及学科的新要求,将20世纪60-70年代的口号“学科互涉的时代到来了”(舒茨,1985:9)提上了学术界的议程。第二种相关的说法是边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明确特征。(克莱恩,2005:1)
这里说的学科互涉,即学科边界的跨越问题,也就是界面的问题。界面及界面研究的观念,不仅具有方法论(或工具论)的意义,而且具有认识论的意义。
首先,界面研究是当代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这也就是克莱恩所说的“学科互涉的内生性”(克莱恩,2005:17)。西格玛·西把当代科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问题:传统学科内部的学术问题。
第二类问题:多学科问题,它们在本质上与其说是策略一行为的,不如说主要是学术的,但并不能在单一学科内部成功地进行。
第三类问题:确定无疑的多学科问题,由社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并且由相对短期的课程区分开来,它们在一些情形下要求一种策略一行为结果,在另一些的情形下要求一个技术性的快速定位。(克莱恩,2005:60)
以上三类问题中的第二、第三类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能够成功解决的,需要借助于界面的研究。正是这些超越了单一学科界限的复杂问题,“制造出一种学科互涉需求。复杂问题使得研究远离传统上认为的学科问题,它们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多维的、含混的、不稳定的。”(克莱恩,2005:49)
我们以认知诗学为例试加以说明。
认知诗学的界面性质——或者说它的跨学科性,是与文学本身的界面性密不可分的。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多学科问题”,因为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某一单一要素的产物:它既不是仅属于语言的艺术品,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者社会思潮的产物。所以,Freeman指出,文学本身是表达、情感和审美的,认知诗学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具有包容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因此,需要把众多文学批评理论整合统一为一个连贯的理论(Geeraerts&Cuyckens,2007:1176;1180)。她评价Brandt(2004)的最新研究成果时说,该成果提炼和修改了Fauconnier和Turner原始的认知合成模型,用以说明文化、情景、情感、评价和道德在意义产生中的作用(Geeraerts&Cuyckens,2007:1186)。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文学是语言、文化、语境、情感、意向、审美等多种要素的聚合体,本身具有强烈的界面性,因此,对文学的研究也必须是界面的。在文末,Freeman呼吁说:“我们面临的诗学挑战是综合(incorporate)这些形式(formal)和情感 (affective)因素——Langer(1953,1967)的‘形式’(form)和‘感觉’(feeling)——建立一种充分的、有生命力且合理的关于审美创造和反应的理论。然而如果我们做不到,将不能宣称已经充分解释了语言中的人类认知。”(Geeraerts&Cuyckens 2007:1193)她所呼吁的“综合”,就是一种界面的研究取向。
其次是方法论的意义,“学科互涉的说法一般是在方法论基础上提出来的”(克莱恩,2005:85)。这也是西格玛·西所说的第二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在单一学科内部成功地进行”。比如英语中的空缺和假空缺(pseudogapping)问题,它既是句法的,又是语义的。Gengel撰文考察了语义和句法成分焦点在此类省略结构中的作用{例如:约翰会选我,而比尔会(选)你}。语义方面,文章采取了当代省略研究中的通行观点;文章同时认为,假空缺表达了与先行词所指事物相对照的意义,从而允许说话人从表达单位的备选集合中挑出特定表达单位。假空缺带来的对照(相反)意义被认为是非穷指的,这与一些语言,如匈牙利语中“同一性焦点”通常所要求的穷指性截然相反。句法方面,作者批判性地回顾了假空缺的现存几种分析方法——要么视为重名词短语转换,要么视为宾语转换;与之不同的是,作者认为焦点也对句法推展有可见的影响(Eguren&Soriano,2007:XII)。利奇和肖特也认为,焦点虽然是一个音位学的问题,但它在句法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末端焦点是书面语篇中制约成分序列的原则之一(Leech&Short,2007:171-172)。诸如此类的界面研究在语言学分支学科中十分普遍,如句法—语义界面、句法—语用界面、语义—语用界面、语音—音位界面、形态—句法界面、音位—形态界面、词汇—语法界面、句法—音位界面、概念结构—句法结构界面、概念结构—空间结构界面、词汇—语义界面、语料库—话语界面,等。
界面研究的第三个学科意义是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如前面提到的认知科学,它作为源学科(parent discipline),衍生出了许多基于认知科学的新兴学科,如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文化学、认知教育学、认知文化学、认知人类学、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诗学等等;再比如叙事研究。由于叙事是人类最古老、最普遍的话语行为,它就成了“由社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多学科问题”,于是,在传统的小说、叙事文研究之外,又出现了叙事学、叙事心理学、教育叙事、女性主义叙事学、政治叙事学、历史叙事学、法律叙事学、空间叙事学等等。这就是克莱恩所描述的现象:“在20世纪的进程中,学科分化并重组成新的专业,是知识增长的主要形式,这种现象导致了大分化和大汇流”,“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构成同一对象”。(克莱恩,2005:55;62)
第四个意义是推动研究的深化。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M.石里克曾经明确指出:“任何科学问题都会把我们引向哲学,只要我们把问题追索得足够深远。当一个人在某个特殊科学中获得了知识(从而知道这个或那个现象的原因)时,当探索的头脑又进一步追问原因的原因(也就是追求可以从中推引出他所获得的知识的更一般的真理)时,他很快就达到他的特殊科学的手段已不能使他再继续前进的地步”,这时,“解释向前推进的过程最终进入的最一般的领域,就是哲学领域、认识论领域”(石里克,2005:18)。其实,除了哲学以外,其他学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把“解释向前推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句子来看看认知诗学能否帮助我们推进研究的深化:
The wind roared,and the lightning flashed,and the sky was suddenly as dark as night.
这个句子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二个小句前用了一个and。根据英语“reduce where possible”原则,它应该省去,而今没有省,有什么意义呢?文体学的解释是:这种连接可以表现语体上的突出效果,比如,强调一连串戏剧性事件的发生。
当我们运用认知诗学原理进行分析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
首先是感觉空间。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证明:被试总是将较大的物象放在比较小者更远的位置上,这是想像摹仿需要遵循的真实感觉空间的认知限制。上面这个句子中,wind似乎比lightning小,而lightning又比sky小;wind离我们较近,lightning次之,而sky离我们最远。所以,这组小句符合人们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空间感知规律,体现了空间象似性。
其次,这三个小句包含有两种对比鲜明的色彩,即白色和黑色。白色就是闪电的光芒。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表明:光——尤其是闪耀的光——是最容易形成生动性和固体性的触发器,它使画面充满了活力,有助于激活读者的想象和感知摹仿。
第三,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小句视为图画。乍一看,这三个小句构成了一幅画,或者一个场景: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天昏地暗。这种印象和感知肯定存在,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在第一个小句和第二个小句之间加入了一个and?没有这个and,上述理解绝对没问题!而现在,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and呢?英语中and有一个作用,就是标志一个语调单位(tone unit)。所以,第一个and的出现,使整个句子明显地成为了三个语调单位,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成为了三幅图片。没有这个and,我们通常把这个句子看作一幅画,现在成了三幅!
三幅画与一幅画的区别在哪里?
第一,运动的连贯性减弱了,但运动的强度却增加了;
第二,三幅画有了三个焦点,而不是一个移动的焦点,从而都得到了突出,更为清晰;
第三,由于语言的线性排列,而且三个小句依然属于一个句子,所以整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有了停顿,而停顿往往是强化的需要,比如音乐序列中的停顿。这里的停顿既是语法的(有and和逗号),又是情感的(信息含量大,感情成分多的语言单位前或后应有停顿),而且还是逻辑的停顿(因为它把一幅画分成了三幅)。
第四,一幅图片是静止的,而三幅图片则是移动的。心理学的实验证明:移动的图片(moving picture)比静止的图画更具有生动性和真实感。
以上的认知诗学分析,不仅能够说明“突出”和“生动”的文体效果,而且说明:这三个小句更具有想像的质感和真实感。
5.结语
克莱恩在描述当今时代的知识状况时说:“今天,知识描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重新考量学科之间的关系,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构成同一对象。随着新的组织聚合层次揭示出来,‘多学科’正成为对研究对象的常见描述。”(克莱恩2005:62)界面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知识背景中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对外语界的学者、教师和学生来说,各种形式的界面研究其实早已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之是“习焉不察”而已。所以,怀疑是毫无道理的,抵制也是徒劳无益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使以往不那么自觉、不那么系统的界面研究,变得更为自觉、更为系统。同时,尽可能避免生涩的、牵强的跨界研究。这样,我们的“解释向前推进的过程”就一定能够更为顺利。
[1]Brine,Geert& Jeroen Vandaele.Cognitive Poetics:Goals,Gains and Gaps[C].Berlin·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2009
[2]Eguren,Luis & Olga Fernández Soriano.Coreference,Modality,and Focus:Studies on the syntax– semantics interface[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7.
[3]Geeraerts,Dirk & Hubert Cuycken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4]Leech,Geoffrey & Mick Short.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M].London &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 Ltd.,2007.
[5]Stockwell,Peter.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M].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02.
[6]Stockwell,Peter.Texture: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7]罗曼·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M].陈燕谷,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8]M.石里克.普通认识论[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M].姜智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外国语文的其它文章
- 对近十年来国内外语界面研究的思考
- 音系学中的界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