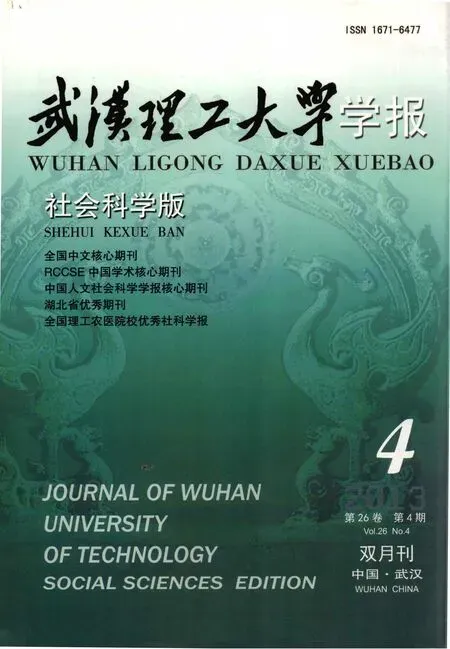“私纪录片”的纪录伦理
成维纬
(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 200092)
私纪录片以其特有的表现方式与独树一帜的影像魅力丰富着纪录片的类型,展现出独特视角下的“生活”。既有别于历史纪录片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有些纪录片展现边缘人群的另类写实,私纪录片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它抛开那些宏大的创作题材,以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方式,将镜头对准自己或家人,可以让人细细审视这看似平常却又独特的日常生活。
一、私纪录片的特点
(一)聚焦对象:自己、亲人、朋友
私纪录片同许多纪录片一样,记录的是普通人的一种生活,触发的是关于人生、关于生活的思考。它所表现的对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虽然没有什么特殊性,只是一种关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从导演的角度来看,它的“不普通”在于摄影机直接对准的是导演自身或是与其有着亲密关系的家人、朋友等,因为彼此之间密切的关系,便很容易进入他们的私人领域,展现出一般人难以看到的“私”的一面。
《治疗》是吴文光导演在其母亲去世后,在整理母亲的影像素材过程中,对一些之前没有留意的细微之处的重新再现,对一些往事的重新复活。重新面对母亲的活动影像,一个已经消失于人世的亲人突然那么栩栩如生地活动起来,说话、表情,一切宛如昨天,于是导演用这样一种形式作一次让母亲重新“活”过来的尝试。在影片中,他将镜头直接对准了自己,带领我们一同去寻找有关他母亲的记忆,就如同片中他在一片漆黑的房屋里打开的那只手电筒,电光所及之处就是他所展现给我们的私人记忆。他的独白“关于母亲的东西都是关于治疗的东西”,他学生时代的日记,关于他母亲曾经的影像画面,向我们展现他回忆的同时,也将他自己曾经隐秘起来的一切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性情的“他”。
(二)呈现内容:隐秘的个人世界
“拍电影有两种,一种是你看别人,看社会,还有一种是反过来看自己”[1]。而私纪录片就属于后者。由于私纪录片所表现的对象是自身或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的人的缘故,从而可以毫无阻力地进入私人空间,窥探那些常人无法进入的领域。因此相较于一般的纪录片,它在呈现内容上更加倾向于展现私人的生活,分享私人的感受。它将镜头对准了看似平常又普通的生活,当细腻镜头捕捉下的真实私人生活一帧帧展开时,那些有关私人生活和感受的东西便一点点化播开来。
在《治疗》中,吴文光导演用镜头带着我们进入了他的“私人空间”。日记作为一种记载个人生活和个人感受的东西,总是与个人隐私联系在一起。而透过镜头,导演将记录他20多年生活的日记本一一摆放在了桌上。他随手拿起了一本日记翻阅,读起了他学生时代所写的或与母亲有关的日记。将可能是他曾经从未与人分享的故事,现在一一都呈现了出来。而他母亲生前的影像片段,他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不敢面对她以前的活动影像,好像她活过来了一样”等,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表达方式:自我心理之写照
私纪录片作为一种十分自我的影像产物,在表达方式上遵循的是一种对于自我的心理写照。如果说拍电影如同临摹佳作要遵从于种种规定的话,那么私纪录片则像是一幅让人可以自由创作的画作。私纪录片的创作者脱离种种形式的束缚,用一种十分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让影像创作的内容都归于一种纯粹的自我内心写照。它打破了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条条框框,在一种鲜明的个人风格的影像创作上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从未有过的感觉。而这样一种自我心理写照,一部分是由于它的内容是一种“私人日记”的形式,另外很大一部分也是由私纪录片创作者所决定的。在私纪录片的创作者中不乏很多非职业的作者,如胡新宇、杨荔钠、李凝等。私纪录片作为一种非职业化创作,是对传统职业模式和专业标准的反叛和消解[2]。因此,私纪录片创作者以一种不受束缚和充满自我的方式,让私纪录片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些私纪录片创作者让影视创作的领域扩展得更为广阔,那些个人或家庭中的私密空间被历史地展现在了镜头前。而那些镜头内的空间,则充满着他们自己的个性。每一个创作者的私影像都是不可复制的,都有其独特的地方。
在私纪录片《治疗》中,母亲是影像创作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导演吴文光将整个影片结构分成了母亲——回忆——现在时——治疗与自我治疗等几个部分,导演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来表现他在治疗与自我治疗中的状态。起初只是在空旷的房间内缓慢行走,进而变为承受着镜中自己的重量,最后变为爬在地上,一口一口用力吞噬着长条的餐巾纸。在最后吞噬餐巾纸的过程中,吴文光表情十分痛苦、狰狞,整个镜头长达三分钟。这让影片充满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又带着很强的实验特征。而导演也毫不忌讳地将创作的过程展露于镜头前,比如在创作时的初衷,在剪辑影片时的状态等,这些在一般的纪录片中都是看不到的,自我反射手法的运用让私纪录片更加充满了个人性的特点。
二、私纪录片中出现的伦理问题
当我们拿起摄影机对准别人的生活时,他人的隐私像是黑夜中被我们拿出的一只手电筒给照亮了的去处。镜头本身是有侵略性的,能够拍摄到十分个人化的生活[3]。不同于在其他题材的纪录片中,导演意识的介入可能很难去改变被摄对象的行为,而在私纪录片中,由于导演与被摄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较容易地去“控制”被摄对象的行为,能够进入被摄者的隐私空间。也正是由于拍摄者与被摄者有了这样一层特殊的关系,在拍摄私纪录时如何对待被拍摄者,怎样去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其中的纪录伦理问题,便变得尤为重要。
(一)拍摄时的沟通
与很多纪录片都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拍摄不同,大部分的私纪录片都是以一种参与的方式从知情者角度拍摄而成的,因而拍摄者的“身份”在私纪录片中变得更为多重。拍摄者既是影片的创作者,又是影片的“演员”。由于拍摄的是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的家人,对于他们的很多事情都有着比较深的了解,稍不注意就会踏入危险的“雷区”,因此在拍摄时与被拍摄者间的沟通便显得特别重要。
日本导演原一男的《绝对隐私性爱:恋歌1974》是一部不能不提及的私纪录片,影片拍摄的是他的前情人武田美由纪的私人生活。武田美由纪允许原一男和他的镜头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通道进入她的生活,完全赤裸裸地剥开自己,其中有一场生孩子的片段让人极为震撼。原一男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是武田跟我说,我想自己生孩子,你一定要拍。”[4]导演按照被拍摄者的要求将生孩子的场面真实地记录了下来,采用了虚焦的处理,虽然在视觉上稍微让人能接受一点,但还是极为震撼,在当时片子中生孩子的场景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轰动。当被问及导演的道德底线在哪儿时,原一男回答称:“在那种地方人的道德底线会飞掉的。所谓的‘道德’是为了压抑人们凶暴的本性和欲望的一种制度、形式。道德是一种规则,用来压抑人过多能量,让社会保持安定,它是一种制度。”[4]在这部影片中,拍摄极为隐私的画面,导演都是经过被摄对象同意的,因而这样最大化地呈现私密生活的同时,也避免了因为过于暴露被摄对象的隐私而产生的伤害。
但对于大多数拍摄自己家人和朋友的私纪录片拍摄者来说,有时稍稍没处理好拍摄者与被拍摄者间的关系,就会对被拍摄对象造成伤害。导演胡新宇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曾拍摄过几部有关他家庭的私纪录片,如《姐姐》、《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等。将家庭的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毕竟是很冒险的事情,或多或少地会造成家丑外扬。有一段时间内,因为这些影片而与家人闹过不愉快,甚至他姐姐说要是再把这些影片传播出去,就要与他断绝关系,最终胡新宇导演还是选择了将这些影片独自收藏。同样是拍摄自己家庭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的导演王芬,用摄影机记录了父母不幸婚姻对家人的伤害,尽管透过一些电影节和电影展映让少数人看到,但后来她表示“我不想再扩大影响了,我不希望这些事情会打扰到我父母的生活”[5]。
在拍摄私纪录片时,呈现最大化的真实与尽可能保护被拍摄对象本身就是一对难以平衡的矛盾。很多导演为了追求最大化的真实而不断地挖掘被拍摄者的隐私,这其中,如何去平衡导演想要最大化呈现被拍摄者的生活与被拍摄者不愿过多暴露隐私的矛盾,拍摄时的沟通便变得尤为重要。导演不能以艺术创作为借口,毫无道德底线地去挖掘被拍摄者的隐私。应该取得一个伦理关系的平衡,以尽可能保证被拍摄者不受伤害为前提进行拍摄,对于被拍摄者不愿暴露的隐私应该给予尊重。不能毫无道德底线地一味追求拍摄的效果而忽视被拍摄者的感受。
(二)剪辑时的素材取舍
如莉莉·瑞弗林在《给我一个吻》中所说:“个人回忆总是困难的。毕竟,要实实在在地去揭示一个人的生活,或多或少总会给他们造成伤害。”[6]235因此相较于一般的纪录片,私纪录片在剪辑上对素材的取舍更是要衡量再三。面对影片《给我一个吻》会把关于拍摄者的家庭和她父母的隐私暴露给公众的问题,为了避免影片给她的父母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导演选择了在她父母去世之后才着手处理影片,这样也最大化地避免了影片带给她父母的伤害。
虽然导演拍摄私纪录片时可以毫无阻力地进入亲人的私密空间,但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区域。有时若不加以合适地控制,甚至会恶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因此在拍摄与剪辑时必须十分注意。在李凝导演的《胶带》中,原先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完整版,一个删节版。在完整版中,他们在表演行为艺术《未完工2号》中有努努比较暴露的镜头。出于对被拍摄对象的尊重,导演剪辑完成后征询了努努的意见,努努婉言表达她不希望出现暴露,于是现今《胶带》的版本就只剩一个删节版了。也许导演保留了那个片段影片效果会更好,但必然会对被拍摄者带来极大的困扰与伤害。当拍摄者手握被拍摄者隐私的时候,平衡其中的伦理关系应放在创作之上。被拍摄者虽然允许你进入他的私人空间,但并不意味着拍摄便毫无底线,出于尊重被拍摄者考虑,合理选取素材是平衡这其中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试想,若导演一味地追求影片的艺术效果而违背被拍摄者的意愿,那一定会深深伤害到被拍摄者。
因此,要处理好纪录伦理问题不仅仅是指需要处理好在拍摄时的沟通问题,对于一些涉及十分隐私的事情在剪辑时也需要再三斟酌。虽然有关伦理问题无法去划定一条清晰的界限,但是每一个创作者内心都应该有一条心灵的准则,那就是尽可能避免对被拍摄者的生活乃至心灵造成伤害。私纪录片《母亲的遗产》的导演明达·马丁就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在剪辑《母亲的遗产》时十分注意素材的取舍,“在纪录片中,更像是生活,只会有开放式的结局。影片的素材会告诉你影片将在哪里结束。我尽可能往深处走,往远处走。我明白我应该尽可能地多去问。有时答案是不能放在影片中去的,因为你不能伤害别人。”[6]250
三、私纪录片存在的合理性
尽管私纪录片有时或多或少会对主人公带来伤害,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包含的道德合理性的地方。私纪录片对于制作者来说,它的作用可以划分成三个层面:宣泄、治疗及救赎。
(一)宣泄
宣泄是私纪录片作用中一个比较浅显的层面,主要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情绪释放。对于创作者来说,私纪录片就像是一个倾诉的窗口。创作者通过在自己的私影像的创作过程中,让自己心中积累已久的或郁闷或烦心或难以与人诉说的经历透过镜头抒发出来,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抚。比如在私纪录片《乡愁》中,导演舒浩仑拍摄的初衷就是为了在自己小时候住的“大中里”被拆迁前,写下心中的乡愁。而对于“大中里”的拆迁是要被改造成类似于“新天地”这样的商业区,导演也用影片作了一次心理的宣泄。当他站在附近的高级酒店俯拍“大中里”时,他感叹到对于他们世代居住的“大中里”,“只是老外眼中的风景,一张被消费的明信片”,对于这样的改造他也十分不满,“难道人们真的会去顶礼膜拜这些摩天大楼吗?我怀疑”。但是对于拆迁这样不可改变之事,导演也只能用镜头去最后记录自己儿时的住所,用私人的影像记录去做一次对于“大中里”的回忆之旅以及表达对于“大中里”要拆迁改造的不满,以此来完成一次心中的宣泄。
(二)治疗
治疗是私纪录片作用中一个稍高一点的层面,有一种心理的治愈性在里面。在私纪录片中,摄影机如手术刀般划开私人隐秘的现实和心理空间,进行一次心理隐疾的剖析和治疗。对于创作者来说,拍摄私纪录片的目的或初衷就是在拍摄过程对自己进行一次反观和整理,在清理心中的淤泥时进行一次情感的洗涤,实现一种自我心理创伤的治疗。
面对母亲的离去,吴文光导演便是通过私纪录片《治疗》来完成一次自我的治愈。就如吴文光导演在《治疗》的影片中所说的那样:“在自我整理过程中,内心的变化,以一种治疗的方式自我成长,自我教育。”而谈及创作初衷,他在博客中也写到:“我母亲去世两年多这期间,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总是缠绕我,内心似乎被催促着该做个什么动作对某种情绪作个了断。我想做个有关我母亲的影像,这是初衷。做这个影像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这些年我尤感需要自我治疗。有关母亲和自己的成长记忆,手术刀一样切开藏于自我内心的‘肿瘤’。”[7]他在《治疗》的片尾中说:“人们通过各种治疗方式来获得内心的平衡。”在这部私纪录片的创作过程里,导演吴文光拿起影像的手术刀划开心中的病处,进行了一次自我治疗,以此获得内心的平衡。私纪录片《治疗》对于他而言已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所能承载的内容,更是一种治愈心中病痛的一味药。在他母亲去世后,“不敢面对她以前的活动影像,好像活过来一样”,通过《治疗》让他能够重新去面对母亲离开的这件事,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不仅是记忆和纪念,也是一次在和母亲重逢并再次厮守的过程中完成的对于自己心灵的一次释放,进行的一种自我治疗。
(三)救赎
救赎是私纪录片作用中最深和最高的一个层面。拍摄私纪录片对于创作者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自我宣泄的窗口,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而更是在拍摄过程中的一种关乎自己心灵的拯救与救赎行为。
如果说宣泄和治疗是私纪录片对于创作者的一个窗口的话,那么救赎便是私纪录片对于创作者的一个心灵出口。在李凝导演的私纪录片《胶带》中,他把自己的肉身整个地全部抛出,扔到这个巨大的现实漩涡中,一个黑洞中,一个看不到光亮的漫长隧道里,一路狂奔,徒劳绝望挣扎,没完没了,几近疯狂[8]。无数次与家人的摩擦,同学生一起预谋的某次“演出”计划,赤身在推土机前的行为表演,突如其来的警察等,在这部影片中甚至暴露的是一些极端私人化的东西。有的时候,你看到他躺在床上自慰,有时镜头会对准手机上某个女性发来的短信,有时候,甚至赤身跳入冰河中游泳,你会觉得这太私人了,但就是这样极度的私人居然最后抵达了公共的层面。用李凝自己的话说:“一个极端的个人性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极端的公共性。”[9]保证对自己的一个诚实的态度,他彻彻底底地将自己抛入了片子中,通过自省或自嘲的方式反抗冰冷的社会机器。在这部影片中,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用一种最为真诚和诚实的态度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剖析和救赎。这部私纪录片对于他的意义,用导演的话来说就是,“我想通过这部影片来实现一种对于自我的救赎,有些人需要明白地活着,而有些人则不需要”①。通过这部影片,他对于自己的前半生作了一次反思,在片尾最终他还是走到了社会体制内,拿着一张简历去应聘,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虽然影片中有些“家丑”的呈现,比如与妻子,与母亲的争吵,但导演也试图用影片本身来做平衡和救赎。“在影片中有一段我们一家人在雨中游园,一家人很美很和谐,算是我对妻子形象的补正吧”①。
四、对私纪录片中伦理问题的反思
(一)要正确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
不论你拍摄的对象是自己或是亲人,如何去对待被拍摄对象的隐私展露问题,创作者应该仔细去斟酌和平衡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矛盾。新浪潮的老祖母阿涅斯·瓦尔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范本,在她的私纪录片《阿涅斯的海滩》中,对于某些涉及比较隐私的部分,采用的则是比较幽默的表现手法。如重现当时与丈夫在海边亲密的场景时,则是演员的“搬演”加上幽默的台词来展现,让人不禁开怀一笑。因而私纪录片导演在需要展现被拍摄者十分隐私生活的部分时,根据需要有时也可以采用“搬演”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将想要展现的内容呈现了出来,也让被拍摄者接受起来毫无压力,减少了对被拍摄对象的伤害。
(二)要尽可能减少对私纪录片主体的伤害
其实纵观一下世界和中国的私纪录片,在表现隐私的部分其差别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对于传播和发行来说,你可以比较容易地买到国外的一些私纪录片,但中国的私纪录片你几乎不可能在网络上看到或是在市面上买到。当然,这一状况既与国外私纪录片发展的时间比较早或拍摄对象已故,发行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有关,也同两者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中国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比较注重“私”与“公”的生活空间界限,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将个人的私人生活和隐私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内,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十分羞耻的事情。
因此,私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尊重被摄对象的这种心理考量,在传播上尽可能减少对于他们的伤害。我们认为,创作者为宣泄、治疗或救赎的目的来制作影片,也应让影片对于被拍摄者有一种治愈性。若影片创作者在前期无法进行一种治愈性的弥补,那么在后期制作乃至传播上应该有所考虑。而这种治愈性就在于,以一种最大化减少对被拍摄对象伤害的方式进行传播。可能现在比较有效的办法便是小范围的交流传播,比如参加国内外的影展或是相关学术性质的小型放映。这样几乎不会被认识私纪录片主体的人看到,减少闲言闲语对于他们的伤害。或许在拍摄过程中被拍摄者受到过“伤害”,但及时地在后期处理和传播过程中加以保护,则有可能将这样的伤害转化为可治愈性的伤害。毕竟对于私纪录片的创作者来说,私纪录片让自己和家人都愉悦才是最好的结果,没有人希望看到私纪录片是挑起家庭矛盾的源头。
五、结 语
私纪录片正是因为拍摄的内容极度的私人化及个人化,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触及隐私,从而有着与道德相矛盾的地方,但也有其道德的合理性。虽然一方面可能会对他人造成或大或小的伤害,但另一方面对于制作者来说也是一种宣泄,一种治疗和一种救赎。正如李凝导演所言:“有时候纪录片作者做片子其实是一种献祭,如同诗人是人类灵魂的祭品是一样的,那么他的家人也是被伤害和牺牲的。”①也许关于隐私我们可以给出诸如“与自己有关而不愿让别人知道的事情”的解释,甚至隐私权的内容在法律上也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有关道德伦理的问题却无法像隐私一样有着明确的法律界限,更多时候需要的是纪录片创作者的自律。正如王光建导演所说的那样,“纪录片导演为了片子成功,有时候很残忍,常常把人家的伤口解开,再撒一把盐。别人的伤疤、隐私,观众大多非常爱看,但自己却会受到良心的谴责”[9]。制作私纪录片就像是站在天平的两端,唯有自己平衡好,把握好,才能让私纪录片的创作达成自己的初衷和愿望。
注释:
① 文中所引用的均出自本文作者与导演李凝之间的通信。
[1]中国新生代导演:戛纳我们来了[N].时代周报,2009-05-28(C1).
[2]樊启鹏.中国私纪录片带来的变化与挑战[J].电影艺术,2007(6):136-139.
[3]陶 涛.电视纪录片创作[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97.
[4]吴龙狄.原一男:“我”的纪录片[DB/OL].(2010-07-06)[2013-01-18]http:∥www.ionly.com.cn/nbo/news/info3/ 120100706/ 1130515.html.
[5]范吉慧.40年吵闹让他们如此苍老:我拍下父母不幸婚姻[N].青年时讯,2001-02-22(07).
[6]罗森塔尔.纪录片编导与制作[M].张文俊,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7]吴文光.笔记:一个人的纪录片:(16)[DB/OL].(2012-03-17)[2013-01-18]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11srh.html.
[8]吴文光.笔记:一个人的纪录片:(10)[DB/OL].(2011-12-02)[2013-01-18]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0zgkw.html.
[9]张立涛.《胶带》中的非反抗与超真实[EB/OL].(2010-10-24)[2013-01-18]http:∥www.mosh.cn/events/ 161754.
[10]王慰慈.记录与探索:与大陆纪录片工作者的世纪对话[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