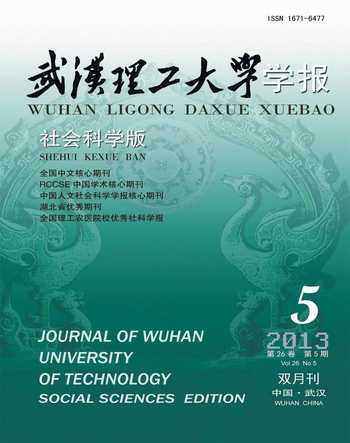自然化认识论的进展——从蒯因到戈德曼
喻郭飞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自从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问世以来,认识论就一直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领域之一。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我们究竟能够知道些什么?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正确利用感官和理性?真正的知识和一般性信念或意见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这些都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而在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葛梯尔问题”的提出,对于传统认识论将知识理解成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JTB)这一做法的批判引发了大家的广泛讨论,许多人开始质疑笛卡尔以来的基础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知识的绝对确定性,他们认为这实际上超出了某个具体的认知者所能满足的要求。很多哲学家试图修改并强化JTB框架来回应怀疑主义对于知识确定性的挑战。而在这场争论中,以蒯因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提出了所谓自然化的认识论纲领。他们认为传统认识论对于知识绝对确定性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人们需要在对概念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之外,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方式从客观角度来研究人的认知过程。通过自然科学而非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的认知活动,从而将规范性的认识论转变为描述性的认识论,使之成为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章节。赞成的一方认为,蒯因的自然化纲领对于现代认识论在研究主题和方法论上寻求突破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而反对者认为,描述性的认知心理学无法为认识论中十分重要的规范性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主义方法论的普遍有效性也还值得推敲。但是毋庸置疑的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方认识论研究中围绕自然化认识论所展开的讨论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试图考察自然化认识论的基本纲领,某些代表人物的具体理论,以及这一纲领本身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一、认识论的自然主义纲领
自从蒯因在1969年发表的文章《自然化认识论》中提出认识论的自然化口号以来,哲学家们围绕自然化认识论纲领的内涵是什么,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将自然化认识论予以推进,以及自然化纲领是否意味着对规范性的削弱乃至取消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以金在权、邦久为代表的一派哲学家对于自然化的纲领提出质疑,认为以自然科学的描述来阐明人的认识机制将会取消传统认识论所关注的辩护,知识的(绝对)确定性等主题,从而使认识论蜕变为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才100多年的现代心理学,其方法论的合理性并非足够牢固。另一方面,蒯因、戈德曼等自然化认识论的支持者则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的视角对正常状态下的认知心理活动,命题态度的形成,命题内容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作出一种自然主义的说明。另外还有以Hilary Kornblith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他们既肯定自然化的纲领对于开拓认识论的研究领域与方法论创新的积极意义,又主张保留传统认识论对概念的逻辑和语言学分析,那么作为这些争论之核心的自然主义纲领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了解传统认识论的人而言,如果我们要谈论什么叫做认识论的自然化,那么首先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是:第一,认识论是否应该被看作是隶属于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其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否是从事认识论研究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再次,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是否应该被认知科学的基本问题所取代?
正如Hilary Kornblith所提到的那样,“自然主义既不是源自于蒯因,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方法论也不是从他开始的”[1]39。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1969年发表的《自然化认识论》一文却对当代认识论研究的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蒯因看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葛梯尔问题”为代表的怀疑论对于传统知识定义的有效性的挑战成为任何研究者必须重视的问题。尽管哲学家们设计出诸如“non-defeater”理论、可靠论、因果论等多种方式来对“JTB”定义予以修补,但是从真信念到具有完全确定性的知识之间所存在的鸿沟却一直难以彻底消除。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认识论一直将追寻知识的绝对确定性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希望将数学、逻辑知识作为样本,按照一种基础主义的模式来建构整个知识大厦,也就是从所谓“自明的”真信念开始,通过可靠的逻辑推理,最终获得具有同样确定性的新信念,并且这些信念的内容与外部世界之间具有一种相符合的关系。这种意图在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像卡尔纳普等人希望借助科学观察,从我们的感觉经验出发,经过恰当的逻辑构造得出科学知识。但是蒯因认为,这种对于逻辑在建构经验知识过程中作用的夸大以及对于认识活动中认知主体所处状况的理想化的处理,完全不符合我们实际的认知过程。首先,科学知识的形成绝不仅仅等同于经验观察加上相应的逻辑推理,从观察到理论的建构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同时与某一组观察相一致的理论可能有多个备选项,这一点在他论证“翻译的不确定性”时就已经得到阐明。此外,在我们实际的认知过程中,由于认知主体会受到其背景知识、某个时刻的心理状态和具体外部环境的综合作用,特别是认知主体的心理与大脑活动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因而他主张将认识论作为现代心理学,特别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章节,从研究人的认知行为过程中具体发生的心理与大脑活动开始,以严格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描述人类知识形成的客观机制,以及“经验证据是如何和理论相关联,我们关于自然的理论是如何超越于手头的证据”[2]。对于蒯因而言,认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我们形成可靠的真信念并能指导行动的实际认知过程,因而它必须被纳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之中。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否和传统认识论毫无共性可言呢?在《指称之根》一书的开篇,当蒯因谈及(自然化)认识论问题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经验心理学的问题,人们既可以在某个时候在实验室中研究它,也可以在某种思辨的层次上探讨它,它的哲学意义是显然的……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真理的一切就是要探明证据关系,即支持理论的观察相对于理论的关系。”[3]3-4因而,根据蒯因的理解,自然化认识论一方面需要说明我们的感觉证据是如何支持科学理论的;另外还要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科学理论从感觉证据产生的实际过程。基于以上看法,蒯因的自然化纲领并不是完全排除哲学方法对于认识论研究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感觉证据与科学理论关系的说明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证据与理论的逻辑关联。而对于自然化认识论所涉及的第二方面的问题,蒯因认为人类掌握科学理论的过程即对于相关的科学术语、假说等诸多内容进行语言学习过程,因而发生学的方法就是最为重要的方法。其中既包含“对于从感觉输入到观察语句的学习机制的详尽的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解释”[3]6,也包含“对于从观察语句到理论语言习得的许多不同的类比步骤的详细的说明”[3]6。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带有浓重的基础主义色彩,只不过他所理解的作为基础的部分是感觉经验,是由科学的语言提供的观察报告。
费尔德曼将蒯因之后的哲学家们所提出的认识论的自然化纲领分为三种类型:“替代论题”、“合作论题”、“实质性的自然主义论题”。蒯因的“替代论题”在认识论研究者中得到的支持并不多,大家更多讨论的是“合作论题”。Philip Kitcher在1992年一篇名为“自然主义的回归”的文章中提到,如果我们在20世纪对于认识论研究中科学成分的漠视是源自哲学领域一种反心理主义的普遍倾向的话,并且要是我们依旧承认认识论是在研究人在形成信念,获取知识过程中的心理机制,那么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相应的成果就必将被考虑进来。“合作论题”并不反对传统认识论的概念分析方式,只不过它认为需要实际确定的是那些(借助概念分析所得到的)原则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真理,而经验科学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
蒯因本人并没有考察自然化认识论的具体实施方案,他所谓的“将认识论研究纳入到心理学的一个章节”实际上就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来具体阐释人的认知活动,也就是利用“sense data”、“visual image”等关于生理(物理)状态的术语来说明我们对于某个对象形成概念,作出判断的过程。但是后来的自然化认识论支持者没有完全按照“替代论题”来进行,以戈德曼为例,他采取的是“合作论题”。在《认识论与认知》一书中,他在可靠论的框架下对重要的认识论概念进行了分析,并引述关于人类认知活动中具体机制的科学说明来支持他的理论。戈德曼既希望保持传统认识论的概念分析方法,同时试图借助认知科学关于我们认识机制的经验说明给认识论提供科学根基。
二、戈德曼的自然化认识论与社会认识论
如果当代认识论主要是对于经验知识赖以产生的根基与机制进行研究,那么很显然,自然化认识论就要排除形而上学的方法以及对于先天因素的分析。我们的知识必须植根于经验基础之上,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经验证据和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逻辑性的,也涉及到心理学和语言学方面。根据米建国[1]109的理解,蒯因的自然化纲领主要反对的是传统认识论中的还原论、先天知识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他强调对于经验知识的发生学描述并不能取代对于知识的辩护。由于近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从认识论出发来为自然科学知识进行辩护和证明的梦想早已被休谟式的怀疑论一扫而光”[1]109,因而蒯因所持的自然化认识论旨在排除形而上学为知识奠基的目标,并且主张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即将认识论研究建立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上,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为知识的产生作出说明。而对于先天知识,蒯因表示坚决拒斥,首先,他反对所谓的先天知识的不可修正性,而是认为经验知识(甚至包括逻辑与数学知识)有可能被修改;其次,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蒯因一方面批评传统经验论对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缺乏充足的理由,另一方面,逻辑经验主义所持还原论的立场也很难成立;再次,在考虑感觉经验同科学假说或者理论的验证关系的时候,感觉经验在可接受性方面更加具有优先性。
与蒯因这种较为激进的“替代论题”不同的是,美国当代的哲学家戈德曼依据可靠论框架提出了认识论自然化的方案。他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基于每个认知者较为有限的经验观察和感觉证据,我们是如何形成关于外部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可靠知识乃至科学理论的。
根据弗尔德曼在“Goldman on epistem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一文里的理解,戈德曼所谓“重构认识论”的计划是通过引入一些被传统认识论所排除的议题,而正是这些议题需要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帮助。对于认识论的自然化,费尔德曼认为蒯因的“替代论题”的核心是:将认识论中的哲学分析完全排除从而将认识论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传统认识论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是对于基本的认识论概念的逻辑和语言学分析,其二是对于怀疑主义关于知识确定性挑战的回应。而蒯因的“替代论题”则完全取消了传统认识论所具有的这两个特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戈德曼1986年的《认识论与认知》一书中,我们却仍旧可以看到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弗里德曼认为,存在另外一种更加温和的认识论自然化的态度,即“合作论题”。“除非我们能够首先确定人们是如何形成信念的,我们才能决定应该以何种方式获取信念才是恰当的”[4]。“合作论题”的支持者们认为自然科学的经验研究成果能够为诸多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帮助,但与此不同的是,戈德曼并不认为所有的认识论问题都必须寻求科学的帮助,至少在《认识论与认知》一书的前半部分,他主要是围绕可靠论的基本框架对于辩护规则进行哲学分析,戈德曼给出了所谓的J规则:
S(认知者)在时刻t相信命题P是有根据的当且仅当a,S在时刻t相信命题P符合某种正确的J规则系统;b,这种符合关系并不和S在时刻t的认知状态相冲突[5]63。
而所谓的J规则是指:一个J规则系统R是正确的,当且仅当R允许存在一些基本的心理学过程,这些过程的例示能够产生满足特定阀值(高于0.5)的真信念的比例[5]106。
对于戈德曼而言,一个信念得到辩护就意味着它能够获得某一可靠的规则系统的支持。而费尔德曼认为,戈德曼在《认识论与认知》前半部分的工作表明他对于相关认识论概念的分析既没有获得经验科学的支持也没有被反对,因而戈德曼的自然化纲领不能归到“合作论题”之中。
对于“先天”(A priori)这一概念,戈德曼也采取了与蒯因极为不同的态度。按照他在A priori warrant and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这篇文章里的解释,他将先验方法看作是辩护类型而不是真理类型,其所谓的先验辩护是在某种具体的心理机制中实现的,只不过它在内容上是纯粹的概念分析而不会涉及到任何经验证据。此外,在本文中,戈德曼认为认识论的自然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科学的自然主义,即认识论作为自然科学的分支,认识论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这一种观点是蒯因所支持的。但是戈德曼认为“不存在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任何经验科学的分支可以胜任确定知识或者辩护的证据、条件或标准的任务”[5]25。第二种自然化的方案是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即将所有的辩护都看作是经验性的,认识论就是要弄清这些辩护方法的细节所在。但戈德曼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需要经验性的辩护,他举了数学知识为例以表明存在先验方法的辩护。因而在他看来,第三种所谓的“温和的自然主义”是较为合适的做法,即所有的认识论辩护都是产生信念的心理过程的某种功能,但是在内容上并非所有的辩护都是涉及经验的。戈德曼所理解的“重构之后的”认识论研究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对于这些心理过程进行说明。
戈德曼在《认识论与认知》的导言部分就明确指出,他所理解的新的认识论与旧的认识论的关联体现在“第一是在认知科学方面,第二是对于与知识和信念形成相关的人际和文化过程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方面”[5]7。在《认识论与认知》的前半部分,戈德曼对于认识论的核心概念诸如知识的趋真性、辩护、认知过程的可靠性以及得到辩护的信念内容与实在的关系进行了哲学分析,并且在可靠论的框架下给出了相应的说明。在他看来,传统的认识论研究主要采取的是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他用“primary epistemics”来指称这一方面的内容,即将认知者看作是单个处在理想认知状态下的个体,而认识论就是要对于这种状态下的认知者从形成真信念到对其进行知识辩护所涉及的主客观因素进行研究。但是在戈德曼看来,人们实际的认识过程除了受到认知者自身内部因素(感知能力、推理能力等)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相关的背景知识、文化环境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即使对于信念的真假和认知过程的可靠性评价而言,也不完全是由单个认知主体所决定的。因此除了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于个体的认知行为进行研究,并且弄清由感觉经验到理论知识的可靠形成机制之外,我们还有必要对于不同的认知主体之间关于“真”的标准的形成,对于信念的评价等内容所涉及的社会维度进行研究。这一看法在《认识论与认知》的后半部分中得到具体体现,在引述了大量认知科学对于感知、记忆、推理、判断等等与信念形成机制相关的解释之后,戈德曼将它们看作是可靠论的辩护策略的经验证据。
而他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领域中的知识》一书则可以看作是《认识论与认知》的姊妹篇,他在此书中具体发展了他的社会认识论理论,与20世纪早期多数的认识论研究路径不同,他将认识论看作一项“多学科交叉的事业”。在他看来,认识论研究可以划分为个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两个领域。以往的认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个体作为单个的认知者如何对自己所形成的信念通过找寻证据,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如自明性、与其他真信念的一致性、与事实相符合等)来进行评价,以决定是否应该将其纳入到知识的范围之内。戈德曼认为,除此之外,知识的形成与评价过程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它借助语言和社会交往来传播”[6]1。社会制度架构对于“真”之标准与合理性标准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他将社会认识论理解成为一门关于最利于形成知识的实践与制度研究的规范性学科。他在《社会领域中的知识》一书的前言中提到[6]1,社会认识论是对于传统以单个认知者为中心的辩护认识论的扩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将形形色色的以科学、文化的社会维度为相对主义进行鼓吹的做法与之混为一谈。正如个体认识论需要借助认知科学为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社会认识论也必须借助社会科学对于交往方式、信息传递等制度方面的研究来解释真理的传播与“真”之标准形成的客观过程。因此他首先考察了“真理”概念在社会维度的意义及其建构的过程,并且具体考察了举证、论辩、信息传递、言论控制等社会机制对于人们真理观念的形成和辩护过程的影响,最后他以科学、法律与民主政治为样本具体分析了真理概念在这些相关领域的建构过程与方式。
戈德曼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认识论主要关注信念的辩护问题,特别是从一个信念到另一个信念之间逻辑推理的合法性占据了认识论的核心地位。其实心理学方面的考虑很早就渗入到认识论之中,它对于具体认知者从感觉经验到信息的处理、分析、评估到最后形成信念的动态过程的关注,使得描述性的心理学对于认知机制的把握成为可能。只是戈德曼认为传统认识论中对于知识作为真信念的辩护仍旧具有规范性的意义,他反对将传统认识论中的概念分析与心理学、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完全对立起来。
三、结 语
以上对于蒯因到戈德曼的自然化认识论之进展的考察使我们看到,一方面,认识论的自然化扩展了传统认识论研究的主题,并且通过引入新的心理学、认知科学的实证方法,使得认识论研究更具科学性与客观性;另一方面,透过对于自然化纲领的一些批评,传统认识论所追求的规范性要求仍旧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并且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之外,我们对于“真理”概念的理解与建构还必须考虑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正如戈德曼后期社会认识论研究所展现的那样,在自然化的纲领之外,我们还应从社会维度进一步深化对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
[1]Chienkuo Michael Mi,Ruey-lin Chen.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M].Amsterdam:Rodopi B.V.,2007.
[2]M.Cahn,Steven.Philosophy for the 21th century,a comprehensive reade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26.
[3]W.V.O Quine.The roots of reference[M].La Salle:Open Court,1973.
[4]Richard Feldman.Goldman on Epistem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J].Philosophia,1989,19(2-3):197-207.
[5]Alvin I.Goldman.Epistemology and Cogn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6]Alvin I.Goldman.Knowledge in a social world[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