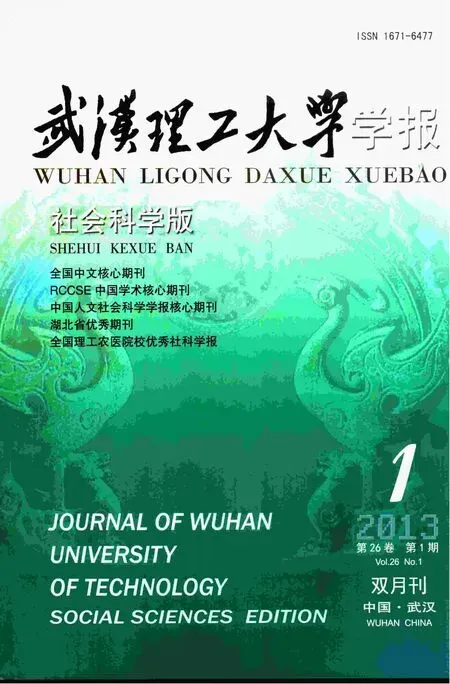米兰·昆德拉与卡尔维诺小说观念异同论
黄世权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530001)
米兰·昆德拉与卡尔维诺是当代世界上最富独创性的小说家,他们以其丰富的创作维持了西方小说在20世纪后期高质量的发展,同时他们还引导了小说的叙事方式和结构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更难能可贵的是,与前代大师们相比,他们还展示了许多小说大家所不具备的理论反思能力,凭借其独到的创作经验和深入的理论探索,面向未来进行思考,引领了小说在21世纪的发展。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①就是矗立在他们丰富作品中的路标。这两部出自天才小说家之手的文学反思之作,自然不同凡响,具有一般理论家所不具备的直觉性和生动性。由于建立在小说家对当代社会现状和文学现状的敏锐观察和反思的基础之上,这两部著作篇幅不大,不无轻盈感的经验之谈,不仅解释了各自创作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也揭示了当代小说固有的困境和出路。从总体趋势上,其显示了小说创作与观念在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移路途中的一些重要标志。
一、轻盈、复调、百科全书
卡尔维诺和昆德拉最主要的相同观点首先是:轻盈、复调、百科全书小说。这几个概念成为他们对现代小说的集中评价,更显示了他们对未来小说发展模式的向往。如果说“复调”和“百科全书”是对现代主义那些代表作品的准备评价,那么“轻盈”则是两人对各自小说风格的宣言,也是他们对后现代小说发展的明确指示。“轻盈”在卡尔维诺的《文学备忘录》中第一个作为范畴提出来,显示了卡尔维诺对这个概念的重视。经过卡尔维诺的推广,“轻盈”几乎成为当今后现代小说的纲领和宣言,引导着当今小说或其它艺术的发展走向,也成为理解现代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甚至整个当代艺术的关键术语。从小说发展的内在规律上看,“轻盈”显示了现代小说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沉重甚至沉闷风格的摆脱:把小说从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负中解放出来,恢复小说自由想象和恣意游戏的本性。其实昆德拉、卡尔维诺等人的示范性创作所带来的使人解放的影响,成功实现了当代小说创作由重到轻的战略转移。
卡尔维诺对轻盈的喜爱是建立在对文学深入的理解之上的。他回忆自己刚开始创作时满脑子也是现实主义的想法,并试图将外部现实与内心的幻想结合起来,但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于是他开始放弃现实社会的重量,转而用轻妙的手法去扑捉内心闪烁的秘密和奇妙的幻想。他一开始就界定了他对轻的理解:“我的工作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有时尽力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首先是减轻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1]2
卡尔维诺当然并不是简单地沉迷于轻,实际上他一开头就表达了一个辩证的思想:“我支持轻,并不是说我忽视重。”[1]2因此毫不奇怪,他区分出两种轻:庄重的轻与轻佻的轻。他注意到欧洲文化中轻的普遍存在和意义,从古希腊神话,奥维德的《变形记》,卢克莱修的哲学,到现代科学如电脑软件,并对意大利的古典诗人卡瓦尔坎蒂和但丁的作者的轻盈意象作为精彩分析,最后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得到启发。他总结了文学中轻的三个含义:一是减轻词语的分量,就是使意义附着在没有重量的词语上时,变得像词语那样轻微;二是叙述这样一种思维或心理过程,其中包含着细微的不可感知的因素,或者其中的描写高度抽象;三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轻的视觉形象[2]17-18。
卡尔维诺的“轻”兼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意义,减轻词语的分量说到底是减轻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从而使意义也跟着轻盈。这里透露出来的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看得出卡尔维诺对如索绪尔语言学以及解构主义等的语言观念是很熟悉的。叙述中的高度抽象,以及突出轻的视觉形象,则更侧重于艺术形式的轻盈化。这里表露了卡尔维诺的文学本质观,稍后他有明白的表述:“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2]29由于重视小说对现实重负的摆脱,对轻松心境的寻求,卡尔维诺异常重视幻想的价值,他对民间文学如意大利童话的喜好,就是看中其中的幻想成分。在第四讲里他充满热情地强调幻想的作用:“幻想是一部电子计算机,它储存了各种可能的组合,能够选出最恰当的组合,或者选出最有意思的、最令人高兴、最令人快乐的组合。”[2]89他认为艺术家的幻想是个潜力极大的世界,任何作品都不能把它全部体现出来,他甚至设想要进行一种幻想教育。这种思想当然是与“轻”一致的,就是要改变传统认知范式和文化惯例分配给文学的认识功能,尤其要摆脱现实主义传统对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过度强调,恢复文学固有的轻盈和幻想的本色,从而引领读者进入幻想的美妙世界,体味自由想象的魅力。这种反拨是对文学的返本归元的思考,是对19世纪欧洲文学发展的一种纠偏。对文学在现代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反思中对文学的幻想本色的维护和发扬,是卡尔维诺对现代文学的突出推进。
昆德拉对于轻的钟爱与卡尔维诺是一致的。不过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述。他认为现代世界是高度复杂的,人类的生存境遇也是复杂的,因此小说应该把简练视为艺术的关键,这就要求坚定地直达事物的核心。这种简练手法极大地减轻了结构的重量。这就是昆德拉对轻的理解。他有一段话简洁地概括了自己对轻与重的辩证理解:
把问题的极端重要和形式的极端轻灵集合在一起——这一直是我的野心。而这不仅仅是艺术的野心,轻松的形式和严肃的主题的结合,显示出我们的梦是何等可怕的无意义——不管那是床上做的梦,还是在历史大舞台上演完的梦[3]98。
对于昆德拉而言,除了小说形式的轻灵,对小说游戏成分的呼吁也可以归结为文学的轻,一种自由嬉戏的轻逸精神。昆德拉认为,现代小说至少有四个呼吁值得认真对待,其中,摆在首位的就是游戏。这种游戏是18世纪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并构成劳伦斯·斯特恩和狄德罗各自名著《项狄传》与《宿命论者雅克》中生动展现的小说奇景。进入19世纪,西方小说拘守心理逼真和反映现实的法则,放弃了小说轻快游戏的传统,小说变得沉重。昆德拉为之遗憾不已。这大概也是昆德拉不太推崇19世纪俄国小说的原因吧,的确那些现实主义的长篇大作几乎都比较沉重,缺乏游戏精神。昆德拉欣赏卡夫卡就在于卡夫卡小说用幻想唤醒了19世纪的睡眠式想象,真正实现了梦想与现实的融合。昆德拉热情赞扬卡夫卡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实现了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步骤,更在于打开了一幅新的景象,让想象像在梦中爆发,自由地突破看似不可逃脱的逼真的律令。显然幻想是使文学变得轻灵的基本方法。
在昆德拉那里,还有一种内容上的“轻”,这种“轻”实际上不是轻,而是一种独特的重,这就是在《存在的不能承受之轻》以及其它作品中也出现的轻,这种轻,用昆德拉的语言来说是“虚弱”,面对强敌强权时的疲乏无力。再进一步说,这种轻,我们可以紧扣昆德拉的语言来说,就是对于存在的遗忘。因为遗忘而飘浮无据,而轻飘无力。这正是现代人类尤其是极权主义历史情境下人们的普遍的可悲的生存境遇。昆德拉用这种吊诡奇谲的方式凸显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同时也展现了小说的没有穷尽的可能性。也难怪他是那么自信:“小说的形式几乎是无限自由的。迄今为止,它在这方面并没有加以充分利用。它尚未获得这种自由。它留下了许多有待探索的形式上的可能性。”[3]84
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卡尔维诺一个重要的小说思想,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与轻盈相矛盾的,但实际上这是轻盈小说的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的开掘,对现代小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要求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内容,那么对于现代小说来说,在摆脱了认识社会和反映生活之后,就必须寻求其它方面的突破。正如卡尔维诺强调的,他主张轻并不否认重,这种对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融入小说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后现代小说特有的重,它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现实之重,而是一种新的知识和话语的重。也就是说,后现代小说并不简单地抛弃重。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第五个范畴“繁复”(内容多样),实际上指的就是百科全书型的小说。进入卡尔维诺视野的既有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的《布瓦尔和佩库歇》,也有现代主义大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介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托马斯·曼的经典之作《魔山》,加上他开头推举的本土作家加达和奥地利现代主义作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尔维诺将百科全书式视为20世纪伟大小说的特点,并强调这是现代后现代小说的发展方向。他说:“我们最喜爱的现代作品,都是繁复多样的解释方法、思想模式和表达风格的聚合与冲突的产物。即使总体设计是经过精心计划的,最重要的也依然不是要把作品封闭在一个和谐的形体内,而是由该形体催生的离心力——以语言的多元性来确保真理不只是局部的真理。”[1]116他自己的小说,尽管外形上没有现代主义大师那种深闳富赡和包罗万象的规模,而倾向于小篇幅,但是他认为《看不见的城市》和《假如在冬夜,一个旅人》甚至《帕马洛尔》这几部具有明显后现代特色的小说属于百科全书之作。卡尔维诺自陈《假如在冬夜,一个旅人》包含十部小说。一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中竟能包含十部小说,轻盈的形式容纳如此繁复多样的内容,这说明卡尔维诺开创了一种大容量高密度的独特小说结构,这得力于他强调的“轻”的第三个含义:叙述的高度抽象。
卡尔维诺更进一步把对百科全书的思考深入到人的生命,为小说与生命的同一性作了十分独到的论述:“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图书馆,一座物品储藏库,一系列风格,而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不断调换位置并以一种可设想的方式重新编排。”[1]124
昆德拉没有用百科全书式小说这个概念,他用的是博学这个词。显然,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昆德拉并不简单地提倡博学,他甚至反对将各种知识杂糅起来,而是强调要保持主题的统一。他对博学的理解与卡尔维诺对百科全书式小说的阐明更有说明力。实际上广泛地拥有知识展现知识并不是小说的艺术功能。
昆德拉对博学的理解是与复调结合在一起的。他对复调的理解是,把种种不同的话语形式如哲学、梦想和叙述交响为一,各种话语均衡发展,同时又保持主题的统一。实际上,这里昆德拉把复调与博学式的小说或者说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统一起来了。昆德拉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博学,也就是那种将各门学科知识杂糅起来而没有统一主题,尤其没有深入探索人类生存境况的小说,他重申布洛赫对博学小说的理解:调动所有理智手段和诗意形式,去阐明那“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即人的存在。对于昆德拉而言,小说运用复调是为了扩展小说的认识功能,更深入地扎进存在之谜,以诗意的形式去触摸表现存在的奥秘,因此他宣称:复调小说需要的是诗意,而不是技巧。由于有扎实的音乐修养和对存在之谜的诗意体验,昆德拉对复调艺术和博学小说的理解都是十分具体的。他的作品的独特的结构就来自复调的精致运用和博学的实践。在各种话语交响一片的同时,他还特别提倡并反复使用一种小说性的论述,即在叙述之中插进看似离题实则与主题和谐映衬的哲学议论。这也是昆德拉小说艺术的重要标志。
复调在卡尔维诺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第五讲《繁复》谈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直接提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我们都知道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也就是复调理论。卡尔维诺对百科全书式的理解不能完全等同于复调,但是他对包罗万象式、非系统性思维、结构的未完成性的肯定,无疑呼应着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基本内涵。
两位大师都心仪复调,是不奇怪的。复调对于小说的意义,经巴赫金的阐明已经与小说的现代发展联系在一起。它将各种异质的话语融合起来,打破意义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创造出一个多义的,平等交流,自由对话,永远开放,没有终结的世界。在资本主义控制一切领域的当代社会,复调艺术有助于从内部打开缺口,颠覆资本主义高度简化的单向度的世界,挽救其它有价值的意义元素。至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地区的极权主义,复调艺术通过异质话语的自由对话,特别是通过昆德拉反复强调的嘲讽艺术的运用,足以撕裂其威严冰冷的外表,暴露其内在的丑陋和可笑甚至腐烂和脆弱。卡尔维诺认为小说的可能性是不可穷尽的,伟大的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他称赞博尔赫斯小说的宇宙模式,甚至有些夸张地发出这样的宣言:书要包含宇宙,并等同于宇宙。显然只有复调、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因引进各种异质话语而达到这种无所不包的宇宙广度,并因这些异质话语而进行不断的激情对话、辩驳,从而使小说永远没有完结。
二、高度简化与语言瘟疫
卡尔维诺和昆德拉尽管对现代小说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这并不说明他们不清楚现代社会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对小说发展的危害。昆德拉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存在被遗忘的思考,切入对当代西方小说处境的忧思。他看到在这个存在遭受遗忘的时代,小说还受到其它方面的威胁,小说陷进“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世界”。昆德拉把这种普遍的威胁概括为“高度简化”。由于大众媒介和政治的联手,促使这种简化成为时代普遍的特征,昆德拉不无嘲讽地称其为时代精神。小说精神与这种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挑战这种时代精神,不与时代精神妥协正是小说的使命。在这里,昆德拉主要的批判对象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和横行一时的苏联东欧的极权主义。对于生活在捷克的昆德拉的个人经验来说,主要的是来自对极权主义的极度厌恶。他有一段充满了义愤的话,实际上是对小说反抗极权主义最强烈的声明:
作为西方世界的——这个世界植根于人类事物的相对性和多义性——一种模型,小说和极权主义世界是不相容的。它不仅是政治和道德的不相容,而且是本体论的不相容。据此我的意思是:单一真理的世界与小说的相对和多义的世界被铸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极权主义的“真理”拒绝相对性、怀疑和提问,它永远不会接纳被我称之为“小说精神”的东西[3]14。
强调小说精神,是这本《小说的艺术》最出彩的地方。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命题:小说必须说出只有小说能说出的东西。这就是面对存在之谜的独特追问。他认为现代小说起源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开始了对个人生存境遇的探索,从塞万提斯到卡夫卡,构成了欧洲小说的一个圆圈,在旷野上寻找自我的堂·吉诃德最后退化为在城堡外徘徊的K。昆德拉这样突出现代欧洲小说对存在之谜的执着与深入:实际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分析的全部伟大的存在主题——考虑到它们曾经被先前所有的欧洲哲学所忽视——都在这四个世纪(欧洲小说再生的四个世纪)的小说中得到了揭露、展示和澄明。以自己的方式,通过自身的逻辑,小说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存在的各个方面:经由塞万提斯和他的同时代人,它深入探索了冒险的天性;经由理查森,它开始审察“内心世界”,揭示情感的隐秘状态;经由巴尔扎克,它发现了人在历史中的根基;经由福楼拜,它研究了过去未曾探明的日常生活的未知领域;经由托尔斯泰,它全神贯注于人类行为和决定中非理性的侵入。它探索时间:普鲁斯特处理了难以捉摸的过去,乔伊斯处理了难以捉摸的现在。而通过托马斯·曼,它又考察了控制我们当下行为的遥远过去的神话规则,等等,等等[3]3-4。
在昆德拉看来,现代小说的发生与现代欧洲是同步的。统一世界的解体(上帝之死)开始了意义多元和模棱两可的世界,这个混沌的世界无法给个体提供统一的意义,个体面对世界,被迫进行探索。这就是欧洲现代精神的体现,也是欧洲现代小说的精神所在。
把小说定义为对存在之谜的探索,昆德拉还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思考。他认为,小说就是从自我的角度,运用虚构的自我对个人的生存和存在的种种境遇进行深入的探索,寻找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他接受“小说是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这样的界定,并且很清晰地理清了小说中的个人生存与历史语境的关系,他接受海德格尔关于人与世界相互融合的观点,强调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因此小说与历史世界的关系,并不是对历史的图解(这样的小说当然是很多的),而是把历史作为一种生存情境来理解和处理,历史世界实际上成为个人生存境遇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实主义传统中的背景。“历史境况不是一种背景,一种人类情境赖以展开的舞台布景,它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情境,一种生长着的生存情境”[3]40。正因为有这样的内化,昆德拉向来都是非常凝练地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并把历史事件提升为独特的生存境遇。他甚至认为了解捷克的历史对理解他的小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②。基于个体生存境遇与历史事件的存在主义式的融合,昆德拉在自己的小说中探索了多种生存的境遇,他特别提示的是“虚弱”这种情境,个体面对强敌表现的虚弱,经常是以陶醉的姿态出现,他认为有一种“虚弱的醉意”。其实,这种“虚弱的醉意”并不是昆德拉的首次发现,早在卡夫卡的《审判》里就已得到了有力的展示,就是约瑟夫·K被杀时那种主动配合的情境。显然昆德拉对个体的生存情境的领悟部分来自卡夫卡的作品,他处处盛赞卡夫卡,并且以卡夫卡的创作来总结小说的探索,因为卡夫卡是把现实与梦幻结合的伟大代表,特别是他深入地探索了人类的生存的可能性:
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存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存在的图形。但是再说一遍,存在意味着“在世存在”。这样,人物和世界双方都必须作为可能性来理解。在卡夫卡笔下,所有这些都一清二楚,卡夫卡式的世界和任何已知的现实都不相同,它是人类世界的某种极限的和非现实的可能性[3]44-45。
昆德拉对小说与存在、历史关系的思考展现出哲学的深度。这也是昆德拉博学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对小说精神的热忱捍卫。
初看起来,卡尔维诺对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没有昆德拉那么激愤,但是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忧思,他直言不讳地宣称一场语言瘟疫袭击了人类,造成语言平淡和意义平庸,这场瘟疫弥漫到社会各个领域,传染了生活和历史,使得历史模糊不清、枯燥乏味,最令人不安的是社会失去了形式。卡尔维诺认为文学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卡尔维诺所说的这场语言瘟疫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病症。他没有过多地描绘这种肆虐人类的瘟疫,也不愿深思瘟疫产生的原因。毫无疑问,这种瘟疫和昆德拉所说的高度简化是相同的,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化和官僚化的结果。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加上媒体对语言和艺术的恶性影响,造成语言无味、意义单一的现象。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社会”。因此这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对的一种瘟疫,不单单表现在语言领域,甚至渗透了社会的所有方面。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社会里,这种瘟疫正在变本加厉。因此,昆德拉和卡尔维诺对现实的尖锐批判也显示了小说的反抗作用,这与传统现实主义毕竟也还是相通的,尽管反抗的方式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昆德拉还保持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嘲讽现实的激情,那么卡尔维诺实施的则几乎是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倡导的形式的反抗,新颖的艺术形式自动疏离沉闷乏味的现实,在幻想的天地里超越现实,反抗现实③。
三、视觉形象及嘲讽
卡尔维诺与昆德拉也还有不同的地方,体现出两位大家对文学的理解和爱好的差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卡尔维诺对视觉形象的推崇,显示出卡尔维诺独特的小说趣味,也透露出小说发展的当代特性。卡尔维诺对视觉形象的喜爱来自以图画为主的童年读物,这些视觉形象多半与幻想有关,因此卡尔维诺又称其为视觉幻想。视觉幻想有广泛的来源,对现实生活的直接观察,生活中的幻影与梦影,文化传统流传下来的艺术形象,以及感觉的抽象、提炼内化等等。他认为优秀的作家都具有这种禀赋,尤其生活在视觉幻想特别受重视的时代的作家,如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浪漫主义时代。
卡尔维诺对视觉形象的重视,也可以归结为他对文学的轻的思考,他在界定文学的轻时就说到轻的视觉形象。尽管卡尔维诺并没有提到当今的主要艺术形式电影,但是他对视觉形象的重视,实际上呼应了电影艺术的追求。不难看出,电影是最擅长构造视觉幻想的艺术形式,比任何其它艺术形式都更能生动地把视觉幻想呈现在读者面前。卡尔维诺生活的时代已经是电影技术和艺术都高度完美的时代。这也是电影艺术对卡尔维诺的文学思考的影响。
昆德拉似乎没有卡尔维诺的潇洒,他对小说与电影的关系没有论述,他的小说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视觉效果的追求。相反,他执着不忘的是小说的精神本质,也就是嘲讽。他反复强调小说是一门嘲讽的艺术。把小说的本质界定为嘲讽,主要源于昆德拉对极权主义的憎恨,对人类沉湎于物质利益而迷失存在意义的忧思。同时也看得出昆德拉对现实主义传统的辩证态度,正是对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自觉继承,昆德拉甚至仿造了“批判的现代主义”一词。这个术语不仅揭示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精神相通之处,更显示出昆德拉的创作原则。他的作品幽默诙谐,举重若轻,对极权主义和人类的愚蠢极尽嘲讽之能事,极富个性地显示了现代小说的批判威力。怪不得他充满感慨地说过,除了塞万提斯的遗产,他一无所有。
四、结 语
由于身处整个西方文化和文学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移的中途,昆德拉和卡尔维诺的创作理念也自然体现了这一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一方面敏锐地洞察到现代社会对小说发展的窒碍(昆德拉说的高度简化,卡尔维诺说的语言瘟疫),两人都表达了深刻的忧思,同时又站在西方文学历史的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清醒地洞悉小说艺术尚有许多没有穷尽或者没有充分开发的空间,如游戏、幻想、嘲讽以及百科全书式的话语组合,等等。两人都从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哲学层面上,对未来小说的发展寄予希望。当然由于两人的处境和文学理念的差别,对小说艺术的志趣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昆德拉对存在之谜,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执着探索,对小说嘲讽精神的执着,以及对复调艺术的细致理解和灵活使用,构成了20世纪晚期西方小说艺术的独特景观。卡尔维诺则对西方的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想具有亲切的感受,对小说的语言属性具有与西方最近的语言哲学相近的看法,他对幻想的重视,对语言能指的游戏功能的理解与运用,对叙述方式和小说文体的持久探索,结出了《如果在寒冬,一个旅人》、《看不见的城市》以及《帕马洛尔》这些实验性的小说,充分显示了自由优美的想象力、文体混用、叙述变革对于小说可能性的开掘。即使是两人同样奉持的轻盈,也是同中有异,各具特色。昆德拉轻得尖刻、热辣,像把向上飞腾的烈火;卡尔维诺轻得从容、优雅,像山间漂浮的云霞。昆德拉轻中含重,卡尔维诺轻中带纯,都开创了现代小说独有的迥别于传统经典的艺术胜境。
而反观当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不论在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方面,还是对叙事艺术的不断创新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少足以传承的经验。特别是对人类生存情境的独创性开掘,几乎已属遗忘。至于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对于中国当代作家而言甚至连梦也不会梦到。在轻视现实、轻视学识的普遍风气里,卡尔维诺和昆德拉这种具有高度理论素养的小说家似乎也不会在我们的土壤上出现。昆德拉说小说是西方的艺术,这如同韦伯说理性主义是西方的思维,德里达说哲学是西方的思想一样,使我们既感到羞辱而又无可奈何。与昆德拉和卡尔维诺这样的大家相比,中国当代小说有不少差距,但最主要的差距还在于在缺乏自觉的小说意识。
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艺术风潮之中,一些作家还在执着于传统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一些则对中国丰富的历史进行现代的想象。在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创作中,比较突出的毛病是简单的模仿,或者玩弄一点大众化雷同化的个人幻想。在昆德拉和卡尔维诺的启示下,我们的当代创作处处是“性”情洋溢和轻浮想象,然而却没有两位大师的神髓,仅得其皮毛而已。其实,即使是后现代主义,即使作为一种小说艺术风潮,也具有极其严肃的一面,绝非任意胡来的,且不说昆德拉的小说嬉笑怒骂之中是对人类存在之谜的探索和展示,即使卡尔维诺的轻盈,也是对小说可能性的探索和想象力的优雅拓展。我们阅读卡尔维诺只觉一片神行,的确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能指游戏的范本,却看不到等而下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常见的胡闹、恶搞、脏乱丑的通病。昆德拉尤其是卡尔维诺的创作与思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普遍接受和奉为准则的后现代主义,这对于当代中国的小说发展是一面很好的镜子④。
注释:
① 本文参考了卡尔维诺此书的两个中译本,萧天佑从意大利语译出的名为《美国讲稿》,五次讲演的标题分别是:轻逸、速度、精确、形象鲜明和内容多样。黄灿然从英文版译出的名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五次讲演的标题是:轻、快、精确、形象和繁复。本文综合了两个译本的术语。对两版的引用,完全是为了行文的需要。
② 尽管昆德拉这样说,其实即使他把捷克的历史事件已经如他所云变成了一种生存情境,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环境转变成海德格尔式的个体存在境域,无疑捷克的历史仍然还是他的作品赖以产生的外部机缘,因而也是理解其小说的重要途径。
③ 见马尔库塞的著作《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阿多诺的著作《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④ 如果模仿以前的陈词滥调,那么也许可以说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后现代主义,美国理论家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以及哈维在《后现代状况》等等著作中对后现代主义的诊断基本上都是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消极方面,如艺术上的戏仿、拼贴、无深度等等。其实昆德拉和卡尔维诺用他们的创作和理念向我们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维度。当然,这两位大家的情形还是有些特别。可以说卡尔维诺的小说已经有了十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而昆德拉正处于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之中。
[1]伊塔洛·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M].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2]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M].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