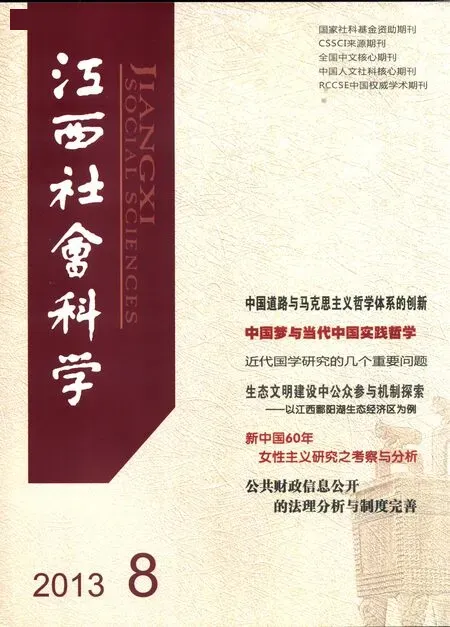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厘定与理论阐释
■韩俊强 孟颖颖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民工”这一隶属特定历史范畴的称谓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泛指拥有农村户籍和承包经营土地,但从事与自己的土地无关的生产活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力。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我国农民工总规模约为2.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亿人。据预计,2020年中国农民工的总量将超过3亿[1]。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在给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发展失衡、失业和社会失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流入城市究竟是喜是忧,关键在于这部分人是否能最终融入城市生活[2][3]。
无论是理论上的经验分析,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实践都告诉我们,解决好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不仅可以缓解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社会矛盾,而且还将释放出强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济更长期的平稳增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显然,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重要性,“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服务,着力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入园上学、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被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也已成为政府新一轮工作的重点任务。
与此相对应,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已有的研究也为深刻认识这一问题贡献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4]。但是,从既有研究文献来看也不难发现,围绕这一问题延伸出的不少关键性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拓展,比如,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概念界定问题。综述已有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合”,至今也没有一个已形成共识的定义或者相对明晰的界定,在这一概念的使用上,往往连表述都不统一,常见的表述有“社会融合”、“城市融合”、“城市融入”、“城市适应”和“市民化”等。概念表述上的多样化与差异化,直接导致已有研究对“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内涵界定的模糊不清,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更给研究者们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是困扰,制约了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拓展。
二、国外学者关于“社会融合”概念的研究
1951年,法国社会学家E.Durkheim在对自杀现象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融合”一词,他指出社会融合是社会个体用基于社会分工所形成的集体意识,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Durkheim定义的“社会融合”是一种泛指的社会融合,即这里的“社会”指的就是社会本身,而非具有明确界定的其他社会集合体。[5](P207)。此后,学者们沿着Durkheim的思维路径,对社会融合的概念内涵不断补充。美国社会学家Parsons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提出了社会融合的概念: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相互和谐并相对稳固,足以对抗外来压力的状态。Schwarz认为社会融合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的内聚性,表征的是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程度和认同程度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6]。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政策研究与社会政策实践的逐渐发展,“社会融合”概念引起了政府和政策研究者们的极大兴趣,并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2000年3月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首脑峰会,强调要把推动各成员国在就业、教育和培训、健康、住房等四个方面的社会融合纳入正式议事日程。Amartya Sen认为,融合社会是指社会成员积极而充满意义的参与和享受平等,共享社会经验并获得基本的社会福利[7]。欧盟认为,真正的社会融合应该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通过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全面地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并在他们居住的社会中享受到正常的社会福利,个人和家庭都能够保障体面的生活。Duffy认为,社会融合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社区中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层面上平等地受到重视和关怀,二是在家庭、朋友和社区拥有相互信任、欣赏和尊敬的人际关系。[8]
与此同时,“社会融合”一词也被引入到移民与迁入地的互动关系研究中,Milton Gordon在研究美国的族群融合问题时,提出了从7个层面来衡量移民的社会融合。[9]John Goldlust等在《移民适应的多元模型研究》一文中,提出移民适应的七大类指标:经济、文化、社会、政治、自我意识的转变、对接受地态度和价值的接受与内化、对移民后生活的满意程度[10]。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中给出了社会融合丰富的内涵:熟悉并接受迁入地的风俗习惯与社会价值观,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获得平等的劳动与就业权利、有直系亲属相伴或团聚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着迁移者融入迁入地社会的速度,促进迁移者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符合东道国社会和迁移者个体的最大利益,迁移的实现在于迁移者和迁入地社会的相互适应。[11](P223)
从国外理论界对社会融合的界定来看,研究者们沿着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路径,扩展了社会融合的内涵,根据研究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出了各自的定义。同时不难发现,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有借鉴意义的,是移民与迁入地的互动关系研究的角度。就移民适应迁入地的角度来看,学者们对“社会融合”给出的内涵理解也不完全相同,对其概念界定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没有达成一致的认同。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定义具有以下两点共性:第一,都肯定了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范畴;第二,都不同程度地共同反映出社会融合的一个基本特征——平等权(公平权)的获得。这些都为本文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厘定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与参考价值。
三、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定义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是基于社会调查所得数据的实证分析,理论研究相对偏少,同时,研究的对象主要聚焦于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少数学者研究了白领新移民等群体的社会融合状况。从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相当丰富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普遍缺乏对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界定。学者们在研究中通常使用普适性定义——借用或套用西方学者关于社会融合的界定[4]。从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内涵的厘定来看,虽然大多学者沿用了西方研究者关于社会融合概念的外延来界定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但维度标准划分的多元化、交叉化,使得农民工社会融合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都存在相互矛盾、模糊不清、缺乏统一性和难以操作等问题,这也直接导致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方式,较为常见的有“社会融合”、“城市融合”、“城市融入”、“城市适应”、“市民化”等。
任远和邬民乐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12]李培林等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是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获得现代性特征的过程。[2]田凯最早从城市适应性的视角指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包括三个层面:与其职业相联系的经济层面、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求的社会层面、更高层次的文化和心理层面。[13]朱力在田凯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农民工城市融入不仅是适应空间地理、职业及居住环境的转移,更重要的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文化转变过程。[14]马西恒和童星以城市新移民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融合是指新移民在居住环境、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15]黄匡时、嘎日达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一个包括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之间相互接纳、认同的多维度过程。[16]
也有不少学者使用“市民化”的概念,来界定农民工向城市市民身份转换的过程。郑杭生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包括由“农民”的职业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二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能够适应城市并具备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能力形成的过程。王桂新等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向城市市民同质化,以及获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合法身份与社会权利的过程。[17]刘传江等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农民工不断摆脱其城乡边缘状态,逐渐走向和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主要包括职业与社会身份的转变,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意识形态、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等几个层面。[18]
四、概念的厘清:评述与讨论
(一)“社会融合”、“城市融合”、“城市融入”抑或“市民化”
从现有研究对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表述来看,存在模糊不清、缺乏针对性与一贯性的问题。如上所述,国内学者们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表述繁芜庞杂,但从研究中所指代的范畴与主要内容来看,这些概念在基本内涵上的语义差别并不大,至于哪一种表述方式更能科学、有针对性地体现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实情况,还未有学者做过专门论证,自然也未达成统一的共识。本文认为,选用“城市融合”来描述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这一过程或许更为贴切、合理,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社会融合”一词起源于Durkheim的《自杀论》,该文中的“社会”指代社会本身,而非某一具有明确界定的其他社会集合体。而后,有个别研究将“社会”的范畴具体化,用以研究某一社会群体的社会融合,如某一企业组织或某类特定群体等。[19]与此同时,“社会融合”一词也开始被学者们用于外来移民(往往涉及族裔、种族群体)与迁入地社会互动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通常将其称为“外来移民社会融合”研究,此处的“社会”意指“迁入地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融合”中“社会”一词的指代发生了变化,由开始指代的“社会”本身,演变为外来移民研究中指代的“迁入地社会”。而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对象定位于城市社会的外来群体——农民工,主要研究的是在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差异仍然存在的环境下,农民工如何跨越制度藩篱,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及怎样更快、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进而融入城市的过程。很明显可以看出,这里的“迁入地社会”就是“城市”。因此,本文认为,用“城市融合”指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适应比“社会融合”的表述更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性。
其二,国内学者虽然给予“市民化”丰富的理论内涵,但“市民化”的表述似乎主观上带有“将城市市民为主构成的城市主流社会,视为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方向与标尺”的感情色彩,而“城市融合”意指由乡到城的人口流动方向,肯定的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沟壑存在的客观现实,去除了某种“身份优越感”的成分。因此,“城市融合”又比“市民化”表述更客观,更具有中立性。更进一步来说,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与“市民”是代表两种社会阶层、两种社会身份的特有称谓,消除户籍身份上的差异,显然只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许多诸如社会保障、子女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配套措施需要同时跟进。虽然在学者们的研究中也界定了“市民化”实现条件的丰富内涵,但是这一称谓似乎更侧重于农民工户籍身份上的转变,将解决农民工户籍身份上的差别与其实现社会融入画等号,在字面上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
其三,关于“城市融合”与“城市融入”哪一个词更贴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杨菊华认为,“融入”暗示着一种不平等的文化和行为主从关系——流入地文化为主、流入者自身的传统为辅,而在客观层面,流动人口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无力传播家乡文化。同时,在主观意愿上,流动人口往往由于向往城市的“好”,而无心传播家乡文化,因此,用“融入”比“融合”更适合中国的情况。[20]本文认为,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一部分农村文化可能与城市文化相冲突,会损害到城市居民的利益,所以,在融合过程中要有所舍弃;而一部分“好”的农村文化可以继续保留,虽然不一定得到传播。此外,至于这部分“好”的农村文化会不会与城市文化相交融,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则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二)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多元论”与“同化论”之争
从国外学者在研究外来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文献来看,研究者们长久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即是外来移民与迁入地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按其理论观点的基本取向,可以分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21]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而对原有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抛弃。帕克将族群的融合与同化视为个人与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并共享彼此的经历和历史,相互渗透和融合,最终逐渐融会成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的过程。[22](P422)与“同化论”不同,“多元论”则“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23]。Kaplan等通过对美国“韩裔族群”的研究,提出了“非零和型同化”的概念,他们发现韩裔移民虽然已经在文化方面适应了美国社会,但在其他方面并未同化于美国社会结构的所有重要方面,并将韩裔移民这种在适应美国文化的同时还保留自己文化内核的适应形态称为“执著性适应”。[24]
其实,现阶段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之路,也同样面临“同化论”与“多元论”的困惑。我们注意到,国内在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时,鲜有学者对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应属于“同化论”还是“多元论”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是,我们从研究者给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认可的是“同化论”,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融合的过程中,农民工要从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向城市主流社会转变。比如,有学者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农民工不断摆脱其城乡边缘状态,逐渐走向和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主要包括职业与社会身份的转变,自身素质的提高,意识形态、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等几个层面[17]。
但是,本文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一个“农民”与“市民”群体相互渗透的双向互动过程,不只是城市文明完全地、简单地对农民工群体的“同化”,在城市融合过程中,农民群体自身所具有的一些良好的传统品质,比如勤劳、淳朴、善良等特质应该加以宣传、鼓励并保留下来,这就像20世纪70年代移民美国的华人群体,他们在适应、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还保留了鲜明的族裔文化和群居特点。[25]所以,我们认为,保留自身一些良好的传统秉性,同时也积极适应新的城市文化,应该是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合理道路。当然,这条道路究竟是“同化”还是“多元”模式,还有待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发展实践来给出答案,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三)平等权的获得与社会融合
整体而言,从研究者们关于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内涵的界定来看,已有研究基本上沿用了西方学者在国际移民问题研究中对社会融合所下的定义。从内涵维度上来看,已经渐进地囊括了经济层面、行为层面、社会身份层面、心理层面及文化层面等多维度内容,肯定了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多维度范畴。不过,与西方相对成熟的社会融合理论相比较,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厘定虽然有着较为全面的融合维度,但是对社会融合的核心特征与基本内涵——平等权(公平权)获得的重视程度略显不足。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将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公民权利,纳入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合实现程度的标准,但这些研究多是将平等权的获得作为城市融合的结果,抑或作为城市融合所必需的条件来进行界定,而忽视平等权的获得在城市融合概念本身范畴中的地位。
本文认为,包括就业、劳动保护、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等权益在内的平等权的获得,不仅是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基本保障与重要基石,更是农民工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基本权利与主要内容,平等权的获得理应作为农民工“城市融合”范畴的核心与基本要义。平等权的实现,有助于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藩篱、减少农民工在新环境的社会摩擦,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城市融合实现的根本前提主要在于确保农民工与市民拥有同等的平等权,任何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不平等、不公正待遇或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会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速度与深度,只有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地解决融合过程中存在的融入障碍,才能促使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真正实现。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是农民工在享有平等权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当然,农民工是否适应城市生活还取决于多种其他因素,包括有能力在城市获得一定的收入,能够基本无障碍地与城市市民进行语言交流,习惯并接受迁入城市的风俗人情与社会价值,有可能取得城市户籍以及有可能与直系亲属相伴、共同生活等等。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
[2]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3]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4]悦中山,等.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J].社会,2011,(6).
[5]Booth, A.,et al.Social Integration and Divorce.Social Forces,1991,(1).
[6]Schwarz Weller H.K.Parental Tie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 to Urban Migrants.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64,(4).
[7]Sen A.Capability and Well-being.The Quality of Life, 1993,(9).
[8]Duffy, k.The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Exclusion Project-research Opportunity and Risk:Trend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Council of Europe,1998, (3).
[9]Gordon,Milton Myr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0]Goldlust,John,and Anthony H.Richmond.A Multivariate Model of Immigrant Adapt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74,(2).
[11]World Bank.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Report 3 1973 - CHA,2005.
[12]任远,邬民乐.城市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人口研究,2006,(3).
[13]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5,(5).
[14]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
[15]马西恒,童星.敦睦他者: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J].学海,2008,(2).
[16]黄匡时,嘎日达.“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对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移民整合指数的借鉴[J].西部论坛,2010,(5).
[17]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8,(1).
[18]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 [J].财经问题研究, 2006, (5).
[19]Scott R A.Deviance,Sanctions,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Small- Scale Societies.Social Forces,1976,(3).
[20]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1).
[21]Sorensen T., et al.Contribution of Local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Personal Social Network Support to Mental Health.Norsk Epidemiologic,2002,(3).
[22]Park R E.Assimilation, Seligman E,Johnson a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Macmillan:New York,1930.
[23]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24]Kaplan G., et al.Mortality among the Elderly in the Alameda County Study:Behavioral and Demographic Risk Factor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1987,(3).
[25]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J].社会学研究,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