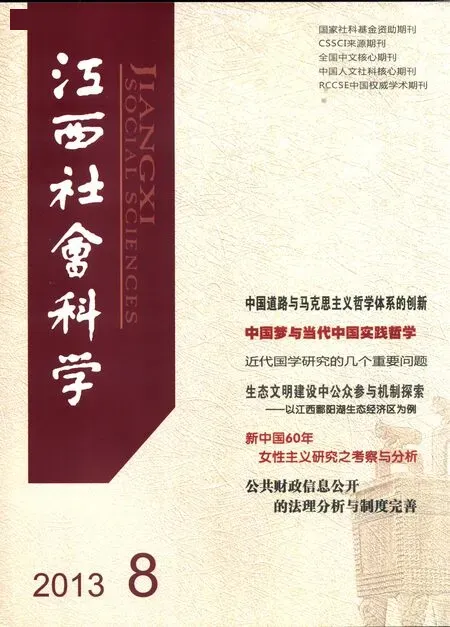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黄 琨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鲜明的特色,作为后来的中央苏区的奠基石,它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从井冈山下来后,人困马乏的红四军在东固受到热烈欢迎。在这里,红四军不仅获得了必要的、及时的修整,毛泽东还发现了一种新的、有着范式意义的割据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1](P321)这种割据形式显然不在毛泽东此前的构想中,所以,在离开东固后不久,他就以非常赞赏的语气向湘赣边界特委推介了东固割据经验,并提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东固式的秘密的割据形式是最好的。正因为此,“李文林式”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具有代表性的、“正确的”四种割据形式之一。
如果简单地概括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割据特点,那就是它仍然维持着原有的乡村生活面貌。通常的割据形式都会运用革命手段来改变乡村政权结构和乡村生活方式,从而保证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实践操作的复杂程度来看,显然后者要远远简单于前者。而从在初始阶段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来看,后者也没有前者密切。问题是两面的,如果没有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密切联系,东固的秘密割据就难以形成,反过来,秘密割据可视为党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的表征。所以,研究革命初创阶段的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东固革命根据地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案例。
一、初期: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高度融合
在动员农民革命的问题上,党刚开始低估了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当党的各级组织都在绘制一幅革命斗争此起彼伏的图景时,革命在乡村其实是仍需引导的。急于复仇的躁动心理使很多党组织采取了过激的动员手段和革命方式,力量尚未达到就去暴动、攻城,过早地暴露了目标,也过早地招致打击。但在东固却是另一番景象。应该说,东固革命能较为“有序”地进行,得力于他们领导人的号召力。多年后,朱德回忆说,共产党领导人很多是地主的儿子,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地主,大部分年轻并受过教育。他认为,作为曾经给过小恩小惠的地主,又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们能得到农民和他们自己的佃户的支持。[2](P279)领导人的号召力与个人在乡村中的地位息息相关,一个有钱人支持革命、参加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一点在宁冈、兴国的革命运动中也能得到验证,两地的主要领导人都具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在动员农民革命的时候都曾获得很大的便利。
虽然作为东固党组织创始人的赖经邦,出生于贫民家庭,但他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县教育局担任巡学(习惯上叫督学);另一位贫民出身的主要领导人曾炳春,也曾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尽管只是一所三四人的学校。在乡村这个极容易产生崇拜的地方,就有被神化的赖经邦在坊间流传。据后来成为中共著名将领的罗通回忆:“他任督学时,我就听人说他是个文武双全的汉子,说他一个跃步能飞过丈宽的沟,一个飞跳能翻过一人多高的围墙,握起笔杆,一篇文章倚马可待,讲起话来,声似洪钟,扣人心弦。”而关于另一位东固革命领导人段月泉的传说是:“他武艺高强,力大无比,能飞檐走壁,会使‘缩身法’,特别是枪法准,百发百中,专击土豪劣绅的心窝。”这种传言反映了他们在乡村中的个人魅力,所以,尽管段月泉是个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专打土豪、为民除害又具有超群的武艺,无疑也有很大的号召力。而因为乡村对读书人的敬重,赖经邦的影响力更是毋庸置疑。
在革命的初始阶段,革命的远景尚未被农民看清时,他们需要的是一种人身、财产的安全感,所以,他们倾向于依赖原本就证明有能力的领导者,这些人大都是富农、小地主的身份。不能忽视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而在乡村能供应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多是家底殷实者,换言之,早期的很多共产党员出身于富农或小地主家庭。两方面的结合促成了革命迅速发展,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富农或小地主进入革命队伍并成为领导者的事实。
这在各割据区域几成普遍现象。一份关于湘赣边界的乡村苏维埃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说,边界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在刚组建时,“有许多投机分子、小地主混进里边来,或者简直是变相的农民协会(从前国民党时代的妥协,多半是平日在乡村中有地位的绅士和富农领袖充当农会委员),要求真正的贫农为基础的薄弱苏维埃,是不可能的”。当中共决定进行重新改组后,问题虽然“渐次的减少了”,然而,“流弊还是不少的”,“小地主富农曾混入各级机关中,操纵把持苏维埃的阴谋还是很多很多的”[1](P277-278)。对此,毛泽东也做过解释:“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3](P52)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地从组织上解决的问题。不说受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农民仍然会在遇到困难时向那些原来的乡村精英求助,仍然会将他们视为可信赖者,即便是要在革命话语下选出一个合适的贫雇农领导者,没有文化、不熟公事、缺乏经验都是一种障碍。在乡村苏维埃的选举中,依据自己的视野,那些有文化、有经验、熟悉公事的传统精英仍然有更高的机会当选。1930年2月16日,新成立的前委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被视为赣西南党内“严重的危机”[4](P173)。1930年11月14日,中共江西省行委在吉安召开会议,主要是讨论富农问题,据估计,瑞金的党员中富农和地主占有80%,上犹县80多人的党组织,地主和富农就有30多人,甚至靖卫团总也在其中。信丰的富农问题在会议中反映最多:不仅赤卫队的官长都是富农,并且信丰的富农领导们可以为保全自己的利益命令群众打仗;他们还作出规定,参加本地赤卫队打仗死伤的优待,参加红二十二军打仗死伤的不理;西北乡的富农以保全红色区域的名义鼓动参加红军的农民开小差回来,以至这种地方主义成为扩大红军的障碍[5](P272)。这些问题是不是能统统归结到富农身上暂且不论,而不难看出的是,即使在已经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富农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怎样改变这种局面,当时党也意识到了困难性、长期性:“土地斗争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暴动久得一点,无产阶级便起来了’”,毛泽东对这种意见也表示了赞同[5](P276)。
按照当时的革命价值标准,只有贫雇农的革命性是可靠的,富农和小地主无论在工作中怎样努力,都是投机专营者。而事实上,这些富农和小地主的加入,对于党在初期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不可或缺。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高度融合保证了根据地的高度稳定。1928年秋末,东固根据地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第一家人民银行,由于东固银行基金充足,信用极好,不仅根据地内的群众争相兑换,甚至在吉安城外都可使用,吉安南昌的纸票反而没人要了[6](P95)。即使在战事频繁的情况下,东固根据地仍然能够保持着与白区的商贸往来,每月阴历一、四、七仍照常逢圩开市。
二、扩展: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疏离
革命的范围由中心区域向外扩展,动员的方式、党组织的构成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当革命在中心区域发起时,主要依靠发起者在当地拥有的威望,领导者也可以在外表看似没有改变的政权结构下进行革命活动,但这一切在领导者个人的影响力不能达到的扩展区域就很难实现。一个内生型的割据[7]在已经发展成熟后,向周边的发展就变成外力型割据的特点,必须要依靠军队作为宣传、动员工作的主体。
怎样利用军队进行革命?一些游击队在组建后,最初的任务只限于杀土豪和筹款。军队要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这种认识在刚开始是很模糊的,连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毛泽东也不例外。
1927年10月,毛泽东部在茅坪安家后,派出两个连经酃县到安仁县打土豪,没收了很多资财。按理应将这些资财分给贫苦群众,以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可是他们研究了好久,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是考虑到怎样公平合理地将这些资财分给全体士兵。据赖毅回忆,他们采取绝对平均的办法,把部队带到空场上,两个连混合成队站在墙的一边,墙的另一边堆着事先堆好了的东西。一切准备停当后,就喊起来:“第三队前一名出列”,“倒数第二队后一名出列……”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资财分掉了[8](P391-392)。
这种情况至毛泽东部撤离茶陵县城后才发生改变。于1927年11月18日攻下茶陵县城后,军队的活动每天仍然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在茶陵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并没有做发动群众的工作[9](P331)。工农革命军在茶陵的所作所为,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立即写信指出:“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做群众工作”[8](P390)。由茶陵返回后,在宁冈龙市召开的第一团指战员会议上,他又指出在茶陵群众工作做得不够。他提出,工农革命军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明确提出了革命军队应担负起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子与做群众工作[8](P389)。
上面只是反映了毛泽东部工农革命军对军队与宣传问题的理性认识过程。不过,在理论认识与自发利用军队去发动群众的事实之间并不是一种因果的关系。1928年2月,赣西南特委批准将东固工农革命军和永丰吉水农军合编,吸收部分工农群众,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纵队下设3个区队,并建有交通队、侦探队、输运队、宣传队等组织。其中宣传队11人,在这支156人的地方武装中占7.7%的分量,表明他们是将宣传和动员工作作为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来看待。
军事动员是一种与初期完全不同的动员方式,在初始阶段效果不一定好于前者。农民仍然需要一种安全感,军队必须表现出可以值得依赖的一面,所以,军事成败甚为关键。据红二团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最反动的地方,经二团游击后,认识到红军是他们自己的武装,二团同志驻在该地,都很热烈地起来参加革命,自动屠杀豪绅地主;斗争失败的地方,在挫折下不觉心寒胆落,一见红军逃之夭夭,所以虽经过几次的游击,几许辛苦,费了多大气力,而得到的成效极少,等于零;以前没有参加过群众斗争的地方,受反动豪绅的蒙蔽,军队来后,才知红军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这些地方都已有了相当的组织[9](P224-225)。在最为反动的地方,军事上的成功就可换得农民的支持,在军事成为动员工作的晴雨表的背后,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已可想见。
所以,某种程度上动员工作已演变为一种军事争夺。红枪会在吉水很有势力,农民的态度一直在它与红军之间随着势力的变化而左右摇摆。1929年3—4月间的时候,农民曾一度附随占统治势力的红枪会,当红军击败红枪会后,农民又回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中共吉水县委书记清醒地认识到农民的重新回归:“多为红军的胜利,红军发展的猛进,而形成军事投机”,但他不得不面对的是“在赣西军事投机是普遍的现状,大有红军消灭,革命无成之叹,一般党员群众都是如此”。[10](P157)
这种无奈正是因为缺少了初期的那种乡村精英的主导,一场重要的军事胜利在效果上等同于乡村精英加入革命队伍后的号召力,只是背后的内容不易为人发现,因而突出了革命“投机性”。这种区域将要付出的代价也势必更大,因为在公开的割据、一场军事胜利后,敌人更强的打击也会随即而至。
三、兵源:一个重要的观察维度
红军在割据区域的补充情况是判断农民支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农民的信赖与支持并不一定要以参军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一个勇于加入红军的割据区域至少可表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是多数。
人员补充一直是红四军面临的棘手问题。战斗的酷烈使红四军每次总要损失一些优秀的干部和士兵,由于无法在湘赣边界的农民中得到补充,明知俘虏兵是带危险性的,也不得不加以使用,即便如此,“有时连俘虏兵都很难得到,有有枪无人的苦楚”[1](P262)。这一点在红四军后来的组成成分中也能体现。据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反映,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萍、湘南的农军和数次战役的俘虏兵,简直寻不见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1](P297)。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前委就曾为红军的补充问题犯愁,在1928年11月25日对中央的报告中,其诉说了自己的苦楚:湘赣边界红军的来源,以俘虏兵为最大数量,“边界农民愿意当兵的少,分田实行,大家便耕田去了,现在第四军的边界工农分子数量是占的极少数,故问题仍然很大”[3](P37)。由于湖南省委曾答应送一批安源的工人来补充,可又迟迟未至[11](P97),其在报告中又向中央提出:“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来此,亟盼实行。”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朱、毛部的另一种补充途径是在非割据区域以招兵的形式完成,攻下长汀城后,朱、毛部以招兵的形式获得了两三百人的兵额补充[12](P168)。
与依靠军队建立起来的湘赣边界割据不同,东固割据区域由于党组织与乡村社会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军队的人员补充较为容易。在东固,1928年9月初,由当地的第7、9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和赣南的第15、16纵队在1929年2月15日会师于兴国莲塘后,由二团部分官兵与第15、16纵队又合编成立第四团,全团400多人,300余枪。据1929年5月江西省委军事工作报告反映,红二团有官兵850余人,其中工人15%,农民50%,会匪15%,俘虏降兵15%,其他5%[9](P134-135)。从中可以看出内生型割据中的红军在刚开始就可以由大量的本地农民补充。
东固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密切联系,在一次战斗中可得以窥见。据永丰县靖卫二队队长向国民党中央的呈文中反映,1929年10月30日,当他们向东固推进时,遭到了有千余人、枪四五百支的红四团和千余人、土快枪三百余支的赤卫队、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的联合阻击而失败[6](P178)。一个成功的革命根据地就应该是共同防御、全民皆兵。
农民的革命训练不能一蹴而就,外力型的割据与内生型的割据相比,在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上有着先天不足。不能否认确有投机钻营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存在,但将阶级位置与政治选择视为必然的勾连,确也对革命造成巨大的伤害。富田事变中,赣西南特委提出:“在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13](P603)从东固革命根据地形成、发展的历程来看,那些在事变中被错误打击甚至遭到错杀的小地主、富农分子,在密切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以及维持根据地的生存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反思富田事变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
[1]江西省档案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79.
[3](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2卷(1927.5—1937.8)[C].东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
[4]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江西党史资料:第十辑[M].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合作编印,1989.
[7]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8]中共株洲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民主革命时期株洲党史资料(1927.7—1931.7)[M].株洲:中共株洲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印,1989.
[9]中共井冈山党委宣传部.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10]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M].北京:中央档案馆,南昌:江西省档案馆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1987.
[11]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1931年)[M].北京:中央档案馆,长沙:湖南省档案馆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1984.
[12]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上)[M].北京:中央档案馆,福州:福建省档案馆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1984.
[13]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