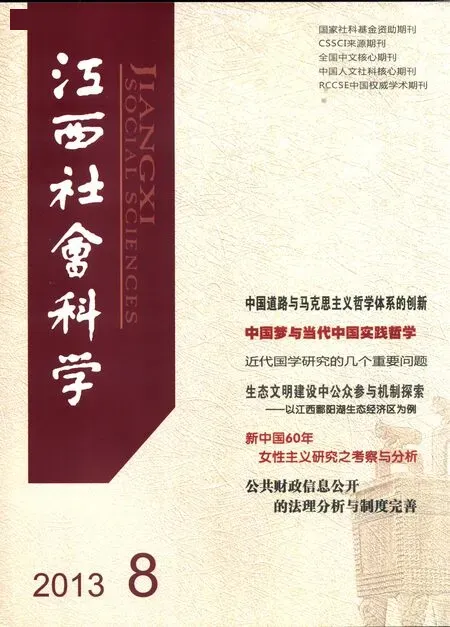论王禹偁的七律诗风及诗学史意义
■张立荣 张 丽
王禹偁(954-1001),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作为天水一朝新生代士人,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王朝,王禹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他关注国计民生,以刚直立朝,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屡屡触怒权贵。一生三进三黜,仕途坎坷而秉性不移,这种人格精神正是北宋新一代士人精神的写照。王禹偁人格与诗品的卓越不凡,使其成为宋初宗白诗风中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其诗文理论与实践对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一、王禹偁七律的创作经历及审美取向
王禹偁在宋初诗人中,七律创作数量最多。王禹偁七律共284首,他的创作活动基本集中在太宗年间。太宗年间正是白体诗风创作的高峰期,相比于五代入宋士人徐铉、李昉,他的七律诗风发生了明显变化。
从《小畜集》所存诗来看,王禹偁的七律创作大致始于太宗雍熙元年(984)中举后知苏州长州县时期。从雍熙元年秋到长州至雍熙四年(987)离开,王禹偁在这富庶的鱼米之乡度过了三年。在以后的诗作中,他将这段时光称为三年吏隐期。这一时期,王禹偁的七律风格基本以闲适为主题,而闲适中又带着淡淡的惆怅和倔犟的不甘心,如作于雍熙元年的《官舍书怀呈罗思醇》,作于雍熙四年(987)的《和郡僚题李中舍公署》、《题张处士溪居》等诗都体现了一种慵懒闲适、优游度日的情怀。诗风也同前期白体作家徐铉、李昉一样,有清丽工整,类晚唐风格的一面。但如果仅此而已,他的七律就与徐、李二人没多大分别,只不过从台阁移向了外郡。关键就在于在这闲适中,王禹偁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总希望能够回到朝中,实现自己补时济世的抱负,如作于雍熙三年(986)的《官舍书怀呈郡守》、《长州遣兴二首》,闲适中包含蓄势待发之意。这正是新兴一代士人和五代入宋士人最明显的区别。闲适之感,是时代风尚。太宗提倡“无为而治”,朝野以官闲为吏治的标准,所以王禹偁初期七律以唱和形式表达闲适之感,是时代诗风的影响。而在闲适中总有一颗为霖为雨、救时补阙的治世之心,有一种不甘平庸、期待奋发的个性精神,这才是新一代士人面貌的体现。也正是这种渴望自我实现,渴望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才使得王禹偁的闲适七律迥别于徐、李二人,像是浓云中却有几道阳光穿过,鲜亮刺眼,力度所在,不能逼视。
王禹偁的七律送行诗基本集中在端拱元年(988)至淳化二年(991)在京任职期间及淳化五年(994)再为知制诰期间。端拱元年(988),王禹偁入朝为右拾遗,此期间他的七律题材发生了明显变化。除了个别咏怀诗外,主要以送行诗为主,另外还有数首寄赠、祝贺类。从题材上看,此期七律功能基本以应酬为主。
就送行诗而言,王禹偁的七律与唐人同类题材之作有很大区别。以刘长卿《送耿拾遗归上都》为例。诗中没有具体的人事关系,耿拾遗的家世地位、门第功德亦无一语提及。只是言及友人间别离之悲,相隔之远,忧伤之情,郁结于胸,回环吞吐,总难有酣畅淋漓的表达。王禹偁送行诗意趣与此迥异,如《送查校书从事彭门》,全诗基本为叙述语气,有赞赏,有期许,就是没有离别之悲,淡化了唐诗对离情别绪的反复渲染,强化了对对方的赞赏与劝慰。
情绪的转变引起创作手法的改变。其送行诗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征实性。《送光禄王寺丞通判徐方》一诗中有作者自注,言:“少仪丈人,顷年载笔徐方,访闻今通判亭,即翩翩廨宇也。父子继出,士人荣之。”[1]这就使得诗句紧扣被送人,是典型的“这一个”,而不可移往他人。唐人送行,如上举之例,几乎只言情,不叙事,固然是送耿拾遗,另换作他人亦未尝不可。王禹偁此种以平淡的叙述性语言作送行诗,并以入实手法紧扣被送人的身世,淡化了送人之作应有的悲情,加强了应酬成分,基本奠定了北宋七律送行诗的模式。
送行诗在北宋七律创作中所占比例极大,这与北宋官员的频繁调动有关,此处不论。只就王禹偁七律诗中大量的送行之作而言,可见在北宋初,官员出外任多有送行之诗,且一般以七律为主的应酬形式已形成规模。北宋中后期,尽管此类诗作用典成分得到强化,有的甚至是句句用典,密不可读,但基本格调与手法已无多大变化。送人之作从唐代重抒情到王禹偁诗重叙事的转变,已初步显示出宋人精神意趣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他们对感情的节制,对悲情的扬弃,对人物事件所表现的求实内敛的心态已逐步表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其著名的五言古诗《对雪》发扬了白居易新乐府的讽喻精神,针砭时弊,激烈刻露,毫不留情,被誉为“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典范。[2](P79)此诗作于太宗端拱元年(988),而此期王禹偁的七律基本忙于应酬,非送行即祝贺,对类似《对雪》的现实内容几乎无所涉及,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不同诗体在内容表现上的分野。
王禹偁于太宗淳化二年(991)九月贬商州,这次贬谪对诗人的心灵震荡极大。他的七律诗风及题材取向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期以怀古、贬谪、咏怀之作为主,并模仿元、白写了五首《放言》诗。这段时期,他不仅以白诗为消遣,并时常涵咏杜诗,得其滋养。因此其七律诗作以贬商州时期数量最多,质量亦最高。
抒发贬谪之情是诗人此期七律诗作的主题。但他的贬谪之情是借多种手法来表现的,这一点和唐人七律贬谪诗略有不同。唐人贬谪七律以柳宗元最有名,柳宗元的贬谪之感多借外物予以委婉曲折的表现,因此有“哀怨有节,律中骚体”[3](P541)之称。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也是唐人七律贬谪诗上乘之作,显示出诗人以为朝廷除弊为己任,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的耿介品质与人格魅力。王禹偁诗既不像柳宗元那样含蓄委婉,也不像韩愈那样激情澎湃。他的贬谪之情表现手法是多元化的。在他的贬谪七律中,“逐”、“谪”之类的字眼常常直接出现,如《送舍弟赴举因寄两制诸大僚》、《春日登楼》等,可见无论与人交往还是独自静处,诗人的心思总时时纠缠于放逐之感,难以解脱,并时时以贾谊自比。
远贬外郡,诗人似乎又回到了远宦长州时期。此期的诗作中,又有了表现闲适之感的作品,但心境不同,诗意自然迥异。前期的闲适中如果还有奋发,此期的闲适却显得惆怅迷茫,如《寒食》、《日长简仲咸》、《和安邑刘宰君见赠》等。他有着与白居易一样的安命守分思想。在世事难遂人意时,他常常将其归之为命,由于没有白居易晚年那种放达的心态,所以他的安命守分往往显得自怨自艾,低沉消极。但即便在贬谪之时,诗人也仍然惦念着能够再有大鹏展翅的一天,他在《酬仲咸雪霁春融偶题见寄之什》一诗中曾言“君愁别离烟花好,我待量移翅羽开”。无论诗人如何对闲适退隐之意津津乐道,济世求宦之心仍然是他不能放弃的初衷。
在此期间,诗人模仿元稹、白居易作《放言》诗五首,是其表现贬谪之情的另一种方式。《放言》五首连章组诗为元稹首创,作于其贬官江陵之时,诗以讥讽议论语气表达了对世事人生的失望及佯狂泄愤之态。此组诗极得白居易赞赏,被认为“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辞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评价极高,并于远谪浔阳途中,拟其体制,续作五篇。
白居易《放言》诗摒弃了元稹诗中的佯狂之态,而对世事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王禹偁《放言》诗继承了元、白借理性议论方式表达自己贬谪后对人生存在价值的思考。他在《放言》诗序中言:“元、白谪官,皆有《放言》诗著于编集,盖骚人之味道也。予虽才不侔于古人,而贬官同矣。因作诗五章,章八句,题为《放言》云。”[4](P720)可见,他对元、白《放言》诗,从内容、形式到心态都全面认可。
王诗虽然也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怀疑,但他对儒道达济穷退的执著要甚于白居易。白居易后期已是穷达皆退了,王禹偁却始终坚持着济世的理想,这使他的《放言》诗,虽然形式类白,却没有陷入白居易那样的虚无,还坚持着“进须行道退忘机”(《放言》一)的原则。王禹偁《放言》诗语言也比较质实,少白诗那种灵性的思考和精妙的比喻。
贬商期间,王禹偁通过对杜诗的观摩学习,提出了著名的“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的见解。学习杜诗使得他此期的部分七律偏离了白居易的直白浅切,而具有含蓄蕴藉、一唱三叹的韵味。如作于淳化三年(992)的《清明日独酌》、《寒食》、《官舍竹》、《村行》、《新秋即事》三首,淳化四年(993)的《幕次闲吟》五首等,都颇有杜诗风味,是此期成就较高的诗作。
诗人在认为“子美集开诗世界”后,同时又提出“伯阳书见道根源”,这就表明他终未能领会杜诗中那种深广的忧愤,再加上受白居易安分守命思想的影响,使得他的部分七律纵然略有杜诗沉郁的一面,却终无其顿挫之感。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言其诗“五言学杜,七言学白,然皆一望平弱”[5](P80),虽然贬之过甚,也说出了部分事实。
王禹偁于太宗淳化四年(993)四月再为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995)五月又因事贬滁州。第二次贬谪,诗人的心态比第一次更加退缩。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咏怀诗,如作于至道元年(995)的《滁州官舍》二首、《为郡》、《自笑》、《夜长》、《今冬》等都表现了相同的思退之意。初次贬谪还念念不忘的“道”,如今也无心去思,朝廷的事情也无意去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至道三年(997)的《病起思归》透露出他明时退隐的不甘心。也就在同年,真宗继位时,王禹偁上《应诏言事疏》,对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被认为是其一生最重要的政论,并直接影响到范仲淹的改革措施。[3](P168)可见,虽然其诗作中常流露出退隐之意,但在思想上仍无时不在做着重新回朝的准备。即使在其最后一次贬黄州之时,仍可看出诗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也是为什么王禹偁最终能从白居易上溯到杜甫的原因之一。同理,也正因为受白之影响较大,而终未能像杜。
二、王禹偁七律创作技巧的沿革与新变
在创作手法上,王禹偁有明显的宗白居易倾向。首先,语言以质朴自然,不事雕琢为主。如其《书怀简孙何丁谓》中有“三入承明已七年,自惭踪迹久妨贤”,顺畅得如同口出,这是王禹偁七律最基本的语言特色,类似诗句俯拾皆是,也是其诗为什么被归为白体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其二,七律诗作多以叙述为主,章法较顺,体现了较强的叙事功能,有典型的“以文为诗”的特征。除了前文所论送行诗大多如此外,其他诗亦有散文化倾向。
其三,“以议论为诗”的特征在王禹偁七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议论入律,显示了七律中理性思考气质的加强,抒情性的减弱。如果说杜甫加强了七律的抒情化因素,白居易则强化了七律的理性气质。王禹偁继承了白居易七律的这一特征。如前文所论《放言》诗就是明显的议论体七律。王禹偁七律中的议论性诗句如同其语言直白一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创作手法,贯穿到了任意题材的诗作中。如其怀古诗《过鸿沟》即如此。
怀古诗与咏史诗不同。咏史诗多就史实发表自己的看法,议论较多,理性较强。怀古诗多就历史遗迹抒发感慨,抒情较多,感性较强。其《过鸿沟》前四句却是议论,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对作为楚汉分界线的鸿沟所能起到的历史作用的怀疑。诗后四句试图借对景物的描写渲染一种衰败之景,表露自己被贬谪的心情。就议论和景物描写两方面分别而言,都较成功。前半段的议论很有见地,后半段的景物描写也非常精彩,但合起来却有一种西装配马褂的不和谐感。方回评此诗言“元之诗学乐天”,可能就是指前半段的议论而言,又评其“殊觉高古”当指后半段作者的感慨。纪昀评其“后半游骑无归”[6](P135),颇有见地。无论此诗风格如何,我们都可看出,即便是在不适合议论的题材中,王禹偁仍不放弃他所钟情的手法。
其四,在七律创作的对仗、字法、章法上,王禹偁都有明显学白居易的迹象。就对仗而言,其诗中流水对非常多,这正是白居易七律一大特征。流水对与上文所言及的“语言质朴”及“以文为诗”相关,是这两种特征在对仗上的表现。如《留别仲咸》、《幕次闲吟》、《再赋一章用伸赠别》等,这些诗中对仗看似随意,实则工整,显示了诗人在严整的格律中游刃有余地运用语言的本领。复字的运用也是白居易七律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在王诗中亦有明显表现。数字的运用也非常频繁,淡化了诗句的视觉密集度,使诗作看起来轻松疏散,毫不费力。
在章法上,王诗有整体模拟白诗之作,如其《上元夜作》正是模仿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诗体式,尽管两首诗表面看来极为相似,但从中已可看出唐宋诗作法的微妙差别。二人诗的前二联,格式虽同,写作手法却异。王诗二句、四句是用叙述性语气,述说了自己不同时间的不同境遇,比较坐实。白诗却用两个地名作对比,至于人物在做什么,由地名所提供的思路即可想见,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想象空间。后两联,王诗亦是直接叙事抒情,人物的活动、心态一览无余。白诗则以抒情为主,空灵跳荡,语浅情深。这也是宋诗质实与唐诗空灵的区别所在。
王禹偁七律学杜诗,在诗中不时流露出的忧国忧民之思与身世之感,使得诗作摒弃了晚唐的愁苦之音,而变得沉郁,有深度,有力度,正是作者所谓的词笔要“健”。比兴手法入诗,也使得他的部分七律偏离了白体的浅切直白,显得委婉多讽,如《春晚游太和宫》、《官舍竹》等,从这些看似描写自然的诗句中,我们能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及诗人孤贞自守的品节。白居易七律不多用典,而老杜诗则被宋人认为“无一字无来处”[7],王禹偁同样吸收了这一手法,在诗中使用了一些典故,但其用典方式比较简单,典故也较常见。这种沉郁风格的形成,比兴、用典手法的注入,使得王禹偁的部分七律显得平淡而有思致。
与徐铉、李昉类似,王禹偁诗也有晚唐七律清丽工整的一面。他的许多景物描写,或清丽,或幽静,或凄清,都表现出作者有意经营,意趣类似晚唐诗风的一面。代表作当是那首有名的《村行》,诗中扬弃了晚唐七律思乡的悲苦,继承了其写景的工丽整饬,其“数峰无语”联也有清新警秀之感。
总之,就整体特色而言,王禹偁七律语言直率,多议论,章法以流畅为主,多用流水对,不太讲究结构布局,明显偏于白居易七律风格,但同时又具有杜诗沉郁含蓄和晚唐清丽工整的特征,体现出一种整合性诗风。
这种诗风的形成与作者的文学思想密切相关。诗人对五代诗风极为不满,认为:“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高公在紫薇,滥觞诱学者。自此遂彬彬,不荡亦不野”(《五哀诗》)[1]。由此可见,他反对五代以来的艳冶之作,希望建立一种不荡不野、典雅醇正的诗风。他欣赏李白诗,认为是“颂而讽,以救时也;僻而奥,以矫俗也;清而丽,以见才也”,他的七律正是这种文学主张的实践。
三、王禹偁七律的诗学地位及诗学史意义
王禹偁幼习白居易诗,其《不见阳城驿》诗序云:“予为儿童时,览元白集,见唱和阳城驿诗。”[1]后贬商州,更“多看白公诗”,受白居易濡染颇深。王禹偁对白居易的体认较为全面,除受时风影响,有闲散颓废之作外,他更继承了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8](P962)的精神,如古诗《对雪》、《感流亡》等皆是这方面的典范。在七律创作上,除闲适唱和诗外,他还继承了白居易七律议论讽刺的风格,如其模仿元、白所作的《放言》诗即为一例。他由白居易直接追溯到杜甫,以诗句偶然像杜而自喜,并认为“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对杜诗的体认源于精神气质上与杜甫的相通,其《吾志》诗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出一辙。清人吴之振《宋诗钞》曾言:“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接流响……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则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也。”[9](P13)吴之振敏锐地看到了王禹偁在学杜方面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这种对白居易、杜甫的关注现实精神的继承,启发了后来的欧阳修、苏舜钦等人,而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声。欧阳修的七律在选材及手法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白体倾向,成为王禹偁七律在北宋的直接继承者。他曾评曰:“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10](P78)苏轼七律也呈明显的白体倾向,成为北宋白体七律创作的代表及最后的终结。他也曾从文章、德行等方面激赏王禹偁,认为其“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11](P603)。欧、苏可谓北宋中期及后期文坛的主盟,从二人对王禹偁从文章到道德风范的全面体认,不难看出,作为北宋自生的第一代士人,王禹偁为北宋历代士人所立的典范作用。
其七律创作在北宋初期诗坛成就最高,他对早期的白体七律从题材、风格到创作技巧等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试,为白体七律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格局。
首先,王禹偁的七律题材远比前期白体诗人丰富。前期白体诗人徐铉入宋后题材范围极窄,除奉和应制,就是寄赠、送别,前已论述。李昉诗由于存诗仅限于唱和诗集,无法全面比较。但从其唱和集诗所体现的精神意趣而言,应与徐铉相近。王禹偁七律除寄赠唱和外,尚有咏怀、怀古、登临、咏物、记游等,其中以作于贬谪期间的咏怀诗最多,成就亦最高。他还模拟元、白作议论体七律《放言》诗,此种七律为元稹首创,自白居易仿作后,唐人七律中无后继之作。百年以后,见于王禹偁集,亦属后世知音。
其次,王禹偁七律的风格意趣也与前期白体诗人截然不同。他的七律诗作中重新恢复了杜诗所注入的爱国忧民传统,尽管数量有限,毕竟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除此之外,其七律诗中以贬谪之意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的贬谪诗与柳宗元的七律贬谪诗不同,柳诗长于以骚体手法表现其悲愤难以化解的愁怨,王诗则多采用白居易式直截了当地叙述议论手法,试图借老庄、屈骚及禅释之意加以化解,体现了宋人的人格意趣异于唐人的一面。尽管有学者认为,作为白体诗人王禹偁和徐铉、李昉一样,很多诗都表现了闲适情趣。其实,仔细体察就会感受到王禹偁的闲适中总有一种无奈,一种不平。他与徐铉入宋后小心翼翼的闲适、李昉志得意满的闲适皆有区别。他的闲适源于他的思想中有着和白居易相同的“安分知足”的一面。但白居易的七律闲适唱和诗多为晚年居洛上所作,这时的诗人在饱经世变、阅尽沧桑后,借禅悦、诗酒聊以度日,是一种全身远害,知足保和的闲适,同时也是一种颓唐的闲适。徐铉、李昉诗多类此。王禹偁则不然,看其闲适诗的创作时期即可明白。他的七律闲适之作集中在吴门三年为吏期和其后漫长的贬谪岁月里。吴门时期,其闲适中透着不甘心,总是蓄势待发;而贬谪期多在愁怀难遣的时候,借以逃遁。终其一生,穷达起落不定,求闲思退之心,固然常在,而忠君报国、革新救弊之意,亦未尝少衰,这两种情绪常交替进行,这也正是为什么其七律最终没有跟随白居易走向颓唐,亦偏离了徐铉、李昉的庸弱而上溯到了杜甫的原因之一。
总之,王禹偁七律中已经含有宋诗渐变的因素,以议论为诗、重理性、重思致及以文为诗、重叙述、重铺排的特征都已逐步露出端倪,因此有“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一说[9](P13),但这种开拓非常有限,仍然在白体的范围里讨生活,就七律这种本身就有程式化趋势的诗体而言,模仿痕迹较重,未能将诸种手法融会贯通而显得较为生硬,明显体现出沿多变少的特点,因此四库馆臣言其欲变五代诗体而力有未逮[12](P1308)。
[1](宋)王禹偁.小畜集[M].四部丛刊本.
[2]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清)王夫之.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傅璇琮,等.全宋诗(第2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清)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元)方回.瀛奎律髓汇评[M].李庆甲,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宋)黄庭坚.山谷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
[9](清)宋荦.宋诗钞·小畜集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11](宋)苏轼.东坡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