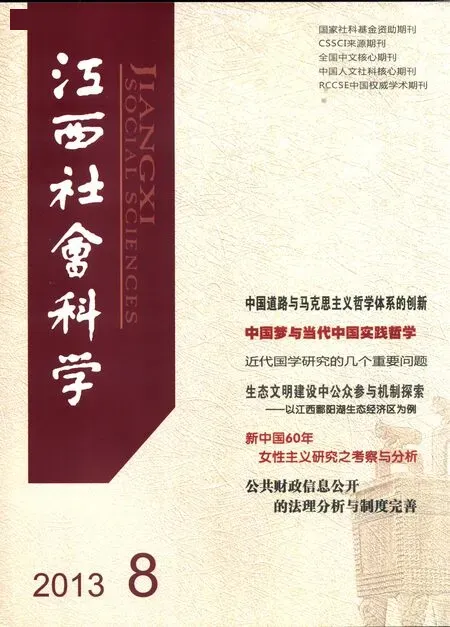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工具论、集体性、公式化——以“白蛇传”改写为中心
■李 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了文学创作,具体又有何体现,是个有待于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十七年文学的生产机制、文艺与其外部环境的复杂关联、文学的传承与革新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蛇传”改写为个案,以期对此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20世纪50年代,外部因素对文学显示出强劲的影响力,文学批评和创作去除了“个人”标签,带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戏改”成为具有任务性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白蛇传作为传统戏曲的重要剧目之一,自然也在被“改”之列,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相当多的“白蛇传”作品。集体改写的特点很鲜明,虽然不少作品署名个人,然而不具有个性色彩——作品包含着强烈的“集体意识”。尽管其声势浩大,然而总体成就不高,主题非常单调,情节严重雷同,人物形象脸谱化。
一、集体改写的弊端
很多白蛇传改写作品的署名就是“集体”,如川剧《白蛇传》由前重庆市戏曲曲艺改进会集体整理。即使那些署名为“个人”的作品,也是集体参与的产物,作者在改写中必须服从集体需要,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意见,根据群众意见构思、修改。如田汉就明确说《白蛇传》是“好些人”在一块儿磨出来的,剧本在周扬的帮助下经过多次修改;赵清阁也明确说她在改写时除参考有关资料外,还不断观摩各种《白蛇传》戏曲演出,和文艺界友人进行反复讨论。这种集体性因素还表现为改写者借鉴同期其他白蛇传作品,故而不同的改本之间会出现情节、人物台词的雷同,最明显的就是豫剧《白蛇传》,它是王景中根据田汉剧作略加改动而成。作者匍匐在时代和集体巨人脚下,缺少了充分的创作自主性,作品势必主题相同,情节、人物相似。
曹禺曾经指出观众对编剧的影响:“至于观众能影响编剧,更是显然的,因为戏是演给观众看的,剧作者对观众的性质若不了解,很容易弄得牛唇不对马嘴。台上的戏尽管自己得意,台下的人瞠目结舌,一句也不懂,这样的戏剧是无从谈起的。”[1](P141)编剧当然不能脱离群众,但是若从撇开群众走到听命群众的极端,同样难以产生优秀的作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对于编剧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几乎“左右”编剧,如曹聚仁所说的“观众批准”与“加工”:“今日很流行‘观众批准’和‘加工’两个术语,他们是观众的教师,观众也是他们的指导人,他们接受了群众的意见来把戏曲加工……”[2](P376)剧作家若要完全听从于群众而剔除了个人的独特见解,使自己的个性泯灭,则无疑是艺术创作的悲哀。集体改写使得文学作品失去独特性,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严重。剧作家夏衍说过:“公式、概念、面谱,是艺术工作者的不能妥协的敌人。”[3](P539)
文学创作不可能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创作不能完全听命于外部环境。席勒说:“艺术家固然是时代之子,但如若他同时又是时代的学徒或时代的宠儿,那对他来说就糟了。”[4](P32)论者们都强调了作者不能顺从时代,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会有更为独特、深刻的思想力量。而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作者们不能独立自由地展现自己的艺术见解。理想的状态是“百花齐放”,不同的作者在作品中显示出不同的个性,适合不同观众的需要,因为观众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只是这种理想状态在当时难以实现。
二、单一的“反封建”主题
白蛇传改写作品主题很单一——反封建,批判以法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颂扬以白蛇、青蛇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新的时代精神得到大张旗鼓的宣扬,阶级斗争、反帝反封建无疑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具体化。戏曲改革所要做的就是“推陈出新”,肯定“新”否定“旧”,将阶级斗争理论贯穿其中;只是过于强调“新”,强调阶级斗争的合理性,使得白蛇传的丰富、复杂内涵被简单的阶级斗争所取代,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显然是对复杂人性内涵的简单化处理。如有论者批评的:“那种强调阶级斗争无所不在,把阶级斗争贯穿于戏曲创作一切题材的理论和实践,曾使现代戏产生大量概念化作品,历史题材的创作和传统剧目的改写,也因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走入反历史主义的死胡同。这种错误的作法,还长期被认为是‘推陈出新’。其实,这种‘出新’恰恰降低了对社会生活(包括历史生活)的认识理解作用,把无比复杂生动的社会生活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僵化的公式。”[5](P665)
激进主义的烈火往往会焚掉人类积淀的文明之花,甚至那些已被确认的永恒的因素,比如人性。韦勒克、沃伦就曾指出过于强调“时代精神”会造成的弊端,“‘时代精神’的概念也常常给西方文明连续性的概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各个时代的特征被想象得太分明,太突出了,以致失去了连续性,这些时代的革命被想象得太激进了,这样,那些‘精神学家们’最终不仅会陷入地道的历史相对主义(这个时代与那个时代一样好),而且还会陷入个性与独创性的虚假概念中。这就会忽略人性、人类文明与艺术中那些基本的、不变的东西”[6]。
时代的变化固然会带来时代精神的某些变化,然而并不意味着全盘抛弃既往,因为否定与继承是并存的。郑宪春说:“要调整旧的戏剧与新的观众之间业已倾斜的心理天平,就只能用改编来实现新的心理平衡,用新的创作达到新的平衡。改编就是否定,即在原有的戏剧形象上注入一些新的精神。自然,否定中也有继承,对于原作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戏剧精神,改编者总是尽量予以保留,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7](P262)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蛇传改写,在激进的语境中强调激进,在否定的思维中强调否定,由此使得作品的工具化色彩过于鲜明。
三、雷同的情节与脸谱化的形象
这一阶段的白蛇传改写,在情节上极为相似甚至雷同——淡化白蛇和许仙(许宣)之间的矛盾,增强法海一方与白、许一方的矛盾,渲染白、许之间的恩爱,暴露法海一方的腐朽、残忍和歹毒。服务于反封建主题和美化白蛇形象的需要,“水漫金山”普遍增加了白蛇筑堤保护镇江居民的情节,有些作品干脆只写水淹金山,对水淹镇江居民之事绝口不提。有的作品虽以白蛇被镇压在雷峰塔下收场——暴露封建势力的腐朽和残忍,但普遍情况则是写青蛇来毁塔,打败法海或者塔神,救出白蛇,以体现人民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很多作品出于凸显正义力量强大的缘故,写小青仅仅经过十几年(或更少)就打败法海救出白蛇。无一例外的是,白蛇之子中状元祭塔、白蛇出塔升仙等情节均被删弃,因为那意味着对封建势力的妥协。服务于反封建主题,有些作品更因极力丑化法海而出现情节上的矛盾之处,难于自圆其说。种种情节矛盾,在当时的作品中非常普遍。
人物形象塑造则完全采取二元对立的原则,非此即彼,缺少性格的复杂性。这一时期作品极力丑化法海,美化白蛇,彰显青蛇的斗争精神,而淡化许仙(许宣)的薄情行为。这种形象的塑造,自然是阶级斗争影响所致。在阶级斗争的呐喊声中,与现实相距甚远的神话人物也被卷入漩涡。
为了美化白蛇,很多作品甚至剔除水漫金山对镇江人民造成的灾难,白蛇不但毫无过错,还救苦救难,像观世音一样受人敬仰、爱戴,这完全有悖于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其形象虽然高大、完美,然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联系当时的创作氛围,白蛇的完美人格无疑是理想革命者的投射。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法海被极力丑化,罪大恶极。法海的形象与白蛇一样,都存在缺陷,十足的美好与完全的恶毒都过于简单化、表面化,坪内逍遥说:“在创造这些人物时,如果不能深刻写出这种善人也还有烦恼,这种恶人也还有良心,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仍会有所迟疑逡巡,那么这种描写必然停留于表面状态,还不能说是达到逼真的境地”[8](P52)。王朝闻也曾批评过人物“类型化”的现象,“从文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关系来考察,某些图解观念的创作意图,某些把好人写成一看就是好人,把坏人写得一看就是坏人,这种类型化的形象,既缺乏艺术性,也是作者思想贫乏的表现”[9]。
在塑造许仙(许宣)的形象上,作品通常写他起先轻信、懦弱,向法海妥协,后来逐渐觉醒,坚决反对法海。王蒙曾就法海、白蛇、许仙(许宣)的形象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解放后的各种剧种的《白蛇传》,无一不是扬白(蛇)贬法(海)嘲许(仙)的。许仙愈来愈象一个动摇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了”[10]。王蒙并没有全面、深入研究过白蛇传,实际上1949年后的“白蛇传”戏曲中,为了显示法海的罪恶,许仙也开始勇敢地反对法海,许仙不再是“动摇分子”。在相当多的作品中,许仙的斗争精神也极为勇敢,有的作品甚至将其斗争精神描写到极致——为救白蛇而被法海打死。
青蛇的斗争形象得到充分展示,在以“胜利”结尾的“白蛇传”作品中,青蛇毁掉雷峰塔,救出白蛇。为了强调青蛇的斗争精神,一些作品甚至无意中走到了反面,青蛇滥杀无辜,不加区别地要将和尚全部消灭。
四、过度的夸张
创作者的主观态度过于暴露,损害了作品的含蓄之美。恩格斯曾一再强调创作要避免情感的过分宣扬,“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蛇传”改写,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爱憎鲜明”、“立场明确”是作者必须注意到的事情,作者有意识地引导读者认识到作品的情感倾向,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褒贬分明的语词来形容人物的言行,或者赤裸裸地加以议论,凸显作者的声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赵清阁的小说《白蛇传》。作者在描写法海时使用大量贬义词来暴露法海的丑陋,如盛气凌人、鬼头鬼脑、狡黠、狰狞、冷酷无情、恶毒、气势汹汹、悻悻然、忿忿然等,还时常站出来表露自己的情感态度。作者过于注重情感倾向的表露,无疑会干扰人物塑造的“公正”,出现“虚伪的夸张”。
“虚伪的夸张”甚至使很多作品出现“硬伤”,比如何迟、林彦的京剧剧本《新白蛇传》的台词就几次出现纰漏。如白娘子对许仙说:“你我夫妻自西湖舟遇至今,数年来如一日,自问无负官人……”[11](P84)其实白、许从舟遇至合钵,时间是一年左右,“数年来”之说显然欠妥。再南极仙翁批评法海之词也不当:“屡次拆散他二人美好良缘,害得妻离子散。”其实,白娘子尚未产子,因此“子散”一说是错误的。类似这种“硬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蛇传作品中比较普遍,很多作品的情节出现严重纰漏。深入考察,我们将发现,这显然不是“笔误”或者“粗心”之类的问题,而是表达了作者对作品主题、人物和事件的情感态度,而这又与当时文学的外部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是社会整体思潮的一个表现和反映。
五、非学理化的批评
文学呈现出非学理化倾向,批评很难发挥应有的功能,其对文学创作的指导很大程度上不是“艺术的”。
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田汉在戏曲改革时曾这样强调:“理论批评是指导和推动戏剧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有好剧本、好演出,不能不期待好的批评文字。”[12]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非但不能“尽职”,反而成为文学的羁绊。就如陈白尘在《太平天国·序》中所说:“不能不令我感到灰心的,是我们的戏剧批评家,一个剧作者要想从戏剧理论家与批评家那里得点创作上之指导,真比上天还难。他们的工作除了鉴定一个剧作者属敌属友,而分别给以或压或捧之外,好像就无所事事。而他们所知道的仿佛也仅是一顶高帽子与一套术语罢了。”[13](P238)
在“戏改”浪潮中,评论界关于白蛇传的文章几乎都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如戴不凡的《评“金钵记”》等,然而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秉持公正、无私的态度。由于文学外部环境的影响,尽管白蛇传的改写普遍存在缺陷,却鲜有人敢于站出来批评。若说当时没有真正的批评者似乎也不准确。许多年后,《傅雷家书》问世,傅雷对于白蛇传改写的激烈批评也就发人深省。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傅雷陪母亲看了“青年京昆剧团赴港归来汇报演出”的《白蛇传》,写下这样最为真实的感受: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于剧本“意见可多啦”,不如老本子“入情入理”、“有曲折有照应,逻辑很强”;改编本虽大有翻案意味,而戏剧内容“并不彰明较著表现出来,令人只感到态度不明朗,思想混乱”,“总之是违背情理,没有logic,有些场面简单化到可笑的地步”……他还总结说:“总而言之,无论思想,精神,结构,情节,唱辞,演技,新编之本都缺点太多了。真弄不明白剧坛老前辈的艺术眼光与艺术手腕会如此不行;也不明白内部从上到下竟无人提意见:解放以来不是一切剧本都走群众路线吗?相信我以上的看法,老艺人中一定有许多是见到的;文化部领导中也有人感觉到的。结果演出的情形如此,着实费解。报上也从未见到批评,可知文艺家还是噤若寒蝉,没办法做到百家争鸣。”[14]傅雷直陈剧本之弊端,直指弊端之根源。在一味强调“出新”的戏曲改革中,人们迷失在狂热的薄古厚今的狂欢语境里。傅雷的批评对于重新认识戏曲改革,具有极大的意义和警示作用。文艺自身内部规律及其与外部因素的关联非常复杂。“戏改”时期的文艺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因而往往损伤自身的艺术性。在集体改写的时代浪潮中,个人性被压抑,作品因此缺少个性特色,故而出现雷同的主题与情节、脸谱化的形象、非学理性的批评等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对于我们在当今宽松的文艺创作与研究环境中,更好地处理文艺与外部因素的关联,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性。
[1]曹禺.曹禺全集(第5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2]曹聚仁.人事新语[M].北京:三联书店,2007.
[3]夏衍.夏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4](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6](美)勒内·韦勒克,等.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郑宪春.中国文化与中国戏剧[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8](日)坪内逍遥.小说神髓[M].刘振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9]王朝闻.寓教育于娱乐[J].文学评论,1979,(3).
[10]王蒙.《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J].读书,1989,(4).
[11]何迟,林彦.新白蛇传[M].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52.
[12]田汉.快马加鞭发展话剧[N].人民日报,1959-03-19.
[13]田本相.现当代戏剧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14]傅敏.傅雷家书(增补本)[M].北京:三联书店,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