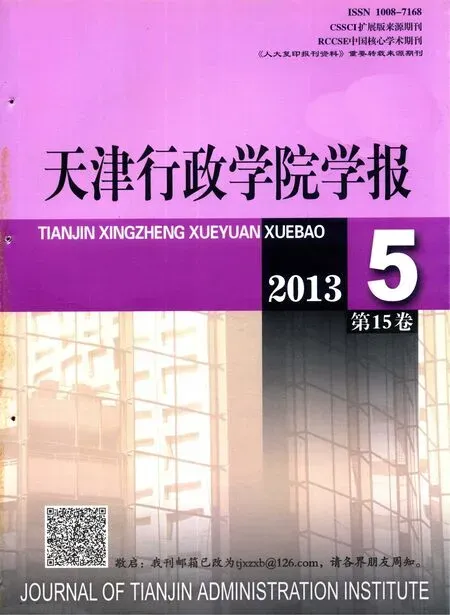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三种误解
刘 近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更多的是被称为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而在国外学者的话语体系中则被称之为“中国模式”[1]。国外一些学者已经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触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核心领域,并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若干需要我们重视的观点:共产主义不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难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输送理想信念;“发展”已不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手段,而成为了最终目的。对于以上种种误解,我们有必要进行仔细地梳理和认真地分析,以期引起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研究者对国外相关动态的关注,进而共同深化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误解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从目前来看,正像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往往以中国模式为理论概念一样,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注并没有、也很难直接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下,但是这并不影响国外学者就此展开比较深入的讨论并形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观点,主要是通过间接否定与直接否定两种思路得出的。
所谓“间接否定”的思路主要是指一些国外学者通过直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而间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最高追求。其实,国外学者在不断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他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问题,抱持何种立场已经显而易见了。可以说,在他们直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也就间接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持的否定态度,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可以说,这种思路影响的范围最广、形成的时间最长。在相当多的国外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所制定并实施的一些政策并不能同社会主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在他们眼中,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其未来的发展趋向也便不可能是共产主义。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中国特色多于社会主义”的水平。其中,在一部分学者那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贴上了“市场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红色资本主义”、“特有的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等各式各样的标签。比如,布鲁斯·迪克森在其《红色资本主义在中国》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已经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民营企业主被中国共产党所吸收,并据此断定中国已经开始走向“红色资本主义”[2](p.157)。相比较而言,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的态度显得更为隐蔽。在沃马克的认识中,毛泽东与邓小平实际上努力追求的是相同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表明了一种日益增强的信念,即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其名称如何,这个制度将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后革命时代出现的道路的独立性。”[3]尽管,这种观点中带有很强的肯定性成分,但是其阐发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中国特色多于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上。
如果说“间接否定”的思路是我们从以上国外学者有关思想中引申出来的话,那么还有部分国外学者则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其中,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的态度可以说是“直接否定”思路的代表。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体制的特征是意识形态逐渐为务实所取代,即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上,已经从一个阶级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4]。中国共产党在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根据中国共产党所提出“和谐社会”目标就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显得过于简单化了。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并具有寻求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宣布不再高攀一种作为乌托邦理想的社会主义,但也决不会‘低就’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不是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是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5]。阿里夫·德里克的误解产生的原因在于,过于强调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思路与方法,进而造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相当程度的割裂与背离。从而使其认为,虽然社会主义理想仍被视为中国未来的终极目标,但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在当前与未来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已经丧失了直接性的影响。这种误解的内容及其论证的逻辑,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6]。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领导中国人民所做一切都是在朝着“乌托邦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在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的优势与活力的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偏离了社会主义、远离了共产主义,而是坚持、发展了社会主义,更加接近了共产主义。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外学者在热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尽管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同时又不约而同地有意淡化和掩饰“中国奇迹”的“社会主义”色彩。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前提性的基础概念仍然没有真正进入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之中。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一方面,中国和平崛起造成的世界向东方倾向,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西方世界希望看到的。另一方面,对于这种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的真正的和根本的原因,他们只能选择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轻描淡写,总之就是不愿归结为社会制度层面。“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最乐于使用的概念[7]。在这种潜意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更难以进入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国模式问题上国外学者还存有各自不同的认识和主张,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的内在原因了。
误解之二: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维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能力
如果说误解之一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质疑基础上产生的话,那么误解之二则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脱离。持此种误解的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一个能够凝聚共识、引领方向的理想追求。在他们看来,这种状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难以继续支撑或维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学专家郑永年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他看来,日益弱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已经导致了精神真空的产生。从目前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发挥的更多的是一种协助政策调整的工具性作用,已经无法给社会成员再提供任何的理想[8](p.246)。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郑大伟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大众和政治合法性还面临着意识形态吸引力的下降和道德真空扩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缺乏一种足以凝聚社会共识并指引国家前进方向的宏伟愿景。而且从经典作家到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他们所提出的种种理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以郑大伟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往往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经典作家对于未来的构想已经黯然无光,原因在于经典作家意识形态吸引力在现实中的影响已经被削弱到了不被社会认同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本身又没有提供其他足以令人信服与信仰的未来图景。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主张都没能有力地唤起和带动整个国家。基于此,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领导集体所面对的核心挑战不单单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紧跟国家的发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启发并引领中国找到新的前进方向[9]。
阿里夫·德里克在对中国模式所做的批判性分析中指出,中国之所以引起世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吸引力不在于“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的成立则是通过否定过去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来实现的,人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否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甚至对共产党领导层而言同样如此。同时,对当今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政策中客观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和实践之间的脱节事实熟视无睹,是极为不成熟的表现。如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已经不再被大部分的中国人所关注[10],他比较委婉地表露出了“砍旗”的意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脱离于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发展道路。对这种观点,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这在任何时期、任何阶段都是不会动摇的。
不难看出,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当前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跟不上社会的进步,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方向或者目标,尽管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已经无力引领整个国家。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无法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景或理想目标,断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很显然,这样就简单地否定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还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引导和激励中国人民全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因此,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面临着被轻易否定的危险。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与理论基础,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解决的是举什么旗的问题,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与方向。无论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还是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此相对的是,部分国外学者现在已经不单单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不属于社会主义,同时更进一步地延伸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为马克思主义所指导了。试用通过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误解之三:发展不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而是最终目的
历史告诉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之路。而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还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都需要发展,离开发展谈理想都是空谈、空想。可以说,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词之一。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发展的重视程度使得国外学者产生了一种最为简单化的误解。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中肯地承认,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确确实实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跨越和社会进步,但是在他看来,“这种进步的实现则是以严重的社会破坏和空前的精神穷困作为巨大代价的。‘信仰危机’在青年群体中正变得日趋严重”[11](p.142)。对此,我们认为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带来了社会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导致“信仰危机”的根源绝对不能直接扣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之上。
同时,还令迈斯纳担心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面临着来自于共产主义理想弱化甚至缺失问题的巨大挑战。根据迈斯纳的理解,毛泽东时代自始至终既以“现代化的中国”,又以“社会主义的中国”作为奋斗目标。尽管也苦恼于目的和手段的冲突,但始终在为实现青年时期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或者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将科学技术当成了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用生产力来理解与解释社会主义也成为了一种思维惯性或定式,忽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和社会主义的目标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动态性特征。“发展经济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像最终目的了”[12](p.213),在实际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几乎将其等同于不断发展的并最终发达的生产力。共产主义理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被无限期地推迟和搁置。
他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中国式资本主义”,并认为其发展成果越丰硕,共产主义理想就越萎缩。对此,像毛泽东晚年最担心的一样,迈斯纳对于后毛泽东时代是否还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热衷于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的问题而满心怀疑[13](p.531)。相比较而言,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事件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具有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真正体现。而富强则成为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对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定义。在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后者被迈斯纳认定为“反乌托邦”性质的。
因此,迈斯纳指出,“当马克思主义被简化成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时,当其理论实质被‘实事求是’这一法则作了新的定义时,当社会主义本身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经济发展时,理想主义被明显淡化也就在所难免了”[12](p.216)。我们从中在体会迈斯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担忧的同时,也不难感受到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的不理解。但对于我们而言,必须在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关系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在保持稳健的步伐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的同时,牢牢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认清理想实现过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避免出现“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在为现代工业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形式中产生出了对自己的否定”[12][p.6]。
总之,在这些国外学者眼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开始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不会失去领导地位,但迈向的也不再是共产主义;一味强调发展(无论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还是“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使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是“忘记了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进入其目标视野的只有发展,而共产主义目标越来越被形式化。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联系。此外,以上误解的产生也折射出他们并没有真正接触和了解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研究。对于这些误解,除了继续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去化解之外,相关理论工作也要跟上,尤其是我们在加大相关问题“研”的同时,也更要在“传”上下功夫,“研”“传”结合,缺一不可。
[1]肖贵清.论中国模式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1).
[2]Bruce 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olitical Change [M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3]李佑新,陈龙.继承、创新与挑战——沃马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J].国外理论动态,2008,(7).
[4]世界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徐觉哉研究员访谈[J].国外理论动态,2008,(10).
[5][美]阿里夫·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
[6]马启民.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评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6).
[7]秦益成,李荷英.国外学者政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2010,(1).
[8]Zheng Yongnian.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Elite,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M].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4.
[9][美]沈大伟.继续执政: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存在[J].国外理论动态,2011,(3).
[10][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J].国外理论动态,2011,(7).
[11]Maurice Meisner.The Deng Xiaoping Era: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1978-1994[M].NewYork:Hill and Wang,1996.
[12][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3][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王 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