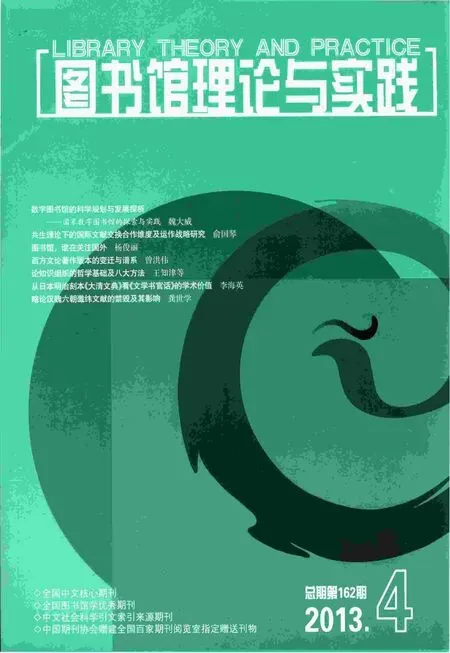西方文论著作版本的变迁与谱系
曾洪伟(西华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在西方文论著作①本文所论涉的西方文论著作主要是指欧美学者所撰写和被我国学界所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作品,不包括国内学者所撰写的有关西方文论方面的著作。版本问题上,我们除了要关注版本的“十三页”(即封面页、书名页、题词或引言页、序跋页、正文页、插图页、附录页、广告页、版权页、书评页、致谢页、书目页和索引页)之外,还应充分重视版本的变迁与谱系。当然,注意版本的变迁与谱系并非仅仅是核对和校正著作的出版信息(如时间)这么简单,而是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系统清理一部著作在本土与异域的版本变迁情况,绘制出关于该著版本的清晰谱系图,这是我们在研究一部西方文论著作之前首先应该做的准备工作;(2)深入考察该著各个版(文)本之间在“十三页”层面上的差异以及其原因,并对其进行意义、内涵阐释;(3)通过比较,探讨一部著作在版本众多的情况之下,应该选择哪一个(些)版本,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相应的西方文论版本遴选原则。下面分述之。
1 西方文论著作版(文)本的变迁与谱系
通过考察西方文论著作出版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西方文论著作在其本土都存在着多个版本。例如,哈罗德·布鲁姆的《The Anxiety of Influence》有1973和1997两个版本,《Kabbalah and Criticism》则有1975,1981和2005三个版本,拉曼·塞尔登等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至今已出版5版,而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术语汇编》目前已是第9次出版。
但是,西方文论著作版本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在本土或者说译出国有多个版本,而且在他国或者说译入国中往往也存在着多个版(译)本。例如,布鲁姆的《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在中国大陆有2个版(译)本,特里·伊格尔顿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在大陆有5个版(译)本。这些不同的版(译)本,有些是由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如艾布拉姆斯的《AGlossaryof Literary Terms》,而有的则是由同一个(批)译者翻译的,如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的《The Theory of Literature》,这充分显示出西方文论版(译)本(在译者层面)的复杂性。另外,在我国还存在着另一种特殊情况,即由于一段时间台湾与大陆之间文化交流的不通畅性(文化分隔),同一本西方文论著作不仅在大陆有译本,同时在台湾也有相应译本。例如,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名著《The Western Canon,Howto Read and》Why以及伊格尔顿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韦勒克、沃伦的《TheTheoryof Literature》等,除了在大陆地区有中译本之外,在台湾地区也有中译本。总体来看,这些台湾版(译)本在翻译水平与质量上普遍较高,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与大陆译本在翻译风格、附加内容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和收藏价值。所以,在绘制西方文论著作版(译)本的谱系图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台湾地区的版(译)本。
关于西方文论著作版本的谱系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原著是以英语以外的其他外国语种(如法语、德语、丹麦语等)撰写的,由于其在学界的影响较大,它被英美学界翻译成英文,然后,国内学界在英文译本的基础上,又将其译成中文;但是,与此同时又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国内学界直接根据其(非英文)原著将其译为中文。例如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弗朗索瓦·于连、勃兰兑斯等的理论著作的翻译就存在这两种情况。由于译者翻译时所依据的文献来源具有多元性(即面对或使用多个不同的版本:英文版、非英文版),因此,从文献来源来看,西方文论版(译)本谱系也具有很大的复杂性。
总的来看,西方文论版本变迁与谱系可分为作者系统和译者系统两大类:前者经作者修订而产生,如伊格尔顿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有1983和1996两个版本;后者由不同的译者翻译产生,如刘峰、王逢振、吴新发等翻译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译本之间,或经相同的译者修订而产生,如伍晓明翻译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三个译本。不过,尽管西方文论版本的变迁与谱系很复杂,但无论是作者系统的版本变迁与谱系还是译者系统的版本变迁与谱系,最终都可以回溯到最初版本的西方文论原著,即用最初的原著版本将整个版本变迁与谱系串联贯通起来。
为什么一定要梳理西方文论版(文)本的变迁与谱系?在以往的西方文论研究中,由于研究者普遍缺乏清醒自觉的版本意识,缺乏对西方文论版(文)本变迁与谱系的有意识梳理,其视阈比较狭隘,往往仅停留于单一的版(文)本上,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忽视了西方文论著作版(文)本的众多性(谱系性)、流变性与联系性,这样,其基于此的结论必然是不准确的。而通过有意识地梳理西方文论著作版(文)本的变迁与谱系,首先在客观上可以改变研究主体错误的认知,改变其对西方文论著作静止、单一、孤立的思维定势,充分认识到西方文论著作版(文)本的变动性、复杂性(谱系性)、联系性,从而使其在西方文论研究中自觉地以整体系统、发展演变、有机联系的目光去审视一部西方文论著作,或者把西方文论著作置放于变迁的著作谱系中去考察与研究:这样其结论自然就是正确的、科学的。因此,梳理西方文论版(文)本的变迁与谱系,对改变当前国内学者西方文论研究的思维与方法,改善和提高西方文论研究的效度、水平和科学性,更新和改变西方文论史的写法,是具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2 西方文论著作众版(文)本在“十三页”层面上的差(变)异
从出版的专业角度来讲,一部著作既然有不同的版本,也就必然意味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作者修订产生的西方文论著作版本谱系中普遍存在,而在译者翻译产生的版本谱系中更是常见:由不同译者翻译产生的译本之间其差别是很明显的,而经同一(批)译者修订产生的不同译(版)本之间其差异也不容忽视。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学界对于西方文论著作版本差异的关注(若有的话)主要集中在正文本上,而对副文本——即除正文本之外的其他十二页——之间的变化与差异则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实际上,西方文论版本在这十二页层面的变化与差异,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左右着文论本体(正文本)研究的性质与结论。因此,我们研究西方文论著作版本的差异,不仅要关注、考察正文本之间的变化,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副文本之间的变迁与不同,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全面、客观、准确的结论。下面以实例来分析、讨论这种差异。
西方文论著作版本正文本的差异。例如,受时代、社会变化和文学、文化理论思潮演进的影响,以及由于著者认识水平的提高,作者往往会对自己先前的著作或进行添加、增补,或进行修改:前者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在其初版《现代性的诸副面孔》基础上,根据当时学术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状况以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及时增加了“论后现代主义”一章,特里·伊格尔顿则根据《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1983年版之后13年内西方文学理论领域内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在该书1996年第二版中增加了长篇“后记”;后者如Raman Selden等对其《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5版进行了大面积、大幅度的修订与改动。另外,同一(批)译者由于各种原因也会对其初译本进行修订或重译,这样也会产生众多正文本之间有差异的版(译)本,如《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文学理论》等。
同时,由于不同译者的翻译,从同一正文本衍生出的不同译(版)本之间,也必然会存在着异文。例如,在伊格尔顿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and Harold Bloom,who has used the work of Freud to launch one of the most daringly original literary theories of the past decade.”[1]伍晓明的译文是:“后者则利用弗洛伊德的著作提出了过去十年中最富有大胆创新精神的文学理论之一。”[2]吴新发的译文是:“布伦姆则利用弗洛伊德的著作,提出过去二十年来最大胆独创的文学理论。”[3]经过与原文对比,可知伍文是准确的,而吴文则欠准确:第一,从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问世(1973年)至伊格尔顿《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的写成(1983年)刚好十年,而不是“二十年”;第二,应该说,在这十年之中,“最富有大胆创新精神的文学理论”不只布氏影响诗学一种,应该还有其他同样影响力巨大的文论出现和存在。
另外,西方文论著作版本副文本的流变与差异现象也普遍存在。例如,“影响的焦虑”是布鲁姆提出的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布氏思想的发展变化,其理论内涵也在发生悄然嬗变,如布鲁姆即对其理论的适用时间范围进行了修正。这是通过其《影响的焦虑》的副文本体现出来的。
《影响的焦虑》初版(1973年)并没有“出版前言”,而当该书1997年再版时,则增加了一个“再版前言”,在其中,布鲁姆特别阐述了自己在“影响诗学”理论问题认识上的两点变化。第一,“影响的焦虑”理论对于莎士比亚也同样适用(在1973年版的《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没有谈论这个问题)。作为伟大的经典作家,莎士比亚最终摆脱了克里斯托弗·马洛的艺术影响,走出了焦虑的阴影,创造出了哈姆雷特、福斯塔夫等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群像。第二,“影响的焦虑”、文学竞争和创造性误释实际上存在并贯穿于整个西方文学史之中,不仅仅局限于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之后(不仅如此,它甚至还超越了文化时空而成为一种普世性存在)。可以预见,这些由副文本(序言)揭示、体现出来的变化会对相关研究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当然,西方文论著作版(文)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实际上,在其他方面,如在译者序、书评、封面、题词、引言、注释、后记等中,这些差异也普遍存在,且往往都具有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因本文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例举。
3 西方文论研究的版(文)本原则
首先,在西方文论著作研究上,我们必须遵循版(文)本精确所指原则,同时还必须兼顾参照最新版本原则。对于译本,还必须遵循优选善本、参照众本原则。在当前的西方文论研究中,由于研究者版本意识淡漠,常常出现版本错指和乱指的现象,前者即指标注并不存在的著作版本,后者即指标注的版本虽然存在,但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或其他版本)的信息。同时,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即版本任选,但结论统指,也就是说,研究者在研究时往往选取西方文论著作众多版本中的一版(往往是第一版)展开研究,但却因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忽略了其他版本的存在或与其他版本之间的差异,从而将根据其中一版得出的结论指向或强加于其他版本。因此,在进行西方文论研究时,我们必须要明确、精准地指出所论著作的版本信息,根据该版本所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指向和仅限于该版本,而不能不加考察、不加区分地跨版本、串版本下结论。
但这还不够。对于具有版本谱系的西方文论著作而言,我们在以其中一个版本作为研究对象时,还必须参照其版本谱系中的最新版本,以保证研究证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可靠性、正确性。虽然版本进化论对于新文学作品而言并不适用,即并不是后来的版本就一定比先前的版本好,[4]但它对于西方文论著作版本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正确的:即新版本往往比旧版本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不同的价值诉求与价值评判标准决定的。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美”的、“真”的,即在艺术上(如创作上、修辞上)是美的,是充分反映了作家创作时的主体意识和意志的。但事实证明,新文学作品在艺术层面上并非越改越好,相反,甚至有越改越差的现象;而受我国特定时期政治气候与氛围的影响,修改后的作品也常常不能反映作家的创作意志。[4]因此,不能说新文学版本谱系中的后来版本就一定比先前版本好。而好的学术著作应该是“新”的、“真”的:所谓“新”,不仅指学术著作的创新性(这一点对于西方文论经典名著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还指能及时反映作者的新思想、新观点;而所谓“真”(与文学作品的“真”不一样),则是指该著应该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著者在这些思想、观点上的变化。由于西方文论家在著述时受意识形态等非学术因素干扰相对较小、较少,因而其著作及修订本一般都能真实地反映作者成熟的意志,即其新思想、新观点。相对于新版本,旧版本由于无法及时地反映出著者理论思想的最新变化,因而一般说来它比新版本价值低。因此,在研究一部具有版本谱系的西方文论著作时,为保证研究结论的新颖性和前沿性,我们应该首选该著的最新版本,以及时跟进和把握作者理论、思想、观点的最新发展动态(这样才符合学术研究求“新”的特点);而在研究最新版本之前的其他版本时,也应把这些版本置放于该著的版本谱系中,以从历史、全面、联系、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它们,避免因以静态、停滞、片面、孤立、狭隘的观点来审视时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不自知。
在西方文论版本谱系中,还有许多汉译版本,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也是国内许多学者从事西方文论研究所依据的对象。那么,面对众多汉译版本,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遵循优选善本、参照众本的原则。所谓善本,即能充分体现“真”和“新”的好译本。所谓“真”,就是能真(忠)实、全面、准确地传达原著内容,这主要是从翻译的层面而言的;所谓“新”,就是能及时反映著者理论观点的最新变化,这主要是从著作的内容角度来看的。符合这两个标准的译本就是好译本,就是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应该首选的译本。根据这两个标准来看,一般而言,修订(译)本比先前版(译)本好,根据新版原著翻译的版本比根据旧版原著翻译的版本好,直译版本比转译版本好。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而在具体的版(译)本遴选过程中,我们应该在上述原则指导下,对具体的版本进行仔细比对,尤其是从翻译技术的层面进行考量,考察其翻译质量,最终择善而从。但是,在具体的译本对比实践中,我们发现,没有一个译本能达到十全十美,也没有一个译本是一无是处,一句话,各个译本都有其优劣,都有可以相互借鉴学习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以善本为主,适当参照其他译本,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所谓参照众本。
其次,在西方文论(接受)史的写作上,应该遵循叙众本的原则。当前国内的西方文论史写作,作(编)者往往只述及西方文论著作的初版本,而对该著的其他版本则忽视了,这样,著者理论思想观点的变化过程则被人为遮蔽,给读者一种作者的理论、学说是停滞不动的假象:从根本上讲,这是违反史学的严谨性、科学性和真实性原则的。既然西方文论著作存在着版本变迁史,它反映了著者思想的流变,是西方文论史的一个重要(微观)组成部分,那么西方文论史就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呈现这种历史,否则,这就是一种残缺的、不科学的文论史写作模式。而所谓叙众本原则,则是指西方文论史写作应该对存在着版本谱系的西方文论著作进行系统的版本谱系清理,叙述版本的源流与变迁,并指出其中所反映出的著者的理论思想观点的变化。而西方文论接受史的写作也应该遵循叙众本原则,只不过它应清理、叙述的是各种汉译版本(包括同一〔批〕译者翻译修订产生的译本,不同译者翻译产生的译本和经直译、转译产生的译本等等),而它研究的也是译者的接受、认知(变化)等等。
4 余论
从上文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西方文论著作版本变迁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阔,除了上面论及的维度之外,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更宽泛的层面上进行研究。例如,同一著作同语种版本之间的对比研究,跨语种版本之间的(比较文学跨文化影响、接受)研究,同地区(大陆)汉译本之间对比研究,跨地区(大陆、台湾)汉译本之间对比研究,中译本与英文本之间对比研究,从原语出发的译本与从英语出发的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西方文论版本(批评)史研究,西方文论版本的出版、传播与影响问题研究,等等。因篇幅有限,本文仅提出问题供研究者思考,而更具体、更详细、更深入的研究则只能留待今后进行。
[1]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Blackwell Publishers,1983:183.
[2]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3.
[3]泰瑞·伊果顿.文学理论导读[M].吴新发译.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228.
[4]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59-60,5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