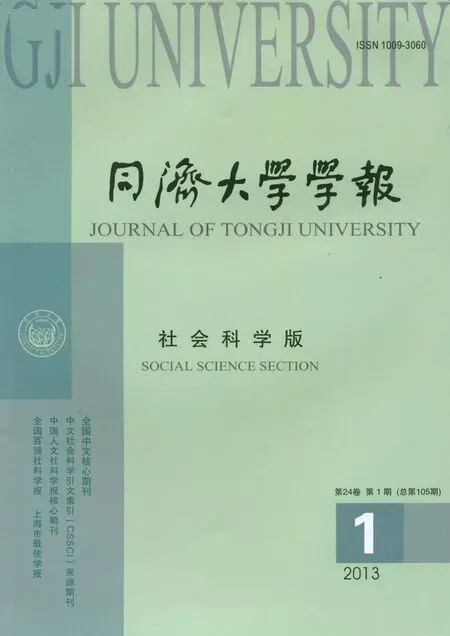法国哲学的魅力
—— 从巴什拉的《梦想的权利》谈起
杜小真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871)
《梦想的权利》论文集①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p.5、p.5.,收录了二十世纪法国杰出的科学哲学家、法国认识论奠基人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生前于1942年至1962年间所写的有关艺术思想的多篇理论文章。编者在出版者说明中指出,这些文章之所以集合于“梦想的权利”名下,出于一个标准,那就是在这部书中,巴什拉无论谈绘画(莫奈、夏加尔、梵高、布拉克②布拉克(G.Braque 1882-1963),法国画家。等)、雕塑(弗洛贡、奇利达等),还是谈文学(巴尔扎克、瓦莱里、埃德加·坡、奈瓦尔等)抑或诗歌(波德莱尔、马拉美、埃吕雅、兰波等),或者描述大海、岩石、贝壳或绳结,都遵循着梦想和思考、或者说想象和反思的联结和交叉的原则。③Vincent Bontems,Bachelard,Paris:Les belles letters,2010,préface.“巴什拉在书中显示出来的不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哲学家,而更多地是一个梦想者,或不如说一位被赋予梦想权利的思想家。”④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p.5、p.5.巴什拉依据这个原则对诸多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解析,不断揭示想象和反思综合的困难和必要,他认为唯有二者的综合可以从文学、艺术家作品中找到梦想的价值。巴什拉认为,人的实现取决于两级的互动:“人类通过梦境世界同时在“呼吸”和“灵魂”两种模式下生活……诗学通过意志和静息将两种生活状态与世界协调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的创造性比科学更能满足灵魂的需要……”⑤引自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原哲学系主任J.J.Wunenburger教授2010年5月在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举办的题为《巴什拉的认识论与诗学—— 法国传统与德国遗产》讲座的讲稿。这部著作堪称巴什拉理论事业的总结,或者说是回归家园——艺术精神家园——之作。阅读这部著作,就是去参与巴什拉的想象和反思的活动,就是随着他,随着他的“看”和“思”,回归“变得复杂之前的激荡世界”,回归哲学的“孩童绘画”。⑥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p.5、p.5.
一、想象与反思
巴什拉的哲学思想丰富多彩。其中最吸引读者的是他始终如一的欲望:理解人类,理解人世间的万物万象——对“多形”的欲望,起点就是他构建的严格而又有活力的认识论思想。这依靠他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扎实的知识基础。
想象和反思(或者说想象和理性)是我们阅读、理解巴什拉作品的导线。(正如人们会说具有科学哲学家和诗人双重头衔的巴什拉一样),《梦想的权利》把这两头集中、有机地沟通起来。不过,无论如何,巴什拉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巴什拉是从作为“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哲学思想出发,以一种精神(心灵)的动力观念把想象和反思贯穿起来,精神从来就不是僵化的,它运动不已,充满力量。而理性就是其力量之一,它的动力即认识的进步;想象是另一种力量,推动和发展精神的运动。①Vincent Bontems,Bachelard,Paris:Les belles letters,2010,préface.
巴什拉科学哲学的认识论的断裂思想要说明的是,理性和想象最初遭遇的是力量的对立。科学家要抵抗语言想象以严格确立科学的各种概念;而诗人要避免单纯的逻辑的语言结构以制造闻所未闻的隐喻。科学理性和诗意的想象共同震撼精神(心灵),不相信最初的明证性,也不凭借习惯和常识来划定世间事物。二者共同对最初的直观进行修正,这也就是进行巴什拉认识论所谓的“induction”(使感应、归纳、诱使等)②在心理学中,induction指已在从个别特殊案例出发把一种规则普遍化的精神活动。在数学中,完全的induction是通过递推的归纳活动。在物理中,电磁(感应)则指的是磁体运动通过线圈使电流运动,反过来,电流在线圈的循环在其周围创建了磁场。在《论近似的知识》中,巴什拉指出:induction是经验(和数学概念相通)的可创造性的条件。后来,巴什拉把induction和电磁感应相类比。。巴什拉指出,在科学中,数学的归纳价值是能够根据物理事实的经验进行推理,而文学、艺术则用词语、画面、雕刻等作品诱发读者或观者心灵中的想象力。可以看出,科学归纳和诗学感应是可类比的,尽管结果不同。
巴什拉的思考显然获益于现代科学的进步成果。比如现代物理学不可逆转地远离天真实在论的最初直观。数理逻辑启发精神,让人们从“真实是由‘诸物’构成的”信念中解放出来,不再推理现象的真实,而是从多样的公式出发。从数学上可思考的东西出发可以推论出物理上可能的东西。“真实世界和它意味着的动力规定论要求不同的直观,就这些活跃的直观而言,必须使用一套新的哲学词汇。如果induction还没有那么多的意义,我建议把它用于这些活跃的直观。”③G.Bachelard,L’activitérationaliste de la science contemporaine,Paris:PUF,1951,p.214.
二、展现“看”的想象现象学
巴什拉在《梦想的权利》中谈的其实都是异于哲学和科学的思想(文学、绘画、雕刻、小说、音乐等等)的事情,但读过之后,你会感到,他不正是在说哲学,在说科学吗?很多时候,一件事往往只有通过和它相异的事才能表达和解释得更加清楚、更加确切。
《梦想的权利》的第一部分,关注的是艺术家的创作:那些绘画、雕塑、铜版画……展现的是画家、雕塑家所“看”见的。巴什拉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美是“看”出来的,也是世界、世间之物和人的注视互动的结果。“世界要被看见:在‘看’的眼睛存在之前,水的眼睛,静水的大眼睛已在观看花朵怒放。正是在这反射 ——表现的反面的反射——中,世界获得对自己的美丽的最初意识。”④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比如,“看”莫奈的《睡莲》,其实是“看”莫奈“看”睡莲。莫奈画睡莲,展现的是他“看到”的睡莲之美,而莫奈画睡莲的目的是让观画者“看”他画中体现的睡莲之美。莫奈的绘画,展现的是他看出来的自然之美,并让观画者领会到他心中的睡莲之美,他一方面激励世间一切趋向美的事物,另一方面则用其全部生命发展他看到的一切美。①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p.14、p.20、p.37、p.15、p.5.再比如,把《圣经》展现为 “图像之书”的俄裔法国画家夏加尔,他的画面上的飞翔的人物和飞鸟,各种闪光的形象,天空中“鸣响”的钟,还有那奇异的色彩,显示了沉迷于“看”的画家的生命力量。他懂得看世界,懂得爱世界,在他眼里,天堂就是一幅美丽的画。②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p.14、p.20、p.37、p.15、p.5.他的画面就是用颜色表现的语言,正在说话的图像,观画者面对他创作的《圣经》画,用注视抚爱画中人物,去“聆听”他们的故事,无论是画面上的夏娃、亚当,还是但以理、伯沙撒、乔纳、约珥,他们都在夏加尔的画笔下成为“精神性的存在”③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p.14、p.20、p.37、p.15、p.5.,观画者都会从画面上的人物获得强大的推动力,经历一种“永恒的历史”。所以巴什拉说:“夏加尔的眼中有这么多的形象,在他看来,过去保留着丰满的色彩,保存着渊源的光亮,它所阅读的一切,他全看在眼里。他所思考的一切,他把它描绘出来,把它刻划出来,把它记录在物质材料里,使之光彩夺目,闪耀真实光辉。”④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p.14、p.20、p.37、p.15、p.5.
德国现象学对法国二十世纪哲学的影响难以估量,带给巴什拉的启迪和教益亦难以估量。巴什拉和法国当代许多哲学家一样,都是从德国哲学那里(现象学、德国浪漫派)获益,并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带入更加新鲜的创造。但我们要说,法国几代哲学家对现象学的贡献也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在美学、艺术理论方面,为现象学注入了生命活力、身体的朝气和感官的愉悦。
巴什拉“看”画,“看”雕塑,“看”小说……那远不止是视觉的“看”⑤其实许多当代法国学者对“看”的问题的哲学解释都异常精彩,比如梅洛-庞蒂,比如萨特,等等。巴什拉在书中谈到雕刻家弗洛贡时说:“……光有肌肉活动是不够的,他必须要理论,有哲学。”他说到弗洛贡认真阅读过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酷爱充实着心理学作品的视觉形而上学。(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10.),而是成为感知活动、思想活动的“看”。也就是说,“看”的开始就意味着“思”的开始。⑥法国现象学对欧洲现象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把“不在场”引入绘画话语分析。画面显现为“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双重现象,如果没有“思”同时活动,那“不可见的”就看不出来。思的目的在巴什拉看来是要追寻画面上的不可见,即那肉眼看不见的“空白”,说到底,就是那抽象的美之所在。因为“画家本人注视的是他没有看见的东西”⑦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p.14、p.20、p.37、p.15、p.5.。画家莫奈、夏加尔、西蒙·塞加尔、布拉克等,雕刻家瓦洛基耶、马科西斯、弗洛贡等,这些艺术家的成功就在于能够提供一个空间,展现一个经过“思”的艺术对象,能够最大限度让观者“看”到眼睛没有或无法看到的东西。另外,巴什拉认识论的重要思想就是科学的对象不是直接的,画作从根本上讲,是看艺术家所描绘的真实场景或人物。很可能是我们熟悉画家笔下描绘的真实场景和人物,比如那片金黄的葵花,那些跳动的青年,那江南烟雨风光……而画家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这一切,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会对之有一认识的升华。因为它会赋予画家之所画以本质和活力。科学家通过间接手段处理科学对象,即被理性加工了的对象(比如说电,比如说光的测量,等等),间接提供关于对象的知识,画家则用画面为观者提供对于外界和他人的知识,画面成为观者和认识之间的中介。这是“看”艺术作品和“看”艺术作品中表现的自然真实的人、物、场景的根本区别,唯有前者方能让观者达到“审美”的层次,即思想的最高层次,也只有在想象和反思艺术作品时,自然世界中的景观、人物才能成为审美维度上的认识对象。巴什拉要告诉我们,艺术家在“看”和“思”——想象和反思—— 的活动中,用艺术作品呼唤哲学回到简单的童年图像,回到思想的源头,引导观画者去认识在哲学解释之前“已经变得复杂和激荡的世界”⑧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3、p.14、p.20、p.37、p.15、p.5.,也就是那在“成为真实之前就是美的世界”,“在得到证明之前就已经被欣赏的世界”⑨G.Bachelard,L’air et les songe,Paris:JoséCorti,1943,p.216.。
三、物质与想象
巴什拉的想象非常重视物质,他在科学经验中发现了“幼稚”经验的痕迹,所以,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欣赏,都需要想象。他依次对火(《火的精神分析》,1938年)、水(《水与梦》,1942年)、空气(《空气和梦想——论运动的想象》,1943年)、土(《土地和静息的遐想》,1948年)四种元素进行精神分析,由此论证了建立在理性心理学基础上的诗学现象理论。诗的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每个诗人那里揭示物质的四重想象。在《梦想的权利》中,巴什拉把对绘画的思考扩展到了文学、诗歌等诸多领域,但仍然沿循的是他建立在对想象的深入探索和研究的基础上的诗学理论原则。他通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赏析论证了建立在理性心理学基础上的诗学现象理论:“感知的现象学本身应该让位于创造性想象的现象学。”①G.Bachelard,La Poè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PUF,1960,p.12、p.12.在巴什拉看来,物质想象先于静观,人在静观之前梦想。四种元素是想象力的“荷尔蒙”。我们自身的存在基础也是遵循针对这四种物质的想象法则。而文学批评的功能不是为了使文学理性化,而是对激情和理智的表达进行研究,两者缺一不可。这是美学应该特别关注、研究的问题。
绘画作品的完成和欣赏亦如此。巴什拉对夏加尔的《圣经》画系列进行赏析。他把夏加尔视作一位伟大的通灵者,他注视着最伟大的过去,用画面指明最初生命的存在。夏加尔的画是他梦想《圣经》文本的结果,《圣经》文本是需要我们阅读的语言,而夏加尔是用画面表现文字叙事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所采用的颜色变成了陈述,绘画成为语言的来源、诗歌的来源。他用颜色告诉我们天堂所在,天堂首先是一幅画。从一幅画到另一幅画,从空间的画到阳光的画,画家实现了物质材料的转化变动,把色彩植入到物质材料中去。对弗洛贡等众多雕塑艺术家的作品的分析,更加突出了物质想象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前面谈到的莫奈的《睡莲》组画也同样,莫奈对水之华的梦想和沉思使之产生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才可能把他心中的美丽展现给我们。巴什拉认为,用眼睛的视线凝视一滩水并不足以感受到水的生命力,只有长久地梦想,才能理解何谓宁静的水、暴怒的水……莫奈的《鲁节大教堂》在巴什拉那里是对画的形态、色彩植入、物质材料想象的范例,没有物质元素,就无法美妙地思考天地万物,就会使想象的含量残缺不全。物质元素成为艺术创造的原则。正如巴什拉所说:“没有什么艺术比绘画更直接地具有创造力……画家基于原始想象的宿命,总是更新对宇宙的伟大梦想,这些想象把人与土、火、水、空气以及大地万物的神奇物质性维系在一起。”②G.Bachelard,La Poè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PUF,1970,p.38、p.133、p.147、p.137、p.148.画家在对火、水、空气和土诸元素进行想象时,开始获得创作的天生萌芽。
巴什拉还通过对多个著名作家、诗人作品的分析,特别阐明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一样,其作者都是在传递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作者笔下的形象、故事、环境都是在表达一种生命的体验。他把这些奉献给读者,一如波德莱尔在物质的诗意想象中发生“感应”(通灵),一如巴尔扎克的《赛拉菲达》描述的富有活力的经历。批评家要引导读者明白,这样的作品立足、关心物质世界,为社会的复杂而痛苦纠结,但读者更应明白,这样的作品最懂得把人的命运和超越行动结合在一起,接受道德与诗之间的结合③G.Bachelard,La Poè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PUF,1970,p.38、p.133、p.147、p.137、p.148.;再比如埃德加·坡的《戈登·比姆历险记》这部不太起眼的作品,它非常具体地体现了物质想象的巨大震撼力量:水之想象、土地之想象等等。埃德加·坡的想象把人之恶与天地之恶整合起来④G.Bachelard,La Poè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PUF,1970,p.38、p.133、p.147、p.137、p.148.,向读者传递梦想的萌芽。所以,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遵循两条线:一是遵循事件这条线;二是遵循梦想这条线,后者则更为重要和根本。“人更多地是由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自己的经历连接起来的……我们无法否认寻求表面意义下的深层梦想意义的双重阅读的价值。”⑤G.Bachelard,La Poè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PUF,1970,p.38、p.133、p.147、p.137、p.148.“读者在这样的阅读中会发现一个新的天地,这个天地就是人的心灵……”⑥G.Bachelard,La Poè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PUF,1970,p.38、p.133、p.147、p.137、p.148.同样的分析也用于诗人(兰波、马拉美、艾吕雅等)的作品。诗歌的语言从根本上讲,如兰波所说,概括了一切:香气、声音、色彩,通过思想的碰撞发出光芒。诗歌是诗人物质想象的结果,而读者的阅读同样也需要想象,这是因为“诗的梦想给予我们的是诸多世界的世界。诗的梦想是宇宙的梦想。它打开一个美的世界”⑦G.Bachelard,La Poè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PUF,1960,p.12、p.12.。读诗和看画一样,都需要随着作者的梦想去追寻和发现画面和诗歌后面没有显现和说出的东西,即诗歌所表现的画面、形象、声音等后面的美。比如兰波的富于声音美感的诗意象征在他的诗作(《彩图集》、《醉舟》等)的各种主题中不断出现,体现了最古老的梦想的原型,他的诗“就像一场被控制的梦,向我们解释超越童年的可能性”①G.Bachelard,La Poètique de la rêverie,Paris:PUF,1970,p.152.。兰波的诗向读者传递着语言的力量,激发着读者的物质想象,正如巴什拉在《“火的诗学”残篇》中所说:“文学的形象是真正超出说的语言、超出献身服务意义的语言的真正起伏。起伏?毋宁说它是巩固各种超越基础的诗学价值,这些超越只显现为奇念喷射。”②G.Bachelard,Fragments d’une poètique du feu,Paris:PUF,1988,p.38.这部著作是巴什拉的女儿Suzanne Bachelard在1988年整理出版的未刊稿。再比如读者在保尔·艾吕雅诗作中,看到了巴什拉所说的萌芽和理性这不朽的两极③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69、p.172、p.224、p.174-175、p.240.,他的诗用这两极教读者去看,去直面世界,去理解世界。巴什拉指出,艾吕雅的诗(比如《凤凰》)展现通过炽热而清醒的目光看到的世界,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心中的生命萌芽,让我们去接受他的启迪:热爱诸物,热爱生命,热爱人。④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69、p.172、p.224、p.174-175、p.240.所以,诗歌说到底,是生命激情与理性合作产生的语言形象,“诗歌是一种即时的形而上学……应该同时展现宇宙的视野和灵魂的秘密,展现生命的存在和世界诸物”⑤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69、p.172、p.224、p.174-175、p.240.。诗人如凤凰,“……即使在死亡中依然确信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彼世展现在作品中,把自己的新生托付给读其作品的人类”⑥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69、p.172、p.224、p.174-175、p.240.造房的,最软的存在是怎样造成最硬的壳,宇宙同冬春的伟大节奏又是怎样回荡在这个封闭的存在之中的;那么,我们将永远梦想不完了。”巴什拉引用一位瓦尔蒙神甫的话说:“蜗牛的外壳,那栋随着主人长大的房子,是世上的奇迹,贝壳是精神沉思的极佳主题。”(参见:[法]安德烈·巴利诺:《巴什拉传》,顾嘉琛、杜小真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369页以下。)。
想象是纯粹精神性的活动,但却不是凭空的。没有物质元素,就无法美妙地思考天地万物,就会使想象的含量残缺不全。物质元素成为艺术创造的原则。艺术家在对火、水、空气和土诸元素进行想象时,就开始获得创作的天生萌芽。
四、诗意的梦想
艺术家要构建的空间并非功利贪欲的空间,而是绝非虚幻的梦想城堡,也就是巴什拉多次提到的“壳”⑦巴什拉对“壳”有许多精彩的分析:“生命所做出的最初努力就是造外壳……从现象学的角度去理解:蜗牛是怎样—— 心灵的安静、孤独的梦想城堡。
《梦想的权利》篇幅不大,却堪称精品之作,可说是巴什拉认识论理论事业的总结,或者说是回归家园——艺术精神家园——之作。
特别要指出的是,巴什拉的想象现象学从根本上讲,是研究形象(image)的哲学:科学的认识活动应该把想象同认识、知识和现象统一起来,即把认识的命运和想象的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亦即把白天的人和黑夜的人⑧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教授J.J.Wunenburger在2010年的北大讲座中曾经对此有过精彩说明:巴什拉作品中体现了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诉求:巴什拉把这两个层面比喻为白天和黑夜。这是一对象征概念之间的碰撞:一边是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特有的(以太阳世纪为代表的)笛卡尔式的“清晰与分明”,而另一边是受德国莱茵河沿岸神秘主义和浪漫派,被黑格尔称作“无法分辨野猫颜色的黑夜”的超越感官的梦境思想。(《巴什拉的认识论与诗学—— 法国传统与德国遗产》)一些学者认为,巴什拉的认识论理论发展到美学和文学领域,象征着人类学二元性的觉醒和胜利,这个发展和提升一方面发扬了法国哲学主观性普遍化的抽象传统,另一方面他的美学和想象把主观性投入到生机勃勃的自然之中,生理和心理在自然中凝结在一起。巴什拉对德国浪漫主义进行法国式的理性化改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比较复杂,值得关注。在此就不展开讨论。、认识的人和想象的人结合起来。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白天或黑夜,不但要想象还要反思,缺一不可。艺术家和作家心中的真实,就是要求看者“看到”的真实。只有在“夜”里看见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真实的东西。其象征意义不但是“叔本华的‘夜是我的孤独,夜是我的孤独和意志’”,而且是“夜也是表象和意志”。⑨G.Bachelard,Le droit de rêver,Paris:PUF,1970,p.169、p.172、p.224、p.174-175、p.240.梦想,就是在黑夜中寻找精神光明。黑夜和白天二元论述的象征意义还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思想中互补的两个方面:想象与反思(理性)。结合二者的活动就是认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理解人类的精神生活。巴什拉告诉我们,想象和理性来自同一源头,面对同一深渊。在自然世界中生活,人依靠的就是这两极:即通过梦想同时在“呼吸”和“灵魂”两种模式中生活。换言之,人类生活对个人能力的要求是两方面的:具体和抽象、图像和概念、诗歌和科学。梦想构建诗的真谛,想象最终超越理性;梦想把两种生活状态协调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的创造力比科学更能满足灵魂的渴望和需求,科学仅对实在的知识感兴趣,而梦想却同时包涵了存在的两个方面。
巴什拉关于想象与物质的思考,让我们想到想象其实是对经验、对艺术对象认识的一种纯化,这是许多人没有注意但又极其关键的问题。因为科学的立场认为重要的不是获得经验性的文化,而是要改变经验性的知识。巴什拉还说到:教育首先是要教授给学生想象的能力,这不仅仅限于艺术教育。普遍的教育理念是传授打着权威烙印的知识,全然不教授对谬误修正的能力,早已剥夺了人们的精神上的新鲜感和知性的生命力。而真正培养有用之人的教育在巴什拉看来是教会学生创造,赋予他们这样的信念:他们本应具有发现和创造的能力。也就是说,教育要让学生懂得:面对梦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梦想是我们每个人去理性和审美地生活的保证。追求这样的生活,就是行使梦想的权利。
五、法国哲学的魅力
巴什拉的《梦想的诗学》让我们感受到法国哲学的魅力。
首先,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如阿铎(P.Hadot)在《何为古代哲学?》①Pierre Hadot,La philoophie comme manière de vivre,Paris:Albin Michel,2001,p.7.中指出的,在古希腊,哲学归根结底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说决定要和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一起生活的选择。法国哲学,特别是当代哲学特别承继了这个传统。这种对哲学的解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改变依靠我们的思想方式的改变,思想的问题一定要通过思想来解决。②这里让我们想到法国近几十年中三位哲学家的生活方式的选择:(1)著名数学家、哲学家Jean Cavaillès(1903-1944)的“逻辑的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次上前线,最终死于德军枪下,被Geoge Canguilhem称作实现了“不用文字确定的伦理学”(参见 Gerges Canguilhem,Vie et Mort de Jean Cavaillès,ed.Allia,2004)。(2)Yvonne Picard(1920-1943),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她选择参加抵抗运动,勒维纳斯感叹这个非犹太女生以非种族原因死于德国集中营的牺牲,让·华尔(Jean Wahl)在1946年在Deucalion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Picard的博士论文Le temps chez Husserl et chez Heidegger,Simone Beauvoir、Derrida、Desanti等都在不同地方提到过这位勇于选择的年轻姑娘(参见Philosophie杂志,2008年冬季版,总第100期,ed.Minuit)。(3)Davis Gritz(1978-2002),巴黎十大学生,导师为著名勒维纳斯研究女专家Catherine Chalier教授。这位法国年轻人选择去耶路撒冷读书,他认同犹太人对《圣经》的解读,认为他们的实践可能并且应该启示非犹太人。2002年的一天,Gritz在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咖啡厅遭恐怖袭击爆炸身亡。Chalier教授接到这个噩耗时,笔者恰巧在教授家,她表现出来的震惊和悲痛令我感动。后来,Chalier教授组织出版了Critz的论文,并且作了长序。参见David Gritz,Levinas face au beau,éditions de l’éclat,2004。所以在这里提出这几个人,确是因为他们明显带着法国学人的自由选择的传统,而且这种选择是哲学理性的,和现在到处泛滥的功利实际的选择相比,法国人的这种哲学追求的光辉更加令人神往。这种哲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人们好好地、理性地活着;并且热爱诸物,热爱生命,热爱人。
其次,视个体生命至上的哲学。斯宾诺莎说过:“没有一个人有要求快乐、良好生活和良好行为的欲望,而不同时要求生命、行为和生活,即要求真实存在的欲望。”③参见[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86页。法国哲学创造性地承继古希腊传统,把个体“生存”或“存在”放在第一位。在法国当代哲学中,生命的价值被提升到最高位置,没有任何东西——哪怕是披着最绚丽、最道德、最高尚色彩的外衣下的追求和真理——比鲜活的生命,比个体的生命,比“活着”更重要了。无论是“绵延”,还是“存在先于本质”,无论是“新科学精神”,还是“生命现象学”①特别要注意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1922-2002)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高宣扬教授对这位生命哲学家深有研究。米歇尔·亨利的哲学研究建立在具体个体生命的这个最本源事实的基础上,个体在每时每刻都经历自己的生命。个体生命是最原初的“知”。人类文化需要哲学,世俗世界需要文化,其实这需要就是生命的需要,这是人类的第一需要。等等,无一不是在高扬生命至上,讴歌生命的无上力量。把生命作为第一重要事情,非同小可,对那些经历过把所谓原则、虚无缥缈的所谓理想和信仰视为第一需要,甚至为此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宝贵生命而无动于衷的悲剧的人们,这种表述确实具有非常深刻的启迪意义和无穷的精神魅力。
再次,善解相异性的哲学。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必定尊重个人之间的差异。相异性的研究在当代法国哲学中地位重要,别具风格,故引人入胜。法国当代大多数哲学家都非常关注“相异性”的问题,特别时值二十世纪下半叶。比如:在巴什拉、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之后,福柯(M.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德勒兹(G.Deleuze)等等②勒维纳斯把对相异性的思考推到极端。他说:“思想的事业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同’向着‘异’的运动,这种运动永远不会回到‘同’。”他对西方哲学传统拘囿自身的漂泊(即尤利西斯(Ulysse)的路线象征)进行质疑,认为是在“同”之中的自得,对“他人的漠视”,他希望人们能看到以亚伯拉罕(Abraham)永远远离故土走向未知土地的历史,对“相异性”进行哲学思考。这个传统和黑格尔哲学中的否定性概念有关;特别是法国哲学家把它理解为作为构建差异的活动。另一种理解思想可追溯到费希特—黑格尔(Fichte-Hegel)哲学传统中对于“承认”(Anerkennen)这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利科也讨论过相关的reconnaissance(承认)。但是他的这个概念不仅包括Anerkennen(承认),也包括了 Wiedererkennen(重新认出),。关注“相异性”,说到底就是关注“个体性”,法国人文传统的启蒙理性的根本就是绝对尊重人的个体。法国二十世纪的知识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成果非凡。最近十多年来,于连(Francois Jullian)的工作促进并深化对“相异性”问题的反思。他从福柯的“异域”(hétoropie)理论出发,提出对不同文化思想进行差异比较的方法。这也涉及对“他人”问题的思考。从萨特“存在与存在”基础上的平等关系到勒维纳斯“为他人”的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都极具现实的启发性。
这种“相异性”有别于传统思辨哲学中的对立—统一的单一模式,注重个体之间的差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差异性并非注定对立③这里想到某位旅居海外的著名西学学者最近的谈话:他说西方有些人,特别是法国人,总把中国人看作他者,这是错误的,这是导致一种对立、冲突……其实,希望人们理解法国人他者理论的真正深义,尊重他者,尊重他者的相异性,并非意味着冲突,他者和我之间的差异,不是可怕的需要消除的东西,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矛盾,意味着对立和统一的法则。若执意消除差异,刻意思想统一,反而会产生或加剧对立和冲突。,解除冲突的途径并非要消除差异,保留差异和理解差异反而会缓和冲突,促成“和谐”。所以,在复杂多变、急躁混乱、缺失理解的当今世界,善待相异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尊重“相异性”,即真正尊重“人权”。大到每个国家,小到每个个体,相异性在被构建的过程中,树立起每个人的人格,保护了“人权”。用“人权”肯定每个人的价值,就是肯定每个国家、每个个体的文化相异性。唯如此,才可能达到所谓的“普世价值”,才可能有“和平”——世间的和心灵的。
最后,可以与不同学科相互对话和说明的哲学。哲学与其他学科的沟通,特别是与文学、艺术的相互沟通,是法国哲学长久以来形成的特色。这其实也就形成了法国文化多样而又绚丽的色彩。正是法国哲学的这些特点(当然远不止这四个方面)使得法国哲学具有特殊的魅力,也使法国文学艺术也具有不一般的风采。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什拉的《梦想的权利》具有这样特殊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