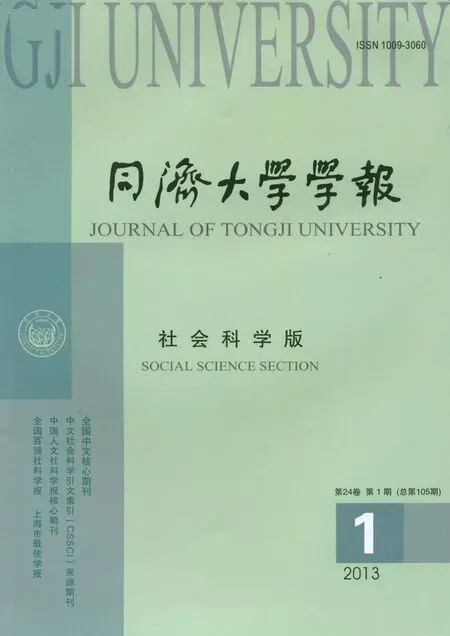论尼采《悲剧的诞生》的核心问题
马小虎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092)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悲剧的诞生》?无论是1872年《悲剧的诞生》一书问世以来的西方思想界,还是1986年此书中译本问世以来的汉语思想界,对此都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总体而论,这些争议围绕两个方面:该书是不是一部古典学作品?它是不是一部美学作品?一方面,这部作品自问世之初,就受到著名学者维拉莫维茨的激烈批判,连尼采的恩师李契尔对此书的态度都很冷淡,①周国平:《悲剧的诞生:尼采哲学的诞生》,《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第39-40、38-44页。再后来人们甚至挑出书中的许多常识性的硬伤。②考夫曼:《尼采与悲剧之死:一个批评》,载于[美]奥弗洛赫蒂编:《尼采与古典传统》,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4-418页。另一方面,这部作品在国内多被视为一部美学作品,在此维度上人们作了热烈的讨论。
然而,结合诸多研究,我们基本上可以作出如下判断:《悲剧的诞生》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古典学作品,也不仅是一部所谓的美学作品,而是一部特殊的哲学作品。③周国平:《悲剧的诞生:尼采哲学的诞生》,《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第39-40、38-44页。虽然此书的题材是古典学的题材,但是尼采的创作意图远不在学究性的考据上,而在于传达一种对源初希腊精神的向往。虽然它涉及到许多艺术现象,但是尼采的重心不在于探讨一种美学,而在于从希腊悲剧中提取出源初的希腊精神。因此,如何源初地领会希腊精神,这是《悲剧的诞生》的核心问题。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希腊悲剧如何借助一种形而上学的意志而得以诞生?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发生了何种转变?希腊的明朗究竟是不是源初的希腊精神?
一、意志形而上学
为了说明《悲剧的诞生》一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必须预先说明什么是形而上学以及什么是尼采的形而上学。1936-1940年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作了6个尼采专题讲座,不仅对尼采的形而上学作了强力诠释,并且对一般而言的形而上学也作了精辟的梳理。依据海德格尔的诠释,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知识,并且开始于这种区分——把存在区分作什么存在(Was-sein)和如此存在(DaΒsein)。④[德]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52、1035页;第890页。这种区分一直伴随着形而上学,且被后世转换为本质(essentia)与实存(existentia)间的区分。他进一步把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概括为五重性:什么存在、如此存在、真理的本质方式、真理的历史与人类。⑤KSA 1,S.50;《悲剧的诞生》,第51页。其中,什么存在和如此存在是最基本的环节。
一般而言的形而上学就是如此。据此而言,尼采有一种形而上学吗?若有,这种形而上学是怎样的呢?依据海德格尔的论述,形而上学发端于柏拉图。柏拉图把什么存在解释为相,形而上学于是就产生了。柏拉图把存在解释为相与善,而尼采则把存在解释为强力意志。因此,“依据柏拉图以来全部思想来看,尼采思想乃是形而上学”。①[德]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52-854页、第889页。形而上学的五重性于尼采的形而上学表现为:强力意志(什么存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如此存在)、公正(真理的本质)、虚无主义(真理的历史)与超人(人类)。这五重性中,最基本的两重性乃是强力意志(什么存在)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如此存在)。②孙周兴:《形而上学的尼采与尼采的形而上学》,载于《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9页。
这就是尼采的形而上学,依据的是海德格尔对尼采晚期遗稿《强力意志》的诠释。而我们眼下面对的文本《悲剧的诞生》乃是尼采的早期作品。我们的问题是,在这部早期作品中,尼采是否已经提出了一种形而上学?若有,那么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以下我们结合具体文本来讨论:
1.“真正存在者和太一,作为永恒的受苦者和充满矛盾的东西(das Wahrhaft-Seiende und Ur-Eine als das ewige Leidende und Widerspruchsvolle),为了自身得到永远的解脱,也需要迷醉的幻景、快乐的假象。”③Nietzsche:Die Geburt der Tragodie (KSA 1),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KG,Berlin,1988,S.38;《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7页。本文写作时依据的是孙周兴教授2010年底完成的本书译稿,后依据2012年刊行本修订。以下简写为:KSA 1,S.38;《悲剧的诞生》,第23页。
2.“作为狄奥尼索斯式的艺术家,抒情诗人是与太一及其痛苦和矛盾完全一体的,并且把这种太一的映像制作为音乐 (Mit dem Ur-Einen,seinem Schmerz und Widerspruch,eins geworden und pruduziert das Abbild dieses Ur-Einen als Musik)”。④KSA 1,S.43-44;《悲剧的诞生》,第43页。
3.“音乐作为意志而显现(Sie[Musik]erscheint als Wille)”。⑤
首先,我们要区分两种表达:一种是真正存在者和太一,另一种是痛苦(者)与矛盾(者)。第1句中,尼采的用词是“作为”(als),“作为”而非“是”(ist,sein),这表明als前后两部分不可完全等同。这可以从第2句中获得支持:第2句中的“它的”(seinem),表明痛苦与矛盾(Schmerz und Widerspruch)和太一本身不可等同,因为“它的……”和“它本身”不可等同;痛苦的东西与矛盾的东西,这两者属于、但不是太一或真正的存在者。而“真正的存在者”与“太一”,这两者应该是一回事。其次,我们要搞清楚太一与意志的关系。根据第2句,音乐是太一的映像;根据第3句,音乐作为意志而显现。综合这两句,可以得出,太一正是意志,而音乐则是意志或太一的映像。
通过以上分析,并依照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结构的诠释,我们可以把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论述作如下概括:相应于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什么存在和如何存在之区分,这里的区分乃是:真正的存在者,也叫作太一,是意志;痛苦与矛盾是意志的存在方式。前者是什么存在的维度,而后者是如何存在的维度。这就是尼采早期的形而上学。对比尼采后期的形而上学——强力意志(什么存在)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如何存在),这里已经提出了意志,虽然还不是强力意志。后期“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可以看作是对早期“痛苦”的具体化与深化。
前面揭示了《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环节,这里还须再设一问:为什么意志在此书中是真正的存在者?尼采指出:“所有真正的悲剧都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释放我们,即是说: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das Leben)却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unzerstorbar machtig und lustvoll sei)。”①KSA 1,S.56;《悲剧的诞生》,第58页。这里的“生命”(das Leben)应当理解为“意志”;它存在于事物的根本处,它是真正的存在者、太一或自在之物,作为根本之物决定其他事物;生命或意志坚不可摧,说明它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存在者,可摧毁的事物不堪为真正的存在者。在史诗(阿波罗文化的代表)中,希腊人的意志强烈地追求形象。希腊人创造出众神的形象,用以给人的生活作辩护,用以对抗痛苦。②KSA 1,S.36-37;《悲剧的诞生》,第33-36页。在抒情诗中,抒情诗人不再是诗人自己,而是意志的存在方式——原始痛苦。③KSA 1,S.45;《悲剧的诞生》,第45-46页。在悲剧中,坚不可摧的意志不再求救于众神的形象,不再害怕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只有在悲剧中,意志,由于坚不可摧,才名副其实,无愧于它的名号——“真正的存在者”。
二、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完成的16年后即1886年在《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一文中对该书的思想作了回顾。其中谈到:“一个基本问题乃是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希腊人的敏感程度,——这种关系是一成不变的呢,还是发生了转变?”④KSA 1,S.15;《悲剧的诞生》,第7页。依据书中的具体文字,特别是尼采自己所设置的一些提示,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形,因此必定是发生了转变。
首先,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在《悲剧的诞生》中有三处提示,尽管这个问题的明确提出要等到16年后的回顾性文字。这三处提示分别是:第3节中西勒尼的话、第25节“最坏世界”的说法和第18节“三种文化”的列举。
1.西勒尼在国王的逼问下区分了“最好的东西”(不要出生)和“次好的东西”(立刻去死)。为什么他说的是“最好的东西”和“次好的东西”,而不说“最好的东西”和“最坏的东西”?细心考察这里的修辞对于理解这里的问题极其重要。实情乃是,在“最好的”和“次好的”之外,还有一种“最坏的”;西勒尼列举了两种,还剩余一种没有明确讨论;使用“最好的”和“次好的”这种修辞,就是要为“最坏的”留出空间,这三个东西才构成了一个全集。
2.什么是“最坏的东西”?依据排除法,“最坏的东西”既不是不要出生,也不是立刻去死,那么就只能是活着。人们常说,有的时候,死很容易,活着更难;所以活着是“最坏的东西”。为了避免过分阐释的嫌疑,请看尼采的回应:“两者[音乐和悲剧神话]都用这种玩法为‘最坏的世界’之实存本身辩护”。⑤KSA 1,S.154;《悲剧的诞生》,第177页。活着,作为最坏的东西,是因为活着就意味着痛苦。为这种最坏的东西作辩护,也就是在面对痛苦。音乐和悲剧神话是一种面对痛苦的策略,那么还有哪些面对痛苦的策略呢?
3.有三种文化,它们各自提出一种面对痛苦的策略。这三种文化分别是艺术文化、苏格拉底文化和悲剧文化,而本书誊清稿则称之为艺术的、理论的与形而上学的。艺术文化通过使人迷恋于美的面纱而继续生活,苏格拉底文化通过知识疗治生命的创伤,悲剧文化通过一种形而上学的的慰藉——现象可变化,而生命永存。⑥KSA 1,S.115;《悲剧的诞生》,第181页。这三种文化,虽然使用的策略不同,但都是为了让人继续活下去,都给出了一种面对痛苦的策略。
现在我们详细考察希腊人与痛苦之关系的转变。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有三种情形,或者说希腊人有三种面对痛苦的策略,即艺术文化之策略、苏格拉底文化之策略与悲剧文化之策略。以下分别讨论这三种策略。
艺术文化让人如何面对痛苦?根据第3-4节,它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发挥作用。首先,它给出一种神正论。希腊人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创造出诸神。诸神存在,而人类却在受苦,这是神正论必须解决的问题。它如何解决?它让诸神和人过同一种生活,让诸神和人一样痛苦。连神都在痛苦,那么人有痛苦就没什么大惊小怪了。希腊人就这样安慰自己。另一方面,神和人之所以痛苦,那是因为没有做好两件事情——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如果做好了这两件事情,那么就不会遭受痛苦了。于是希腊人的注意力就被转移了,从注意痛苦转移到注意人类自身的实践行为如何保持在限度之内。
苏格拉底文化让人如何面对痛苦?如果具备了相应的知识(明察),那么就具备了相应的德性(明察必定转变为力行的能力;德性本身就意味着可以转化为成功的行动),那么就可以办好事情,获得幸福,避免痛苦。死亡是一种极端的痛苦,苏格拉底如何面对它呢?“通过知识和理由消除了死亡恐惧”。①KSA 1,S.99;《悲剧的诞生》,第111页。这是怎么回事?此处需要根据柏拉图著作《菲多》来理解:“我们深信:如果我们想要对某事某物得到纯粹的知识,那就必须摆脱肉体,单用灵魂来观照对象本身”。“那些真正爱智慧的人是仰慕死的,至少死在他们看来不像其余的人那样觉得可怕。他们对肉体十分不满,深愿灵魂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②[古希腊]柏拉图:《菲多》66D、67E;载于《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19、221页。同时,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经常论证灵魂不朽;关于灵魂不朽的知识让苏格拉底不惧死亡。总之,苏格拉底不惧死亡,因为他觉得死亡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悲剧文化让人如何面对痛苦?首先回顾前两种文化面对死亡的策略。艺术文化的策略:如果恪守在限度之内,那么就不会遭受痛苦;苏格拉底文化的策略:如果有了知识,那么就不会遭受痛苦。可以看到,这前两文化的应对策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如果……,那么就不会遭受痛苦。而现实问题乃是,这个如果……的……,这前半句,我们能够做到吗?前两种文化的应对策略都是假言的方式,假言的方式就意味着局限性,局限于前提可以获得满足的情况。一旦前提得不到满足,它就束手无策了:这在反复无常的现实生活中反而是更常见的,因为意志(我要……)汹涌澎湃地冲击着限度,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人无比苦恼。于是,迫切需要一种绝对的方式。而悲剧文化应对痛苦的策略就是一种绝对的方式:无论现象如何多变,无论痛苦多么沉重,“生命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③KSA 1,S.56;《悲剧的诞生》,第58页。此处的“生命”可以理解为“意志”。
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发生过转变,有这样三种情形,或者说,希腊人有三种面对痛苦的策略。这其中,悲剧文化之策略对希腊人而言最重要且最有力量。悲剧文化不仅在策略上胜过另外两种,而且还把希腊人从否定意志之渴望的危险中挽救了出来。尼采把狄奥尼索斯式的人和哈姆雷特作了比较,发现他们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曾一度发现行动无力改变现实,从而对行动产生了厌恶。这种危险乃是一种佛教式的使人否定意志的危险,只是由于悲剧才把希腊人从这种危险中抢救了出来。④KSA 1,S.56-57;《悲剧的诞生》,第59页。只有狄奥尼索斯精神或悲剧精神,才能使人“从印度走向希腊”,从而获得拯救。⑤KSA 1,S.132;《悲剧的诞生》,第150页。
三、希腊悲剧的诞生
悲剧如何诞生?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第1节第1段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纲领,用以解答这个问题:在希腊世界存在两种对立的力量,这就是造型的阿波罗元素和非造型的音乐性的狄奥尼索斯元素。这两种元素的互相结合产生了既有狄奥尼索斯元素又有阿波罗元素的阿提卡悲剧。这两种元素的互相结合乃是由于希腊“意志”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奇行为。于是,悲剧如何诞生这个问题,就可以被分解为以下两个问题:这两种元素到底是怎样的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如何结合在一起?
如何理解阿波罗元素?尼采为了作答,借用了梦和醉两种生理现象,设想梦与阿波罗元素相对应,醉与狄奥尼索斯元素相对应。我们完全可以撇开梦与醉来面对尼采的相关文本。庄严的诸神形象与超凡神灵的迷人形体,这些美的假象由阿波罗掌管;阿波罗象征着一种面对痛苦的策略,这就是用美的假象掩盖生命的痛苦。尼采引用了叔本华的一段话:“有如在汹涌大海上,无边无际,咆哮的波峰起伏不定,一个船夫坐在一只小船上面,只好信赖这脆弱的航船;同样地,在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里,孤独的人也安坐其中,只好依靠和信赖个体化原理。”接着他解说道:“我们可以把阿波罗本身称为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神像,其表情和眼神向我们道出了假象的全部快乐和智慧,连同它的美。”①KSA 1,S.28;《悲剧的诞生》,第23-24页。据此可见,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第1节就已经把阿波罗诠释为应对痛苦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就是,信赖美的假象及其快乐与智慧。
如何理解狄奥尼索斯元素?尼采在第2节中讲得更清楚:“它不重视个体,甚至力求消灭个体,通过一种神秘的统一感使个体得到解脱。”②KSA 1,S.30;《悲剧的诞生》,第27页。阿波罗象征着对个体化原理与美的假象的执着;与此相反,狄奥尼索斯象征着表象的破碎与对太一的接近。阿波罗象征着假象的快乐,而狄奥尼索斯象征着太一的快乐。假象的快乐与太一的快乐都是为了面对人生的痛苦而采取的策略,两种策略的不同牵涉着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区分了太一(意志)和表象。
前面我们已经把“悲剧如何诞生”化解为“如何理解两种元素”与“两种元素如何结合”这样两个问题,既然对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两种元素已经作了疏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这第二个问题:这两种元素如何结合?书中第7-9节诠释了悲剧的诞生。悲剧是从合唱歌队中产生的,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敷衍了事的回答,必须追问这种合唱歌队是怎样的合唱歌队。尼采说:“我们必须把希腊悲剧理解为总是一再地在一个阿波罗形象世界里爆发出来的狄奥尼索斯合唱歌队。……一种狄奥尼索斯状态的客观化,它并不是在假象中的阿波罗式解放,而倒是相反地,是个体的破碎,是个体与原始存在的融合为一。因此,戏剧乃是狄奥尼索斯式认识和效果的阿波罗式具体体现。”③KSA 1,S.62;《悲剧的诞生》,第65-66页。悲剧是走向阿波罗形象世界的狄奥尼索斯合唱歌队,是狄奥尼索斯的阿波罗式的客观化。然而,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两种元素到底如何结合——它们结合的动力没有交待出来。书中第7-9节仅仅说明悲剧是两种元素的结合,还没有说明结合的动力,而第9-15节就已经开始讨论悲剧的死亡了。这样,真正需要解答的问题被搁置了。我们于何处追寻其解答呢?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借助第16节。第16-25节作为《悲剧的诞生》的第3部分,主题乃是讨论悲剧如何再生;但同时它也对第7-15节即书中第2部分的主题(悲剧的诞生和死亡)作了精辟的回顾。在第16节中,尼采说:“在我们投身于那场斗争之前,让我们先用前面已经获得的认识把自己武装起来。”④KSA 1,S.103;《悲剧的诞生》,第115页。他回顾了用来诠释艺术的两大力量——阿波罗元素与狄奥尼索斯元素,并且回顾这两种元素所象征的意义(假象的快乐与太一的快乐),紧接着引用叔本华的话传达了意志形而上学的内容(音乐是意志本身的映像,音乐是一切现象的物自体)。为什么尼采在此要插入意志形而上学的内容?在第16节的第3段开头(之前与之后均在引用叔本华,插入意志形而上学),尼采终于明确地提出了我们一直追问的那个问题,他的表述是:“当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种本身分离的艺术力量一并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产生何种审美效果呢?或者简言之,音乐之于形象和概念的关系如何?”⑤KSA 1,S.104;《悲剧的诞生》,第117页。他的回答是:音乐具有诞生悲剧神话的能力。音乐在提升到最高境界时也必定力求达到一种最高的形象化,音乐只能在悲剧中为自己的狄奥尼索斯智慧找到象征性的表达。⑥KSA 1,S.107-108;《悲剧的诞生》,第121页。于是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这两种元素如何结合和悲剧如何诞生得到了真正有效的回答:音乐使两种元素结合,音乐使悲剧诞生。这就回应了《悲剧的诞生》第1版的书名《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然而我们千万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而要坚定不移地走完最后一步:音乐是意志的映像,因此真正促使两种元素结合、促使悲剧诞生的乃是意志。这样才彻底回应了此书第1节第1段的话——这两种元素的互相结合乃是由于希腊“意志”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奇行为。于此,悲剧的诞生与意志形而上学的亲密关系昭然若揭。
希腊悲剧借助形而上学的意志把阿波罗元素和狄奥尼索斯元素加以结合而得以诞生。因此,希腊悲剧本身兼有两重元素——阿波罗元素和狄奥尼索斯元素。欣赏希腊悲剧之际,不仅可以看到外观,而且能够看到汹涌澎湃、热血沸腾的内部意志;不仅对悲剧主角的苦难感同身受,而且能够感到一种更强大的快感;①KSA 1,S.144;《悲剧的诞生》,第160页。不仅能够使人领略到阿波罗元素和观看的快感,而且能让人领略到假象世界被毁灭的那种更高的快感。②KSA 1,S.151;《悲剧的诞生》,第172页。
然而由于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剔除了悲剧的两重元素,悲剧走向了死亡。一方面,欧里庇得斯对戏剧开幕和结尾的安排,使戏剧的悬念丧失殆尽,不能让观众关注主角的痛苦,也不能让观众紧张地与主角同甘共苦。这样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效果都没有达到,两重元素也就被剔除了。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知识信念——事物之本质皆可探究,知识可以修正存在——同样摧毁着希腊悲剧的两重元素。本来欣赏希腊悲剧的要义在于感受痛苦之同时感受意志的强大,而苏格拉底的知识信念,给人以一种知识的乐观主义,人们不再能够感受痛苦,反而转身于反省自己的德性,人们也不再能够感受意志的强大,反而转身于追求灵魂之净化和永生。
希腊悲剧的诞生在于对两重元素的同时居有,而希腊悲剧的死亡在于对两重元素之共同丧失。同理,希腊悲剧之再生就在对两重元素的再次居有。然而1870年的尼采和1886年的尼采对此却表现出不同的姿态。1870年的尼采把希腊悲剧的再生寄望于带有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德国哲学和德国音乐。他认为,以康德和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摧毁了苏格拉底的知识乐观主义,是一种概念化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同时,以巴赫、贝多芬和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音乐也象征着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复苏。德国哲学与德国音乐——这两种带有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德国精神,可以让希腊悲剧得到再生。③KSA 1,S.118,127-129;《悲剧的诞生》,第133、144页。而1886年的尼采却对此两种力量不再抱有希望。他认为,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和狄奥尼索斯精神完全相异,特别是叔本华的“听天由命”与狄奥尼索斯精神格格不入。同时,德国的现代音乐很可能是一切艺术形式中最没有希腊精神的。这时尼采认为,他在1870年对德国哲学和德国音乐的希望从根本上败坏了他所向往的希腊精神。④KSA1,S.19-20;《悲剧的诞生》,第12页。如此看来,希腊悲剧之再生可以借助何种力量,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有待思想的问题。
四、希腊的明朗
在1886年《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一文中,尼采对《悲剧的诞生》的写作经过,特别是该书所牵涉的问题作了精要的回顾:1870年普法战争之沃尔特会战炮声响彻欧洲之际,尼采却独自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沉浸于思想和解谜,因而既忧心忡忡又无忧无虑,记下了他有关希腊人的种种思想——那是这本奇特而艰深之书的核心所在。”几周之后,当尼采在法国的梅斯城下时,他还在牵挂着对于所谓“希腊人与希腊艺术的明朗(Heiterkeit)”的疑问。⑤KSA 1,S.11;《悲剧的诞生》,第3页。在此文的第4节,他进而追问道:一个基本问题乃是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究竟是一成不变的还是经历了转变的?⑥KSA 1,S.15;《悲剧的诞生》,第7页。依据尼采这篇16年后的思想回顾,并结合此书的具体解说,可以确定《悲剧的诞生》牵涉的乃是“有关希腊人的种种思想”,而且这正是此书的“核心所在”。《悲剧的诞生》中“有关希腊人的种种思想”包括以下内容:希腊之悲剧如何借助一种意志形而上学而得以诞生,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发生了何种变化,“希腊的明朗”究竟是不是源初的真正的希腊精神。
关于前两个方面前文已作交代,这里专论“希腊的明朗”究竟是不是源初的、真正的希腊精神。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所谓希腊人与希腊艺术的明朗”之观念到底是哪些人物的观念。依据相关研究,温克尔曼、海涅以及黑格尔均把希腊人与希腊精神领会为“明朗”。温克尔曼对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作品作过著名解说——“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oΒe)。温克尔曼很早就把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作为两种对立的类型来解说艺术原理了,而且他的这种解说——“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就是为了对抗“过于激烈与狂野”的狄奥尼索斯。这样看来,尼采对明朗观念的批判针对的乃是温克尔曼。此外,海涅谈到过希腊的明朗(Heiterkeit),而且尼采对海涅的这种观念作过批判,文字见于尼采1870-1871年间为《悲剧的诞生》所写的一份未发表的扩充版导言之中。①[美]奥弗洛赫蒂编:《尼采与古典传统》,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6页、第329-330页。中译本转译自英文,英文serenity是Heiterkeit之对应翻译。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黑格尔在解说希腊精神的时候,也使用了明朗(Heiterkeit)一词,尼采也许读到过:“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各种形形色色的材料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美丰富者化为规定性与个体性。希腊世界的丰富,只是寄托在无数的美丽、可爱、动人的个体上,——寄托在一切存在物种的清晰明朗(Heiterkeit)上。希腊人中最伟大的便是那些个体性:艺术上、诗歌上、科学上、义气上、道德上的那些杰出人物。”②[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1页。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像尼采一样,海德格尔也对明朗观念作过批判:“希腊哲学的穿透力不是在所谓的希腊人的明朗(Heiterkeit)中获得的,似乎希腊人存在于睡眠中。对希腊人之劳作所作的详尽考察刚好展示出,为了通达存在本身,为了穿越闲谈,所需要的诸种努力。”③[德]海德格尔:《柏拉图:智者篇》(GA19),克劳斯曼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然而,在尼采看来,诸如“希腊的和谐”、“希腊的美”、“希腊的明朗”之类的说辞,乃是一些毫无用处的漂亮话,乃是对希腊人的一种敷衍,乃是对希腊理想的放弃,而且也颠倒了古代研究的真正意图或倾向。④KSA 1,S.129-130;《悲剧的诞生》,第147页。诸种明朗之类的观念根源于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的败坏,尽管德国人向来善于向希腊学习,甚至于一提到希腊就有一种家园之感。然而现代以来,这种学习变得越来越肤浅、机械、越来越走向文字校勘和显微镜式研究的学究气道路,越来越丧失了向古希腊学习的真正意义。
然而德意志民族向希腊学习的这种颓败倾向绝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自身的问题;相反这种颓败倾向深深地植根于希腊自身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即是悲剧从诞生到死亡的变化,即是希腊人与痛苦之关系的种种转变,即是源初的希腊精神向阿波罗式明朗与苏格拉底式明朗的转变。而现代德意志学者恰好就把希腊精神领会为阿波罗式明朗与苏格拉底式明朗了,于是错失了源初的和真正的希腊精神。
关于阿波罗式明朗与苏格拉底式明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作了相应的解说。书中第1节解说阿波罗元素时,就已经提示出阿波罗式的明朗:“造型之神的那种适度的自制,那种对粗野冲动的解脱,那种充满智慧的宁静(Ruhe)。”⑤KSA 1,S.28;《悲剧的诞生》,第23页。这里阿波罗式明朗的要义在于适度、自制与智慧,懂得了适度与自制,进而也就懂得智慧。书中第9节进一步解说道:由于悲剧是两种元素结合的产物,故而悲剧本身含有阿波罗元素。在悲剧中的阿波罗部分中,阿波罗式的明朗得以彰显;这种明朗以确定的方式和美化的方式,能够打消许多恐怖因素,带给人们惊喜和欢乐。⑥KSA 1,S.65-66;《悲剧的诞生》,第70页。悲剧死后,明朗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奴性的明朗,这是由于悲剧的死亡,希腊人放弃了理想性,不再相信过去以及将来的理想性,恰如奴隶一般,不再懂得承担责任和追求伟大,仅仅看重眼下的快乐。①KSA 1,S.78;《悲剧的诞生》,第84-85页。关于苏格拉底式的明朗,于此书第15节提及:苏格拉底的科学乐观主义,相信知识可以带给人快乐,这是苏格拉底式的明朗。②KSA 1,S.101;《悲剧的诞生》,第113页。关于希腊明朗,此书于第17节尾段作了总结性的陈述:希腊精神之表层的诸种元素,可称之为非狄奥尼索斯精神,而非狄奥尼索斯精神表现为希腊的明朗。这一非狄奥尼索斯精神或希腊的明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阿波罗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可称之为阿波罗式的明朗,其根本特征是用美的假象来战胜苦难。另一种是苏格拉底式的明朗,其根本特征是用知识去指导生活,去战胜苦难;因为它的根本信念乃是自然可知、知识万能。③KSA 1,S.115;《悲剧的诞生》,第129页。
在尼采看来,所谓希腊的明朗,无论是阿波罗式的明朗,还是苏格拉底式的明朗,都不是源初的真正的希腊精神。源初的、真正的希腊精神乃是借助意志形而上学而诞生的希腊悲剧的精神。希腊悲剧的精神,既不需要借助美的外观去安抚众生,也不需要借助万能的知识去抵御苦难;从而在根本上,无需忧虑所借助之外物的致命缺陷和某个时候的突然坍塌。它只需借助希腊人自身就完全可以居有的形而上学的意志。这种意志自在而强大,勇敢而无畏,甚至渴求可怕之物有如渴求敌人,以便检验自己的力量。④KSA 1,S.12;《悲剧的诞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