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把戏
文/翩翩
人生不过是演独角戏,就像一个骑独轮车的小丑,躲在帷幕后苦学苦练,只为等到别人看到自己技成的瞬间。掀开帘子,在镁光灯打到自己的倦容,掌声热烈开来,就必须迅速带上面具,修炼出无比精致的笑容。
这世间,有很多很多各色各样的人,打探你,追究你,探问你做某件事情的意义;好些人,就算你告诉了他们做某件事的初衷,他们也不是真的关心你,他们只是好奇心作祟,才想在你的人生之路上,听到解释,进而为自己的选择减少点麻烦。我不是足够伟大的人,可以做明星照亮黑途,我没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豁达,也没有“色即是空”的看淡,我需要很多感情,去把自己的肉身撑满,也需要很多体验,去安慰平凡单调的生命。人生在世,本就是苦中作乐。佛说人在腹中,就有胎狱,只有历经艰苦,才能忘记前世。不过能有人关心你,还是件幸事。一个人赶路久了,特别是幽暗的夜,晚风把叶子一片片揪下,露水打湿了虫子的叫声,在筋疲力尽时忽然看到前方有一凉亭,有甘凉的泉水和为下一个路人准备的油纸伞,也是件暖心的事儿。
好多人,随便地恋爱,看到一个人,就紧迫地相随,然后像盘树根一样纠缠,付出,以为这就是爱情,其实也不过是寻一个遮蔽困苦的凉亭,希望能在这油纸伞未凉的体温上,生出对爱最美最纯粹的幻想,进而佐证自己并未失去爱一个人的能力。我相信爱就像骨子里的血液一样,它不会随着身份、学识、外貌、年龄而变化,它是推着轮椅也愿登山的坦荡,和就算竹篮打水一场空也愿一分一分存钱,一天一天陪老的天真。而现今的尘世,一个傲人的胸部,或者一辆敞亮的车子,一个买醉的深夜,抑或一张虚幻的照片,就可以让你的嘴巴随便对一个人说出爱这个字;一盏迷离的灯光,一杯酒精的下脑,都可以让不识真名的你们十指相扣。这样的爱,又有几分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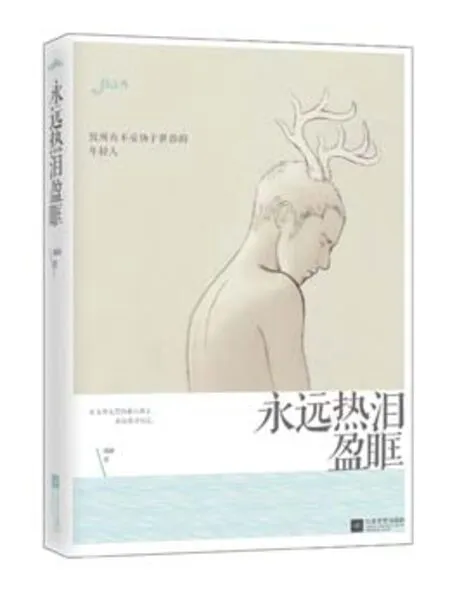
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了。想起千禧年前,能喝一碗酸梅汤,吃几根自己冻的冰棍,在大树下跳跳皮筋,看些路边摊掉了扉页的小人书,收到暗恋的同学递来的纸条,都觉得幸福的小事,现在已愈来愈难寻。吃的越来越好,爱人越来越多,城市越修越高,休闲娱乐的玩意儿应接不暇,马路宽敞敞的停了一溜又一溜的车辆,有些向东,有些向西,我们却像走在黄线上一样迷茫慌张,不知是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是独自一个人走,还是叫几个同伴,结伴而行更安全。高大的楼房,就像板着脸孔的巨人,以拒绝的姿势喝住你:这是有钱有权人玩的天堂。而无背景无仰仗的人,就像从楼房脚下的阴影里爬出的蝼蚁,一只只,往返于加班的午夜列车,或肮脏的苍蝇馆子里,只有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拧亮台灯,才觉得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代越来越难让人琢磨透,也许是因为生活在里面的人,已经习惯了提速的生活,也不想被他人琢磨透吧!没有人喜欢扒光了衣服被人用放大镜去看。有些人,并不想自己走,却被世俗的舆论逼着走,你不走你就是他人眼里的怪物;有些人,是看着别人走了,自己就慌不迭的走了;而更有些人,是为了逃避现时的责任,想赖在青春里多做几个晚熟的梦。
城市就像一个人,人也像一座城,城里住着舍不得离去的人,人心住着舍不得丢下的城。城市有生老病死,人有喜怒哀乐,城市有摧枯拉朽,人有日益麻木,城市和人,只有并排的紧紧牵着手站在一起,才能抵挡住兵荒马乱的替代和岁月一天天的啮噬,才能应付的了接踵而来的变化和幻觉破碎的悲哀,才能没那么的寂寞,而我们终究不过是,城市里住着的一群,害怕寂寞的人而已,只是找了高明的借口。它叫做——梦想的把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