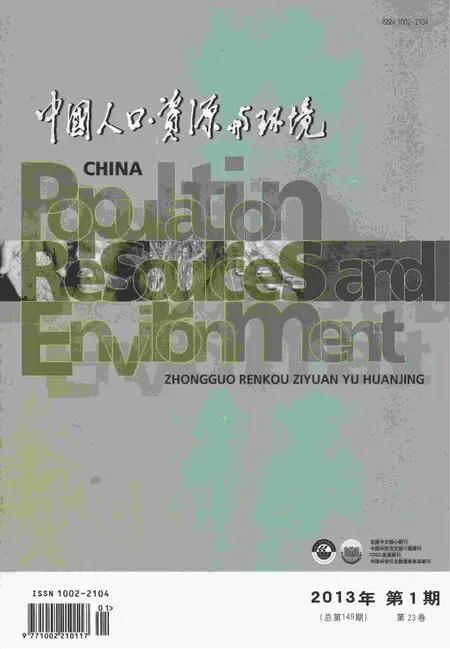信息社会进程中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与城市融入
梁 辉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2.湖北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3)
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是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当今“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却被封闭的体制挡在城市门外。农民工进入城市,面临的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离开了流出地乡村基层政府的管理,又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关照”,人力资本积累过程断裂,可用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急剧减少[1-2]。调查数据显示,年轻的农民工对手机、网络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依赖性。“80 后”农民工中72.9%的人有手机,62.59%的人去过网吧[3]。可以说,信息通信技术和产品的可获得性已经趋于公平,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拥有了手机,但这些先进技术产品为农民工群体所获得后,对他们的生存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研究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可以通过改变农民工的人际传播与互动模式,从而改变社会网络的结构,影响他们的交往、参与及信任结构,并最终影响城市融入的进程。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就是人际传播,是人们获得生存资源、发展机会最重要的载体和工具,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4]。而农民工进城后,以乡土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传播的频度、效率都有了提高[5]。这里的人际传播包括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和借助媒介的间接传播两种。进城之前,乡土文化中的人际传播以面对面的交流为主,而在进入城市之后,农民工的交流形式除了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之外,更多地依赖于电话、书信、网络等传播媒介的间接交流,甚至间接交流方式起到更主要的作用。本文研究的就是,以手机、网络等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为传输媒介的间接人际传播,帮助农民工结成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并进而如何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进程。
1 人际传播:农民工的无奈选择
1.1 原有乡土文化和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
农民工曾在乡村生活了比较长的时间,而中国的村落文化及社会结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积淀,形成了特有的信息交流方式,即通过人情关系来进行信息的传播。他们习惯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日常社会交往和情感互动为目的的交流方式,并据此建立人际传播网。在进入城市之初,受村落文化的思维惯性影响,通常也会选择相对可靠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或者街坊邻里作为信息交流的对象,来应对陌生的城市生存环境。
1.2 信任是农民工选择人际传播的关键因素
农民工选择人际传播,本质上是选择了信任。中国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谁是最可信赖的人”。在农民工看来,真的信息往往来源于群体内部,来源于亲缘关系,假的信息往往来源于无亲无故的人或由社会发布[6]。在城市里,农民工很难跟城市市民、政府以及大众传媒建立起信任感。
之所以难以形成这种信任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信任的形成跟熟悉的程度相关。费孝通认为,“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等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按频数分布进行排序发现,农民工最信任的是在城市的老乡,其次是工作中的同事,第三是城市工作的亲戚,最后是房东、当地的管理人员、邻居;另一方面,求助与帮助是农民工与市民交往的另一种特殊方式。社会信任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益、资源交换和交换双方的心理基础。信任一方将资源委托给另一方,其间重要的心理机制是,委托方对受托方回报的必然性的认识。“城市市民不信任农民工是农民工不信任市民的前提,他们还没有设计出一种和城市人共享利益的信任机制。”[7]
1.3 市场失灵、组织低效,只能依赖人际传播网
首先,制度阻碍带来的信息接触机会的不均等性等使得农民工群体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道德风险。由于农民工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在与用工企业的交易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此,厂商便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蒙蔽农民工,如不签订用工合同、不为他们买保险、不支付工伤事故赔偿等。农民工为了消除市场失灵给他们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而选择让他们最为信任的初级社会关系网,作为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
其次,找工作的成本也是他们选择人际传播网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农民工来说,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严重供过于求的市场,市场无力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市场找工作,不仅成本高,难以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后,收益也非常低。对农民工来说,无论流出地还是流入地的社会组织机构(职业中介、劳动服务公司或政府部门等)均增加了他在城市的就业成本。
总之,有价值的信息无从获得,与雇主的相互信任无从建立,求职者与雇主的相互约束没有体制保证[8-9],都使得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选择了人际传播这一单一而传统的获取信息方式。
2 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对现状的分析
2.1 影响因素分析
2.1.1 职业
职业是决定农民工社会网络边界的主要变量。李培林[10]把农民工分为三个阶层:“一是占有一定资本并雇佣他人的业主;二是占有少量资本并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三是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打工者”一般来说,职业不同,人际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同。研究发现[11],从事餐饮、装潢、集市贩卖、裁缝、修理服务等行业的属于雇佣与自我雇佣性质的农民工小老板,在与城市社会其他人群的互动中,有许多已属于工具性的人际传播;而仅靠出卖劳动力的属于“雇工”性质的农民工与其他人群的互动,则多属于满足情感交流的非工具性人际传播。
2.1.2 居住方式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有两种居住方式:聚居(工棚式和村落式)和散居(租房式和进入家庭式)。已有研究发现,散居的农民工与老乡间人际交往较少,生活方式与当地常住人口已无太大差别。从职业上看,散居的农民工大多来自服务业或商业,很多保姆也采取家庭式散居。而聚居使农民工较容易地接触到亲缘和地缘关系,在人际交往上更倾向于本群体内部。建筑业和大型加工业多属工棚式聚居,与市民和主流文化相对隔绝;个体工商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多属村落式聚居,与市民和主流文化接触也较少[12]。一些“城中村”由此产生,郑思齐等[13]发现,“城中村”中移民的劳动力产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普通住房社区中的移民。
2.1.3 家庭
家庭功能分化程度影响农民工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人际交往选择。通常,家庭功能分化越低,意味着从家庭内部可能得到的支援越多,寻求支援的人际交往更依赖于家庭成员之间。反之则越依赖于家庭外部而寻求社会支援[14]。不仅在农民工群体内部,这在城乡之间也有明显差异。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由于共谋生产的强经济关系,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很高。而城市家庭已丧失了生产功能,城市生产活动的非家庭化和各种业缘群体的发达,使他们比农村居民有更多的需要和机会去发展家庭外关系。
家庭成员之间居住地的空间距离也与家庭成员人际传播网络有关。空间距离越近,越容易被要求提供社会支援。空间接近程度与相互交流的频繁度成正相关。霍曼斯等人认为,频繁的接触能够导致更多的支持性关系。经常通过电话交流能起到传递彼此需要的作用。经常性的面对面交流能使双方得到物品和服务上的支持[15]。
2.1.4个体因素
不同的性别,具有不同的心理特点,他们会利用新技术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如女性通常会借用网络工具来倾吐日常琐事,对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发现,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网民比例比男性高11%[16]。
年龄也会影响人际传播网络中人际交往的数量和质量。一般地,年龄越大,其接触的人更多,那么建立起的人际关系网也更加复杂,可利用的社会支持网络和资源也更加丰富。也有人认为,年龄与人际交往之间呈反向关系。原因在于,年轻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更加活跃和频繁,获得的社会支持也会更多更广。
受教育水平越高,社会支持网络规模越大。通常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越强,这将增加与其他人构建社会关系的机会。此外,受教育水平意味着能够为其他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的交换将会进一步拓展其社会关系网[17]。
收入越高,意味着所能支配的社会资源也多。那么,更有可能为他人提供帮助,这将对于一个讲求双向互动的人际关系网络构建具有促进作用。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已婚人群比未婚人群在人际传播网络的构建上更具优势。
2.1.5 流动经历
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时间增加,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认识和适应性增强,对城市里的其他群体也从陌生到逐渐熟悉,这些对于他对城市信任感的加强具有强化的作用,进而促使社会交往增多,社会资本也随之增加。
更换工作的经历也对人际传播网络有影响。农民工流入一个新城市后,他们有动机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关系构成更具多样性。更换工作的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丰富工作经验,以利于拓展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2.1.6 方言熟悉程度
在一些文献中,开始将方言熟悉程度作为城市融入的衡量标准之一。虽然新媒介技术发展迅速,但语言仍然是人们交流的重要媒介。农民工若能够讲一口不错的当地的方言,这将迅速拉近他们与城市市民之间的距离,减少他们之间的陌生感,增强其间的可信度,对于他们构建次级人际关系网具有促进作用。
2.2 人际传播网的人群差异:农民工与农民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
2.2.1 农民工进城后与原来的区别: 人际传播建构方式的差异
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与乡村社会的差异就根本而言在于社会形态的不同[18]。适应了乡村社会中人际交往模式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对新技术的接受与使用或许并不滞后,但他们在乡村社会多年积淀下来的建构人际关系的模式遇到了挑战。因此,对农民工而言,最大的挑战体现在人际传播建构方式的差异上。
传播媒介更加丰富。传统的乡村人际传播形式单一,是面对面式的,语言、姿势或表情为主要的人际传播媒介。而新技术的普及使得农民工不需要再像过去面对面式的交流,不再受距离的限制,可以通过手机发短信或打电话,通过电脑和互联网发送电子邮件、网聊等。
传播内容更加多样。以前人际传播的内容大多是家常里短、生活境况,话题以感情交流为基础,以村落为中心。而新技术使得农民工有机会接触到城市里多元的信息,这改变了他们以往人际交往的单纯性和亲密性,人际交往趋于复杂,且更具目的性。通过手机或是网络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主要包括工具性传播内容(求职信息、技能培训信息、住房信息、健康医疗信息、法律政策信息、投资理财信息)、情感性传播内容(情感信息、子女教育信息)、社交性传播内容(娱乐消费信息、衣着饮食信息、时事信息)[19]。
情感性减弱。新技术使得农民工在交流内容上更为丰富的同时,也改变了其中的结构。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农民工在进行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更多关注于“求职信息”、“技能培训信息”等,而对情感信息、家长里短的谈论逐渐减少,也即情感性相对减弱。这主要是因为,新技术的使用消除了地域距离的限制,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这本身就是会削弱在交流时的情感性。另外,农民工在获取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时,新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使他们不再是从其老乡那里,也许还会跟陌生人进行交流。
可信度减弱[20]。农村生活空间较小,世代形成的人际关系熟悉亲密,因此自然形成高度的信任。而农民进入城市后,基于求职或是生活上的原因,建立了新的关系,但是这一关系相比较之前乡土文化中的关系,稳定性大大减弱,信任程度也大大削弱。原因在于,农民工就业的“流动”性意味着他们之间关系的短暂性,使得在流动中建立的社会关系很难形成互动,“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而流动人口所拥有的资源无疑是难以给对方带来更多利益的,从而导致他们之间信任感下降。
2.2.2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与市民的区别
新技术对人际传播网的影响是不分地域、身份的。在城市里,新技术同时改变着市民和农民工的人际传播方式,但是,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格局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加之城市文化与农耕文化、教育水平、工作类型和时间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农民工与市民的人际传播网在新技术普及的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信息传播媒介不同。市民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大众传媒,而农民工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是人际传播[21]。农民工按照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结构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非制度化信任为基础的,这种人与人互动所形成的纽带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而城市市民之间的人际关系似乎并没有像农民工那样呈现出这样明确、层次分明的差序格局。再加上市民拥有以他们的生活为主体的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拥有需要更高技术水平和信息产品的博客、论坛等。使得农民工在人际传播的效率和质量上都比市民高。
信息传播内容不同。工具性传播是指带有功利目的的信息交换行为,实现的是物质性的利益;非工具性传播是指不带有功利目的的信息交换行为,实现的是精神性的利益[22]。农民工进城之初为摆脱孤独、释放心理压力,和老乡、亲戚的交流以非工具性为主。一段时间之后,农民工为实现职业升迁、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而不断拓展人际传播网络,这时的人际传播内容开始转为工具性传播。而城市的社会关系多是契约化、制度化和非人格化的,人际传播的内容也以工具性传播为主。
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职业分布,决定了他们与市民的日常接触主要集中在城市生活服务类的信息上。城乡交流信息以工具性信息为主,与农民工打交道最多的应该是农民工集中工作的相关部门人员,他们作为管理者,必然要在工作和生活等诸方面与农民工经常打交道。对于市民而言,是从他们与农民工与其生活相关度而言进行交流的,因此主要集中与保姆、装修工、小时工等的信息交流和信息观察上。因此,他们在城市里的人际传播网拓展也相当有限的。而市民的人际传播对象则要比农民工的广泛得多,他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生活就业方面的信息,进行业缘关系的拓展,更多地是通过其他方式(如旅游、聚会、休闲娱乐等)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网,来丰富他们的生活,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3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信息传播网更新与城市融入能力提升:一个理论框架
3.1 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了农民工信息传播网络的更新
以往社会学的研究中不涉及社会互动过程中各种传播媒介对社会关系的不同影响,而传播学的研究又忽略了某种传播媒介的使用对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关系中作用的差异。因此,我们还需要研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而言,手机等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给他们社会关系的建立带来怎样的影响?
从掌握的文献看,相关研究主要从信息通信技术对中低收入群体社会网络构建、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等方面展开,研究结论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种观点。一方面,沉溺网络使人对社会交往失去兴趣,对社会网络有消极影响。Fischer 发现,人们使用通信网络保持和远方的联系、与认识的人交流,而不是与陌生人建立新的纽带[23]。Sebastian Ureta 认为,手机甚至导致新的社会排斥产生[24]。另一方面,互联网提供了低成本的通讯工具,人们在虚拟世界寻找感兴趣的论坛或参加网上社团,增加了个人社会资本。另外,手机使低收入群体打破原先的社会排斥,直接进入移动通讯技术建构的信息网络,为改变信息贫富状况提供可能[25]。
专门针对农民工信息技术使用的研究较少。一般认为以手机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为农民工浏览信息、娱乐和聊天提供了工具,在陌生人社会便于与朋友保持联络[26-27],一吐打工生活的不快和郁闷,甚至逐渐改变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另外也加快了“招工”、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等信息的传播,提高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13],并赋予他们抵抗恶劣的工作环境、超时加班及低收入的状况的力量。
以上的研究给了我们思路的启发,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制度上的障碍,与城市居民间的不信任和城市居民的歧视是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主观原因。那么,以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为媒介的人际传播以及由此构成的人际传播网络,是否给农民工突破城市融入中的这些障碍提供可能呢?
首先,新通信技术对农民工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具有维系的作用。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初,基于信任和成本的考量,依然会选择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网,或者称为初级社会关系网。随着流动性的加强,也给这种关系的维系带来困难,而手机等易携带的传播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他们以全新的方式与家乡之间维系亲近和经常性的相互联系。
其次,新的传播技术帮助农民工实现人际关系网的拓展[28]。人际传播一直都是人们获得生存资源、发展机会最重要的载体和工具。如果将农民工在进城之初所依赖的,以情感性为特征的血缘、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定义为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那么这种关系网虽然降低交易费用,却强化了其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其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29]。在构建城市的职业上升通道、提升社会地位、增进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等方面是不利的。因此还需构建次级社会关系网络,也就是工具性的社会网络。而手机等信息通信媒介为此提供了可能。首先,网络中介传播作为一种水平式传播,不同于现代社会层级体制下的垂直式传播,再加上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从而更有可能克服现实世界中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间沟通的种种障碍,使他们暂时忘掉各自的身份。其次,手机等信息通信工具的易携带性也克服了农民工流动带来的组织构架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搭建的“虚拟”网络完全可能帮助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的重构。
最后,新技术对农民工人际网具有选择性强化和补偿的作用。如果说农民工流动初期需要的,是金钱等的物质帮助和如分担体力劳动等的具体的行为援助的话,那么在渡过了进城的适应期之后,就会逐步向高层次的发展性需求转变,如提高工作技能、享受同等待遇等,被认同和归属感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农民工也是理性的经济人,遵循MR=MC 的原则,在既定约束下进行社会交往投资,直到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为止。Linda Yueh 曾提出一个社会资本投资模型,将社会资本投资看做是一种成本收益决策,考虑了时间、物质(货币或实物礼品)和非物质资源(如感情、友谊等)因素,这些因素以经济或非经济收益的形式折算成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经济收益可以是通过关系找到一份工作,非经济收益可能是广交朋友或保持亲戚间的和睦友好关系的效用[30]。
3.2 信息传播网络的更新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一般是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认同自身新的社会身份的过程与状态[31]。因此,农民工进入城市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人口流动,除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地域空间转换;从土地农业生产到以标准化、规则化为特征的城市工业生产的生产空间转换;从基于血缘、地缘的乡土社会到基于业缘的不同交往规则和行为模式的社会空间转换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主观层面的价值观念与身份认同的转换。信息传播技术和工具在农民工群体内的普及导致农民工信息传播网络的更新,并进而通过以下几个路径影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
图1给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反映了在信息技术变化条件下,信息网更新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和影响,指出了在信息化社会进程中农民工人际网络演化。
3.2.1 信息传播网络、自我认同与城市融入

图1 信息传播与农民工城市融入Fig.1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migrant workers city into
从主观方面,信息通信网络能够在建构城市身份方面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超过对农村的认同,而他新的城市身份还没有形成,因此他们重建身份的需求强烈。已有文献[32]将身份认同作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指标,正如社会身份理论所说,“通过与别的群体对比,个体和群体需要社会身份来提高他们的自尊和内聚力。”农民工群体所需要便是城市身份的自我认同[33-37]。首先,认清自己的新角色,在陌生的城市“告诉自己我是谁”;然后通过兴趣爱好、消费模式等的自我展示,在自己群体内部或者当地居民中“告诉别人我是谁”;在相互交流和交往中再“告诉自己别人是谁”,从而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而信息通信技术为媒介搭建的人际传播网络,在这一自我认同过程中起到桥梁的作用。
首先,信息通信网络可看做是提升“想象中的自身”社会地位的特殊方法。曹晋对上海钟点女工手机使用情况的分析发现,女工们利用手机灵活安排家政服务时间,抵制那些歧视自己的女主人的劳动续约,手机成为一个有效地避免雇主与钟点工当面冲突的处理劳资关系的工具[38]。这些都表明,以手机为代表的新的传播技术提高了农民工对个体生存环境和自我发展的掌控能力,或者说,信息传播网络帮助农民工在主观上实现了自我认同①社会身份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有关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最终是通过个体的自我心理认同来完成的。。
另一方面,信息通信网络实现农民工联系他人的需要,完整自身、对抗孤立阶段的需要。手机的快速动员和联络作用帮助钟点工们一致提升家务计时劳动的价格,雇主面对整体提价也只好接受[38]。自我认同的建立源于两种讨价还价能力,包括市场讨价还价能力(market bargaining power)和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借助信息传播技术构建的人际传播网络提升了农民工群体集体性协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加强了农民工组织能力。
3.2.2 信息传播网络、流动性与城市融入
农民工是一个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群体,Knight 等研究发现中国农民工流动性普遍高于城市劳动者,也数倍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另外还呈现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如教育程度高者有非常显著的资源流动倾向,而教育程度低者则往往出于风险规避倾向于不主动流动。从对北京市农民工就业史的研究发现,主动流动给农民工带来的收益比被动流动更高[39]。章元等[40]的研究发现,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并不能直接给他们带来更高的工资水平,但是却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流动性来间接地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有调查发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流动次数有影响,而社会资本对职业流动的方向有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再次职业流动的方向越向上[41]。还有不少的研究都发现,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社会地位提升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人力资本,而信息传播网络便是信息社会下社会资本形成和巩固的重要途径。
可以说,以信息传播技术为媒介的人际传播网络促进了农民工的流动性。一方面,流动经历的增加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从而更有可能提高流动者与工作之间的匹配程度,提高边际生产力。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促使了流动,而流动的过程又形成更大的社会网络,这样的循环累计,经历的增加在帮助农民工打通职业上升的通道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References)
[1]杨云彦.社会变迁与边缘化人群的能力再造[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6):3-8[Yang Yunyan.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bility Recreation of the Marginalization Group[J].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2008,(6):3-8.]
[2]杨云彦,徐映梅,胡静,等.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J].管理世界,2008,(11):89-98.[Yang Yunyan,Xu Yingmei,Hu Jing,et al.Social Transformation,Interventional Poverty and the Ability Recreation[J].Management World,2008,(11):89-98.]
[3]辛岭,王艳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S1:93-100.[Xin Ling,Wang Yanhua.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Level of Farmer and Farmer’s Income in China[J].Technology Economics,2007,S1:93-100.]
[4]范红,曲元.手机短信的大众传播功能和效果[J].清华大学学报,2004,(6):72-76[Fan Hong,Qu Yuan.Mass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and Effects of Text Messages of Mobile Phones[J].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2004,(6):72-76.]
[5]陶建杰.都市生活中的乡土关系—对进城农民工生活方式的人际传播视角解读[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79-83[Tao Jianjie.The“Xiangtu relation”in city life:an analysis of peasant migrants’life mode from the angl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7,(3):79-83.]
[6]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J].社会学研究,2003,(1):1-11.[Zhai Xuewei.Social Mobility and Personal Trust:On the strength of trust and the strategy of getting jobs for rural migrants[J].Sociological Research,2003,(1):1-11.]
[7]卢国显.信任:农民工与市民主观距离的实证分析[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2):25-30[Lu Guoxia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ubjective Distance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and City Residents[J].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2007,(2):25-30.]
[8]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Bian Yanjie,Zhang Wenhong.Economic Systems,Social Networks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1,(2):77-89.]
[9]李红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的断裂现象[J].青年研究,2011,(2):15-22[Li Hongyan.Fracture in the Information Accessing Channels for Young Migrant Workers to Getting a Job[J].Youth Studies,2011,(2):15-22.]
[10]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42-52[Li Peilin.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J].Sociological Research,1996,(4):42-52.]
[11]朱虹.生活方式的变迁与手机社会功能的演变—基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调查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3):42-50.[Zhu Hong.Lifestyle Chan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Mobile Social Function[J]Academic Jou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Phy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1,(3):42-50.]
[12]文一篇.不同居住模式下农民工的信息接触与城市融入状况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1.[Wen Yipian.Research on the Status of Information Contact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Two Different Residential Models [D].Changsha:Zhongnan University,2011.]
[13]郑思齐,廖俊平,任荣荣,等.农民工的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2):73-86.[Zheng Siqi,Liao Junping Ren Rongrong,et al.Housing Policy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Economic Growth[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1,(2):73-86.]
[14]蔡禾,叶保强,邝子文,等.城市居民与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J].社会学研究,1997,(6):8-15.[Cai He,Ye Baoqiang,Kuang Ziwen,et al.The Comparison of City Intendion For Seeking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City Residens and Suburban,Rural Residents[J].Sociology Research,1997,(6):8-15.]
[15]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1(1):76-82.[He Zhaiping.Research of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broad[J].Social Science Abroad,2001,(1):76-82.
[16]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J].新闻大学,2011,(2):145-150.[Zhou Baohua,Lv Shuping.Empirical Research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New Media Use[J],News University,2011,(2):145-150.]
[17]周云,彭光芒.人际传播中的信息交换与利益实现[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5,(4):18-21.[Zhou Yun,Peng Guangmang.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Interest Achievement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5,(4):18-21.]
[18]李红艳.手机:信息交流中社会关系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手机行为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1,(5):60-64.[Li Hongyan.Mobil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hone Behavior Research[J].China Youth Research,2011,(5):60-64.]
[19]陶建杰.农民工人际传播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5):97-104.[Tao Jianjie.A Study on Migrant Workers’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J].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2010,(5):97-104.]
[20]王波.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与人际传播[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88-91.[Wang bo.The Social Spac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Migrating Population[J]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7,(3):88-91.]
[21]徐丙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2-96.[Xu Bingkui.Social Network of Peasant Migrants in City and Thei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7,(3):92-96.]
[22]李红艳,宋文军,旷宋仁.农民工与市民作为受传者的信息传播内容之分析: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信息传播内容的实证研究[J].图 书 与 情 报,2009,(5):44-47.[Li Hongyan,Song Wenjun,Kuang Songren.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when Farmer-workers and Residents are Acceptors:An Empirical Study on of the Information between Farmer-workers and Residents[J]Library and Information,2009,(5):44-47.]
[23]Fischer,Claude S.America Calling: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to 1940[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22-422.
[24]Ureta S.Mobilizing Poverty?Mobile Phone Use and Everydany Spatial Mobility Among Low-income Families in Santiago[J].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8,24:83-92.
[25]邱林川.从信息中层到信息中坚[J].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10).[Qiu Linchuan.From the Information Middle to the Information Backbone[J].21stCentury:Internet Edition,2006,(10).
[26]Ngan R,Ma S.The Relationship of Mobile Telephone to Job Mobility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J].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2008,(21).
[27]杨善华,朱伟志.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的解读[J].广东社会科学,2006,(2):168-173.[Yang Shanhua,Zhu Weizhi.Phone:Select“Active”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Mentalit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Phone Interpretation[J].Guangdong Social Science,2006,(2):168-173.]
[28]樊佩佩.从传播技术到生产工具的演变—一项有关中低收入群体手机使用的社会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82-88.[Fan Peipei.From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Productive Tool:A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Use of Mobile Phone by Chinese Mid and Low Income Classes [J].Journalism &Communication,2010,(1):82-88.]
[29]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Zhu Li.On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the Peasant-worker Strata[J].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2002,(6):82-88.]
[30]叶静怡,周晔馨.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0,(10):34-46.[Ye Jingyi,Zhou Huaxin.Social Capital Conversion with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From the Survey Evidence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J]Management World,2008,(5).]
[31]杨瑾,谭娟娟.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4):42-44.[YangJing,Tan Juanjuan.The Research of Peasant-workers’Social Inclusion and Happiness Index 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J].Journal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08,(4):42-44.]
[32]李艳,孔德永.农民工对城市认同感缺失的现状、原因与对策分析[J].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5).[Li Yan,Kong Deyong.Migrant Workers’Missing of Urban Identity[J].Shandong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ors’College,2008,(5).]
[33]雷蔚真.信息传播技术采纳在背景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探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88-98.[Lei Weizhen.The Roles of ICT Adoption in the Migratory Adaptation of the Rural-urban Migrants in Beijing[J].Journalism &Communication,2010,(2):88-98.]
[34]陈韵博.新一代农民工使用QQ 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0,(8):80-85.[Chen Yunbo.An Analysi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Social Network Built by Using QQ[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2010,(8):80-85.]
[35]丁未,宋晨.在路上: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为个案[J].现代传播,2010,(9):95-100[Ding Wei,Song Cheng,Kong Deyong.On the Road:Mobile Phone With Migrant Workers Autonomy Gain—by the Case of the Western Bimodal Village Migrant Workers’Job Experience [J].Modern Media,2010,(9):95-100.]
[36]丁未,天阡.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与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研究[J].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8,(12).[Ding Wei,Tian Qian.A Study on the Use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ake the Taxi Drivers from You County in Shixia Village of Shenzhen as Research Cases[J].Communication and China:Fudan Forum,2008,(12).]
[37]郑松泰.“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10,(2):106-124.[Zheng Songtai.Young Rural Workers’Living Ecologies and Self-identific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information-led [J].Sociology Research,2010,(2):106-124.]
[38]曹晋.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2):71-77.[Cao Jin.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Gender:a Case Study of the Use of Cell-Phone by Migrating Domestic Women in Shanghai[J].2009,(2):71-77.]
[39]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7):70-76.[Bai Nansheng,Li Jing.Research of Employment Mo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J].Managemen World,2008,(7):70-76.]
[40]章元,李锐,王后,等.社会网络与工资水平:基于农民工样本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8,(6):73-84.[Zhang Yuan,Li Rui,Wang Hou,et al.Social Networks and Wage levels: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amples of the Migrant Workers[J].World Economic Forum,2008,(6):73-84.]
[41]刘金枚.社会网络、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Liu Jinmei.Social Networks,Human Capital and Reflowing of Vocation of Peasant-workers[D].Wuha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