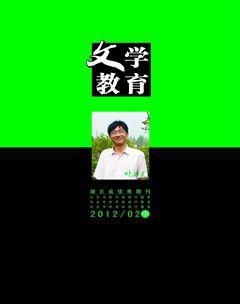荒诞的幸福与局外的哲思
刘双 单科峰 张庚
[摘要]阿尔贝·加缪,一个熠熠生辉的不朽名字,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界碑,著名的存在主义大师。他以简洁、明晰、纯净的笔力,为人们呈现出二十世纪以来以荒诞为特征的生存状态,“阐明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其名著《局外人》、《西绪福斯的神话》、《鼠疫》以及《反抗的人》等都以其深沉的精神力量和深刻的哲理关怀给人们以隽永的启示。
[关键词]加缪;荒诞;局外人;西绪福斯的神话
《局外人》中莫尔索是个公司的小职员,他很平庸,对别人很有意义的事,在他看来都毫无意义:升迁,去巴黎工作,亲情,友情和爱情。但是,他在特定的环境下遭遇了一系列事,这些事串联起来构成他与社会的冲突,尽管他自己始终不这么认为。他首先用葬礼上的平静表现、“大概是不爱”的坦然回答,继而又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开枪打死与自己无关的阿拉伯人,以此来否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逻辑。这是作为人的荒诞的第一方面:人脱离自己,脱离所谓的人性。《局外人》的开篇实在是极不平常的:“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样亲昵的称呼多半是从孩子口中说出来的,而偏偏莫尔索是个上过大学的年轻人。他在临刑前,以极其冷静又极其枯涩,不乏幽默,又带有几分激情的口吻,讲述他普通单调的生活,直讲到不明不白就被判处死刑。从头至尾,没有一句辩解,没有一句假话,这也正是他被判死刑的深层原因。人们不理解也不会容忍一个人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而没有哭泣,就是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并且还在母亲的棺木前抽烟、喝咖啡……更有甚者,他在母亲下葬的第二天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看滑稽电影,而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以至于名声不好的邻居求他帮忙写信惩罚自己的情妇,他会同意。他生活态度消极萎靡,对人对事的反应都是无动于衷、机械迟钝。女友问莫尔索是否想跟她结婚,他说:“怎么样都行”,一定让他说出是否爱她,他竟诚实地回答:“大概是不爱吧”。最后,他模模糊糊地杀了和自己毫无相干的人,对法庭的辩解漠然置之,却有兴趣断定自己律师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最后他用他平静的力量再次震撼我们:“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那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莫尔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从他对周围人们信奉的价值观念的疏离、轻蔑与无视,从他对本能、即刻的肉体满足的强烈要求来看,他近乎一个白痴。然而若真以为他是个白痴或蛮荒的原始人,那么也只是从莫尔索周围的人们和社会的角度去评价他,是站在局内向外张望,迷茫的清醒。现代主义文学塑造了许多个经典的奇人、怪人、多余人、畸零人的形象。纵观现代主义文学的旷野,徘徊在真与假、生与死之间的都是令我们凄然、愤然、愕然的“非人”。而莫尔索不是他们之间的一员,并且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原人”,或者是“纯人”。他是一个有着正常的理智的清醒的人,是站在非理性背面的荒诞的人,他是超脱于现实社会价值观念和习俗行为模式、有着清醒洞察力的局外人。他是个明白人,他用自己的遭遇诠释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最后拒绝对上帝的皈依更标志着一种纯粹人性的觉醒。他认识到了“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真实”。莫尔索固执而不妥协;追求真实地生活,虽死不悔。《局外人》中的律师、检察官和陪审团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莫尔索没有否认自己犯罪。惩罚的结果也相当失败,因为在惩罚之中,莫尔索依然没有感到一点悔恨。他虽然对回忆产生激情,对生有留恋,但没有找到构成生命本质目的的激情,也没找到生的理由。
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近乎可笑的说法隐藏着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任何违反社会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这个社会需要和他一致的人,尽管社会本身构成的目的之一是维护人的尊严和个性。任何背弃或反抗它的人,都会被检查官要走脑袋,莫尔索就是这样被社会抛弃,被罚出局。
正是由于发现了“荒诞”,莫尔索的消极、冷漠、无所谓而又执着于生命瞬间片段的人生顿时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小说因而具有一种局外的哲学。当加缪指明,“荒诞的人”就是“那个不否认永恒、但也不为永恒做任何事的人”时,我们不难想到那个人就是莫尔索。“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荒诞的人”就是“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为“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这就是加缪为我们还原生活原本的真实吧。他让我们变得更有勇气,更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