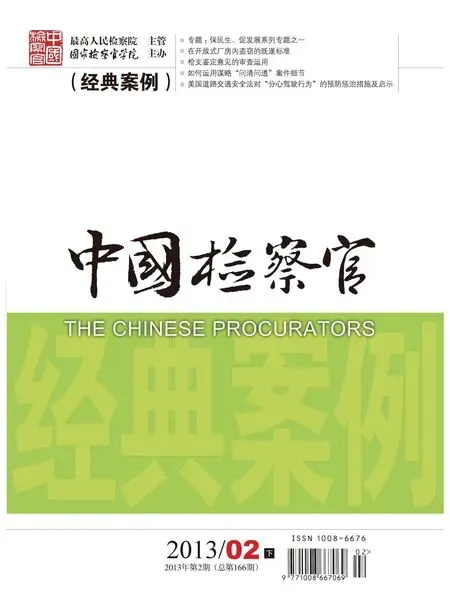误把枪支当做玩具枪销售的行为如何定性
文◎周 宇 王宏平
[案情]2012年7月的一天,李某在廊坊一集贸市场以120元的价格从一卖玩具的老头手中购进一箱玩具,回家后发现箱子里两支玩具枪。李某在大兴区某镇集贸市场摆摊时将两支玩具枪放在摊位上准备出售,标价为每支160元。两支枪状物的外观均为黑色塑料质地,长约50厘米,以弹簧为动力,打塑料子弹。2012年7月15日19时许,李某在该集贸市场销售玩具时,民警发现其准备销售的两支枪状物可能是仿真枪,并将李某抓获。经鉴定涉案两支枪状物均为枪支。
本案争议焦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客观上李某买卖的枪状物经过鉴定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枪支。李某非法买卖枪支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严惩,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现无证据证明李某主观上具有非法买卖刑法意义上枪支的故意,且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对李某判处刑罚也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的精神。
[速解]本文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首先,现无证据证明李某主观上具有非法买卖刑法意义上枪支的故意,认定李某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李某的两支枪状物是从农贸市场购进,在农贸市场摆在摊位上和其他的玩具一起出售,价格为160元。通常的非法买卖枪支案件中,一把枪要卖几千元,并且是通过高度隐蔽的方式进行交易。从李某的职业、购进和销售枪状物的场合、设定的价格、枪的外观等方面来看,李某一直认为其销售的两支枪状物就是玩具枪,其根本没有认识到其销售的“玩具枪”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李某在主观上没有买卖刑法意义上枪支的故意,李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
其次,如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对李某判处刑罚也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的精神,不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200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同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对执行上述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对于行为人因生产、生活需要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法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发布上述通知的背景是,实践中有些案件,行为人非法制造、买卖的枪支、爆炸物均是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是由于《解释》规定的涉枪、涉爆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比较严格,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较重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些人主观方面并无实施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故意,如果不讲政策,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甚至判处重刑,社会效果显然不好。从严格执法的角度考虑,任何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都应当被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但是绝不能不加区别,于是发布了上述通知。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处理涉枪、涉爆申诉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对于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涉枪、涉爆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诉,经审查认为生效判决不符合2001年9月的通知精神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并依照该通知的精神予以改判。200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解释》进行了修正,增加了一条,基本内容是因正常生产、生活需要,以及因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非法买卖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可见,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刑法打击面过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对于涉枪、涉爆的行为不能不加区别,搞一刀切。只不过对《解释》的修改仅涉及了爆炸物。本案中关于枪支的问题和上述有关爆炸物的问题类似。犯罪嫌疑人李某买卖玩具枪或者仿真枪的行为当然具有一定的潜在危险性,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对于销售仿真枪的可以进行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的行政拘留,这种行政处罚足以对李某这些小商贩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没有必要适用刑法对其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