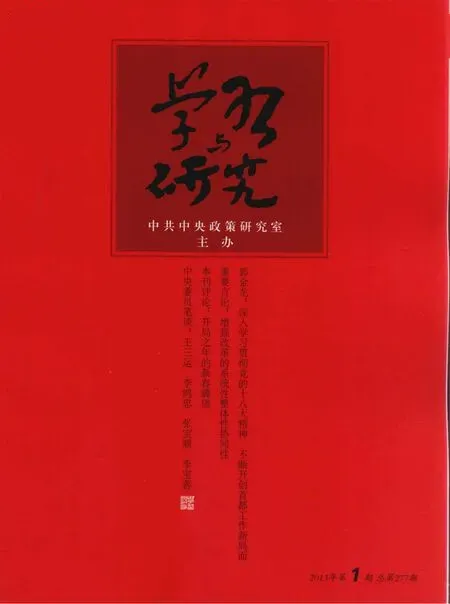公私之辨:看王阳明对佛教的批判逻辑及深度
吕 昂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自佛教于汉时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壮大后,儒家对其的抨击就一直没有停止。抨击的对象也渐渐由用至体,由体及用,无一不包。佛教上有迎合士大夫完整周密的理论体系,下有迎合普通民众的种种教义与传说,而且不断吸收儒道两家植根于中华文化中的影响因素加以融合,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不足为奇。至禅宗,三教合一已在其前诸多佛教宗派中国化的基础上第一次完整构建,而儒者也佛老并称,视之为大敌。韩愈《进学解》中言“觝排异端,攘斥佛老”[1]p37。但在排斥的过程中,儒者也吸收了佛教中的大量资源,对儒家义理进行重新阐释,并由此产生了第二次以儒家为主体的三教合一,即传承数百年的宋明道学。也正因此,道学常被人解读为“阳儒阴释”,“暗袭佛老”。道学中的心学一脉,更是被视作套上儒家外衣的禅宗。陆九渊在世时,便已“天下皆说先生是禅学”[2]p425。集心学大成的王阳明也被称作“阳明禅”。
禅宗对心学有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当代很多学者进一步指出,不能简单的将阳明心学与禅学等同起来,并提出了二者之间的一些区别。但当言及王阳明对佛教的批判,往往将其解读为阳明子不了解佛教或了解的不够全面。“然阳明之批评禅学,正如明儒之批评阳明,皆不免门户之见。”[3]p80然而王阳明出入佛老近三十年,而且在心学理论建构中能熟练运用禅宗思想,因此在作出判断前,有必要将王阳明对佛教的批判逻辑做一番梳理。
一
王阳明在批判佛教的同时,也丝毫不掩饰其对佛教某种程度上的赞许。他对王嘉秀“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的看法表示赞同,更是不止一次的声称佛老与儒学的区别只有“毫厘”:
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4]p36
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4]p98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4]p257
“毫厘”往往是王阳明论述佛儒之异的起点,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辨析。
首先,“毫厘”的字面意义是什么?张元冲在请教王阳明时说:“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4]p1179王阳明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再观王阳明著述中对“毫厘”一词的使用,大部分后面缀有“千里”,“毫厘千里之谬”,“其始也毫厘,其末也千里”,“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可见王阳明所指佛儒区别的“毫厘”不仅仅是微小差别的字义,还包含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意义。
其次,“毫厘”所指的准确含义是什么?王阳明在正德二年(1507)的诗作《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中规劝其宗伯乔白岩弃道入儒,“问我长生诀,惑也吾谁欺!”[4]p680鉴于宋明道学家对佛老的看法往往没有明显区分,王阳明在诗作其二中对“毫厘”已有了明确的解释:“毫厘何所辩?惟在公与私。”[4]p680
再次,王阳明指的是儒佛学说的哪一部分相差“毫厘”?其一,按前引张元冲义,是性命之学相差“毫厘”。其二,当有人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4]p98王阳明回答说:“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4]p98按此义,是存天理,循天理之心相差“毫厘”。其三,按前引“皆求尽其心也”义,是尽心相差“毫厘”。其四,王阳明在给王纯甫的信中说:“学以明善诚身,只兀兀守此昏昧杂扰之心,却是坐禅入定,非所谓‘必有事焉’者矣。圣门宁有是哉?但其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实地用功,则亦未易辩别。”[4]p157王阳明在此引用孟子对浩然之气的解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把“必有事焉“解释为“有所事也,如‘有事于颛臾’之‘有事’。”[5]p285王阳明显然不会同意这种“心外之事”的理解。他说:“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4]83按此义,是致良知的修行方法与坐禅入定相差“毫厘”。四处合观之,再看王阳明“心即性,性即理”,“良知者,心之本体”之论,可见相差“毫厘”的部分是本体,或更准确的说,是围绕着本体的一系列发用。若以阳明四句教为喻,即“有善有恶意之动”相差“毫厘”。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相差“毫厘”是指关于本体良知,形而上方面的公私义利之别,但这里的小小不同最终造成了儒佛之间的巨大差异。此处的“自私”,并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贪私”;此处的“自利”,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功利”。王阳明对此区别的非常清晰,他批判当世的学者说:
博文而非约之以礼,则其文为虚文,而后世功利辞章之学矣;约礼而非博学于文,则其礼为虚礼,而佛、老空寂之学矣。[4]p267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4]p56
很明显王阳明认为佛家的“私”、“利”是不同于普通的功利,甚至是可以以之批判普通功利的。王阳明在论述中,主要从两方面指出和批判佛家的“私”。
首先,从现实的角度讲,人人皆有父母。佛家的“私”是“外人伦”,这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佛、老之空虚,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遗也。”[4]245以这样的逻辑,王阳明成功的劝说了一位僧人还俗:
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4]1226
“爱亲”是孟子对“良知良能”的解释,以“良知”为学说核心的王阳明对此理解自然是非常深刻的。虽然没有详细记载是如何“谕之”的,但可以想象这番话的巨大说服力,因为王阳明早年静坐入定时是经过同样的心理斗争的:
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4]p1226
从儒家伦理观的角度,从人人难以割舍的亲情开始阐述的“外人伦”确实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但从义理与逻辑上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反驳。学佛并不一定要出家,“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6]p182,即便出家,也有“一子出家,七祖升天”的逻辑可以在世俗伦理上自圆其说。鉴于此,王阳明又从更深刻的角度指出佛家的“私”是“私心”:
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以为异也。[4]p257
佛家的分割内外陷入“自私自利”,起于“自私自利”又未免于“内外之分”。哪一种是王阳明想表达的含义?两种应该都有。从儒家世界观的角度,“无内外”的前提是外界实有,外在世界与我心的统一必然基于二者的平等地位和兼顾的手段。这样看来,认为“四大皆空”而“心生万法”的佛家否定了世界的实有性,在儒家看来自然是分割了内外,“尽绝事物”,只务养心也就是自私自利的。儒家本位的世界观与佛教相比,也许更易被人接受。但以之从义理上批判佛家的话,只能陷入各说各话的局面。王阳明想要超越佛家,只能从其研究最深入的本体论入手,因此王阳明强调“内外之分”前有起于“自私自利”的“私心”。所谓“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内外之分”前指向的自然是纯粹的本体。不妨再看一处例证: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4]p67
王阳明禅学造诣于此论述中一览无遗,甚至可以看做对禅宗的“无念法门”的完整诠释。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指出佛家是“自私自利之心”,但否定佛氏之学是“如此将迎意必”,而文中又将“自私自利,将迎意必”连用两次。基于此,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将迎意必”由“自私自利”导出,而“自私自利”不一定会达到“将迎意必”的地步。何谓“将迎意必”?《庄子·应帝王》言:“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而不伤。”《论语·子罕》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王阳明自己则解释说:“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4]p110可见不“将迎意必”也就是不刻意,无私念,顺从本然的,在王阳明的认知中佛家正是如此的。连私念都不包含的“自私自利”指向的显然只有本体层面。
二
“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以心本体论来概括阳明心学与佛学,两者应该都不会反对。王阳明对于佛家的本体,也是在溢美之外方有微词的。王阳明对佛家本体的批判,可以说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4]p106
这里王阳明对本体的认知非常准确,对佛道二家的批驳也正中要害。本体是形而上的,第一义不可说的,因此佛道二家说到本体“虚”“无”的极点之后圣人也不能做什么增添改动了。但说了“养生”,“出离生死苦海”——“加却这些子意思”就是对本体的认知有所障碍了。而这便是最高层次上佛家的“私心”,即便无关利益,无关心物,无关私念。“说似一物即不中”,无论作为传播的手段还是其他,只要涉及了形而下,对形而上而言便是“私”。以形上层面的“私”为基础,王阳明成功的把所批判的佛家之私统一起来: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4]p26
“未当理便是私心”,不合本体就可以称之为“私”。“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实有私心。不染着世间一切情欲之私本身就有将迎意必的趋势,并非佛法根本义。“外弃人伦”非但不当本体之“理”,甚至不当伦理。而这些都是一统事,王阳明语境中具有多层次含义的“私”就可以概括他对佛家的一切批判了。
关于“私”的批判虽然直接指向了佛家的根本,但这样的批判无疑是一把双刃剑。王阳明在质问佛教的同时也要回答同样的问题,他必须解释如果佛道都是“加却意思”,那么儒家的纲常伦理,教化治国难道不是加却了更多意思吗?而且既然本体是形而上的存在,那么在形而下的语境中或是工夫中怎么可能避免“加却意思”呢?对此,王阳明解释说:
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4]p106
首先,作为本体的良知是一体的。陈来先生曾指出,心性本体的虚无性与存在本体的实有性是王阳明哲学中一直存在的矛盾,而王阳明的处理方式是“以有为体,以无为用”[7]p228。这样的分析固然精妙非常,为我们理解王阳明的理论提供了很大帮助,但王阳明自己却一直在强调本体的不二。“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圣人无二教,而学者无二学。”[4]p266在《大学问》中更是将《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都指向“一体之本然”。无论是心性本体,存在本体,或为理解而概括出的其他本体在王阳明的理论和境界中是合一的。
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智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曰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可岂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蓍固是《易》,龟亦是《易》。[4]p18
“弊病”是见得偏,而“偏”的本身不是弊病,是道的一部分,就如同蓍占和龟占都是《易》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依然强调本体的虚无性,说纲常伦理是加却意思,那么修行,出家,都是加却意思。与形而上对比而言,形而下之间不存在比较。如果承认本体的一体性,那纲常伦理都在本体之中,不包含纲常伦理就是见得偏了。所以: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4]p1179
一以贯之,兼容并蓄方是圣人之道。事实上不仅是本体,知行合一,本体工夫合一,没有任何事物是不包含在其合一之中的。无论将王阳明的理论怎样分解,不能忽视其本质上的一体性,而所做的分析只是角度的不同。这样包含一切而非派生一切的一体之本体自然就是我,也是天,所以能够包容一切所以没有任何障碍。
其次,作为本体的良知是现实的,或者说是自然的。这样的现实性是在一体性的基础上展开的。但在表达上难以绕过本体和现实相对的层面:是先天的工夫、本体,而我心也自然而然的加以应对:
先生尝言:“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请问。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4]p99
不执著于相的本身也是相的一种,也不能加以执著,而这样的不执著又成了一种相……如此推演下去,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不如一开始就不去考虑不执著,这才是真正的不执著。现实在这一层面上就是本体,这样的现实当然不会成为障碍。
三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4]p124
王汝中解释说在逻辑上,必须设立我心实有之本体,心念一至,即为实有,心念不至,即为幻象。学者之工夫便是扩充我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在现实的用功之中,没有意识到而自然的,方为实有,“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而要靠意识到才能去做的,即为幻象,不是本体了。所以本体是先天的,“斯人千古不磨心”。王阳明同意王汝中的见解,但他自己却并没有进行这样的拆分,因为正确的分析也很容易陷入“支离”的状况。在王阳明看来,想达成本体一定需要工夫,只有能达成本体的才能叫做工夫,本体工夫是合一的。先天的本体也就意味着先天的工夫。之所以纲常伦理不是加却意思,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如此,世间本来就如此,几千年本来就如此。它依托于个人的情感自然而然的存在,便
对于当世儒学而言,阳明心学作为繁琐支离,记诵词章,功利训诂的反动出现,而成熟的佛学尤其是禅宗毫无疑问是极好的思想资源。事实上,王阳明对佛教的批判并没有超出佛教自我批判的范围,他的批判一部分可以看作禅宗对佛教其他宗派的批判,另一部分也不背离佛家核心理论,可以看作佛教进一步合理世俗化,政治化的先导。在阳明心学的建构过程中,王阳明一方面要排佛,一方面要面对心学近于禅学的指责,王阳明辩解说:“今之为心性之学者,而果外人伦,遗事物,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而可谓之禅乎哉!”[4]p257而对于禅宗而言,我心即佛,佛法在世间,又何必以人伦事物为外呢。从这个角度讲,王阳明岂不是更纯粹的禅者?但这并不是质疑王阳明的儒家自我认知,禅宗作为三教合一的产物,也包含着大量的儒学成分。
王阳明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实践者,他在出入佛老三十年后最终选择了儒家来实现自我的完满,也真正成为了儒家圣人之一。在分析王阳明对佛教的批判深度时,不能以牺牲儒家的神圣性为代价。对佛家多层次的吸收和借鉴是阳明心学的重要特征。王阳明的排佛理论依托于他对佛教的正确理解,是深刻的,即便攻击上并不充分,但在防守上是无懈可击的。在《谏迎佛疏》中,他从寿命,教化方式,神通几方面将释迦牟尼与尧舜对比,但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在证明儒家拥有同样的功能。正如佛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增强自身的社会功能,王阳明所为儒家指出的方向,就是在以佛家本体思维充实儒家心性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终极追求,完善自身的宗教功能。王阳明的理论逻辑是,儒家已经拥有了佛教所有的功能,而儒家的功能佛教不能代替。后一点虽然不能这样断定,但即便如此,王阳明也可以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没有必要在儒家占据统治地位,作为主要思想传统的中国选择佛家。同样,既然“有”和“无”都可以解释世界,那么也未必要通过缘起而导出虚妄空寂,通过消解方式而达成的本体和通过流转方式而达成的本体的指向并无差异。正因如此,很多高僧对王阳明不乏赞美,因为剔除不应执着的三教本位而言,其言不违佛法,他对佛教是有所贡献的。
[1]徐发前撰.韩愈文集探元决异.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2]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
[3]陈荣捷著.王阳明与禅.台湾学生书局,1984.
[4](明)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
[5](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
[6]陈秋平,尚荣译注.金刚经心经坛经.北京市:中华书局,2007.
[7]陈来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