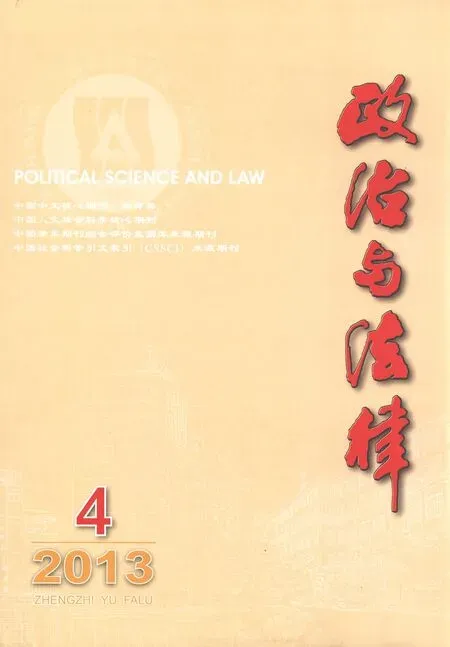论维多利亚宗教法律思想*
于 浩 曾 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重庆401120)
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 1480年-1546年)为西班牙神学家、多明我会修士、萨拉曼卡学派的创始人,是十六世纪天主教欧洲极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他的著述涵盖诸多领域,而对公民权利和王权的本质、教会权力以及欧洲侵略扩张的正当性等问题的论证,使其获得崇高的学术声誉。维多利亚是第一个提出人民权利(ius gentium)的人,因此成为奠定现代人权概念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将社会的合法主权理论进一步扩展至国际层次,并进一步认为这一层次的统治者也必须尊重并对全体成员负起责任。世界的公共利益在这一层次上要优于每个国家单独的利益。他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用武力来正当化,而是必须以正义和法律作为依据。维多利亚也藉此提出了国际法的概念。维多利亚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萨拉曼卡大学任教,教授神学和法学,其后萨拉曼卡学派的重要人物索托(Domingo de Soto)、莫里纳(Luis de Mol ina)、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皆受其影响甚巨。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维多利亚的译介及研究较为不足,仅两部译著即努斯鲍姆的《简明国际法史》和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第五卷)》对维氏的思想有所涉及,而维多利亚本人的著作更无一本被翻译出版。近年来国际上对于维多利亚的文本研究多从国际法的角度切入,而维氏作为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在神学方面的造诣同样精深。故笔者将维氏的宗教思想与法律思想相结合,将“教权超然”与“政权既在”这一组概念作为维多利亚宗教法律思想的中心论点,借助《维多利亚政治著作选》,重释中世纪末欧洲基督世界教权与政权的争纷和妥协,希望能在梳理维多利亚宗教法律思想的同时推动国内学界对维多利亚的研究。
一、教会的起源和内涵
公元四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藉此基督教在罗马获得了合法地位,并迅速发展成为罗马国教。同时,教会作为帝国的统治工具也由此滥觞。在传统基督教观念之上,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由“上帝之选民”组成。从这一观念出发,教会成为了一种神圣化的由上帝意志支配的超越世俗的共同体。而维多利亚进一步为教会赋予了抽象观念之上的意义。
考察源流,维多利亚指出,希腊文的“教会”(ekklesia)原初乃表群集之义,随之引申代指市民大会,进而琉善(Lucian)在其对话录(Dialogue of Mercury and Maia)中又使用了ekklesiazo一词作召集与会之义,随后又出现了ekklesiates,义为召集之人;及至罗马,即基督教出现之后,ekklesia的变体ecclesia才频繁地在基督作家的作品中出现。1接下来,维多利亚又依据奥古斯丁的说法辨析了希腊语中ekklesia与其近义词synagoga之间细微的差异,即后者尤指犹太人之间的群集,而前者的召集之中兼有呼唤之义而无人种之别,强调的是一种“声音”上的召唤。然而,毋论ekklesia抑或synagoga在基督教的经文(旧约、新约)中都几乎没有出现过,而出现得最多的词是以上两者的又一次进化——congregation,我们可以称其为圣会,这又朝纯基督语境上的教会(church)迈进了一步。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厘清维多利亚从词源上为教会的演进过程梳理出的逻辑脉络:从单纯的人的聚集到成规模的聚“会”,并在对象与方式上初步形成了特异性(ekklesia,声音上的呼唤;synagoga,犹太人的聚集);进而人之群集又被赋予了某种目的性,并且此种目的性逐渐成为所在群体的共同意志,因而聚会的本身亦变得神圣起来(congregation);最后,群体的目的性终被塑造成了信仰,群集者、与会者皆为有信之人,是时,教会(church)便告诞生了。
维多利亚之所以要从词源上对教会的诞生进行解读,是因为从词义的源流嬗变之上,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自雅典而耶路撒冷,ekklesia至church内在因素的增补与缺失,从而对教会这一抽象观念产生总体的把握。这里,维多利亚刻意突出了教会的抽象观念。强调教会并不单纯只是“人”的集合,更为重要的是,教会是“信”的集合。这里的“信”是一种超越社会政治与国家政治维度的抽象观念。2既然个体的“信”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超越了社会与国家的政治维度,那么“信”的集合又何如呢?维多利亚将教会(亦即“信”的集合)定义为“精神权力与实体权利之间的纽带”,3既不完全从属于精神,又不彻底堕入到实体,这样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再者,倘若赋予“信”的集合(共同体)以实在意涵,从此岸跨至彼岸之后又从彼岸跨回此岸,那么“上帝之国”与“尘世之国”便将不再有云泥之别。而确认教会的抽象观念将问题引向了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
其一,基督教会是世上存有的唯一的“信”的集合。维多利亚称其为“信”的共同体。也就是说,“认信基督”这一抽象行为本身是建立在对基督之外的“信”的否认的基础之上的,即否认多元宗教的正当性。
其二,有关异教徒的准则,是建立在第一条的基础之上的。既然世上只有一个“信”的集合,即基督教会,那么也可以说,世上实际上也同样只有一种“信”,即“唯凭基督”。所有无此种“认信”行为之人抑或放弃“唯凭基督”论断之人皆可称其为异教徒。“若不听信他们,便告之教会;若是不听信教会,便视之为可鄙的异邦人和税吏。”(《马太福音》18:17,这里的“听”又对照了ekklesia意涵之中的“呼”,有了ekklesia的“呼”才会有“认信者”的“听”以及异教徒的“不听”)而早在公元五世纪,波西米亚人胡斯(John Hus)便归纳了异端的三种类型:买卖圣职(simony)、亵渎上帝(blasphemy)以及变节叛教(apostasy)。4就此,维多利亚提出了四点有关异教徒的准则:(1)教会可立法对“认信者”进行甄别,并对异教徒进行审判;(2)异教徒须服从教会之训诫;(3)浸洗乃是教会之圣礼,异教徒只有在适当时刻方可享受;(4)当牧师甚至教皇成为异教徒,在未革除教籍之前,仍视为教会成员。5
维多利亚提出异教徒准则的目的实际上是试图构建一种基督秩序观。维多利亚提出了两套等级秩序,一套是天上的秩序(宇宙秩序);一套是人间的秩序(尘世秩序)。维多利亚认为,上帝最初的设想是为尘世万物创造各自多元的价值,但最终万物的价值都趋向了同一,即尘世秩序服从宇宙秩序的安排。6此观点承袭了公元九世纪末大主教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提出的真实秩序,即教会(尘世秩序)反映了上帝心意中的秩序(宇宙秩序)。
二、教权超然及法的超越价值
(一)教权的确认
维多利亚对权力的领域重新做出了区分,即分为人世领域与超自然领域,二者各自独立,互不影响。其后萨拉曼卡学派学者大都延续了这一谱系。7由此,世俗统治者国王再无统治精神领域之权力,反之,作为耶稣基督身体的教会亦同样不能染指人世领域之权力。8然而作为精神与世俗双重载体的“人”,却在这一谱系之中产生了矛盾。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对米兰地区大主教的职权之争便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格里高利七世提出的立场是,既然皇帝需要教皇为其加冕,那么在基督世界之中,代表世俗权威的皇帝必须要服从代表超自然权威的教会,进而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而亨利四世则根据君权神授理论对教会做出回应,认为教皇此举是凌驾于上帝之上,违背了律法。众多学者将其解读为基督世界的最高权力之争,其实,这样的论断忽略了“人”的双重载体作用。“人”到底可以具有怎样的属性,这个问题才应该是论争的关键。如果说“人”通过恩赐而获得神性,而这样的神性又与其世俗的性质彼此独立,那么基督世界的最高权力便成了一种基于“人”之上的思辨事业。
对于“人”在权力谱系之中的作用,维多利亚认为,虽然上帝权威的传承与认知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自然的启示或是所谓的信仰之光(the light of faith),但也不可否认“人”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而此种传承与认知(追求的不仅是自然与政治上的目标,同样也有超自然的精神上的目标)需要一种引导的权力,进而形成一种基于共同体之上的权力,即教权,因而,教权虽然有一部分是归属于实体法,但大部分仍归属于神法。9
另外,维多利亚还认为教权的形成,最初便是一个“神形结合”的过程,不仅需要信仰上帝的灵魂与智慧,还需要信仰他外化的身体上的行动。这样的论断具有浓厚的男权意味。“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创世记》3:16)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此种原始的“管辖关系”,才产生了最初的尘世权力。因而维氏认为这样一种最初的“管辖关系”(尘世权力)是正义的(righteously)、无罪的(innocent),因而男权是可以被神圣化的,经过长期的衍化过程,最终形成超然神圣的教权。针对“神形结合”并基于男权而产生的教权,我们可以做出两个层面上的理路区分。
其一,教权的形成是有关善恶观的尘世“降落”。阿奎那认为“人”的内在具有一种辨善去恶的洞见,而这样的洞见是上帝所赋予的一种“理性启示”(rational apocalypse)。“人”只要遵照这样的启示,便是获得了一部分永恒法的指引,并完全符合自然法之原理,所思之念想,所行之诸事则必然会被认为是善的,即所谓的“善即存在”10。依据奥古斯丁的教导,存在的一切便是上帝,恶则是上帝的缺席,那么便可得出,上帝即是善,没有上帝即是恶的结论。最根本的善为永恒世界所有,我们在尘世所看到的善是由于其“降落”,而恶是永恒世界所不具有的,我们所看到的恶本身便是起源于人间世界,是故,只有善的“降落”却不曾有恶的“上升”。11从永恒世界到人间世界,便是善的“降落”过程,其“降落”在尘世的表现分为四个方面:(1)自我保存之本能;(2)爱慕异性,生育儿女之倾向;(3)求真祛魅之热望;(4)形成自然共同体之需求。正是由于善在尘世的“降落”,教权才有了存在的正当性。首先,教权可以通过从上帝之处获取的理性来引导世人避免尘世中某些情况下由于上帝的缺席所带来的恶;其次,教权可为人类繁衍居宁传递福音带来便利;再次,教权可为认信基督确立一个“一”的标准;最后,教会作为认信基督者的共同体,进一步对教权的超然性进行了确认。
其二,教权的演进导致了教会中的世界主义。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地中海沿岸各国所独有的民族神迅速地消亡了,最初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成为了世界的神,教会的权柄也由此伸向世界各地。“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你们从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以弗所书》2:13-17)“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6-28)在这一层面上,教权成为了推进福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力量,而上帝又应然地成为了其唯一的主权者。这一观点又从另一个理路上对教权的超然性进行了确认。
(二)维多利亚对法律的划分
维氏对法律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参照了阿奎那的法律四分论,即将法律划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四种类型。他将法律直接分为两个层面:神圣的与人世的,而前者又分为自然的和实在的两类。维多利亚认为,所有的神圣法在上帝之处是永恒的,然而却并非在人世永恒,自然法则是起源于永恒法之中的,当神圣之法不存在,人类也可以通过自然法得救,并且神圣之法对于幼儿的重要性要更甚于成人,因为“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1:5)
有关法律本质的问题,阿奎那认为法律是一种理性的功能,属于我们的自然理性。而lex(法)是从l igare(约制)起源的。法只能存在于观念或是智识之中。维多利亚就此问题参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首先维氏分析了里米尼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Rimini)的论点。格列高利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著述(《反福斯图斯的摩尼教》Contra Faustum Manichaeum):“永恒法是一种理性,抑或上帝的意志。”因而,法律属于意志的范畴,或至少是上帝的理性与意志。作为十四世纪奥古斯丁主义的代表学者,格列高利自然旗帜鲜明地反对将信(faith)与理性(reason)混为一谈,同时也极力强调了人理性的局限性;而维氏引述的另一种观点来自伦巴德(Peter Lombard)所著的《第一语录》(SentencesⅠ),其中,伦巴德详细区分了两种神圣的意志:一种是上帝的真实偏好与内在意愿(uoluntas beneplaciti);另一种是第一种意志的外在表现(uoluntas signi),即所谓的“上帝之怒”,从这样一个维度来看,法便仅仅只是意志的外在表现而不能称其为内在的意志。维多利亚则更倾向于后者,维氏以为,意志并不能藉自然法而施行,而自然法并不是一种意志而是一种理性和启示:“耶和华啊,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诗篇》4:6)“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21)是故,维多利亚得出结论:建议只能和理性产生关系而与意志无关,若想要称为意志(法律行为),则必须要通过立法,并且只要是合乎法律的,则必然合乎理性,倘若不合乎法律,便必然不合乎理性。
对于法律的颁布,维多利亚专门对其进行了探讨。首先,维氏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立法权。这一论点是基于阿奎那的共同体理论,以并非所有人都热心于共同体事务为假设基础。阿奎那将共同体分为了两类,一类是非完整的共同体,另一类是完整的共同体。12在这一体系之下,前者是不具有立法权的,因为一个非完整的共同体的自行立法所指向的只能是私益,这便与阿奎那的法律“第一原则”,即立法指向共同的善好(善即当行)相违背。在立法层面上,维多利亚则进一步区分了誓言与法,其殊异在于前者不具有强制性而后者具备。譬如在圣徒日所进行的斋戒行为,维氏便认为是一种誓言而非法律,因为对于个体而言,斋戒仅仅属于“律己”之范畴而不可“由此及彼”地自我演绎。
在维多利亚看来,一些基于自然法的精神之力是源于人类神圣的本能或行为。这同样也是教会超然权力之基础,作为“信”的抽象集合,惟有人拥有了某些神圣的本能即自然法上的理性,教权的超然性才可以在个体之上得到映射。然而归根结底,世上一切精神之力皆来源于上帝,“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18)随后上帝又再将一部分权柄交与教会。不论是引导之权力,“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希伯来书》13:17)还是赦免之权力,“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马可福音》2:10)维氏认为“精神之力”13较之世俗权力更为完美与卓越,并且“精神之力”与世俗权力之间存在一种佑(bless)与被佑(blessed)的关系,是故“精神之力”位于世俗权力之上。对此维多利亚用了这样一句话作结:“如若我们不想永远陷入谬误险恶的怪圈,便必须要正视那超然的真实存在。”14顺理成章,教会亦便拥有了立法权和司法权,主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区的法官。
在立法问题上,维氏沿袭了阿奎那提出的“第一原则”,认为立法须指向共同的善,却质疑人法是否能将人引向既定的善。就此,维氏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立法三原则:其一,世俗立法者(国王)之追求乃是“自然之善”,即共同体之善,精神立法者(上帝—教会)则追求“道德之善”;其二,教会之立法权独立不受尘世权力影响,其神圣性亦不由尘世权力确认,就如同国王不可为教会立法一样;其三,世俗立法者之目的乃是区分“循法”与“悖法”,精神立法者则是主要按照“善”与“恶”来进行划分。
三、政权既在:宗教外衣之下的万国法
(一)万民法浪潮
维多利亚早年思想受人文主义、唯名主义和托马斯主义三大流派影响最深。15然而随后维氏发现,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世纪后(特别是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后)基督世界解体为多个教会和民族君主国所面临的困境。“帝国和教皇的代表性自然近乎消失,但西方人仍然被体验为一个精神和文明的统一体(unit)。如果该秩序的各种制度已经丧失了它们的代表价值,灾难将会刺激人们去寻求新的制度,而通过这些制度,实际延续下来的文明的实质(civi l izational substance)就能够获得更为充分的表达。如果我们提早使用后来的术语的话,帝国基督教时代之后就是国际主义和国际组织时代”。16是进一步践行宗教改革还是面临民族战争之虞?维多利亚是那个时代立于风口浪尖的人物。
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留意这样一个论断,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浪潮之中,随着板结的基督世界共同体的瓦解,欧洲各国的民族问题第一次变成了所谓的国际问题。维多利亚在基于国际主义的语境之下提出了一个新型的概念:“一个高于单一共同体的一个超越共同体”。17此概念打破了古代与中世纪基督世界世俗国家的封闭观念,解决在这个“超越共同体”之下的普通单一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所依靠的将不再是十字军的坚甲利刃,而是一种国际政治模式之内的法律技术。既然基督教世界的外延已经无法覆盖整个世界,并且随着美洲新大陆以及东印度的殖民,一种新的“万民法”之概念应运而生。对于这一新的“万民法”,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是一种独立政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万民”在此种意涵之下便衍生为了“万国”,因而此种新型的法律概念并不是一种“人际间”的规则,而毋宁是一种“民族政体间”的准则。根据前文论及的维多利亚所建构之权力谱系,对于教会的“圣灵权威”与国王的“世俗权威”已有了确然的界分,换句话说,只要某种基于国际主义的政治体之间的世俗行为的发起者(行动者)是教会,那么此种行为便是违悖法律的;如果此种行为的发起者(行动者)是世俗统治者(国王),而教会之所为仅仅是履行授权之职,那么此种行为便是合法的。
有关基督教民族与非基督教民族之间所产生关系之合法性,维多利亚总结了三项基本原则:其一,一方进行相关的任何行为都需要一个合理的协商程序,并且毋论其是否合乎法律,此种行为首先要确定是符合良知的;其二,如若协商之结果显示此行为不合乎法律,那么此结果必须得到尊重,并且法律将不保护藐视此协商结果之人,即使先前之行为事实上是合乎法律的;其三,一旦接受了协商之结果,认定相关行为合乎法律,那么即使事实上此行为不合乎法律,也必须保障其法律之内的权利。
随着西欧各国对美洲扩张步伐的加快,维多利亚所提出的民族政体之间的法律原则愈加显现出其重要的时代特征。不论是手握上帝权柄的教会,还是掌控世俗权力的国君,都亟待一种基于统治权威且复作用于民族政体之间的法律技术来消弭基督世界与非基督世界之间的精神裂缝。可以说,“随着中世纪英雄主义和圣徒精神道德的崩溃,理性道德不光彩的一面出现了,因为缺乏强烈的精神,维多利亚不能以蔑视或听之任之的态度来接受存在的不合理性……因此,维多利亚成为双重意义上的背叛者:当拒绝承认战争是万物之父时,他背叛了自然;当扭曲的理性为胜利者做正当性论证时,他背叛了精神”。18是故,维多利亚只有通过一种民族政体之间法律技术的影响来对这个他已然“双重背叛”了的时代进行总体的把握。美国法学家斯柯特(James Brown Scott)在论及维多利亚所处时代境况时有言:“帝国之日已然升起,其夕照为途经新世界之唯一光亮。然而,自某一处观,旧世界虽与之并立,却鲜有观照,仅当忽略罗马法之精神时,旧世界方可重现。众谓之为十五、六世纪之法律复兴,其本质在于根源与功用,而非数个世纪之后骤然的法律复归之热望。”19
(二)新世界:战争法与基督信仰
从十六世纪开始,对于基督教世界裂解为若干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性研究已经开始系统化,与维多利亚同时代的几乎每位学者都在撰写基于民族主权国家冲突背景之下的题为《论法律、权利与正义》(De legibus and De iure iustitia)的著作。维多利亚称其所在的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现代历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并且此事件将毋庸置疑地成为“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分水岭”。20随着天主教会在西欧主要国家的日渐式微,西班牙接过了保持经院哲学传统连续性的重任,既然传统的基督世界大厦已轰然倒塌,那么以维多利亚为首的萨拉曼卡学派就只能在此大厦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政体之间的统一秩序,即超越个体的“共同体之共同体”。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对传统基督世界封闭的国家概念的反向发展,从一种“人类身体之共同体”发展为一种“人类理性之共同体”。
而用自然法代替神法处置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则是维氏赋予那个时代国际法体系的最为显著的特征。21调整此类关系的主体并非代行上帝权柄的教会而是世俗的统治者国王。维氏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推导出遵循自然法的功效便是防止人(基督民族、非基督民族)由于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而趋于分崩离析。我们并且可以将维多利亚的国际法体系理解为万民法的自然法化,自世俗社会的开端,这样的自然法系统便开始影响到了人间的正义问题。此处,自然法对于世俗政权的影响展开为两个方面。
对于西班牙帝国来说,维多利亚的普遍性共同体框架仅仅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伪装,一种来源于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的自然法所构筑的一种交互体系。其实质是在民族政权间的经济、贸易、人际冲突等事由上获得自然法授予之权利。
对于印第安人(野蛮人)来说,他们有同等地参与到此普遍性共同体框架之内的权利,维多利亚主要阐述了二者间平等的贸易权,如印第安人有用当地充裕的黄金白银来向西班牙人换取当地或缺的陶瓷器具之权利,并且具有自行评估交易价值之权利。在维多利亚所建构的体系中,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在贸易层面上具有同等的福利与权利。
显而易见,维氏建构的以上普遍模式仅仅是针对政治体之间温和的冲突形式,当西方政治文明与非西方政治文明最为基本的冲突根源即基督教社会与非基督教社会彼此间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之时,一种极端的冲突解决方式即战争便凸显出来。关于战争,特别是基督政治体与非基督政治体之间的战争,维多利亚首先提出了四个原则性问题:(1)到底基督教政治体可否发动战争?(2)发动战争需要凭藉何种权力?(3)何为应然之正义战争?(4)在与地方进行正义战争之过程中可采用何种措施?22
针对第一个问题,基督教政体可否发动战争,一方面,依据《圣经》的指引:“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12:19)“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9)“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同时,路德也认为:“当魔鬼发觉它不能通过强力来战胜某些人的时候,它会尝试着从长远的角度来战胜人……为了抵挡魔鬼不断的攻击,我们必须忍耐,要耐心地等到魔鬼厌倦了它的把戏的那一天。”23
而维氏则从八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反证。其一,他援引了奥古斯丁的说法“善待于人,知足常乐”,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战争,我们应遵循此指引。其二,借用阿奎那的观点,基督徒有合法权利拔出利剑,与恶人和损害秩序之人作战。其三,认为战争是符合自然法原则的:“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被虏去,就率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至大马士革左边的何把,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创世记》14:14-16)。其四,维多利亚指出战争之目的不仅仅是保障财产的安全,同时也是对重大错误的一种惩罚与报复措施。其五,维氏提出发动战争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基于对敌人所造成的损害的惩罚与报复,也只有此种“惩罚”的存在,才可避免敌人卷土重来,造成第二次侵害。其六,战争的目的必须是维护共同体的安定与和平。其七,倘若罪孽得不到救赎,且影响到了共同的善好(纵然不可能全世界都获得善好),那么发动战争便是正当的。其八,对于神圣善意的教民来说,发动正当的战争不仅是为了保护其人身与财产之安全,同时也是在进行一场道德的捍卫战。24
针对第二个问题,发动战争需要凭藉何种权力,维多利亚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证:其一,根据《法律汇编》(Digest)之中“强力须由强力约制”的原则,任何人,即使是个体公民皆可发动自卫战争,并且自卫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保障其人身安全,同时亦保障其财产安全;其二,任何共同体皆有权力宣布及发动战争;25其三,依据奥古斯丁著作《反福斯图斯的摩尼教》(Cont ra Faustum Manichaeum)中有关发动战争权柄之归属问题的论断,国王乃是共同体所选出的代表,故被授权代表共同体发动战争。26
针对第三个问题,正义战争的原因与起源,维多利亚首先进行了一个假定:在一场战争之中,总有一方是正义的,同时另一方一定是非正义的。事实上维氏有关正义战争的论断都是建立在这一逻辑假设的基础之上。对此,维氏专门列出了不属于正义战争起源之原因或条件,即不同的宗教信仰、帝国扩张、个人荣誉与国王之好恶不可成为正义战争起源之原因,正义战争起源必须在侵害发生之时,并非所有的侵害都可作为正义战争起源之原因。
针对第四个问题,对于在正义战争之中所采取的措施,维氏提出了五点:其一,在正义战争之中,个体可以为共同体的利益做出任何举措;其二,在正义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可以合法地改造失败的一方,并且重构其价值体系;其三,在正义战争结束之后,胜利的一方可以合法地掠夺失败的一方的财产以弥补其“非正义”所造成的损失;其四,在正义战争中,国王可以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其五,即使在正义战争结束之后,两国回到和平状态,损害的权利得到修复,被强夺的财产物归原主,战胜方仍可合法地对非正义方所造成的损害进行报复。
通过解答以上四个原则性问题,维多利亚最终为自己的战争法体系找到三剂良药。首先,既然国王已获发起战争之权柄,那么他在获得发起战争的权柄之时亦获得了避免战争之天职。“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12:18)国王在其国家无可避免地卷入战争之时也要尽量保证减少战争所带来的死亡。其次,一旦发起正义战争,国王需要保证其所发动战争之最终结果是指向和平而非毁灭,旨在伸张正义而非践行杀戮。27最后,战争的胜利者必须保持基督徒的节制与谦逊,其身份也由“诉讼方”演变为“法官”来对战争进行审判,补偿受损的一方,同时也让施虐方(有罪的共同体)不至于应惩罚而毁灭。
而格劳秀斯对这三剂良药具有清醒认识,他在《战争与和平法》序言中写道:“在整个基督世界中我看到的是泛滥的制造战争的许可证,即使是野蛮民族,这样的行为都应该是令人羞耻的;我同样看到世上的人们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无理由亦可拿起武器,发动战争,此时,神法抑或人法都被弃之如敝履,恰如一纸敕令可以让一个疯狂的人行无法无天之恶事。”28格劳秀斯作为维多利亚思想深远的“继受者”,也同样敏锐地洞察到了战争法体系与教权、政权之间的冲突。
针对第一剂良药,关于国王在操持战争权柄的同时承担避免战争之天职,格劳秀斯在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三十年战争之后认识到不可能存在或是创设一种道德力量来禁止国家战争,而只能通过一种国家体系之内的行为/关系准则来限制战争的破坏性。而这样的行为准则同样是基于中世纪以来便根植于欧洲大陆基督世界的道德要求和法律规范,作为战争的发起者,国王不能超越这一规范;作为战争的终结者,国王同样需要在这一规范之内。在这里,格劳秀斯首先就否认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如果说战争是作为一国行使主权的一种形式,那么这样的权力是在国王手里而非民众手里;其次,国王又不能脱离基督世界所形成的习惯和规范来单独行使这样的权力。
针对第二剂良药,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生活的必须”和“好生活”这两重社会目的。格劳秀斯所要带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维多利亚所追求的结果事实上也没有达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二重目的“好生活”,而是一种“必须”的底线,赋予战争在国际关系的框架内最起码的人性,也就是法律所能保证的最基础的人性。
针对第三剂良药,格劳秀斯将自然法视作国际法的基础,基于自然法,一国对于另一国所造成的超出理性范围的损害应该予以补偿,这同样也是维多利亚认为的战争胜利者所应行之事。不同的是,格劳秀斯进一步区分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有关补偿问题的区别,在他看来,只有非正义的战争才存在补偿的问题,正义战争则不存在补偿问题。
也正是由于维多利亚开出的这三剂良药,其战争法体系才不至于被冠以“毁灭政权”甚至“毁灭人类”之称号,这也使得维氏的战争法体系与新教派(尤其是路德派)的劝勉产生了一丝共融之可能。民族政权在维氏的战争法框架之下的“既在”亦同样是遵循“个体—共同体—个体”这一逻辑理路的。29
维多利亚有关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另一重要思想是教会法在非基督教世界中存在的合理性论证。德国法学家魏尔克尔(Car l Theodor Welcker)有言:“人道主义绝不可能从希伯来人的超自然主义产生,因为人们对这种思想的领会越认真越高超,则一神的权威和法律,对于人的一切力量和快乐以最优良和最高尚形式借以表现的人类宗教自由的抑压也必越甚。”30维多利亚则尝试为信仰合一的基督教在新世界的传播与发展探寻另一条进路。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15-16)基督教在美洲大陆的传播便是遵照这一逻辑:(1)基督徒有权利在世界范围内传福音;(2)非基督信仰者可认信可不认信;(3)认信者获救恩,不认信者获罪。维多利亚亦未跳出这一《圣经》中基督教到世界宗教的传统逻辑。维氏认为,基督世界以外的人倘若不知基督,其所言所行并不为罪,然而一旦当福音传至于斯,当地人知晓了上帝之存在,那么若再言触犯上帝之论,行亵渎神灵之事便要获罪。32对此维氏亦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一,任何政权的存在都必须经过上帝之授权,因为上帝创造万物,除非其交与一部分权柄,否则任何人都不得进行统治。其二,“耶和华差遣我膏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撒母耳记》15:1)“这是守望者发出的命,圣者发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但以理书》4:17)其三,“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记》1:26)故统治者乃依据上帝之形象创造,并且上帝之形象是无罪孽的,也就是统治者无罪孽。其四,罪人所犯乃是冒犯主之罪,因而顺理成章地失去统治权。其五,据奥古斯丁所言,罪者甚至不配其所食之面包,更何况统治权。其六,上帝赋予人类祖先亚当、夏娃伊甸园的统治权,而后由于其罪孽又将之剥夺。
根据以上六点,得罪之人应然地失去了其尘世的统治权,也就是说,亵渎上帝的统治者将受到自然法(万国法)的惩治,从而失去其统治权。35同时,此项神圣事业的执行者只能是天主教廷授权的西班牙人,从而避免了新教等势力的染指之虞。及至当地基督信徒的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教皇便可合法地重新加冕一位新的基督徒统治者,且毋须听取当地民众的意愿,从而使得原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自动失效。同时,在美洲新大陆上,西班牙的神圣法庭即宗教裁判所也赫然建立。教权开始插手殖民地事务,在新世界里,与政权合为一体,维多利亚的万国法体系失效。
而沃格林将维多利亚称作狂热地汇集了所有能够想的、将会证明西班牙征服之正当性观点的“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33实际上是有欠妥当的。维氏在其万国法体系之中为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统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然而他是用一种含蓄的、有所限制的方式,其对于非基督教世界既在政权的权力保护,承认既在的非基督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在其战争法框架下对人自然权利之伸张皆对后世的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政治体理论产生了显著影响。
四、结语
维多利亚在研究了教会的起源和内涵之后将教会定义为信者的集合,同时这一信的集合有且只有一个,便是唯凭基督的教会。维氏受阿奎那思想影响颇深,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将权力两分,分成了世俗的政权与超自然的教权。而教权虽不能染指世俗权力,却有着自己超然的权力,便是有关宗教生活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就是这一理论的产物。维多利亚同时作为一名神学家和法学家,依据《圣经》构建了一个基于万民法原则的高于普通共同体的超越共同体,建立这一超越共同体的初衷是调和基督民族与非基督民族的矛盾,通过战争法的规范作用,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其后通过不断地发展与衍变,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国际法的雏形。维多利亚跟同时代的众多经院哲学家相比,在政权与教权的纷争之中更为强调的是一种秩序的理性。在继承阿奎那的法律“第一原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教权的本质剥离出来——一种精神之力,同时追求精神之善。虽然在维多利亚那里,世上一切权力之根源仍来自上帝,但是作为个体,在尘世生活中所享受之权利已越来越和至高无上的上帝权柄形成了官能上的界分。
在探讨基督教世界和非基督教世界中的既在政权时,维氏则是以一个法学家的睿智思维来确认各民族政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政治体之上的“存在即合理”论。对于基督教政权在拉丁美洲的殖民扩张,维氏依据基督教义确立了上帝子民在异邦传福音以及衍生而来的诸多合法权利,同时又对一部分违悖自然理性和自然秩序的行为进行了声讨与规制。在维氏建立的民族政体共同体框架(即国际法体系雏形)之中,对不论是基督政权在非基督世界的既在问题,还是非基督政权其本身的既在问题都进行了基于自然法上的平衡。
事实上,有关维多利亚思想的两大中心问题,即教权超然与政权既在的问题,在《圣经》上早有明断:“凯撒之物当归凯撒,神之物当归神。”(《马太福音》22:21)
维多利亚作为近代国际法的拓荒者,从中世纪教会思想中汲取解决新问题的知识工具,如对“万民法”的洞见使国家概念较早期经院哲学更为清晰,甚至预见了主权理论。而其所持守的普遍人类社会并为共同法所支配的思想,成为国际法学的理论基点。因而研究维多利亚思想对于追问国际法形成的社会基础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34
注:
1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7.
2参见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
3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50.
4 Hus:The Letters of John Hus,trans,Matthew Spinka,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2,p7.
5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8-49.
6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55.
7维多利亚之后的萨拉曼卡学派代表多明戈·索托(Domingo de Soto)在权力谱系上继承了维多利亚的两分论,并根据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伊西多尔等人的思想,将权力领域的两分延续到法律领域,强调了法在普遍领域的作用与法在超然领域的作用。见Fernandez-Santamaria:Natural Law,Constitutional ism,Reason of State And War,Peter Lang Pub Inc,2005,p80-81。
8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2-73.
9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3-74,138.
10阿奎那所谓的“善”的意涵是“什么是可欲的”,而存在表明的是“是什么”,并不涉及可欲性的问题。参见[美]克拉克、吴天岳、徐向东主编:《托马斯·阿奎那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11维多利亚认为这也是使徒给某些哲人定罪的原因,因为哲人们将永恒世界的某些组成尘世化,从而导致了恶的“上升”。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2.同样,关于恶的“上升”,中世纪出现的一些异教作品中也可窥其一斑,有关“以赛亚的异象”,便是描述先知以赛亚在天际观看撒旦与上帝使徒之间的战争,而作品中所用的形容词为恶的(evi l),即为恶者的战争。如此便悖离了奥古斯丁的教导。Wakef ield,Evans edt:Heresies of the High Middle Ag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450.
12维氏在这里并未就基督徒与异教徒的立法权做出甄别,由此便产生了一个矛盾,倘若立法者所颁布的法律是一代一代传承的,那么追根溯源法律的源头便在摩西和先知的训诫之中,然而对于异教徒而言,是不能了解到摩西和先知的话的,那么异教徒的法律从何而来?对此,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St.John Chrysostom)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法律是上帝从一开始就灌注在人的理性之中的,即自然法,而非由摩西或是先知所“传达”的。见Stanley Ber tke:“The Possibi lity of Invincible Ignorance of the Nature Law”,The Cathol 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Studies in Sacred Theology,Vol55,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41,p8。而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则进一步指出这样一种“理性灌输”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上帝降临西奈山这一事件并不是人类法律从无到有的“分水岭”,其原因在于,“摩西十诫”中的每一条诫命都可以在上帝降临西奈山这一事件之前找到源头,因而,人类立法这一历史事件也同样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见Alan M.Dershowwitz:The Genesis of Justice,Warner Adul t,2001,p215-216。
13见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82-83。
14 Ramón Hernández:“The International ization of 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Domingo de Soto”,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15,Issue4,1991,p1042.
15在人文主义上,维多利亚受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Erasmus of Rot terdam)影响最深,同时还与客居巴黎的西班牙人文主义学者比维斯(Luis de Vives)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在唯名主义上,维多利亚最常提及的是瓦伦西亚的唯名主义者塞拉亚(Juan de Celaya),同时也涉及阿梅恩(Jacob Almain)、梅杰(John Major)等同时代学者;在托马斯主义上,维多利亚称自己有两位最为钦佩的导师,其一是费纳里奥(Juan Fenario),其二是布鲁瑟兰斯(Peter Bruselense)。Ramón Hernández:“The International ization of 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Domingo de Soto”,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15,Issue4,1991,p1035-1036.
16[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5卷):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17 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53.
18[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5卷):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19 James Brown Scott:The Spanish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Law: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His Law of Nations,Lawbook Exchange Ltd,2000,p7.
20此观点是维多利亚在萨拉曼卡大学任教期间的一次讲演中提出的,维氏认为,及至当时,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已然面临了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应对此危机是“有益的,适时的”。并且维氏将此历史事件看作是国际法的起源。见James Brown Scot t:The Cathol ic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Francisco de Vitoria,Founder of Modern Law of Nations,Lawbook Exchange Ltd,2007,p63-64。
21维多利亚提出的用自然法代替神法作为国际法调整政体之间关系基础的理论遭到了后世众多思想家的反对,霍布斯(Thomas Hobbes),泽茨(Richard Zouche)以及瑞切(Samuel Rachel)等提出了用人法代替自然法成为国际法基础的观点,其认为,万国法(Law of Nations)乃万国间法(Law among Nations),由众多习惯与条约构成,而非基于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理性。见Harold Hongju Koh:“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The Yale Law Journal,Vol.106,1996-1997,p2608。
22见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95。
23[德]路德:《〈加拉太书〉注释》,李漫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07页。24斯柯特(James Brown Scott)对于维氏提出的“惩罚与报复”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提出了两个延展性的问题:其一,与“履行职责”(due di ligence)与违悖正义(denial of justice)之关系;其二,国家人格化的问题,斯柯特认为维多利亚的“惩罚与报复”理论使得国家具有了人格化的“恐惧”,使得其在做出了错误的举动之后会惧怕随着而来的“惩罚与报复”。见James Brown Scott:The Cathol ic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Lawbook Exchange,Ltd,2007,p33-34。
25 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00.
26 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01.
27参见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15-317.
28 Hugo Grotius:The Law of War and Peace,in Peace Projects of 17th Century,1972,Para.
29维多利亚之后美国的一些实证主义法学家如肯特(James Kent)、维顿(Henry Wheaton)等就维多利亚的“个体—共同体—个体”的逻辑理路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国际法(战争法)特别是在美国是受到普通法的影响最重,即从个体的习惯到共同体的习惯,即“个体—共同体”的逻辑,与奥斯丁(Jonh Austin)所提出的政权之间的“道德制裁”(moral sanctions)、“普遍敌意”(general hosti lity)、“强力受制”(violate received)等概念有着一定的契合,而没有像维氏一样,最终将政治体冲突之结果又复归到个体(君主)的身上。见Harold Hongju Koh:“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The Yale Law Journal,Vol.106,1996-1997,p2608-2610。
30[德]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6页。
31 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40.
32此处维氏对剥夺得罪之人统治权的法律进行了巧妙的处理,维氏将诸冒犯上帝者之因由归结为缺乏统一规范所导致的对上帝的“不适”(inappl icable),于是需要一个普遍性的规范即万国法(jus gentium)来规诫惩治诸得罪之人。这样,便巧妙地规避了神法对于世俗权力之影响,从而教权仍可位居幕后窥伺政权之争而不必担心破坏其超然性。见Antony Anghie:“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Internation al Law”,Social Legal Studies,1996,5,p328。
33参见[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5卷):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34参见[美]努斯鲍姆:《简明国际法史》,张小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