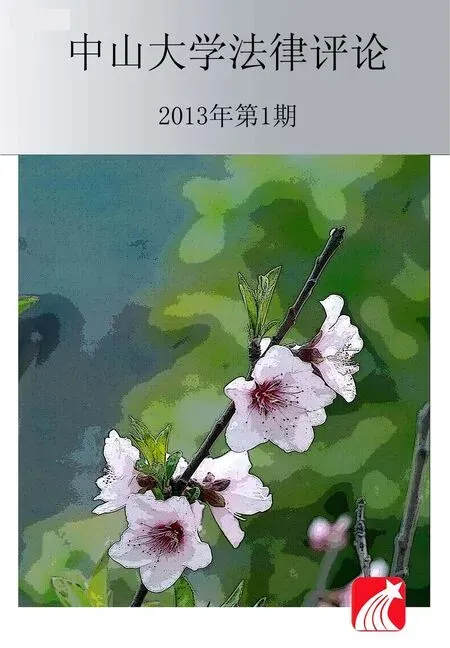社会转型与人权
——以孟买为住房权而斗争为例[1]
杰西·霍曼(著) 吴小薇(译)
社会转型与人权
——以孟买为住房权而斗争为例[1]
杰西·霍曼(著) 吴小薇(译)
在孟买,拥有居住空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这座城市里,住房问题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人权,尤其是住房权的发展,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部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印度最高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将住房权视为生命权的一部分的发展转变,以及这种司法理念对孟买居民复杂的现实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文章通过考察住房权这一扩展性人权的发展,并将住房权判例法和更多近期的关于环境、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发展方面的诉讼案例进行比照,以重新全面地描绘边缘化群体的住房权。这样的分析揭示了在不同的视域里,人权应该被如何解释、规则应该保护哪一方利益的不同思想。事实上,如文章所揭露的,之所以对住房权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对印度转型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国家,以及边缘化群体在这个国家所处的地位有不同的理解所造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住房权的斗争应运而生,因为关于公民权、市民参与,以及城市的未来等内容的含义都是存在异议的。文章最后就大众意义和法律意义中人权表达的转变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一些结论,表明关于社会转型的冲突性的认识,对印度大多数边缘化市民住房权的实现,已经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一、介绍
和世界上很多城市一样,孟买既承受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压力,也得益于其所带来的发展。作为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成为很多人理想的移民地,他们在这里将有可能脱离农村的贫困并获得更多的机会重塑新的生活。然而,人口的增长使得这个城市的基本设施都已处在超负荷状态,现有50%—75%的孟买居民在非正规居住区或贫民窟里居住,忍受着可怕的生存条件,并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在孟买,拥有居住空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住房问题一直是这个城市很重要的社会问题。由于城市住房资源的紧缺,一场激烈的争取住房权的运动[1]这篇文章把涉及人们对于住房权的意识觉醒、为构建这一权利所作出的法律上的努力,以及就这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而发起的政治运动等内容称之为“住房权运动”。尽管很多关注或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士并不承认这是一场“运动”,但这却是解释这场政治、法律、社会斗争产生日益深远影响的最佳方式。正在发展起来,其中,把住房权视为人权的一部分是主要的诉求内容。在国内、区域和国际层面上,住房权的司法应对体制是区别于其他的法律应对的。而这场住房权运动在社会范围内不仅培育起了人们强烈的权利意识,也促进了人们为争取住房资源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行动。
然而,在孟买的住房权斗争中,改变对人权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聚焦印度住房权的司法情况,揭示了关于孟买和印度未来发展的不同愿景对这一权利实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第一种愿景中,孟买被置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背景下,其实质的平等和社会的正义是通过亲贫政策的推广,以及向边缘化社会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物资来实现的。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愿景中,孟买则被视为一个世界级大都市,精英聚集于此,私人资本和企业资本能自由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并在全国的范围内激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
在这两种悬殊的愿景里,住房问题的地位也是相去甚远的。一方面,住房既代表着基本生存所需,也代表着公民权。另一方面,对住房进行规划建设被看作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此,在孟买,对住房资源的争取和斗争,不仅关乎人们的生存和物质满足,而且还与身份归属、权利、财富、公民资格等内容息息相关。
本文沿着这两种不同愿景的复杂脉络,通过分析印度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对住房权作出的不同解读,从而描绘出两种愿景之间的冲突和联系。文章首先分析了住房权相关案例,来研究住房权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权在印度的发展。接着,将住房权的判例和更多近期的关于环境、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发展方面的判例进行了比照。这些近期判例把非正规移民定义为城市入侵者和环境污染者,这便意味着对他们人权保护力度的削弱。文章的最后批判了司法参与在印度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批判了未来孟买的发展方向,以期找出其中人权表达改变的原因。
文章表明,人权虽然为边缘化群体提供了有力的话语和政治工具,但是,人权事业取决于激进的权利重释,而重释的结果既可能是权利的授予,也可能是权利的剥夺。人权的定义是永远无法最终确定下来的,在社会的任何变迁动荡中,为人权的斗争必将一直持续。在印度,这场关于住房权的斗争,表明了为控制人权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斗争的实践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印度乃至世界范围的社会转型中,一些有争议的人权所扮演的角色。
文章的第二部分概述了现在孟买的住房环境,从而呈现这场为争取居住空间的斗争是在怎样的政治、社会和地理环境等复杂背景下发生的。第三部分则以孟买住房权运动及其发展为主要内容。第四部分研究了印度最高法院的司法对住房权所进行的保护。第五部分探讨了立法对住房权案件的反馈,其中包括探讨修复、赔偿、“截止日期”的概念。第六部分分析的内容则是,在环境保护运动中,一些相关判例把非正规移民和贫民定义为城市入侵者和环境污染者,这种对人权的新应用,是如何使这些非正规居民在住房权案件中理应获得的法律保护受到挑战的。第七(一)部分研究了拥有清洁环境的权利所产生的影响,第七(二)部分集中分析了关于农村发展的案例,第七(三)部分思考了将孟买重塑为“世界级”都市这一愿景的影响。第八部分提出了人权表达发生根本变化的两个原因。作为结论的第九部分则就社会转型中的冲突愿景对孟买人权实现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些分析。
二、孟买的住房问题
这一部分将介绍孟买的住房情况以及这样的住房条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以明晰孟买住房问题的由来。这对于理解孟买的住房权斗争十分关键,因为这场人权斗争是在复杂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在最初的时候,孟买现在所处的土地是不存在的,它只有一些从陆地延伸到海洋的低洼岛屿和小型渔村。然而,在殖民统治之下,孟买逐渐开始发展为一个大都会,它的版图包括了孟买岛和撒尔塞特岛,并通过向郊区扩张和填海来不断扩大城市的面积。
作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和印度的金融、贸易中心,孟买一直以来对于移民者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他们被这个城市的光环和无尽的可能性所吸引,而为了逃离农村的贫困也使得他们来到大都市寻求新的生活。因此,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让孟买的基础设施和政府部门都已经难以负荷。孟买只拥有400平方千米的土地,却拥有着1800万人口。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各种非正规住区,包括贫民窟、山区,以及破烂不堪的分间出租宿舍[1]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建造的供工厂工人居住的居所,这种单间的出租房屋现在已经十分拥挤且残破。,或者是移民自己搭建的临时棚屋。2003年,大概约2500个私人的贫民窟,坐落在仅仅6%的城市土地上,容纳了550—600万居民。接近8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不符合标准的、狭窄的且不安全的房屋里,承受着“随时都将被转移的威胁”。
可以说,孟买是一个被定义为贫民窟的城市,但是贫民窟这个词语常在两个层面上被错误地理解。第一,从文章后面更多的细节描述可知,在孟买,并不是所有缺少正式住房的人都住在贫民窟,有些人还住在其他非正规和非法的住所,或处在其他不同层次的无住房或无家可归的状态。第二,贫民窟这个词隐含着环境脏乱、社交障碍、经济落后等意思。这些固有印象中的词汇并不能恰当描绘非正规居民的住所和周边生活环境。相反,孟买的这些非正规住区实际上却是高度组织化的和充满活力的社区。它们不仅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城市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注入了活力。
在没有正规住房的人里,“贫民窟居民”数量最多。在孟买的日常用法中,贫民窟指的是居住者在没有法律正式认可的情况下,迁入其并不具有正式产权的土地并建造住房所形成的聚居区。然而,孟买贫民窟在法律上的定义和住房的占有权或者所有权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和住房质量有关。根据《马哈拉施特拉邦贫民窟区域(改善、清理和重建)法案》[1]《马哈拉施特拉邦贫民窟区域(改善、清理和重建)法案》由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于1971年订立,并于2005年修订,在文章后面简称为《贫民窟区域法案》。的规定,任何缺乏相应服务设施、不卫生、危险、不适合人类居住、拥挤的建筑都可归为贫民窟。这一法案通过“贫民窟修复计划”,对很多贫民窟区域进行改善建设。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能为住房所有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贫民窟这个名称仍然被沿用至今。
不同贫民窟居住区的条件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区别。这些影响因素包括:贫民窟居民的宗教成分、社会经济地位和种姓成分;政治势力或者犯罪集团势力的渗入;知名社会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存在;所处的物理和地理位置;连续有人居住的时间长度或其已形成的特性。这些因素,连同土地所有者的身份,通常就可以决定贫民窟居住区社区服务和公共事业的水平,以及其安全性和稳定性。
然而,就算在最繁华和由来已久的贫民窟里,有着那种几层高的建设质量较好的混凝土结构楼房,人们的居住条件通常也还是很可怕。这一部分原因是由房屋所处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孟买大多数的贫民窟都建在边缘和贫瘠的地区,包括红树林沼泽地、垃圾堆填区、墓园区、易受洪水和涨潮影响的平地区、危险的高压电缆区或者其他“不适合人类长居”的区域。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和便民设施的缺陷也加重了贫民窟不宜居的程度。大多数居民并不能方便地上厕所和获取清洁、安全的水源。简陋的排污系统通常不能有效排走季风雨水,使得贫民窟区域遭受洪水和毁坏。在贫民窟里,房屋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只留有很狭小的通风空间或公共空间。
孟买的第二种没有正规住房的人群是街道居民。如果说贫民窟的居住条件很差的话,那么街道居民的居住条件则是极度恶劣。他们通常是刚刚移民到城市来,不过也有一些家庭是好几辈人都一直居住在街道上的。由于不断受到驱逐,街道居民扩散到这个城市的高速公路边、人行道、铁路边,以及其他“有空地的空间”。在这些地方,他们筑起仅能提供最基本遮蔽功能的家:
这是典型的狭小空间,四周用大的麻布袋或者是纱丽布围起来,上面则用粗麻布、旧的塑料质地的床单、有时也用防水帆布盖为屋顶,四周用一些木杆作为支撑……空间只有四英尺[1]1英尺=0.3048米。乘五英尺宽,仅足够容下家里四五个人。
而其他街道居民则在露天的地方睡觉。他们在为自己划出私密居住空间时受到了很大挑战:本身是绝佳公共空间的街道,还必须也能当作家。这些居民享受着即使有、也是极少的社会设施,构成了这个城市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的市民群。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街道居住社区是稳定的,那里有商店、小型的工厂和其他小型商业企业。
租户是孟买最后一种居住面积不足的人群。这其中的一些租户住在政府承认的正式居住区内,但是房屋却由于年久失修而破落不堪,其居住条件就和贫民窟的条件差不多。孟买令人窒息的房屋租金控制法案[2]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租金控制法案》,1999,No.18,《议会法案》,2000(吸收了1947年的《孟买房屋租金、酒店和公寓房费控制法案》)。这些法案规定了房屋租金的最高限额,使得房屋所有者的租金来源减少,因而更加忽视对住房的修缮。是使得城市的出租房屋破损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的立法导致房屋所有者无力也无意去维修他们的房屋。而其他的房屋租赁,则由于房东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欺诈、腐败,以及当地犯罪分子的威胁而变得并不安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租赁看上去是符合规定的,租住的家庭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仍然会受到恐吓和敲诈。另外,还有很多个人或者家庭租住的是非正规住房。这些“看不见的租户”处于双重不利的状态,不仅是因为他们所住的非正规区域外的房屋或者临时营房会被随时拆毁,而且还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和正规居住区内的租户同样的法律保护。
以上的描述说明,要将贫民窟和街道棚屋、分间出租宿舍以及其他租屋清晰地区别开来是有难度的。Appadurai写到:“没有安全居屋的贫民是无处不在的。”[1]Arjun Appadurai,Spectral Housing and Urban Cleansing:Notes on Millennial Mumbai,12 PUB. CULTURE 637(2000).所有的非正规居民都缺少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家”,这和孟买对非正规居屋进行拆迁有着很大联系。印度人民法庭在2005年6月曾发布称:“从2004年12月8日起,超过80000间房屋被政府拆除。”拆迁规模的大小会受到政府政策改变的影响,而一次性涉及成千上万房屋的大规模拆除并不罕见。
这些不同种类的非正规居住区所处的地位是尴尬的。这里的居民占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在地位上却是很低下的。他们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却被忽略,得不到相应尊重。他们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最必要的劳工资源,但也改变不了他们被边缘化的地位。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是这个城市能正常运转的不能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体面的公司职员、护士、邮递员、银行职员、文秘人员”,组成了这个城市的工薪阶层。孟买的这些非正规居住区的存在,并不代表孟买经济的不景气。例如,拥有超过一百万居民的亚洲最大的达拉维居住区,每年有着预计7亿英镑的经济产出。他们的工资很多都在基本最低生活线以下,但他们却是孟买最主要的劳动人口。另外,生计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和住房的问题分离开来。人们的居住地通常是他们工作和经济来源的基础。人们都愿意在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居住,不管是在正规居住区内的家务性工作,还是在城市核心区的办公室工作。
在人口统计学上,不能把这些非正规居民简单地划分为一种人。他们中的一些只能通过乞讨、拾荒或者做清洁工等等来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其中的另一些人则自视为中产阶级,他们让小孩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而他们还会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和地方政治运动中。
在孟买,确定一个非正规居住区里居民的典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尽管有时,一些标准可以将非正规居住区划分为不同种类,但是,这样的社区群落的外延是非常丰富的,以至于并不能都恰好地划分到研究或分析所期望的种类当中去。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非正规的组成部分,对孟买的城市运作和发展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非正规居住区里的居民却不能拥有完整意义上的生活,而是被边缘化了。
在认识孟买非正规住房在政治、地理和社会等层面存在的复杂特点后,可以得出“贫民窟”不仅仅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法律上、地理区域上和人口统计学上的概念。常被称为“贫民窟居民”的这些非正规居民的存在,应该能起到定义这座城市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特征的作用。在孟买的法律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贫民窟居民和城市之间的这一复杂关系一直都是其中重要的议题。
三、孟买住房权运动的发展
文章上一部分对孟买住房问题现状的介绍,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住房权斗争的背景,而文章的这一部分将简要论述孟买这个城市独特的住房权运动的发展。
在印度,由国家内部发起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独立和积极能动的司法则作用着并解释着对于印度的国家结构和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的宪法。印度宪法的内容包括了国家法律所保护的基本权利[1]《印度宪法》第12—35条。以及在“国家政策之指导性原则”中规定的国家为保护基本权利实现而应提供的社会和经济保障[2]《印度宪法》第36—51条。。
在印度独立于英国统治的斗争中,有着西方形态的权利意识的渗入,而在印度宪法的文本里,也反映了西方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权利及自由宣言的内容。然而,尽管受到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在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上,印度政府的角色和西方民主政府所应承担的角色还是不一样的。就如Singh争辩的,宪法要求的是:
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权利,不管其个人是否主张。国家必须知道人民是享有权利的,这与他们是否要求这些权利无关。国家不仅要尊重和不干扰这些权利,同时还应该以积极的行动保护每个人的权利。[1]Mahendra P.Singh,Co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India,in Human Rights,justice&Co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40(C.R.Kumar&K.Chockalingam eds.,2007).
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度宪法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所预设的则是干预的角色。
在孟买,以拥有体面和足够的住房是一种应得权益为主要诉求的政治运动最早出现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那个时候开始,如Hazareesingh所指出的,“在权利这个问题上……孟买已经成为了社会公众压力聚集的中心”[2]Sandip Hazareesingh,The Quest for Urban Citizenship:Civic Rights,Public Opinion,and Colonial Resista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ombay,34 Mod.Asin Stud.812(2000).。甚至早在殖民地时期,住房作为应得权利的斗争,就已经和生计、工作环境、市民参与、公民权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孟买的城市人口都有着很高的教育水平,与此同时,他们在残酷的被拆迁和再安置中也受到教育和影响。这两种“教育”的结合,可以看作权利和权利意识文化完美的孕育基础。如de Feyter所说:“经历过人权危机的社会群体,会认识到人权是和具体的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的。”[3]Koen de Feyter,Localising Human Rights,in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76(W.Benedek et al.eds.,2007).的确,在孟买,人权运动和斗争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相当多的斗争是围绕着住房这个问题的。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政府尝试驱逐住在孟买铁路线边沿区域的几千个街道居民而引发过一阵抗议的浪潮,非政府组织和基层民间组织为之发起运动,要求修正宪法,规定住房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些运动认为政府在住房权的法律规定上扮演关键的角色。虽然要求修正宪法的尝试失败了,但是这些运动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住房问题成为了国家公共和政治讨论话题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主要由参与街道游行示威的个人和组织向法院提起关于住房权的诉讼中,另一种以权利为基础争取住房资源的形式则出现在印度最高法院对于印度宪法第21条——生命权所进行的司法适用和解释中。
在讨论孟买住房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住房权和围绕着它的政治运动在其中处在重要的地位。孟买住房权运动这段长久的历史,与公民权和社会变迁、政治斗争和城市化及现代化的推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孟买的住房权斗争中,法律所起到的作用是复杂的,这正是文章现在所要设法去了解并解决的问题。
四、从司法的角度看对住房权的法律保护
在这一部分,文章将举出法律对印度住房权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所作出的回应的具体例证,阐述并分析印度最高法院依据印度宪法第21条所作出的关于住房权的司法判决及引出的相应司法理念。文章此处将以住房权的标志性案例为出发点,分析法院的司法推理,并研究这些判例法所揭示的印度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会介绍住房权在印度宪法中的体现。
印度的司法是宪法基本权利的保卫者。在解释宪法的基本权利及自由中,以及在根据国家政策之指导性原则将这些内容延伸到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中,印度的司法都扮演着积极能动的角色。而印度最高法院在这一方面则已经有了创造性的实践。尽管在独立的早期,法院仅对宪法进行“文理上”的解释,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法院便开始发展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解释技巧,去确保这些社会正义政策的实现。关于住房权的司法审判则是这一司法能动性的突出表现。
尽管印度最高法院广泛地采用国际上的规范去建立对印度人权体系的理解,但在分析方法上,印度司法理念中的住房权和国际人权条约中的住房权还是不同的。相反地,印度在其宪法第21条生命权的基础上,创设了关于住房权的独特的司法理念。
这一做法可以被解读为印度认为其本国宪法对人权的保护,并不劣于任何其他国际规范对人权的保护:Mani指出,印度的司法将第21条解释为“遍及所有人权的任何方面,不管是权利本身还是由其延伸出去的内容”[1]V.S.MANI,Human Rights in India:A Survey,in Human Rights:Fifty Years of India’s Independence 173(K.P.Sakensa ed.,1999).。基于法律的解释,宪法第21条现在所包含的权利保持了对生命权的根本性的扩张。印度最高法院被形容为无畏的能动主义者,有人称其“拓宽第21条中生命权和个人自由的范围的这一贡献,是世界范围内能动司法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2]G.B.Reddy,Supreme Court and Judicial Activism:An Overview of its Impact on Constitutionalism,3 SUP.CT.J.20(2001).。
这一对生命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扩张解释,并非最先出现在社会经济权利的案件中,而是出自关于被拘留者权利的案件中:在Maneka Gandhi v. Union of India这一重大的案件[3]A.I.R.1978 S.C.597.里,法院开始把握宪法第21条的解释权并将第21条的内容迅速扩张至法律文本所指向的程序保障所及的范围之外。Ramanathan写道,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法院开始把宪法和“被边缘化的大多数”[4]Usha Ramanathan,Of Judicial Power,Frontline Mag.,Mar.16,2002,available at http://www. hinduonnet.com/fline/fl1906/19060300.htm.联系起来,用人格尊严重新诠释和充实了生命权的概念,加强了这一领域的法律的发展。
表面上看,1981年审理的Francis Coralie Mullin v.The Administrator,Union Territory of Delhi案[5]A.I.R.1981 S.C.746.并不涉及住房和居所问题。原告只是就对她的拘留是否合法进行了起诉。不管怎样,这一案件向法院创造了扩大解释第21条的机会,而它本身则成为之后关于住房权案件的司法推理的源头。Bhagwati法官在判决中写道,生命权“是最珍贵的人权”,“形成了其他所有权利的基础”。因此,生命权必须“以一种更广泛和开阔的视野去理解它,赋予它深远的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并应强化个人的人格和作为人的价值”。法院以这种方式表明了扩张权利的哲学基础。Bhagwati法官继续提到:
我们认为,生命权涵盖有尊严地活着的权利以及其他相关的一切,也就是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足够的食物、衣服、住所,能便利地通过不同的方式阅读、写作和表达自己,能自由地迁徙、和社会的其他人自由结交和结社。
当然,这一权利的构成部分的内容和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无论如何,它都必须包括获取最基本的生活必需的权利,以及使人们能维持上面所提到的功能和活动的权利以期能最低限度地表达自己。任何侵犯和损害人的尊严的行为,都将构成对生命权某种程度的剥夺……
法院因此赋予生命权以拥有基本的物质生活必需品并有尊严地活着的特性。
Olga Tellis v.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案[1]Olga Tellis v.Bombay Mun.Corp.A.I.R.1986 S.C.180.中,在代表孟买的贫民窟和街道居民的诉状里,毫不回避地向法院提出了有关住房和居所的问题。孟买市政公司在不作任何通知和赔偿的情况下,试图驱逐一个大型社区里的非正规居民,用巴士强制把他们搭乘迁移到城市郊区。上诉者争辩称,这样的驱逐,使他们失去自己的家园和谋生手段,正是剥夺了宪法第21条所确定的生命权,为保障这一权利,他们要求政府应为之提供替代性住房。
法院遵循了Bhagwati法官Mullin案的判例。根据国家政策之指导性原则,Chandrachud大法官在判决中写道,考虑到国家有责任“去保障市民获得足够的谋生的方式和工作的权利,把谋生的权利排除在生命权的内容之外,会显得太过拘泥于字面意思”。虽然他注意到国家并非要通过积极的方式去强制提供给公民工作,不过他依然保持认为“任何人非经公正和公平的法定程序被剥夺了谋生的权利,都可以就这一剥夺行为侵犯了第21条所赋予的生命权而提出质疑”。
在确定生命权包括谋生的权利后,法院指出,“如果上诉人被驱逐出他们的居住地,他们将被剥夺生计的这一假设则会成立”。法院列举了对农村贫困问题的结构性原因的细致分析,并与城市的非正规居住的问题联系起来,才得出了这个结论。Chandrachud法官指出:
引起农村持续贫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可供大多数农村人口使用的农业生产用地实在太少了。农民人均农田用地只有0.4公顷,根本不足以让其量入为出。没有土地的劳动力根本没有资源基础,他们构成了贫困的核心。由于经济压力和缺乏工作机会,农村的人口被迫移民到城市去谋生。
由于生命和生计之间的紧密联系,法院认为,对居民进行驱逐只能发生在第21条规定的“根据法定的程序”的条件下。这个判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程序性保障:在居民的生计将会被剥夺的情况下,必须是通过合法的程序才可对之进行驱逐和迁移,否则将损害其宪法所规定的生命权。
然而,法院驳回了上诉者对人行道本身有使用权利的实质请求:
上诉者提出的街道居民在人行道上搭建棚屋和行人在人行道上通行这两者相互冲突,且前者应该优于后者的这一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主张街道居民有占有人行道并在之上搭建棚屋的权利是不正确的。
虽然法院也认为,请愿者的侵占人行道的行为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发生的非选择性的行为……而非基于他们的选择”,但还是指出了,市政当局要求他们搬离住屋的指令是有正当理由的。上诉者并没有占用人行道建立住家的权利,因为“在没有必要的授权的情况下,无人拥有将公共财产用作私人用途的权利”。
在这一案件中,法院主动阐明了构成公平程序的要件。法院要求市政当局把所有的拆迁推迟至季风季节结束或者是更久之后,还要求孟买市政公司为那些原住房被登记在册、可证明在原居住区内长期居住的街道居民提供替代性住所。
随后的隐含生命权包含住房权内容的系列案件都遵循了Olga Tellis案的这一判例。在1990年审理的Shantistar Builders v.Narayan Khimalal Totame案[1]Shantistar Builders v.Narayan Khimalal Totame(1990)1 S.C.C.520.中,另外一群街道居民提出要法院执行法律的规定,以制止强大利益集团的土地资本积累,并同时提供住房给经济上“处在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以对之进行安置。在修正扩张建设和供应津贴住房的指导原则的过程中,法院重申:“在任何文明的社会,生命权都应该得到保障。这包括了获得食物、衣物、合宜的环境和适当的住所以维持生存和生活的权利。”另外,法院还提出人“不仅需要对生命和身体的基本保护,而且还需要有适宜的住处,以使其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智力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样的司法推理不仅包含了人应享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的内容,同时也接纳了人应获得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这一宪法性权利的观点。
在关于住房权的案件中,法院的司法过程体现了其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指导性原则。1996年审理的 Chameli Singh v.State of Utta Pradesh案[1]Chameli Singh v.State of Utta Pradesh(1996)2 S.C.C.549,553.则是这一方面的典型。在该案中,提起诉讼的是被国家政府强制征收了土地的地主。政府希望获得土地为宪法规定其适用政府平权措施的“表列种姓”提供住房。而地主则依据宪法第21条,辩称政府征收其生计来源的土地是损害了他们生命权的行为。
地主的争辩并没能说服法院。实际上,当时的判决根本没有涉及地主所提到的土地和生计之间关系的说法,这样看来法院并不接受这样的辩词。相反,Ramaswamy法官(在判决中)援引了经济公正和物质分配要有利于边缘群体利益的序言原则。法院的这一司法推理是建立在法律的创设是为了保护最贫困的人的利益这一法律假设上的,这一假设不能被强势者所援引。在判决中呈现出来的平等、经济和社会之公正的概念,则活化了这一推理过程。
法院的判决代表了其对支持政府公共政策的明显倾向,且并没有考虑对私人财产权的影响。法院在注意到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极其恶劣的住房条件”后提出,国家向达利特人(种姓人自称)和部落承诺把提供住房作为“战备状态”的经济政策,明显是为了履行它的宪法和国际义务。因此,法院最后得出了土地所有者的私人权利必须“让步给更大的公共利益”的结论。
而在法院的这个说理中,第二个具有说服力的重要部分则是其对住房和居所的定性。在这一点上,法院强调了住房和居所是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重要基础,指出“人们对适宜的住房的需要……打败了平等权、经济公平权、居住权、人格权和生命权本身等这些宪法权利要实现的目标”。它接着提出国家为受压迫的群体提供机会和便利的这一义务,是“根本的且意义重大的”。
Chameli Singh案中的住房问题是带有公共目的的,并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法院所陈述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人们应该拥有稳定的住所,以保障自己在身体、精神和智力上都能充分地发展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成为对社会有益的公民,承担基本的义务,并平等地参与到国家的民主中。让人们有尊严且平等地活着的最终极的目标,则是要让其能够成为不断自我提升的有教养的人。
换句话说,印度宪法中住房权背后的深意是,既承认私人房屋权,也看重为个人提供居住条件以培育其成为社会有益公民这一公共利益的实现。
在1997年,法院审理了第三宗重要的住房权案件 Ahmedabad Municipal Corp.v.Nawab Khan Gulab Khan[1]Ahmedabad Municipal Corp.v.Nawab Khan Gulab Khan,A.I.R.1997 S.C.152.,再一次处理马哈拉施特拉邦街道居民的权利问题。在这一案件中,法院援引了 Olga Tellis案和Chameli Singh案的判决先例,指出了生命权明确地包括了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并列举出了国家为保障这一权利所要履行的宪法义务。
Nawab Khan Gulab Khan案的判决是对Olga Tellis案中关于街道居民驱逐问题的处理原则进行适用的一个尝试。Olga Tellis案的判决要求驱逐必须在符合宪法的范围内进行,在使这个判例标准化的过程中,法院在处理Nawab Khan Gulab Khan案的住房权问题时,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原则首次同时出现,而法院则尝试在判决中均衡各方的利益。
该案的判决中,Ramaswamy法官援引了相关的条例,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他提到国家有责任为贫困和弱势的群体“提供”居住的权利。另外,他提到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必费劲去找寻政府允许人们在人行道上搭建棚屋的原因,而只是需要对这些居住在街道边的人们所处的困境表示怜悯。他争辩到,阻止印度人移民和在有更多谋生机会的地方定居下来的尝试是违反宪法的。但“很不幸地”,他发现在印度独立半个世纪后,在印度的农村只有极少的基础设施存在,也只有极少的为改善这一现状的综合计划在开展。
这个判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概述和评估了政府重新安置这些街道居民的计划的充分性。这一计划可以追溯至Olga Tellis案的判决中要求政府为受驱逐影响的居民提供替代性住房的责令。然而,在Nawab Khan Gulab Khan案中,法院缩小了对非正规居民的保护力度。
例如,Ramaswamy法官指出,越早驱逐街道居民的“侵占”越好。判决建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侵占情况进行长期的监视。并进一步提议说,如果在侵占一出现的时候就尽快解决它们,则遵循自然公平原则的程序的需要也可以免除。在这个案件里,Ramaswamy法官提出了一个很短的告知期限,譬如说“两个星期或者十天”,并称考虑到有了这个合理的告知期限,“在实际情况中,驱逐行动之前的听证的权利并不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则大大降低了对非正规居民的法律保护力度。
Ramaswamy法官还认为,街道居民对他们的棚屋并不能进行财产权的转移。任何对这些棚屋的租赁和买卖从一开始都是无效的,任何从其他非正规街道居民手中获得棚屋的人,都是没有资格被重新安置的。另外,法院强调国家有责任移除街道居民,以使街道为路人所通行。Ramaswamy法官援用了Olga Tellis案关于街道居民没有权利将公共空间用作私人用途的这一主张。他再次强调,行人“可以以合理和安全的方式,在街道自由通行并从事日常的活动”,但是街道居民却不可以这样做。Nawab Khan Gulab Khan案中明显的利益冲突,在文章第七部分更多近期的案例中也会看到,但是在后面的那些案例里,非正规居民被描述为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且更不值得同情。不管怎样,Olga Tellis系列判例依然保持着良法的特征,并对人权的理论、实践和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印度最高法院的住房权判例法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欢迎,因为它以一种具有洞察力、长远目光和全局性的视野去考察人的生命、生活,以及所有人权(从平等到生计,从社会融入到教育)的实质性的内在联系。然而,Kothari争辩称,这些判例在数量上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每个判例所引申出来的法律原则都只是针对各自具体的情况,其救济方法也有其特定性。[1]Jayna Kothari,Social Rights Litigation in India:Developments of the Last Decade,in Exploring Social Rights: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183(D.Barak-Erez&A.Gross eds.,2007).她指出“在关于住房权的主要判决中,印度最高法院都没有给予具体的正面的指令以确保这一权利的实现”。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判决都揭示了生命权和适足的住房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判决阐明了关于生命权的多方面的诠释,涉及对相关的物质需求、结构性的平等、人格尊严、机会,甚至是智力发展等问题的关注,使我们能从中理解体面地生活和生存所应包含的各个层面和个中的联系。
而基于这样的理解,在国家有责任保障公民人权实现的这一对话中,人民即可获得重要的谈判空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概念性的空间不仅仅存在于道德、宗教或者政治争论所需要的范畴上,而且也存在于法律的范畴中。这一理解还挑战了人权的法典化会僵化权利内容的观念、会对一些成文宪法带来麻烦的担心以及会用于对抗一些国家的权利法案所采用的说法。它同时还大大地削弱了如住房权这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如生命权这类公民、政治权利在哲学上和特性上是有所区分的论断。
这一理解的影响同时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如Ghai所说:印度最高法院已经“开启了一个公共的、世界范围的关于人权的对话,这是建立在其自身对权利以及对印度社会和经济条件有独特理解的基础上的”[2]Gash Ghai,Foreword,in Human Rights,Justice and Co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x.xi(C.Raj Kumar&K.Chockalingam eds.,2007).。譬如,南非宪法法院在住房权受损案件的审理中,在考虑立法应该如何合理应对住房不足的各种情况时,就运用了尊严的概念;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发展起了关于有尊严地活着的权利的判例法。印度以外的学术界也开始对有尊严地活着的权利,以及在这一权利里蕴含的社会经济要素进行研究。例如,Gearty和Griffin都将尊严这个概念作为他们最近在人权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亮点。[3]Conor Gearty,Can Human Rights Wurvive?(2006);James Griffin,on Human Rights(2008).最后,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开始把人格尊严和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商品等特性纳入到生命权的概念中。例如,直到最近依然将重点锁定在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特赦组织,也发起了“人格尊严国际运动”,并从中认识到:
贫困不只是收入上的缺乏;它使人们在实现他们的人权、有尊严地活着的过程中,不能获得相应的资源、能力、安全和权利。只有通过全面地尊重人权,包括拥有适宜的居所、健全的身体和知识,才能使普遍的人格尊严得到实现。
这些例子表明,尽管印度关于生命权的司法理念只是法律对于居民住房的剥夺所作出的特定回应,但是印度最高法院的这些司法推理,对于人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国际性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五、立法对司法能动主义的应对
生命权包涵了有尊严地活着的权利和住房权的内容,这一关于生命权的司法理念的影响是重大的,它对印度贫民窟居民、街道居民,以及其他处在社会边缘的或者无家可归的个人所产生的影响则更加直接和深刻。这些司法理念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日常生存带来了什么改善?对住房权进行司法保护所产生的结果在孟买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文章的这一部分,将就相关案件的判决所带来的两个具体的和具有实践性的影响进行研究。第一个与贫民窟和街道棚屋拆迁案件中关于修复和赔偿的规定相关;第二个与基于“截止日期”概念而产生的保护相关。
并不是所有这些对策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正面积极的。现实的情况是复杂的,住房权在孟买社会转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也并不是能够轻易断定的。
印度最高法院在Olga Tellis案中所确立的判决有着重大的意义,它适用的范围不仅限于案中特定的那些上诉者,而且牵涉到了城市里所有的非正规居民。法院规定(部分):
政府应该在马拉瓦尼或者其他合理或不偏远的地方,为那些在1976年普查中被登记了的街道居民提供替代性营房,尽管这不是拆迁的前置条件;政府还必须为那些有身份证明且他们的房屋在1976年普查中被登记在册的贫民窟居民,提供替代性的居所来重置他们;那些已经存在二十年或更长时间、已经改良过的贫民窟将不会被拆除,除非它所处在的土地或者附属的土地需要用于公共目的,这种情况下,贫民窟居民也将获得替代性居所……
这个规定便是在基本权利的案件中,司法对救济方式进行革新性发展的例证。这样“非传统的和非常规性的”救济是为了要带动起国家和当权者方面的积极行动。尽管对这些救济的效果和适当性存在不少争议和质疑,但是其大部分的内容还是被认为是合法的。这些裁决要求政府要落实新的政策,采取积极的措施创造某些社会条件,并承担其他更多法院强制要求执行的任务。而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和执法机关确实也遵循了这些裁决。
在Olga Tellis案之后,其中的几个裁决被政府所采用,而且还被转化为更广泛的立法。其中包括,利用“截止日期”的概念为非正规居民提供保护,以及规定非正规居民在被驱逐的情况下有权提出修复和赔偿,从而产生了一个以Olga Tellis案的关键裁决为中心的立法框架。
这一框架的大部分内容现在都包含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贫民窟区域(改善、清理和重建)法案》中。这个法案建立在两个主要准则的基础上:第一,根据法案,一些特定的非正规居住区的居民能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他们在被驱逐的情况下有权要求“修复”和“赔偿”;第二,依据“截止日期”来获得保护,法案规定在“截止日期”前建立的房屋是“受保护的建筑”,其中的居民也有权获得修复和赔偿。
(一)修复和赔偿
《贫民窟区域法案》的立法框架涵盖了对孟买非正规居住区的法律保护、改善、清理、重建等内容。它为非正规居民提供了很大程度的保护。重要的是,将这些内容以法案的方式固定下来后,当政府有所偏离时,政治活动分子和非正规居民便可以此作为游说的手段。同时,这也提供了一个政治谈判的切入点,这在进行选举的时候尤为重要,[1]湿婆神军党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提出要为居民提供免费住房的竞选承诺。尽管这样的策谋是有争议的。而在接下来要分析的重要问题中,包括了法案的实际执行情况,政治意图,以及判决规则不能完全渗入立法本身等问题。
法案适用于非正规居住区,如所有的贫民窟,而根据其第二章,在被通告的情况下,街道居民社区也在保护的范围内。法案将非正规居民分为两种不同类别。第一种是“受保护的居住者”。他们拥有由政府发放的证明其在居住区居住超过一定年数的证件。在拆迁的情况下,这部分居民可以根据法案的不同条款获得法律保障。而那些不属于受保护居住者范围的人,则无法获得这些法律保护,他们的住房也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
法案所提供给受保护居民的保护,并不等同于他们就拥有了土地或者土地上的住房的所有权,更确切地说,这些保护只是政府在清理贫民窟的过程中要执行的实体和程序上的任务。因此这并不代表对居住权的完全保护。但是,根据法案,政府只能出于“更大的公共利益”才可拆毁受保护居民的贫民窟或者街道棚屋。另外,有可能被驱逐的居民必须获得再安置和修复。修复是指每个家庭都可获得替代性住房以作为对他们失去原房屋的赔偿,重新安排的住屋通常是在专门建造的多层楼房里。虽然法案建议替代性住房应该“免费”,但是在现实中,非正规居民常常要为他们的新住房支付很高的费用。如果家庭一直用他们的住房来经营小型商铺,他们将有权要求换得替代性的商铺空间。因为法案有考虑到贫民窟和街道棚屋不仅仅意味着是人们容身之所,而且还是经济活动和社区构成的基础。
在一些情况下,如果居民拒绝接受修复,或者政府提供的替代性住房对他们来说很不方便的话,他们则有权要求获得经济赔偿以使自己能够去购买其他的住房。然而,孟买的土地价格是极高的。在现在的市场上,除了富人,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在城市购买一个替代性住房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一个受认可的贫民窟区域购买一小块占地只有帐篷大小的土地,都要花费孟买家庭年均收入的两倍费用。在城市里,未被占用的土地是不存在的,废旧工厂区和工业区正在转型成商业综合区,或者金融服务区和技术产业区。因此,即使被驱逐的家庭获得了经济赔偿,最终也难逃要被迫迁到住房条件更差、更不稳定和更加边远的地方居住的结果。
修复是指将贫民窟或者街道居民家庭重新安置在正规的居住区域内。通常,它牵涉要先搬迁到“过渡营”:居住者在等待长久性住房建好前所住在的只有一个房间的临时住处。在孟买,由政府备案的涉及重新安置的问题比比皆是(尽管这样的处理对于一些非正规居住区的居民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虽然过渡营是设计用于暂时性居住的,但由于长久性住房建设的延迟,人们常常要在过渡营里居住好几年时间。也正因为新的长久性住房建设时间很长,在原来的非正规居住区被夷为平地后,人们必须先转移到过渡营。再者,过渡营本身并不是一个宜居的住处。
其次,即使是长久性的修复住房,建筑质量通常也并不理想。另外由于很多居民都靠在自己的住房经营小型的生意或者工厂来谋生,这些修复住房也并不能满足他们经济活动的需要,这是由房屋的狭窄和结构性差的本质造成的。根据《贫民窟区域法案》设定的大多数的修复计划所分摊给每个家庭的空间都是很小的,只设定在225平方英尺(21平方米)。非正规住房通常是从一个房间开始慢慢展开的有机建设,这样便可以去容纳一个不断发展的家庭,甚至是用作店面或者生意经营,而修复住房则不具有这样的可持续容纳性和灵活使用性。
修复住房的选址通常在远离原居住点的地方,这为居民的生计带来了更严重的消极影响。在很多文化语境中,把社区搬离原地点所产生的问题都有被广泛研究,并产生了相关的丰富的文献资料。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很多对人权造成的侵犯,往往都是由那些出于善意或者是经过谨慎规划的迁移所引起的。贫民窟修复计划使得孟买成千上万的非正规居民不断地迁移,但是政府对于这些居民所饱受生活颠沛流离之苦却基本不关心。在城市里,工作机会和家庭所在地有着紧密的联系,住所的迁移通常会造成人们失去谋生的机会,而这正是Olga Tellis案的判决试图要阻止发生的事情。尽管在街道居民区和贫民区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人们受雇佣的比例都很高,但家庭收入通常却仅在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人们也就基本负担不起往返工作所产生的交通费用。
最后要提到的是,《贫民窟区域法案》只保护那些在法律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已经在他们的住所连续居住的非正规居民。更多近期的移民、新建房屋者或者房屋购买者都是不被保护的。在司法和立法上,截止日期本身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内容,文章接下来将会对之进行分析。
(二)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是指在《贫民窟区域法案》的3Y(1)部分规定的日期,它是划分非正规居民的重要分水岭。那些可以证明在截止日期前在其住所长期居住的居民,则有权获得实质性和程序性的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在被拆迁的情况下,他们有权要求修复和赔偿。
然而,截止日期是一个被激烈争论的概念。采用截止日期的第一个问题是证据问题。为了证明在截止日期前的居住权,非正规居民必须拥有能认证其连续居住的地址和时长的相关政府文件,这种身份证明在《贫民窟区域法案》的规定中被称作“photo pass”。然而,由于贫民窟和街道居民聚居地本身的非正规性质,它们常被排除在官方政府认可的范围之外。并不是所有的非正规居民都可以得到所需的认证证件。很多已经在私人而非政府土地上建造房屋的居民从未被发予身份证明,这使得他们不可能享受《贫民窟区域法案》的保护。但有些时候,尽管当地的居民具备相关身份证明,政府也会声称他们是通过欺骗性的手段获取了这些证明,而着手拆毁那里的贫民窟。在这些非正规的群体里,基于标准身份认证的修复计划要实施起来是很困难的。
其次,很多人争论称截止日期会不可避免地违反人权,因为相关规定所给予的保护是建立在歧视性基础上的。截止日期通常是在一个选举拉开序幕之前由政府任意地设定的。此外,一直有主张称截止日期这一概念或许应接受宪法的挑战,Ramaswamy法官在Nawab Khan案中就曾指出,“宪法规定所有公民拥有可以迁徙、定居以及居住在印度任一地方的基本权利,任何个人或组织无权阻碍”。还有争辩称,截止日期并不是用来确定住所的非法性,而是用来确定人的非法性。总的来说,尽管截止日期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管理的统治手段,但是它还是赋予了城市非正规居民具体的法律权利,并成为非正规居民经常组织政治运动所指向的核心问题。
正如前面提到的观点所指出的,截止日期不但不是中立的,反而常常被当作政治手段来使用。对于政党来说,非正规居住区代表着重要的“选票银行”[1]“选票银行”是指来自单一社会群体的选民联盟。——译者注,因此他们常常在竞选中利用截止日期这一工具,通过推迟截止日期来“收买”更多的选民。更糟糕的是,在最近的一次竞选中,一个政党承诺把截止日期从1995年推迟至2000年。这使得其在非正规居住区中赢得很高的支持率,并如其预期在选战中胜出。然而,该政党却在当选后拒绝承认其竞选承诺,并继续对非正规居住区推进拆除工作。然而,这一问题不会就此完结。在一些特殊的计划如孟买机场重置计划中,政府已经同意推迟截止日期。与此同时,基于政府之前的承诺,媒体现在报道都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截止日期是2000年,而目前政府的行动看上去是“很小心的不去触及”那些在1995年至2000年之间建起的贫民窟。由于法定的截止日期依然保持是1995年1月1日,因此,现阶段对1995年至2000年间建立的非正规居住区所给予的保护,是基于孟买当政者意愿的改变,而不是基于法律的授权。再者,推迟截止日期在法律上是存在阻碍的,因为在2001年,政府在和孟买高等法院签署的宣言书中写道:“将不会推迟1995年1月1日这个截止日期,并将尽快移除所有的侵占。”
虽然《贫民窟区域法案》存在本身固有的问题,以及在法案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由于政府政治意愿的缺乏、腐败和欺诈所引发的问题,但是这个法案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它已经向成千上万的孟买非正规居民提供了法律保护。其中一例发生在达拉维,法案为一个大规模的重建项目所涉及的居民提供了保护。这些非正规居民依据《贫民窟区域法案》,通过结合政治和法律的策略提升了自己的谈判能力,并使其在面对强大的对抗利益时获得了保护。他们成功地让法院采用在孟买其他地方所适用的迟五年的截止日期,并且促使政府考虑把修复的房产面积从225平方英尺增加到400平方英尺。
达拉维的这个例子反映了孟买非正规居民处在非常奇怪的矛盾状态中。在一些时候,大众民主给予他们极大的权利,但他们还是处于极易受侵害的状态和社会边缘化的位置。这使得法院对他们提供的保护存在被剥夺的风险。这将会在文章下一部分——印度最高法院新兴的环保司法的背景中进行讨论。
六、关于非正规移民的人权论的转变:环境、发展、现代化
把住房权从生命权中抽取出来,是有尊严的生命权的强有力的司法表述。通过立法行为,以及法院推迟驱逐的救济方式,让非正规移民获得重要的程序上的保障。不过依据这类判例所产生的保护并不像曾经那般稳固了。更多近期的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里,已经不再有宪法规定的要确保穷人体面生活的表述,而是转变为要保护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
非正规移民基于生命权所享有的法律保护,受到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司法能动主义的退缩,也不是来自宪法第21条关于保护人们财产和生活所需的中心的改变。基于第21条的住房权所面对的考验,是来自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文章的这一部分将在三种不同的背景下分析这种转变。第(一)部分论述的是生命权中出现的环境权的相关内容。第(二)部分将分析在农村发展计划中,尤其是备受争议的Narmada水库大坝相关案件中显现出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问题。第(三)部分讨论的问题则是在近期的一些案件中,孟买所呈现出来的“世界级城市”的姿态,以及政府在对待非正规移民在城市中所处地位这一问题上的各种表现。
(一)获得干净环境的权利:“绿色”计划人权论
关于非正规移民住房权的司法理念转变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争取把环境权纳入生命权的运动。在新出现的环境相关的案件中,非正规移民被描绘为不值得同情,有时被认为是完全不值得获得宪法保护。
由于生命权是一个广泛的司法概念,这便开放了空间让“民间社会团体”在生命权的基础上主张各种权利。这些民间社会团体通常由印度不断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组建,代表着有出色游说能力以及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大多由国际组织或者国家本身支持。部分这样的团体向法院主张环境权是生命权的一部分,并通过这样的行动主义方式来推进以环境可持续性为中心的“绿色计划”,以此来抵制以穷人当前生活所需为关注点的“褐色计划”。
在孟买,大多这样的行动主义主要与地处城市的Borivili国家公园(或称圣雄甘地国家公园)有关。该公园占地103平方千米,这一片重要的野生区域是豹和其他动物群的栖息地,同时也是孟买洁净水源的源头。但是,却有数以万计的人在这里居住并建起了非正规的社区。实际的情况是,公园现在同时容纳着私人住所和工商企业,其中包括一家政府运营的猪肉厂和几家采石厂。环保团体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迁移公园里的居民,理由是这些居民是非法“入侵者”,并应该为污染了环境和破坏了生态负责。
关于“侵占”国家公园的诉讼,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03年。最终,在Bombay Environmental Action Group and Another v.A,R,Bharati and Others案中,法官Thakker执笔的全体一致的判决中,孟买高等法院就这些诉请作出了一个共同决定。法院着重指出,孟买环保行动组织“通过行动助益了国家发展计划的目标推进”,“其关注的环境、生态、野生区域问题,政府当局也应该分担重视”。相应的,法院要求重新安置33000个能证明在截止日期前持续居住在国家公园的“受保护的居住者”,并逐出不能提供证明的居住者。
“受保护的居住者”可以获得替代性住房,即使这些住房远离他们的原居住地,并需要他们用高价购买。另一方面,没有身份证明的居住者会被看作入侵者。与Olga Tellis案的判决有很大不同的是,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政府当局在处理这些居住者的时候,不需要依照“程序也就是法律”:
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权利,或者是不能证明自己对住所的权限,或者是非法占有居住地,或者是低劣的入侵者,则不能援引“稳定/固定占有”的原则,并主张其不能被驱逐。
把这些居住者看作入侵者,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在宪法第21条的程序性保护范围之内,这不仅意味着孟买非正规居民的权利会明显减少,同时也意味着贫民窟和街道居民在这个城市里所处的位置和重要性在司法语境中产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这个案件中,法院的角色尽管非常重要,但也不可以被高估。在这场涉及政府不同层面和政府部门之间各种竞争利益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斗争中,司法的判决只是代表了这一斗争的其中一方面。尽管法院最终裁判要对这些“入侵者”进行搬迁和驱逐,但实际上很多驱逐都是在法院最终的判决出来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且距离搬迁计划的实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民间社会团体已不仅仅是对非正规居住区的合法性发起挑战,而是进而对非正规居民的公民权造成了明确的侵害。例如,在2004年,一群“杰出的”孟买市民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剥夺贫民窟居民的选举权,声称有“必要”更新选民名单,提出要“把所有铁路周边、人行道、游乐场地以及其他用于公共用途场地里的入侵者剔除在外”。在2005年,孟买市政公司就曾疏通选举事务主任把已拆毁的贫民窟的居民从选举登记册中删除。
这些民间社会环保力量的作为看上去好像是一种社会参与,但实际上也可被看作一种社会隔断,也即Ellison和Burrows所说的,是“一种积极的、但以自我抽身为主要目的政治活动”[1]Nick Ellison&Rogers Burrows,New Space of(Dis)engagement?Social Politics,Urban Technologies and the Rezoning of the City,22 Housing Stud.295,306(2007).。也就是说,城市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试图和贫困问题撇清关系,他们拒绝接受这些问题是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所产生的问题这一事实。相应的,他们不仅拒绝承认穷人拥有社会公民身份,而且还表露出要减少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态度。
这些基于“穷人不管怎样都是非法的,因此不享有任何权利”的观念的民间社会力量,暗示了权利在社会归属和社会成员资格问题中的深层意义。那就是人权不仅仅是完整的社会和法律人格的有益获得手段,而且是其构成的基本。通过人权这种当代语言,人们获得社会身份的诉求可得以实现。再者,获得他人包括国家的承认,实际上是获得对人的属性的承认。因此拥有人权“等同于拥有了人类属性”。
在孟买,民间社会团体通过发起运动去否认非正规居民居住在特定区域的权利和孟买公民的身份,是为了试图把这些非正规居民从这个城市中抹去。这样的动机是由剥夺权利或者否认权利所造成的毫不人道的例证,同时也是Ellison和Burrows一致提出的要把穷人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的欲望的表现。因此,如果孟买非正规居民的权利不被承认,这便是预示了同时也是允许了他们的同胞可以不再将他们当作人类去看待。
尽管最高法院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反对孟买富裕阶层要剥夺非正规居民公民权(选举权)的要求,但关于国家公园的诉讼却表明,司法机构已经开始认为环保论是具有说服力的,并且在认可拥有洁净、有益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方面,已经作出了驱逐成千上万的非正规居民的判决。这不仅仅发生在孟买,还发生在印度其他很多处在快速发展中的城市。
显而易见的是,印度司法机构已经接受居住在洁净和有益健康的环境中的权利进入到生命权的扩张解释中,但不寻常的是,关于环境保护的案件被纳入生命权范畴的过程中,伴随而生的是关于非正规居民的司法理念的巨大变化。文章接下来将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遵循Olga Tellis案先例的案件在形式上都没有改判,但非正规居民所受到的法律保护却在慢慢减少。例如,虽然在Olga Tellis案中讨论的广泛原则,Ahmendabad v.Nawab Khan Gulab Khan案也可适用,但是非正规居民获得保护的依据的关注点已经从非正规居民的权利,转向政府具有保持街道整洁和对贫民窟的清理进行有序管理的职责。
和所有的公共利益诉讼一样,住房权案件的审理同样经历了法官在中产阶级、贫困群体和国家三方利益的竞争中努力作出平衡的过程。在很多这种案件中,贫困群体在司法过程中获得的同情越来越少,伴随着的是他们权利范围不断缩窄。在Olga Tellis案中,当时的主审法官Chandrachud对街道居民的描述尽管带着反感,但同时也是充满着怜悯,有时还显示出尊重。他描述到,很多非正规居民追求拥有的只是“简陋但体面的住所”,并强调他们“主张居住在街道和贫民窟的权利,并不是为了要作出非法或不道德的行为,也不是要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这个案件的判决同时还考虑到隐藏在街道居民生存环境下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结构性原因,指出:
剥夺一个人谋生的权利实际上就等于夺取了他的生命。的确,这解释了农村的人口大量地移居到大城市的原因。他们移民是因为在农村无法谋生。促使他们离乡别井的原动力,是他们为了生存的挣扎,也就是为了生命的挣扎。
另外,主审法官还形容了他们居住在街道上是因为迫不得已: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大城市里,只要还有其他选择,没有人会愿意居住在街道边上或者是贫民窟里。任何在乎的人只要瞥一眼街道边上和贫民窟里的住房,都会知道那根本就是地狱。
然而,这已经不再是关于贫民窟和街道居民的主导的司法观念。Almitra Patel v.Union of India这一环保案[1]Almitra Patel v.Union of India A.I.R.2000 S.C.1256.,以公共利益诉讼方式要求德里政府当局策划并落实固体垃圾处理计划,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个案件中,Kirpal法官所作的判决对于涉及非正规居民的司法理念的改变具有巨大的影响。他把德里的污染问题归咎于贫民窟居民,他在判决中写道,这些居民“不讲卫生”,他们“未经授权的聚居”使得城市垃圾的处理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他指出:
过去的几年里,贫民窟的数量在成倍地增加。公共土地的大部分区域就这样被无偿地侵占以用作私人用途。……以纳税人成本获得土地的承诺……这样的提议只会吸引来更多的土地强夺者。把替代性住所免费提供给公共土地的入侵者,实际上就像把财物送到扒手的手中一样。……越来越多的贫民窟不断出现。在德里,替代“贫民窟清理计划”的是“贫民窟建造计划”。这也导致了家庭垃圾被抛掷在贫民窟里面或者周边范围的空地上。而要控制这一问题,至少可以首先从防止贫民窟数量增长上入手。
法院因此要求土地所有者迁走这些非正规居民,并把土地免费提供给德里政府当局用作垃圾堆填场和堆肥场。如Ramanathan指出,“贫民窟居民由于没有为土地的使用支付费用,而导致其被用作免费的垃圾堆填区,由此认为贫民窟居民是有罪的这个观点被很多人所注意”。这个案件对非正规居民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界定。Olga Tellis案曾把非正规居民描述为在恶劣的环境中挣扎谋生的市民,而现在,这些贫民窟和街道居民则被描述为机会主义者。他们充其量是“经济移民”,而最坏的情况下则是罪犯。无论是哪一种角色,他们都是比垃圾更令人厌烦也更没有价值的物体。
(二)农村的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论
上一部分提到的Almitra Patel案的判决,只代表了现在仍在持续的公共利益诉讼中的其中一种司法观点,它表明了在很多这些案件中都有一个潜在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关于讷尔默达河萨达萨若瓦水坝建设的系列诉讼中,对这些关乎印度农村发展案件的最具有争议的讨论即可说明这个潜在问题。
水坝建设在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而讷尔默达河的水坝建设体现的正是“独立后国家建设的精神”。这一水坝工程横穿三个邦,以供给电力、饮用水和灌溉为目的,然而这个工程不久便被卷入到一场持续的环保和社会抗议浪潮中,部分的争议点在于2500万—4000万人由于水坝的建设要被迫迁移。
围绕水坝建筑的诉讼和政治斗争是艰难而复杂的。然而,这样的斗争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近期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所表现出来的司法态度都说明了农村发展、强制迁移和现代化论之间的深层关系,尽管有时的表达比较隐晦。
最高法院2000年审理Narmada Bachao Andolan v.Union of India and Others案[1]A.I.R.2000 S.C.3751.则让环保主义者和社会权利活动者感到焦虑。在这个高调的诉讼中,最高法院驳回了迁移和重新安置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是违背印度宪法第21条的主张,这些印度人很多是部落居民以及由于贫穷或社会身份被边缘化的人。Kirpal法官指出“对部落居民和其他人进行强制迁移本身并不导致对他们基本或者其他权利的侵犯”。根据明确的国际上的法律规范,强制迁移表面上看即侵犯了人们的住房权,而Kirpal法官的这一表述无疑违背了这一规范。但它进一步表明,由于水坝的建设而造成的居民迁移和被安置到修复区对这些居民来说是有益的,因为“这会让他们的居住条件得到好转,相比原来居住的部落村庄,他们在新的安置区将拥有更多更好的生活便利措施。逐渐融入社会主流的过程将给他们带来改善和发展”。事实上,Roy指出,认为迁移和重置是一种“积极干预和缓解居住地丧失的方式”的这一论点现在仍在被不断重复和强化。[1]Arundhati Roy,The Cost of Living:The Narmada Dam and the Indian State,in Experiencing the Stae 53,64(L.I.Rudolph&J.K.Jacobsen eds.,2006).她称通过这样的方式,现代化造成的代价被描绘成了好处。
根据现代化和发展论,这种观点与认为印度农村贫困人口的迁移和城市贫民窟居民的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似乎是背离的。正因如此,Narmada诉讼和Olga Tellis案、Chameli Singh案这类住房权案件都很不一样。更麻烦的是,该案的判决和Kirpal法官自己在Almitra Patel案中作出的判决也不一致。在Almitra Patel案中,判决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放弃在农村的土地和生计,与人们迁移到城市并被迫在城市的非正规区域找到住房、艰苦营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尽管也是在Narmada案中存在的事实,但这样的迁移在该案中却被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
Narmada案的判决使环保主义者、贫困的农民群体、反对迁移的非政府组织团体和部落村民联合到了一起。然而,在很多涉及侵犯住房权的案件中,例如Chameli Singh案,以及在很多涉及环境权利的案件中,例如Borivili国家公园诉讼,环境都是被置于与非正规居民的生活和权利相对抗的位置。在这些案件中,出现了清晰的阶级分层:中产阶级和保护环境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穷人则被看作城市垃圾的制造者。
但是事实却是,印度城市中高收入群体制造的垃圾要远多于非正规居民制造的垃圾。一项研究表明:在德里,高收入人群人均每天的垃圾制造量是420克,中等收入人群是150克,而贫民窟居住人群只是80克。非正规居民的人口密度虽然很高,但较之正规居民,他们有着“更轻的生态足迹”,实际上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是最小的。但是在Almitra Patel案中,正是“由贫民窟制造出来的垃圾和固体废物”被法院要求“应尽快并优先处理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侵占”了印度城市的很多区域,其中包括孟买的Borivili国家公园,但是他们却没有受到非议或者是法律规定的搬迁计划的管制。因此,Mahadevia和Narayanan指出,“贫民窟居民违反法律的说法,只是一个对穷人持有偏见的表述,而不是对违法行为不能容忍的表述”[1]Darshini Mahadevia&Harini Narayanan,Shanghaing Mumbai-Politics of Evictions and Resistance in Slum Settlements 32—33(Ctr.for Dev.Alternatives,Working Paper No.7,1999).。再者,将非正规居民视作“污染者”的这种归类有着令人反感的言外之意,因为在印度歧视性的种姓制度的历史中,“最低级”的种姓被认为是“有污染性的”,而在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受到排挤。
(三)孟买的冲突愿景:世界级城市论
印度的城市在印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像Blank所说的,城市“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城市化通常被理解为人类社会脱离传统生活方式的象征”[2]Yishai Blank,The City and the World,44 Colum.J.Ttansnat’l L.875,886(2006).。城市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前沿”。在一些案件中,环境权和住房权相互对抗的紧张关系,揭示了城市发展在印度未来中的不同图景。一方面,印度的城市肩负着可以让任何人都能在其中开启新生活的使命,无论人们是多贫困或者是边缘化。而另外一个方面,印度的城市也承担着推动国家向全新的方向发展的使命,这个国家的未来将会是更高效、更洁净,并有规划推进现代化。
德里作为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的首都城市,如Roy所说的,必须被“装扮成应该有的样子”。班加罗尔作为印度的硅谷,也正在自觉地将自己改造为一个高科技全球服务行业的中心。而孟买则一直披着印度最现代和最都市化的城市的外衣。孟买是印度的“大门”,作为金融中心,它代表着印度的资本和全球贸易的实力,是印度通向世界的门户。
孟买将自己定位在传统的理性发展的图景中,在这里,以效率为先,规划会战胜自然,通过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使得人们的生活可以被客观地评价和测量。但这个理想的目标,和当下的现实以及可预期的城市的未来存在极大的反差,被称作“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化的极端形式”。
从印度对孟买未来的规划中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应当向着一个更加自由、市场化、现代化的新印度发展和转变。2003年,麦肯锡国际咨询公司受委托为孟买制定一个新的发展计划。在他们的报告《孟买愿景:将孟买打造成世界级城市》里,包括了一个要在2013年之前将孟买改造成一个全新城市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孟买将被“改造”成另一个上海、悉尼或者是纽约。《孟买愿景》计划去促进经济的增长,改善并增加公共和私人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低收入者的房屋拥有率和购买力,提升污染防控能力和基本必要的服务水平,简化建筑批准程序,通过把公司化运营方式适用到主要的政府部门中以使政府变得更加高效。尽管这些改进措施大部分看上去都没有争议,但是这样的愿景和规划还是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包括其想象中的这个城市,以及其所主张的这种发展进程。
对贫困人群和边缘化人群造成最直接影响的,是这个计划中要把贫民窟居民数量从占现在的城市总人口数量的55%—60%减少至10%—20%的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计划通过提高土地可用率至50%—70%,新建80万套廉价房屋去重新安置现有的贫民窟居民,预备30万套廉价房屋以满足其他需求。但实际上现在有超过600万孟买人居住在非正规居住区,就算《孟买愿景》的修复目标可以实现,也远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
减少非正规住所、以正规区域的房屋作为代替的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市场激励机制和鼓励私人企业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鉴于这个报告本身代表了公共政策的私有化,而这也是印度政府转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一个表现。但是,政府与此同时还是一直坚持其公共管理的角色,并采取了更多及时的措施去减少非正规居民的数量。而正在实施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拆迁工程,已经造成30万人被驱逐,所涉及的甚至还包括已经很壮大且有着很长历史的贫民窟。政府当局作出这样的举动,也许是因为知道在《孟买愿景》中提到的其中一个“模范”城市上海的重建,当时牵涉的强制迁移人数达到150万。
但是,拆除非正规房屋,以及把孟买有规划地重建为一个“正规”的城市,只是《孟买愿景》对非正规居民产生更深影响的一个有形信号。如Davis所指的,这样的城市重建计划必然造成城市空间根本性的重新分配,“涉及的富裕阶层和贫困群体的生活交集的大幅缩小,更是超越了传统的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化”。这也显现了一种传统的观念:“不发达的”和“平民的”区域“虽然处在城市里但并不是城市的一部分”,因而,则可以把城市设想为精英阶层天然拥有的独占物。
实际上,《孟买愿景》描绘的是一个理想化中的城市,在这里,能看到的非正规居民是很少的。在读了这份报告,然后去研究相关的规划如贫民窟修复机构的达拉维重建计划之后,不难看出,在作者想象中的这座城市里,有着内驻亚洲顶尖跨国公司的雄伟的办公大楼,有着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有着规整的停车场和街道。《孟买愿景》的封面和封底印刷着的是傍晚时分的孟买前滩。霓虹灯点缀的天际下,人们在林荫大道上漫步,在海堤边歇坐,几辆经典的孟买的士在种着规则棕榈树的滨海大道上驶过。贫民窟修复机构的网站上,宣传着新的达拉维将拥有“很多生活便利设施,也就是将拥有更宽阔的道路、充足的电力和水源供应、户外活动场地、中小学、大学、医疗中心、社会文化中心等等”。网站把现在贫民窟里让人窒息的脏乱的街巷照片,与计划中未来的整齐、白色外墙的高层楼房的照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孟买愿景》根本没有提及过非正规居住区的喧闹、混乱和嘈杂。
《孟买愿景》的结束部分向读者呼吁到:“孟买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更是印度皇冠上的一颗宝石。但是,这颗宝石却已完全失去了它的光泽。”而只有落实《孟买愿景》中的建议计划,“才可再次恢复它的光辉”。这样的表达,让人不禁联想到独立前的孟买,当时的统治阶级通过殖民军事力量保护其享有的财产所有权、贸易权和土地所有权,并严格限制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个殖民城市的精英阶级对很多社会问题都漠不关心,而是由于政府激进的强拆计划、控制土地使用权的决心以及剥夺孟买非正规居民的公民权这个一时的决定,才使得孟买这座城市得到复兴。
发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些法律案件表明,司法机关还是受到孟买这个精英论愿景的影响的。例如,在Malpe Vishwanath Acharya v.State of Maharashtra案[1]A.I.R.1998 S.C.602.中,印度最高法院指出,把租金水平冻结在20世纪40年代水平的《孟买租金控制法案》是武断且不合理的。虽然人们都意识到过分苛刻的租金控制对于孟买正规区域出租房屋的维修和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这一法案对于孟买人来说还是有着象征意义。它代表了独立前的孟买在社会斗争方面进入到了极盛的时期,包括住房权在内的公民权利在那时被看作“城市复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构成部分”。而现在的司法对于租金控制法案的否认,则可被解读为对这种斗争成果的否认。
即使这种租金控制的法律法规没有被完全摈弃,但最高法院对其意义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改变。在Joginder Pal v.Naval Kishore Behal案[1](2002)5 S.C.C.397.中,Lahoti法官就提出,虽然孟买租金控制法案的制定对租户有利,但与此同时,若这些条文被理解为照顾了地主的利益,法院则应该毫不犹豫地偏向地主。在租金控制的立法中,这些条例的注入,是为了保护在某些情形下也处在弱势地位的地主。
在现实中,孟买城市的大多数土地是相对集中在少数势力强大的地主手中的。这是在孟买众所周知的事实,有鉴于此,法院在司法的过程中偏向于地主而非租户,进一步表明了司法开始背离穷人的需要。
最后要说的是,文章第六(一)部分和的六(二)部分所讨论的案件,必须和关于非正规居民的司法理念转变的分析联系在一起。把贫民窟和街道居民看作入侵者和污染者的观点正在被不断强化,并且这一观点也为案件的判决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这些相关案件包括 Almitra Patel案、Nawab Khan案和Borivili国家公园诉讼。
从Olga Tellis案和Chameli Singh案,到Almitra Patel案和Narmada案的判决,这些在前文被分析过的案件都显示了司法已经彻底修订了对于非正规居民的态度。司法对人权规范的重新设想,可以并且已经对人权的保护和保障进行了重新解释,保证人权的方式并非是赋予权利和提供保护给最贫困和最边缘化的人群,而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利并驱逐他们。为此,基于生命权而发展起来的司法理念和制度,现在看来只是一个动摇的基础。为保护住房权而提起诉讼,现在会被看作一个冒险的策略,只会作为最终不得已才选择的对策。
但是这一风险并不在于法律原则本身的表述不清晰,也不在于在宪法第21条所保障的生命权的问题上司法能动主义的消退。风险存在于宪法应该保护印度社会何种根本利益这个问题上社会和司法重心的转变。近期的住房权案件如Nawab Khan案,以及环境权案件如Borivili国家公园诉讼和关于Narmada水坝的农村发展诉讼的共同主题,则是要清除城市里的非正规元素,并为计划中的繁华、高效、发达的“世界级”城市的建设扫除障碍。
七、重塑印度,重塑人权:隐藏在重新定义“非正规居民”背后的深层因素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将试图探寻出社会和司法对于非正规居民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对非正规居民的定义、他们对这个城市的价值、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这些问题上的显著改变?在这些转变的背后,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印度最高法院法官的组成并不稳定。第二则与印度的高层级司法部门在国家发展中的特殊角色,也就是司法在印度发展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追求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引起关于非正规居民司法理念改变的一个首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是审理住房权案件(包括早期的Olga Tellis案、Shantistar Builders案和Chameli Singh案,以及近期更多的如Nawab Khan案等)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更迭。Olga Tellis案的审理发生在最高法院对人权保护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法院在司法上经过了数十年对宪法的顺从之后,开始改为主动去控制宪法,并从根本上重塑自身的角色,以及重塑在印度获得和保护人权的司法路径,而这在保护贫穷群体方面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即使是在这个时期,个别激进主义的法官所产生的影响也十分引人注意,一小部分法官对于边缘人群的人权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这里讨论的案件中则可明显看出来。在把住房权纳入到尊严生命权的案件中,Bhagwati法官和Chandrachud法官扮演着关键的角色,Ramaswamy法官也作出过有重要意义的判决。而在另一方面,Kirpal法官则在重新界定非正规居民是入侵者和污染者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关于法院能动主义的合适性和合法性的内部讨论也一直非常激烈。另外,稳定的审理宪法性案件的主体是很难确定的,因为宪法性案件可能只会由一小部分法官审理,而最高法院的法官数量已经从原来的8个增加到现在的26个,这导致在受任命的法官席位中,可能会同时出现不同的法理依据。因此,由最高法院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展起来的关于住房权的司法判例,只可看作法院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尽管这些判例确实是良法,且在一些情况下有着重要意义。
所有的法院法官席位都会不断发展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并不必然地导致对早前法院在人权方面的司法判例的摒弃。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原因去解释这种观念的转变:从曾经的住房权判例以社会正义为明确目标,转变为现在的判例法中以保护完全不同的人权利益为目标。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印度宪法体制里,在印度最高法院的国家管理职能中找到其中一个原因,文章接下来将对之进行分析。
印度宪法“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规定国家各种参数的文本……而且还是蕴含着特定的价值、理想、意义和传统的资料宝库,这是超越其工具性作用的”。宪法为国家确定了根本的社会目标和达成维护正义的准则。如Sudarshan所争辩的,制定者“制定的这一套意识形态上的准则,所有印度的政党在国家的管治中都应该承认其根本的地位”[1]R.Sudarshan,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in 2 State and 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55,55—56(T.V.Sathyamurthy ed.,1997).。宪法的制定是为了消除政党政治中内部斗争所产生的问题,并明确国家的角色是“一个整体的、合法的概念,它确认了政治共同体的根本价值,即运行好政权和权力”。印度宪法“预设国家拥有必要的‘掌舵’社会完成其计划目标的能力”。这要求政府能够在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表现出其权威性和果断性。
Brass将这样的调节模式界定为“国家管治”[2]Paul Brass,How Political Scientists Experienced India’s Development State,in Experiencing the State 110,121(L.I.Rudolph&J.K.Jacobsen eds.,2006).,即印度政府有“规范、控制、指示、引导、调节、决定或限制”的责任,但随之而生的潜在问题是,印度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意味着它“不可能完全有效地去管理……”。这一国家管治的独裁主义的定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问题,意味着印度通常是在采用高压方式进行“国家管治”,并预期在其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会牺牲掉部分人的利益。
印度最高法院在印度政府对国家进行管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一个司法审查机关,同时,时事评论员们以及法官他们本身也都认同它的管理角色。最高法院主审法官Balakrishnan在法庭外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最高法院对国家管治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将之解释为“让政府有效运行的任务”。在文章所分析的几个案件中,也能看出法院扮演这一管治角色的方式。法院在其中承担起执行立法计划的责任,包括了从土地收回到废物处理,从环保行动到贫民窟修复。法院的管治功能使得这些创造性的和能动主义的社会政策能够合法地在法院以外执行和实现。
与相对弱势的立法和执法机构对比,法院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它的管治角色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最高法院曾被这样形容,它的“不甚明确的判决带来了几乎神秘的力量”,这和行政、立法机关这些政府政治机构的“衰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Rajagopal就把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形容为“正在丧失或者已经丧失其功能的政府机构,只能勉强或者已无能力执行法律和宪法授权的任务”。因此,最高法院的管治功能给法院带来了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去填补行政和立法机关的留白,虽然有时这样的功能和角色会使法院拥有一个强大的和具有影响力的地位。
鉴于这种关系,最高法院经常要支持并完成立法和行政机关核心的但不能实现的目标。这样,最高法院则需要根据“国家政府的逻辑”去运作和行为。正是司法机构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这一关系,很好地解释了关于孟买非正规居民的司法界定的改变——因为印度政府对印度本身在全球经济中的重新定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其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印度社会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商品化之上的。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印度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就已经是建立在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市场逻辑”基础上的,随之伴生的有“撤销管制、非国有化、收回投资和数码化”。这样的逻辑标志了印度脱离了曾经的严格计划经济和高度国有化经济的建设方式,虽然很多规划好的经济改革都还没有实现。但是如Nayar所说的,正是这些改革措施的不可逆转性,[1]Baldev Raj Nayar,Political Structure and India’s Economic Reforms of the 1990s,71 PAC.AFF.355,377(1998).加上它们是建立在关于印度国家和经济发展的全新设想的基础上,标志着印度经济和社会关系会发生最显著的改变。
把贫民窟和街道居民看作在城市里没有合法居住权的入侵者,这一关于非正规居民界定的改变,表明了印度要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的热切,这也挑战了全球化即人们被迫进入“一个令人厌恶的世界”的说法。正好相反的是,对很多印度人来说,平等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中,是印度应该努力奋斗以达到的终极目标。Appadurai争辩道,即使是被边缘化的阶层,也希望“加入到这个被真实存在或想象中的外来物所深深影响的世界”。尽管如此,如《孟买愿景》所展现的,这个想象中的未来城市,是一个街道居民、贫民窟市民和贫困的租房者都并不存在的地方。就像当时殖民时期的孟买,这些新的发展计划只是为了迎合精英阶层的需求和愿望。
文章中所分析的这些案例,说明了推动这个社会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背后的原因。街道需要被清理以便让车流更顺畅通行,而霸占了公共空间的“障碍”也必须被清除,以便让路给私人投资工程和正规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住房的供给,必须从以租金控制和政府提供分间出租宿舍给劳动者为主导的模式,转变为私人建造、以市场价值销售公寓的模式。同时,私有化的内在动力是应该由市场自行发挥其本身的作用,因此,司法机构则不需要通过扩张解释人权的方式,将土地和住房资源重新分配给贫困群体。作为一个很好的管治机构,最高法院继续承担着立法和行政机关未完成的任务。然而,在国家政府设想的把印度建设成为全新、文明、倡导市场自由经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计划中,最高法院的判决现在更多支持的是地主的经济利益,以及为了满足全球性公司进驻、公共设施私有化和城市美化等需要而重新安排空间资源的计划。正是印度改革愿景的变化,支撑了新的人权论,并夺走了曾经承诺给非正规居民的人权保护。
八、结语
人权在印度社会转型斗争中扮演的角色,表明了在完全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社会愿景里,人权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曾经的住房权判例法里表现出的人权司法理念是建立在平等和具有包容性的公民权基础上的,而近期的关于环境和发展的判例所表现出的司法理念则带有精英主义和排他主义的倾向。这两类判例的对比,说明了人权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极不稳定且极具争议的状态。
尽管如此,孟买不断发生的关于支配空间、住房、获得财产权和公民权的斗争,都证明了人权的力量。在一个以人权的宪法化和神圣化为自豪的国家中,关于人权的讨论和人权诉求的实践是非常具有分量的。当诉讼可以产生带有有形影响的司法理念体系时,这样的讨论则为权利上的游说提供了概念性和政治上的空间。但是基于人权而获得的成果是很容易灭失的。法院放弃对住房权的亲贫解释,以及更新的、更吸引人的如追求环保权和繁华的“世界级”城市的目标的出现,都表明了这场关于人权的解释和获得标准的斗争是“必然要发生的……但却是松散的(会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然而,对于贫民窟和街道居民来说,不管是通过政治、法律或者是其他方式中止他们的人权诉求,都是对那一个“美好的”孟买愿景的屈从,是对他们被社会遗弃、被剥夺公民权的屈从。
幸运的是,孟买非正规居民并不是落后、懦弱和受迫害群体的代名词。他们在改造自身社区的斗争中是积极的,他们对人权的利用也是具有创造性和与时俱进的。他们对人权的主张支撑起了“这个世界性的、多元文化城市的强大形象”,在这样的城市中,“平凡人的非凡勇气”为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带来了希望。即使在冷漠的国家管治和司法制度下,这些公民也还可以通过全新的、创造性的方式对人权进行“重新调节”,带来更多正义和公平的结果。
为人权的斗争从未真正胜利,或者说,只要人权仍被诉求,这场斗争便会有输的可能。孟买的住房权问题的现状,则是人权标准争论,以及权利的主张、失利、恢复这一斗争过程的显著例子。而这样的过程,是任何以权利之名而发起的社会斗争都必须经历的。尽管人权在某些情形下可以被解读为违背了公正的社会改革,但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参与到这场关于人权的公正的争论中,去反对那些不公平的和剥夺权利的解释,逐渐实现正义、包容、社会公民权和公正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
(初审:谢进杰)
[1]作者杰西·霍曼(Jessie M.Hohmann),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研究员,E-mail:jessie.hohmann@gmail.com。
译者吴小薇,女,中山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xiaoweilaw@126.com。
感谢作者授权发表本文中译版。原文发表于Yale Human Rights&Development Law Journal,vol. 13,2010。译文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简化了原文部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