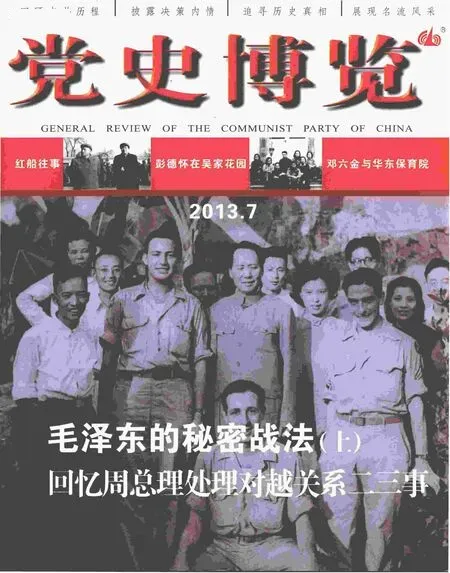彭德怀在吴家花园
■ 刘一斌
从1959年9月底到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去大三线,彭德怀一直在吴家花园住了6年。他的党组织生活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党委副书记伍辉文因此定期前往看望,常委刘子正负责经常性联系照料。在此期间,伍辉文、刘子正与彭德怀常有直接接触,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口中得知了一些具体情况。彭德怀为人耿直,胸怀坦荡,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组织观念很强。他学习勤奋,勤劳简朴,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没有任何架子。不管什么人去看望,他每次都亲自送到门外,等客人上车走远后才回去。这些优秀品质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子正几次向笔者谈及他与彭德怀的接触情况。他在1981年5月14日写信给伍辉文,约其联名撰写回忆彭德怀的文章。伍辉文在16日约石民等知情人回忆,并把党校保存的有关彭德怀的材料交石民参阅整理。18日,伍辉文回函刘子正,并附有石民整理的材料,嘱咐称:“给你提供的材料哪些可用,哪些在公开发表时不宜用原话,我也没有考虑好。我看是否有这样一点须注意一下,即不影响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因刘子正在“文革”中遭康生迫害受到“审查”,迟迟未作结论,文章终未写成。现将二人谈及的情况,择其宜于发表部分综合整理如下,以完成他们的遗愿。
慨然搬家 住进“花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因致毛泽东的一封信,随即在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遭到错误批判。回到北京后,军队系统在大范围内继续批彭,在此情势下,他已无法在中南海居住。1959年9月底,彭德怀搬到北京西北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名曰自修马列主义。为此,彭真、杨尚昆、安子文等前往安置,专门把中央党校的党委常委找到吴家花园,当面作了布置和交代。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遭康生陷害,自身难保,不便与彭德怀接触,没有去。其他在家的常委伍辉文、刘子正、杨志、吴明等全部到场。彭真说:“彭总到党校,请你们带他学习、读书,主要是学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他都经历了,比你们知道的更多,这方面你们还要向他学习。有些问题清理清理,你们与彭总商量研究,订一个学习计划。”彭真接着说:“不要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谁也不敢接近了,都是同志,开诚布公地对待。你们帮助彭总读书,有什么问题可以开诚布公地谈。”
杨尚昆嘱托说:彭总今后暂时安排在党校学习,党的组织生活在党校,看文件和生活问题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管。虽然他受到批判,可他是我党的老革命。你们要派组织原则强的主要干部担任联络工作,有重要文件及时送收。彭总有什么要求要及时向中央汇报。安子文说:彭真同志说了,你们党校帮助彭总读些书,思想上清理一下,要热情相待,犯了错误能够认真接受教训就好。这件事对常委以外的任何人都要严格保密。伍辉文当场提议刘子正负责联络任务,得到了杨尚昆的首肯。彭真当面叮嘱道:“刘子正同志,彭老总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了。这里离党校较近,希望你们多照顾着点彭老总,他的党组织生活以后也在你们这儿过。老总要看文件,看各种书籍,希望你们一一给以解决……还有,再请一位讲师,给他谈谈政治经济学。”

随后,中央党校党委常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如何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进行了研究。大家表示,帮助彭总读书学习,是中央交给党校的一项任务,一定要完成好,要拟订个学习计划,帮他有选择地读些书。会上选定了两名教研室的负责同志任彭总的学习秘书,帮助他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寻找一些参考材料,定期交谈交谈。确定党委的负责同志要定期去看望彭总,多关心他,大体上每月一次,谈谈心。这一任务自然落在伍辉文的肩上。刘子正已在中央领导面前被确定为联系人,常委会再次予以确认,并要求他经常去彭德怀处看望,了解到有什么问题和需要,及时报告解决。领导的嘱托,党委的决定,良知的驱使,感情的倾向,使刘子正一直倾心竭力地承担着这项不为人所知的工作。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毫不避讳地接触彭德怀,在不干扰彭德怀读书学习和正常休息的前提下,经常去看望他。天长日久,耳濡目染,他对彭德怀的品格更为钦敬。
生活俭朴 热爱劳动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的是一处坐北朝南的小院,名字虽雅,环境却荒僻,四周除了农田外,便是稀疏的农户。彭德怀的居室是正房,屋里布置简单,没有太多的陈设,除了一套沙发外,只有几把凳子,墙上挂着一张北京市地图和一张全国地图。彭德怀不喜欢花花草草,便和警卫人员一起在院内种了些庄稼。此外,他还种了向日葵、南瓜、茄子、辣椒等及一些其他瓜果,并在院内挖塘养鱼。他在池塘南边还种了一小块水稻。这种习惯,也是以劳动作为积极的休息,同时有意在做些试验。刘子正每次去吴家花园,见彭德怀干活,就随同一起干,挽起袖子锄地,卷起裤脚下塘,两人边干边聊,相谈甚欢。1961年8月间,伍辉文同刘子正一起去看望彭德怀,特意从党校南院的桃园里摘了些桃子带去。他们进门见彭总正赤着脚,裤腿挽起老高在院子里的池塘边劳动,便一同干起来。彭总指着池塘说:“我们来了以后,同警卫班的同志把池塘里的泥挖了挖,池子里养上了鱼,把池塘的泥做了肥料,种了些瓜菜。我吃不多,可以给警卫班的同志改善生活。”
彭德怀是位刚正不阿、胸襟坦荡的人。几经接触,他觉得刘子正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有时便袒露些心迹,抒发些郁闷。刘子正内心完全理解,深切同情,但只能做些浮浅的安慰,思想上的共鸣则在不言之中。彭德怀初见刘子正时,毫无顾忌地脱口就问:“你相信一亩地能打万把斤粮食吗?”刘子正甚解其意,便间接答道:“我过去在农村没有见过,现在也没有亲眼见过。去年杨老(杨献珍)在党校种的麦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一亩地也就打了七百来斤。这是实事求是、可以信赖的产量。”于是,彭德怀亲自种试验田进行验证。据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记述:彭总1959年秋季到了吴家花园后,自己开荒种了两分地的麦子,掏大粪,深翻地,精耕细作。由于担心麻雀吃了影响产量还日夜守护。1960年按收成折算一亩地也才收了700多斤。刘子正自己在党校辟地种麦,虽精心耕作,科学管理,保证水肥,也只打了近700斤。他如实对彭德怀汇报说:“看来,一亩地产700多斤,比较靠谱。”刘子正用事实表态,委婉地支持了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做法。
认真学习 严以剖己

1960年,中央指示全党高级干部都要批判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三版)。中央党校党委从2月25日到7月12日,用近5个月的时间连续学习讨论了20多次,彭德怀每次都参加,从不缺席。1960年10月至12月,彭德怀还参加了校党委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讨论会,连续28次。每次他都积极到会,踊跃发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有一次谈到物质利益问题时,彭德怀说:“苏联搞物质利益太过分了,我们一点儿不讲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在11月的一次讨论会上,彭总联系实际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表现出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政治魄力。他说:“左”和右,其实质都会破坏革命成果。“左”超过现实,右是落后现实。纠“左”纠右都不容易,“左”不是无产阶级的正常情况。
另一次,彭德怀同党校一名教员谈到反“左”反右问题时,说:“庐山会议,由于集中力量反右,所以掩盖了一些‘左’的错误。刮‘共产风’,对生产力破坏极大。有些干部,明知不对也不敢说话,右倾帽子太大,吓死人。”他还联系到历史上的减租减息问题说:“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提出的,在解放战争中就出现了有钱的人不往外借,需要的人又借不到钱。历史时期不同了,同样的政策就行不通了。”
彭德怀从大局出发,严格解剖自己。他曾几次主动地向党校的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他说:我现在认识到,我这个人迟早要犯错误的,不犯错误才奇怪,因为我参加革命,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参加革命前,在我的思想上,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的思想,而且还有法国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为了统一中国,统一中国是我强烈的愿望。但是如何才能求得真正统一,我是不清楚的。我没有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前,我也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根本改造,仍然用旧观点和旧经验看待新事物。他又说:在旧军队时,我一不搞女人,二不搞钱。我搞政治,别人要搞我,都没有把我搞倒,于是,我产生了自信心,把这种自信心带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错误的。这种自信心带有盲目性。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十二条”)。彭德怀表示:“这个指示很好,很重要,应该好好贯彻。”他还说:“十二条”,最好再加一条,大队干部应该民主选举。根据过去经验证明,由群众自己选出来的人是最可靠的。1962年2月春节时,伍辉文、刘子正去看望彭德怀,又听他说:“自从整社‘十二条’下来后,我的情况改变了。庐山会议时,我只看到‘左’没有看到右。如果没有我的那封信,中央对‘左’的现象也许纠正得会更快,想到这一点,使我觉得惭愧。”1961年3月,伍辉文、刘子正等人去看他时,他正在摘录庐山会议的简报。谈起庐山会议时,他说:“22号前是一个方针,22号以后情况就复杂了。我写的那封信,起了一个很坏的作用,使一部分‘左’的问题得不到纠正。这是我感到痛心的。”
出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彭德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基于对人民利益的负责,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61年上半年,彭德怀学习政治经济学,在联系实际讨论时说:“说我对计委提意见是有野心,那倒联系不上。斯大林过去说过,苏联五年计划工农业产值争取每年最低限度递增14%~15%。我们一年要翻一番,我看达不到。两年,甚至三年翻一番就不错了。”在谈到经济发展的计划性时,他说:“大搞群众运动是对的,但是不能因为一提意见,就随便改变安排,结果计划是一回事,安排又是一回事。采取遍地开花,小型的可以,整个国家生产计划就不能那样。五八年7000万人上山就影响农业,也影响工业。五八年钢的数量不少,质量不行。轻的,薄的,硬的,厚的,我们都不能解决。钢铁质量不好,发展尖端科学也困难。”
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彭德怀说:“这是斯大林晚年的著作。他搞了那么多年,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个平衡问题,不过叫有计划按比例更科学更严密。”他还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话不错。但是不能总让它不平衡,具体工作应该设法克服不平衡。工业生产各部门联系很紧密,和打仗不一样,和土改也不一样,打歼灭战行不行得通?”他几次提到,庐山会议时计委有位同志(指贾拓夫)写过一篇关于计划工作中几个方面的比例关系的材料。他说:“当时这个材料被认为是错误的,没有人看。我认为那个材料很好,现在觉得那个材料还是不错的。”
1961年,彭总在看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的党史讲稿后说:“毛泽东同志领导民主革命这一段是正确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正确的,就是五八年急了一点儿,快了一点儿。人民公社可不可以重点试办?普遍办我看晚一两年,甚至二三年也可以。”

据伍辉文回忆,他去看彭德怀的次数比较多,与彭总谈话、接近比较随便,在接触中深感彭总为人正直,态度诚恳,心地开阔,始终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们见面时,伍辉文主要是听彭总谈。彭总经常自省地说:庐山会议,我那封信起了不好的作用,本来庐山会议是准备纠“左”的,因为我的信,就反右了。我的信影响了及时纠正当时实际存在的“左”的错误。与此同时,他也有压抑不住的心理抗辩,经常说有两个问题想不通:一是说他“有野心,反对毛主席”。彭总说:我只是有些问题与主席有些不同看法,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二是说他“里通外国”。彭总说:我对苏联很有看法,在石油问题上苏联卡我们,那时我们每年能搞到600万吨油,日子就好过一些。
心系人民 惜民疾苦
彭德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只想做一点儿有利于人民的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被当作反面教材受到批判。会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今后有害于人民的事,我一定不做。”当时他还有一句没有写出来的话,那就是“如果我还能做些有利于人民的事的话,我愿意尽力去做”。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多次向党校的领导流露并要求向中央反映,让他到生产大队去劳动和工作。他说:“我干不了一天,就干半天,现在国内外事情这样多,大家那样忙,我这算什么?”“我还有劳动习惯,到大队参加劳动,每天挣五分(工分),自食其力,否则成了高薪阶层。”“老当寄生虫不是办法,尸位素餐,心中惭愧。”彭德怀很想到农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在一个支部做些工作,搞一些调查研究,有什么问题就向中央反映。彭德怀说:“如果中央不同意,还要我在这里,那就把我这里所有的人员撤去,汽车也可以交出去,留下一个看门的和三间房就行了。我自己能劳动,现在有秘书,一个警卫班,炊事员,司机,看门的,人很多余,浪费很大。”他经常表示,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总要做有利于人民和有利于社会的事,决不做寄生虫。
彭德怀在挂甲屯吴家花园期间,关心群众疾苦,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经常与附近群众交谈,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他们稻子收成如何,工分挣了多少,工分值多少,生活有无困难,等等。他有时约生产队干部到自己家里聊天,请他们看电视。当有的基层干部向他表示不愿意当干部时,他尽力做工作,勉励他们好好干。附近农民家里的老人死了,他亲自到灵前吊唁。农民家里有病人,他用自己的汽车去接医生。他还花了五六百元买电线杆、电表、电线,让15户邻居安上了电灯。
由于彭德怀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成年人都亲热地称他为“彭总”,小孩们都叫他“彭爷爷”。多少年过去后,吴家花园周围的群众,一提起他,仍感念不已。
接触社会 实地考察
彭德怀一直想走入社会,实地看看,了解一些基层的情况,修正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1961年10月底或11月初,他想到湖南老家走走。在此之前,他不止一次地同伍辉文等人谈过。他说:老待在这里当寄生虫不是个办法,想向中央提个要求到下边去,到公社,到生产队去看看。他打算先到湖南,再到太行山老根据地看看。他说:我还可以参加些劳动,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老吃闲饭不是个办法。彭总的想法,几经报告,获得中央的允准。在他动身去湖南时,伍辉文、杨志、范若愚等人去送行。他们先到吴家花园,警卫员说彭总已经走了。他们又急忙赶到火车站。彭总已经上了火车,见他们到来,就从车厢里出来,对他们说:我今天准备走了。这次在党校学习了快两年了,也读了些书。现在想下去走走,到湖南老家看看,到老根据地看看,一方面可以参加些劳动,一方面作些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些情况,供中央参考。
彭总去湖南不到两个月,回到北京后给伍辉文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他到湖南了解了一些情况,准备向党校党委汇报一下。第二天,伍辉文、杨志就专门去看望彭总。彭总说:“农村的情况有些好转,但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苦,吃的不够,有些东西也不好买。”彭总还说:“我在那里的生活还可以,嫂子养了些鸡,每天给我两个鸡蛋吃。”彭总问:“你们以前去过湖南没有?”伍辉文说:“我去过。”彭总接着说:“你们看到的湖南的杉树林、竹林,现在都给砍光了。树林、竹林的恢复,恐怕不是三五年的问题,三五年恢复不了。有些问题我已向中央反映了。”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的一段发言,对彭德怀的触动比较大。他原来准备到太行山也作些调查研究,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表示,现在不能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仍觉得时不相宜,说:“我不愿现在下去,因为现在正是整社期间。去了说话不好,不说话也不好。下去可能会遇到同情的人,当然这部分人很少,但是哪怕是千分之一的可能,我也应该避免。”
无比钦敬 永为楷模
刘子正在联系和照料彭德怀的岁月里,竭诚尽心。他知道彭德怀并不需要生活照料,而需要在心理和情绪上的慰藉,应帮助其排解政治上的郁闷和心绪上的孤独。其间,杨献珍也受到了批判,被康生污蔑为与彭德怀“一个山上,一个山下”遥相呼应反对“大跃进”运动,因而不便去看望和接触彭德怀。但是,杨献珍对刘子正谈到的一些观点及其流露出的真情实意,常由刘子正与彭德怀畅聊时有意无意地表达出来。可以说,杨献珍和彭德怀两人之间,由刘子正代其互通款曲。如果说伍辉文等人去看望彭德怀是代表党校组织,刘子正则更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说话内容更为宽泛和自由。刘子正切身感受到彭德怀人品的高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事实的尊重,对追求真理的执著,对人民的关心,对党的热爱,称他是一位纯粹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对他由衷地钦敬。彭德怀待人真诚,通过接触,对于刘子正对他“亦师亦友亦尊长”的态度,颇有信任感。他们交流无戒忌,如亲朋之信任,如师友之真诚,如同志之崇高。刘子正将彭德怀品格作为终生的学习目标。
1964年1月,刘子正调离中央党校,南下杭州前,特意去彭德怀处辞行。刘子正把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话:“永远学习彭总坚持实事求是、维护真理的精神。”“文化大革命”中,刘子正自身难保,但当他听到彭德怀惨遭迫害,最后含冤去世的消息时,悲情难抑,长叹一声:“历史将还他以清白!”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子正才如释重负地说:“老革命终于可以平反昭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