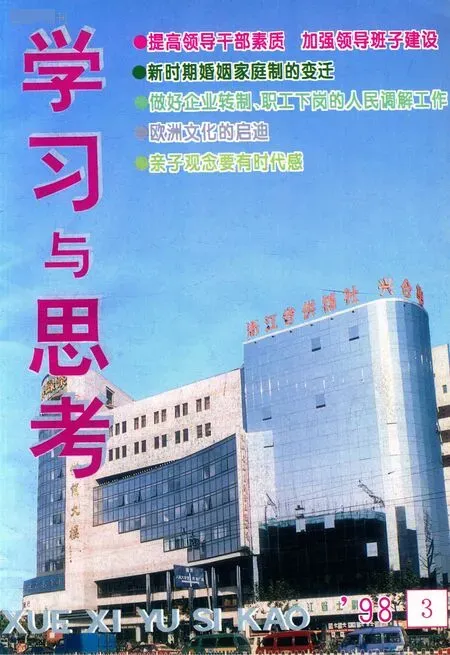关于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入刑的思考
□ 易 万
在我国,公款吃喝的奢侈浪费现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顽疾,公众早已对此怨声载道,但又无可奈何。在我们这个将浪费视为是极大犯罪的国度,当人们面对触目惊心的“餐桌上的浪费”时不免痛心疾首、咬牙切齿,并不约而同呼吁严惩浪费之人。在中央三番五次下发文件禁止公款吃喝仍禁而不止的前提下,更有人建议将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入刑。在几年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他认为“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此外,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认为“浪费不但可耻更是犯罪”,并呼吁应将浪费当成犯罪来限制。社会上其他不少有识之士也认为,要想有效遏制变本加厉的公款吃喝挥霍浪费现象就必须施以重拳。
对那些拿公款吃喝的“硕鼠”,当然不能仅依靠其个体的自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更需要从制度上对他们加以约束。将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纳入刑法的归置范围也绝非无稽之谈,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我国《宪法》第12条和第14条分别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了其目的是“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由此可见,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是为我国法律所不容的。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理论,犯罪应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即严重的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罚当罚性。其中,严重危害性是具有决定作用的犯罪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都是从这一本质特征中派生出来并由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这也就是说,首先因为对社会形成了危害并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刑事法律规范才将其规定为犯罪并设立相应的刑罚处罚。①苏惠渔:《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而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恰恰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如果贪污五千元就会锒铛入狱,而挥霍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公款的“硕鼠”却可高枕无忧,这又怎能捍卫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法律对他们的无动于衷只会使挥霍公款之人更加肆意妄为。因此,我国有必要对拿公款吃喝挥霍浪费之人施以刑事制裁,以强化法律对该行为的威慑。
虽然,笔者认同通过刑事制裁的方式以约束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但是笔者对设立“挥霍浪费罪”的观点有所保留,因为这些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在本质上就是贪污,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故没有必要浪费立法资源增设“挥霍浪费罪”,而只需运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解释为贪污罪的其中一种行为方式即可。
我国的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贪污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本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为故意。本罪的定罪起点数额为人民币五千元。
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侵犯的客体与贪污罪均无太大差别,都是既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又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此外,该行为的主体也应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故不涉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因为一个普通百姓糟蹋自己的钱财只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无法上升到刑事制裁的程度。而官员以公款吃喝,为其买单的则是纳税人的钱财。在主观方面,该行为也是故意,即明知肆意挥霍浪费国家财产吃喝是超出合理标准或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却仍故意为之。
对于贪污罪的客观行为,虽然根据人们对“侵吞、窃取、骗取”的一般理解并不包含挥霍浪费公款的行为,但是对此可以运用刑法解释学上的扩大解释,将“侵吞”解释为包含挥霍浪费公款在内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允许扩大解释,禁止类推解释”。扩大解释是依据刑法的立法精神,将刑法规定中所使用的词语的含义扩大到较字面含义为广,以阐明刑法规定真实含义的解释。这种解释方法,仍然以条文为依据,并未脱离刑法条文的立法精神范围。而类推解释,是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援用关于同它相类似的事项进行法律解释。①郑泽善:《刑法总论争议问题比较研究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页。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本质上就是对公共财产的侵占,只不过在形式上是先将公共财产转化成了山珍海味、高档烟酒等具体之物,然后他们再以吃喝玩乐的方式进行自我享用。将侵吞公共财物的行为扩大解释为挥霍浪费公款,并没有超出该词语可能包含的意思范围,而且也符合贪污罪的立法精神。故将“侵吞”扩大解释为包含挥霍浪费公款在内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事实上,将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认定为贪污罪的做法在审判实践中早已有所体现。2009年10月,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岱山县高亭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傅平洪时,对他用公款为自己吃喝玩乐埋单的44万余元,也全额认定为贪污款。②洪信良:《“挥霍浪费罪”?搞笑》,《钱江晚报》2009年11月23日,第A16版。
对于该行为定罪起点数额的界定应当慎之又慎。要想有效遏制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虽要动用刑事手段,但又不能过于冒进,否则可能矫枉过正、适得其反。基于我国国情,国家工作人员在日常公务中公款吃喝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也不乏必要开支与合理开支,因此在界定该行为定罪起点数额之前,首先应明确必要、合理开支与挥霍浪费的区别。笔者建议可以从必要性和关联性这两个方面来界定某项公款吃喝支出究竟是属于必要、合理开支还是挥霍浪费。必要性是指公务活动必然产生的开支且以必要为限,若一项开支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则不符合必要性的要求。因此必要性的根本要求是首先要做到不上高档菜肴和杜绝高档烟酒以避免奢侈,其次要做到点多少吃多少以避免浪费。关联性是指公务活动的开支应与其行政目的相关联,若与公务活动目的关系不大或根本不相关的开支就不具备关联性。例如,有些单位借公务用餐之名在用餐结束之后赠送礼品或发购物卡给与会人员,这些借公务用餐之名开销的礼品和购物卡就与用餐的目的不具备关联性。若一项公款吃喝的开支不具备必要性或关联性就应认定为挥霍浪费。
对挥霍浪费行为具体定罪起点数额的界定应与贪污罪的定罪起点数额相衔接,但又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挥霍浪费公款数额虽然不大但情节严重的情形。我国贪污罪的定罪起点数额为人民币五千元,鉴于挥霍浪费行为在本质上与贪污罪具有相同属性,故建议将该行为的定罪起点数额也确定为人民币五千元。但这并不意味着挥霍浪费公款不足人民币五千元的人都可逍遥法外。那些挥霍浪费公款虽不足人民币五千元但情节严重的人,因其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仍应受到刑事制裁。笔者认为可将以下几种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视为情节严重:多次挥霍浪费公款的,挥霍浪费的公款为救灾款、救济款、扶贫款等特定款项,因挥霍浪费行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这样既保证了法律的统一性又可避免留下法律漏洞。
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行为有着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近几年中央连续出台多个文件仍无法有效遏制这类现象的情况下,以贪污罪惩处这类行为的方式或许能为彻底根除这类现象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思路。然而,从根本上说,彻底杜绝公款挥霍现象除了加大制裁力度,还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健全的公务接待制度、财政预算决算制度和有效的监管制度等方面多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