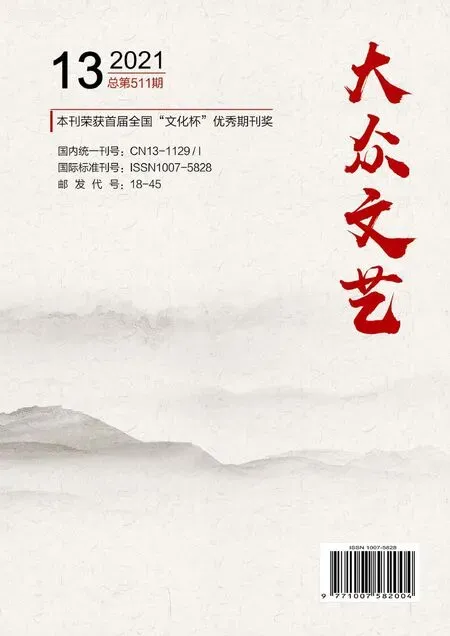昭觉彝族服饰纹样的生成
张 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馆 重庆 404100)
凉山彝族地区是中国珍稀的文化化石标本栖息地,其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服饰纹样记录着昭觉的地理人文。研究昭觉彝族服饰纹样的产生土壤的各个因素,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对彝族文化有更为全面和透彻的了解,再者,对具体设计理念灵感的启发也必须以此为起点。
然而,空洞的大背景罗列不能直观和有针对性地解答问题,下面笔者就从现存纹样标本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简练孤独的舞者:彝族服饰与地理自然关联
凉山彝族地区地处高山耸立、地形复杂的西南蜀地。山川与外界相隔,交通闭塞,因此形成了彝族分散居住、支系庞杂的生存状态。彝族聚居的凉山州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干湿迥异,加之高山地形的海拔差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显著。在中国西南一隅,彝族的舞者孤独而纯真,服饰是肢体的伴奏和心灵的吟唱。自然环境和生产劳作的影响是彝族服饰纹样能够时代传承的重要因素。彝族的不同时代的人之间受环境制约的稳定因素使由功能衍生出的文化审美和心理倾向有了相似的经验支撑。举例来说,由于彝族人长期从事农牧业,服装上很多服饰和纹样都与动植物有关,那些花草虫兽是养活着彝族世代人的共同的物质根基,那种心理倾向自然可以共通、流传。
二、心灵彼岸的憧憬:昭觉服饰纹样与原始的崇拜
古老原始的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各个地区和不同时期的人都有着相似的崇拜模式:对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灵魂不灭的笃信、对彼岸世界的模糊向往。与成熟的宗教信仰不同,原始的崇拜没有固定的人格化形象,反而自然中的万物皆可寄情。宽泛流动的各种实体中,往往像火、水等。总体来讲,凉山彝族宗教观念以祖先崇拜为核心,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物崇拜为一体,影响着彝族人的生产生活,并制约诸多的民俗现象。凉山彝族的宗教信仰至今仍然处于原始朴素阶段,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处于主导地位。虽然有宗教活动的程式化仪式,却没有统一的宗教。
三、乡土世俗的浸润:服饰纹样与彝族生活
彝族人将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的元素进行抽象,因而获得了符号化的信仰对象。
因为火将生食烤为熟食,让黑夜点亮光明,于是他们便崇尚火。他们将火和火镶绣于服装上。在他们心中,火镰就是火的象征,能够给人类带来温暖,是任何事物无法取代的。在服装上对应有大量的火纹、火镰纹以及喜爱红色装饰。因为万物有灵的信仰,在生活中崇拜的鸡、马、羊、虎等动物都纷纷出现在服饰的绣片上。凉山彝族服饰亦体现了对雄鸡的崇拜,事实上,这种崇拜来源于对鸟的理想化解读,彝人认为雄鸡是最有智慧的禽鸟,人们崇拜雄鸡是认为雄鸡是光明和正义的象征正义力量的代表。能战胜邪恶势力,能驱魔避邪,能以光明代替黑暗,因此他们在服饰上绣大量的鸡冠纹。当地的幼儿都戴有鸡冠帽.父母通过给孩子戴上鸡冠帽的方式,以祈求孩子美好的将来。除此之外,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托、昭觉等地的女子服饰上绣有大量的羊角纹,这体现了凉山彝族对羊的崇拜,其根源在于凉山彝族的远古先民是甘青高原的以羊图腾的游牧民族。凉山彝族长期以来处于半耕半牧文化,羊是凉山彝族人民的衣食来源.在其万物有灵的宗教崇拜中,羊也是其崇拜的对象。此外凉山彝族服饰上的马牙纹、牛眼纹等体现了也凉山彝族人们对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动物的崇拜。
在彝族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他们还创造了富有鲜明特色的民居习俗。他们的居住环境与建筑与凉山的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凉山彝族民居的建筑有一种有趣的分类:即是按照屋顶的防水用料上分,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便是瓦板房。防水的屋顶用一种木板铺盖而成,从远处看,这种架设在房顶上自然形成错落有致的多角几何形最终定格为黑色布底上的一道道瓦楞形纹样。
四、视觉符号的博弈:世俗权力与纹样的符号象征
在已有的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元朝统治者建立了土官制度,也被称之为土司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在元朝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在元朝,对土司的任命逐渐形成制度,朝廷赏赐给土司的印章、虎符等信物,以及对土司承袭、外迁、惩罚都有了相应的规定。土司对政府还承担一定的朝贡和纳赋义务。
土司制度作为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元朝中央对凉山彝族的统一方面有显著成效,四分五裂的部落社会被顺利的纳入中央统一集权的管理之下。明代作为土司制度分水岭,这一制度受到各方挑战后逐渐走向衰落。
实际上,最初他们作为祖先崇拜仪式的祭司,虽然对“毕”“摩”存在几种不同的解释,但在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认为他们的主要职能是赞颂经文,祭拜祖先,掌握天命神权。毕摩在彝族社会中虽然是极为重要的社会阶层,从服饰纹样上却没有像土司那样有具体的对应显现。然而,我们通过昭觉地区与云贵两地毕摩受汉族等其他文化的影响程度比较可以帮助理解昭觉地区服饰纹样所处的较为封闭的文化语料库。现在在彝族北方方言区,语言仍可作为区分各种文化样式的参照系和区分标志。毕摩文献占了这一地区彝文文献的很大一部分。断续的偶然性的儒道佛、天主等宗教传入和政治制度(解放前)沿革都未能对毕摩文化造成根本性的颠覆和冲击。外来文化的一厢情愿的独奏没有引起昭觉人的共鸣。
所以,毕摩文化的重要性远胜过有直接对应纹样的土司制度。因为这是与彝族人始终共生的祖先流传下来的原生态文化使者。在毕摩黑色服饰与其它花哨纹样不同:具有一种承载文化底蕴的自信和朴素。
小结
昭觉彝族人是大自然的子民,是火的子孙,神圣的日月星辰、山河虫鱼被他们珍视崇仰。世俗的纷争打破了众多少数民族自足的藩篱,让各民族的面貌变成统一的程式化,却未能让彝族人的血脉、信仰、文化、服饰失去民族的魂魄。正是上述分析的种种因素,给我们今天的设计留存了珍贵的文化和视觉财产。每种纹样都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化载体,在彝族自足的文化语境中传播。
[1]张作哈,朱德齐主编.《凉山彝族民间美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2]易谋远著.《彝族史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
[3]四川省昭觉县志编撰委员会编著.《昭觉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4]阿余木呷著.《中国·彝族民间经典传说故事画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