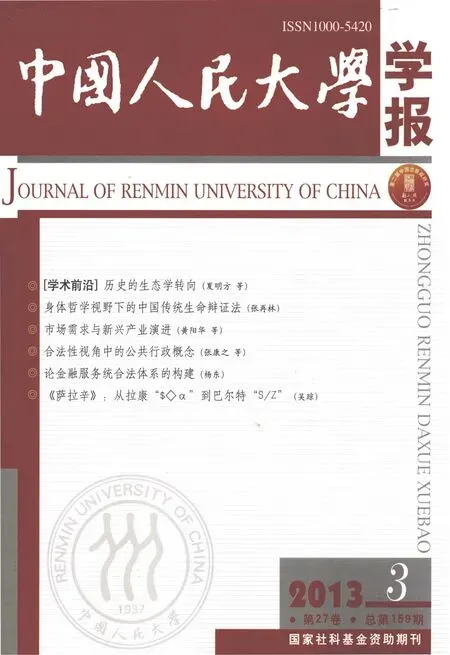身体哲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生命辩证法——兼论中西辩证法
张再林
一、身体:中国哲学的新视野
就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如果说早期的现代哲学的关注焦点是由认识论哲学到语言哲学,从而导致了人类哲学范式的理论更新的话,那么,近期的现代哲学的关注焦点则是由思辨世界到生活世界,从而实现了人类哲学范式的根本性的理论转向,即所谓的世俗化转向。在哲学世俗化转向这一大背景下,作为这种大背景的依托的我们自身的 “身体”视野的开显,就不能不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而又极其重要的维度。我们看到,一方面,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之维的研究,主要是从自我与身体、心理活动与情绪、古典医学与身体、工夫与身体、精神、身体、国体等向度,以希腊传统、哲学与宗教理论等为背景并受比较哲学与神学的启发,把古典中国的身体观念与西方观念对照,探究古典中国的理想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够得到证成。另一方面, “身体”进入华文学界研究者的视野,当以杜维明先生提出的 “体知”思想为其先声,以杨儒宾先生提出的 “气化”的身体观点为其后续。此后,华文学界的身体研究主要沿着身体观 (包括医学的身体、人文的身体、修养的身体)和身体感两个取向进行。比较而言,身体感比起身体观则是以更深入、更细致的方式探讨身体及其形式和内容。
如果说上述研究从各个方面为我们凸显了身体在中国思想中的重要性的话,那么,笔者近些年所做的工作,则是在此基础上对身体进行一种所谓的 “现象学的还原”,进一步把身体提升到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也就是说,笔者认为,有别于西方传统的那种意识性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并且唯有将中国传统哲学定位于身体性哲学,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哲学之何以从根本上迥异于西方哲学而二者有云泥之别,我们才能明悟中国哲学理论形态之独特而其所以是中国式的。这意味着,在中国哲学中,身不仅以其 “亲己之切,无重于身” (萧统语)的性质体现为我们每一个人亲切可感的血肉形身,也一体两面地体现为一种业已彻底本体化和超验化的所谓 “道身”,其以一种本体即显体的形式,已无所不在地泛化和体现在世界的一切领域之中,从中不仅为我们生发出发端于 《易经》的中国古人根身的宇宙论,还有滥觞于 《周礼》的古人根身的伦理学和基于 “天祖合一”的古人根身的宗教观。同时,这种中国哲学的身体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哲学的所有领域里,也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以至于可以说,一部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身体哲学的发展史。《尚书》提出 “天之历数在汝躬 (身)”, 《周易》提出“近取诸身”、“安身而后动”,《周礼》提出 “反求诸其身”,《论语》提出 “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提出 “反身而诚”,如此等等,均为我们表明了早期中国古代哲学以身为本的致学传统。诚然,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外来佛学的影响,由于饱受佛学思想浸淫的宋明理学的出现,使中国传统哲学开始打上了一定的思辨哲学的烙印,使中国哲学似乎一反初衷地背离了其原有的身本主义传统,如程朱的 “理本论”思想的推出、在理欲之辨名下的理学的 “中国式原罪说”的兴起,恰恰反映了这一新的取向特征。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这种背离充其量仅仅是其整个发展历程中的一段插曲,是对传统否定之否定中的一个环节,故继宋明理学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明末清初 “后理学”思潮的崛起,是身本主义的重新勃兴,以及对中国传统身道的物极必反的再次肯定。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所谓 “身道不二”的思想的崛起、王夫之所谓 “即身而道在”的命题的推出即为明证。因此,整个中国哲学的历史,就是循着先秦哲学 “身体的挺立”到宋明哲学 “身体的隐退”,再到明末清初哲学 “身体的回归”这一理路来演进、实现和完成的。而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一 “反复其道”的历史再次雄辩地表明,唯有身体而非意识,才是中国哲学中不可易移的本有之有和颠扑不破的终极性设定。
除了把中国传统哲学定位为身体性哲学之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还尝试性地为该哲学破译出一种有别于西方哲学范式的全新的哲学范式,一种 “身体→两性→家族”的中国式的哲学范式,而非 “意识→范畴→宇宙”的西方式的哲学范式。从这种不无生态化的范式出发,笔者认为,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坚持一种 “反思”的取向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坚持一种 “反身”的取向;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具有一种 “祛性”的特性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具有一种“尊性”的特性;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以 “还原论”或“整体论”为其原则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是以 “家族论”为其原则。[1]基于这种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范式,我们将从中国哲学的一般性理论进一步地深入到辩证法理论。我们的研究将表明,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不仅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思维辩证法的所谓的生命辩证法,而且这种生命辩证法的特征亦与中国身体性哲学的特征一一相应,并由此体现出中国哲学世界观与其方法论二者之间高度的一致性。
二、中国传统生命辩证法的三个特征
一种教科书式的说法似乎约定成俗地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即:中国传统的辩证法 (也即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以其始终未脱认识上的原始蒙昧而仅停留在一种所谓的朴素的辩证法。其实,这完全是对中国传统的辩证法的一种浅尝辄止的并不可原谅的误读。它不明白,和西方传统的辩证法一样,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同样具有不无成熟的理论形态,同样是一种经由哲人深思熟虑、经由哲人不断反思不断淬炼的思想产物。所不同的是,如果说西方传统的辩证法可概括为纯思性、正反型、总体论三个理论特征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则以涉身性、阴阳型、全子论这三个完全不同的理论特征与之相应。
(一)涉身性
西方传统的辩证法的第一个理论特征可概括为纯思性。怀特海称,一部西方哲学的历史,不过就是一部之于柏拉图学说的脚注的历史。这一看法,不仅对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论成立,对黑格尔的西方式的辩证法的理论也同样成立。正如柏拉图的整个哲学是建立在纯思的理念基础上那样,黑格尔的辩证法亦未脱 “思辨的原罪”,而具有极其鲜明的纯思性的特点。在黑格尔那里,其辩证法的纯思性是如此的彻底,该辩证法既始于思维的理念又终于思维的理念,以致对于这种辩证法来说,世间的一切矛盾、一切对立,都可以在 “思想王国”、“观念王国”里既得以展开,又得以迎刃而解。与这种纯思的极度膜拜相对应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坚持自然界中没有任何新事物,自然界中仅有对象和现象的简单循环这一观点。对于黑格尔来说,理念虽必须假道自然才能反思自己,但自然就其作为那种既不纯粹又惰性十足的 “坏的感性”而言,它却充其量不过是供奉圣洁而万能的理念之神的一具牺牲,而使自身最终与高贵的辩证法的品质无缘。
有别于西方辩证法的纯思性的中国辩证法的涉身性,则可视为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至为突出也至为根本的特征,并由此出发使中西辩证法貌为相似,实却判然有别、泾渭分明。
这种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涉身性首先表现在,正如其辩证法真正滥觞的中医理论以及该理论的辨证施治的主旨所集中表明的那样,与西方传统辩证法不同,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并非始于对人头脑的思想谬误的纠正,而是始于对人自身的身体的疾病的对治,其辩证法大师与其说是为人启迪智慧的智者,不如说是使人药到病除、使人起死回生的医生。故就其理论的初衷而言,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与其说是知识论的,不如说是治疗学的,而使自身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极其切身的生命关怀的鲜明烙印。医、易相通,中医理论是如此, 《周易》理论亦不例外。作为中国古代辩证法又一 “圣经”的 《易经》更多关注的,不是在一个“意见”纷争的观念世界里,我们如何使自己的思想拨乱反正、去伪求真,如何使自己的思想趋向绝对的真理,而是在一个险象环生、风险重重的现实世界中,我们如何使自己切身的生命转危为安、救亡图存,如何 “安身”、 “存身”、“获身”以及不断完善自身的 “修身”,还有那种如何使自身生命自强不息的 “大生”、如何使自身生命日富日繁的 “广生”。无独有偶,这种极其切身的生命关怀的思想同样也体现在中国古代另一部辩证法的巨著 《老子》中。 《老子》之所以煞费苦心地告诉我们应如何 “无为而为”、如何 “致虚守静”、如何 “持满戒盈”、如何 “敛迹藏锋”,显然,这一切并非是为了洞悉宇宙本身的真谛,而是旨在使我们自身生命的 “长生久视之道”得以明喻。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古人的所谓 “黄”、“老”并称之真正隐秘。因为,老子所不厌其烦地大谈的所谓 “道”,实际上不外乎就是黄帝这位一代圣医的那种 “休养生息”之道而已。
因此,这种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虽如西方传统的辩证法一样都讲所谓的 “辩证”(辨证),但此“证”并非彼 “证”。如果说西方传统的辩证法所谓 “辩证”的 “证”,是指通过语言 (思想)的“辩论”而获取的抽象概念的证据之 “证”的话,那么,中国传统辩证法所谓 “辨证”的 “证”,则是指与中医显微无间的所谓 “藏象”学说一致,根据望闻问切所得来的具体的身体体证之“证”,具体的 “生命征候学”之 “证”。故中医所谓的 “八纲辨证”,为我们表述的是身体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种体征。同理亦然,《易经》的六十四卦,为我们表述的并非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六十四种概念范畴,而是以一种 “生命符号学”的方式[2](P26),表述的是征候学意义上六十四种生命意向的象征。如 “乾”卦象征着我们自身生命的自强不息, “坤”卦象征着我们自身生命的厚德载物,如此等等。而这种生命征候学意义上的 “辨证”性质在 《老子》的学说中更是表露无遗,它使老子的辩证法更多谈论的不是认识的真伪,而是生命自身的诸如动静、刚柔、强弱、进退、取予、祸福乃至生死这些态势和性征。因此,无论在中医那里,还是在周易、老子那里,其辩证之道已不再是黑格尔式的被概念逻辑彻底风化的一具思想的僵尸,而是以其可被触摸到的体形、体态、体质、体感、体温,而直切我们鲜活的、生动的生命之中。
这一切使源于 “辨证施治”的中国传统的生命辩证法,体现为一种人类最早的 “黑箱式”的理论,使其与其说是指向了合规律性的真理论,不如说是指向了合目的性的控制论,也即指向了一种具有信息信号回馈的,可以自组、自调、自稳的生命系统的理论。同时,也正是由此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与西方传统的辩证法不同,其已不再是流于一种言说和思维的技艺,而是作为一种地地道道的生命的策略、生命的智慧,堪为中国古代实用理性的集中体现、实用理性的核心内容,以至于其不仅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中,也无所不在地体现在中国古代诸如医学、伦理、政治、艺术、兵法等一切现实生活、现实事务的学说之中,以其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性质而成为古人的步入其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必由之径,以其 “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成为古人一切生命践行的普遍准绳。相形之下,西方的那种仅仅停留于坐而论道的辩证法,以其古人所谓的 “玩弄光景”而使自己几近于“儿戏”之论。
(二)阴阳型
西方传统的辩证法的第二个理论特征可概括为正反型。所谓正反型,是指辩证法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均以思想命题的正题和反题这一逻辑对应方式而展开。这种辩证法的正反型的逻辑模型,发端于苏格拉底讨论问题时所运用的反诘法、反问法,为康德的正题、反题之二律背反学说所正式奠定,在黑格尔的学说中,随着一种所谓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模型的推出,标志着其真正走向了理论的自觉和成熟,并最终成为黑格尔构建其整个辩证逻辑学说体系方法论的不二法门。例如,在黑格尔的 《逻辑学》一书中,其“存在论”中有所谓“质”——“量”—— “度”这一正反合,其 “本质论”中有所谓 “本质”——“现象”——“现实”这一正反合,其 “概念论”中有所谓“概念”——“客观概念”——“理念”这一正反合,而 “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这三者,则在一个更大的逻辑范围里同样体现了一种正反合。因此,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所谓的对立统一乃是一种正反合式的对立统一,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所谓的否定之否定乃为一种正反合式的否定之否定。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一种正反型逻辑毋宁说业已成为其辩证逻辑中支配统摄一切的“元逻辑”,它以一种真理 (正题)谬误 (反题)此消彼长、相互颉颃的方式,再次向我们表明,以黑格尔学说为代表的西方式的辩证法,其法则与其说是植根于现实的 “大言大辩”的自然世界,不如说是指向了超现实的 “较真式”的“思想王国”、“观念王国”。
一种中西辩证法的比较不能不使我们发现,如果说西方传统的辩证法以其合题、反题的推出,体现了一种所谓的正反型的辩证法形态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则以其阴性、阳性的推出,使一种所谓的阴阳型的辩证法形态得以真正揭示。而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之所以力推阴、阳,并以之为其理论 “元型”,这不仅由于其认为 “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内经·灵枢·寿夭刚柔》),也即认为人生命的身体形态实涉阴阳二性,还由于其坚持所谓 “阴阳化生”,也即坚持人生命的生成活动同样造端于阴阳二性。那么,为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所极力标举的阴阳,其真正的所指到底是什么呢?一旦我们领悟到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法的涉身性,这一问题的答案就会不揭自明。不难看出,正如中国传统辩证法的 “道”实乃“身道”一样,该辩证法的 “阴阳”实际上也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它不过就是我们自身身体得以发生的雌雄配子之男女两性。无怪乎中国古人提出 “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 (《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至阴生牝,至阳生牡”(《淮南子·坠形》),也无怪乎 《易经》宣称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其不仅将乾阳与男性、坤阴与女性明确地打并归一,还在其爻辞、系辞中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关于性活动的不加掩饰的描绘,以及引起丰富类比联想的暗喻、隐喻。①如 《易经》“咸”卦的爻辞实际上为我们描绘的是男女两性的交感活动,《易经》系辞中所谓的 “乾”之 “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所谓的 “坤”之 “其静也翕,其动也辟”,同样可看做是对性活动的一种描绘。故中国传统的辩证法的 “阴阳”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其生命辩证法法则中的 “性基因”这一生命根据的真正确立,并以其对生命的有性生殖性质的强调,而使自身与西方那种无性克隆的思维辩证法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正如在西方传统的辩证法以正题——反题两一体为元型,为我们构建出辩证的逻辑学的整个体系那样,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以阴性——阳性两一体为元型,使一种辩证的生命学的整个形态得以和盘托出。因此,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中,其生命之辩证不外乎为阴阳之辩证,以至于《黄帝内经》提出 “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以至于医家张景岳提出 “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景岳全书·传忠录》),而使阴阳 “一以贯之”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药理等理论中。这种阴阳的 “一以贯之”也同样体现在 《易经》的生命辩证法中。《易经》不仅谓 “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而且还以阴爻和阳爻两两相交为生命发生之 “几”(机),为我们衍生出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整个生命图式和谱系,以至于在 《周易》那里,阴阳交则泰,阴阳不交则否,以至于在 《周易》那里,阴阳交的从头开始,乃为我们指向了生命的 “物不可穷也”,生命的生生不已的 “未济”,阴阳交的最终穷尽,一如 《内经》提出 “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那样,则标志着生命的 “终止则乱,其道穷也”,生命的寿终正寝的“既济”。
值得注意的是, “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史记·外戚世家》)。一如司马迁为我们指出的那样,这种阴阳的生命辩证,不仅可以 “近取诸身”地体现在我们自身的身体中,乃至在古人看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仅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如同中医理论所阐明的那样,实际上都是 “雌雄同体”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也如同“(阴)魂”、“(阳)魄”两词所指出的那样,亦之于男性与女性兼而有之。与此同时,这种阴阳的生命辩证,还可以以一种 “依形躯起念”的“根身现象学”的方式,进而体现在植根于我们自身身体的人的行为、人类社会活动乃至自然现象之中,乃至在古人那里,世间的一切东西都被泛性化了,都具有阴禀阳受的属性,都遵循着“一阴一阳”、 “一屈一伸”之道的规定。这样,在古人眼里,人的行为有阴阳,它表现为人的行为中动静、取予、进退等等的对立统一性;人类社会有阴阳,它表现为人类社会中进步与保守、兴盛与衰败、战争与和平的此消彼长;自然界亦有阴阳,由此才有了乾天坤地、日月相推、寒暑更替以及五行之相生相克这些自然的形态和运动。因此,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既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深度生态学意义上的世界,又由于 “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这一观点的推出,在使我们从深度生态学的世界走向性别生态学的世界的同时,在为世界植入 “双螺旋式”的性基因的同时,使 “太阳男神”和 “月亮女神”双双成为该世界的上帝。
(三)全子论
西方传统的辩证法的第三个理论特征可概括为总体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思想命题的正反合是其核心,但并非它的全部,它的全部乃是该核心通过各个范畴之相互联系、过渡而全面展开的整个过程,亦即黑格尔所谓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然而,由于黑格尔把这种否定之否定不是看做事物自身不断的否定,而是看做理念经由对自身的否定再次回到理念的过程,这就使他的否定之否定不是更多地体现出新生事物的独特性、丰富性,而是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绝对理念的理论自洽自圆,一种绝对理念的无所不包、无往不克的 “大一统”;这就使黑格尔的辩证法虽走出了西方传统的分析主义、个体主义的理论误区,但却以其突出的 “终极系统论”的特征,并与普鲁士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体制保持一致,为我们隆重地宣布了一种极其绝对也极其独裁的总体主义新哲学的诞生。在这种总体主义的哲学中,实际上既没有独特的个体的立足之地,又与辩证法所强调的 “批判的、否定的精神”、“革命的代数学”的精神相悖,一反黑格尔曾有的激进的 “反康德主义”初衷,最终将辩证法应有的时间、历史、进化等核心性质判处了死刑。因此,也正是在后一点上,我们看到了现代哲学家罗森茨威格对苏格拉底的批评同样适用于黑格尔。也就是说,他们二人都以一种对预定论哲学最终的理论皈依,使自己与其说是发明辩证法的大师,不如说是埋葬辩证精神的历史罪人。[3](P67)
然而,在中国古代生命辩证法那里,其所谓的 “阴阳化生”之 “生”,也即 《周易》所谓“生生之谓易”的 “生生”之 “生”。也就是说,这种 “生”并非是一次性的、完成式的生命的“生”,而是无限性的、进行式的生命之不断孕育繁衍的 “生”,一种 “形有阴阳,自相匹偶,生生不已”的 “生”,一种代际间的通过父母,由父到子、由子到孙的子子孙孙永无穷匮的 “生”,也即一种在阴阳之间 “动态的互文主义”的“生”。这样,这种 “生生”之 “生”,就使一种所谓的 “上下文之上下文”、所谓的 “场中之场”、所谓的 “背景中之背景”的 “生命格式塔”的生态系统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中国古人所理解的生命辩证运动,实际上为我们指向了一种为《易经》所隐含、为明代思想家罗近溪所明揭的“身向家的生成”的 “家族化的生命巨系统”[4],意味着这种辩证运动既是以 “家”为生命组织的原始的基本 “单位”①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以 “家”为生命组织基本 “单位”的思想,除了可见之于中国人通常的 “家”的概念外,还可见之于汉语中诸如 “自成一家”,诸如 “一家饭馆”、“一家商店”,以及诸如 “女人家”、“孩子家”这类 “家”的表述上。,同时又是 “以家为归”、以 “家”为生命趣向的终极旨归。我们看到,这种 “家”的本位、 “家”的旨归,最终又使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从古代走向了今天,与当代最新的所谓的 “全子论”的理论不期而遇、殊途同归。
基于阿瑟·凯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所创造出的 “全子”或 “子整体” (holons)这一术语,由肯·威尔伯 (Ken Wilber)所系统阐释的所谓的 “全子论”是这样的一种理论:一方面,它不同于传统的分析主义的个体论的理论;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打上黑格尔哲学印记的现代结构主义的整体论,即系统论的理论。后者正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那样,用一种精细的还原论取代粗疏的还原论,坚持绝对整体的 “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而最终使自己沦为生活世界的头号敌人。相反,这种全子论一如普罗提诺所谓 “单一就是全部,全部就是单一”的命题、怀特海所谓 “多成为一,并被一所增益”的命题所示,乃为一种既强调个体又强调整体的部分/整体的理论。[5](P37)无巧不成书的是,这种部分/整体的理论主张同样也体现在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中,并使其自身与以黑格尔学说为代表的绝对的总体主义化的西方传统的辩证法迥然异趣。例如,中医的辩证理论对人体的理解并非是一种或部分或整体或解剖学或功能论的理解,而是在把整个人体理解为一个独立的 “大全息元” (全子)的同时,亦把人体的各个部分同样理解为各个独立的 “小全息元”(全子)。这使中医的辩证理论以其诊断中所谓 “三寸之脉”、“五寸之舌”的提出,以其坚持小局部寓含和浓缩了大整体的思想 (如 《灵枢·五色》篇提出五官含有五脏的信息),不啻可视为人类的 “一叶可以知秋”的生命全息理论之最早的发现。再如,在 《易经》的辩证理论中,正如其整个六十四卦可以被视为一全子式的“生命的巨链”那样,该六十四卦中作为每一链环的每一卦,亦同样可被视为一全子式的自组织的生命单元。这使 《易经》的辩证理论与其说是通向了一种黑格尔式的整体取代个体的总体论理论,不如说是以其 “君子以族类辨物”思想的推出,以其坚持事物可以触类旁通、可以举一反三,而使一种中国式的个体即整体的家族论式的理论范式、系谱学式的理论范式得以真正彰显。
除了以其对整体和部分并重的强调,而使自身与西方传统的和现代的总体论中无视个体的取向划清界限之外,当代全子论理论还由于为 “系统”引入不可逆的时间,由于一种所谓基于全子层级性的“进化的系统论”思想的推出[6](P24),而使自身进一步地与西方传统的和现代的总体论中那种“祛时化”的 “伪历史主义”分道扬镳。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分道扬镳,使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与全子论理论又一次可以结为同道。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之所以有别于西方传统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不仅在于它在整体系统中为我们恢复了部分的个体应有的地位,还在于其以对事物 “生生”之旨的强调,而使自身在肯定系统的历时性的同时,在大力彰显系统的发展和进化之维的同时,彻底告别了那种所谓终极系统的设定这一一成之规。固然,中国哲学以其所谓“无往不复”、“周而复始”、“五德终始”的提出,似乎为我们体现出一种历史循环论的思想,但一如 《易经》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在中国哲学中更多看到的却是日新的进化与原始的复归的儒道互补,是系统开放性与封闭性二者的 “翕辟成变”,是超循环的 “正反馈自生与负反馈自稳往复循环”的一般进化论机制模型,是 “八卦衍生律”所展示的生命之进化的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是系谱学意义上代际生命的相继相生、世代生成。因此,唯有在中国哲学中,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才获得新生。因为,真正的否定之否定,与其说是黑格尔式的向绝对理念一劳永逸的、大团圆式的回归,不如说是一种生命自身既克服又保留、既发展又继承的扬弃活动。
三、中国传统的辩证精神的时代意义
虽然我们无意于厚此薄彼,也无意于否认西方传统的辩证法以其力纠科学主义思维的独尊,而在人类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哲学中所具有的历史和理论上的合理性及重要地位,但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对中西辩证法的比较却不能不使我们承认,中国传统的生命辩证法由于克服了西方传统的思维辩证法的 “思辨的原罪”,由于实现了向现实的鲜活生命的回归,使我们不仅发现了人类的辩证法的思想基础和理论 “原型”,也从中触摸到、洞彻到了该辩证法底蕴的无比深刻和深邃。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日益风靡,人们把辩证法视为形而上学哲学的历史垃圾弃如敝屣的今天,唯有通过对于中国传统的生命辩证法精神的重新发现,才能使人类的辩证法在现代思想形态中再获新机,并以其对百病缠身的人类现代文明的辨证施治,而再展其历久弥新的不朽的理论魅力。
故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辩证精神虽古老但仍有其鲜活的时代意义。在笔者看来,这种时代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的辩证法的涉身性,在使辩证法从思想王国回归到生活世界的同时,也使其从一种抽象玄虚的思辨的真理而落实为一种不无具体切身的生命智慧。无疑,这种智慧不仅可以如同中医理论曾做的那样,从宏观的哲学的高度,使饱受生命之苦的现代人得到身心的关照和治疗,也将如同 《周易》、《老子》、 《孙子兵法》曾做的那样,为进退失据的现代人提供行为取舍的辩证指导。因此,我们相信,随着作为一种生命及其行为法则的中国传统辩证法的重新发现,辩证法将彻底告别其一种思维游戏的诡辩法,而重新回归于古人的那种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庸言庸行之道、那种 “担水劈柴无非妙道”的现实生活之道。
其次,中国传统的辩证法的阴阳型,在使我们认识到 “阴阳化生”乃为生命的原发机制的同时,也使一种生命的 “阴阳和合”的 “和”的法则、而非一种思维的 “同而不和”的 “同”的法则成为一切生命形态固有的真理。显然,在人类迎来生态学的世纪并重建其生态平衡的今天,对这一真理的重新揭示同样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在男性话语一统天下的现代文明中重新恢复女性话语应有的尊严,使人类有可能再建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原生态的、深生态的人间伊甸园,而且还在一个无性克隆、复制式生产主宰一切的世界里,以对现代文明那种 “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的同一性帝制统治的彻底的颠覆,为我们迎来了 “和的世纪”这一人类历史新的纪元。
最后,中国传统的辩证法的全子论思想的理论和时代意义更是显而易见的。它的部分即整体的思想,以一种 “第三条道路”的推出,为消解现代文明中冥顽不化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使自我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成为可能。它的扬弃式的进化系统论的思想,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桥引,使人类这一 “发展的困兽”既可以走出现代主义的 “唯进步论”的误区,又不致误入后现代主义的 “唯回归说”的陷阱,并使我们最终认识到,人类文明的真正选择,既不是一味革故鼎新的不断革命、不断推新,又不是仅仅停留于发掘古尸的 “掘墓”,而是一种一只脚踩在生物层面另一只脚踩在人类层面、另“上下其行”,一种生命既代代相传又日繁日富的 “接生”。[7](P181)
[1] 张再林:《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载 《世界哲学》,2008 (4)。
[2] 张再林:《身体·两性·家庭及其符号》,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3] 张再林:《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张再林:《以家为归——罗近溪哲学主旨再探》,载 《河北学刊》,2013 (1)。
[5][6][7] 肯·威尔伯:《性、生态、灵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