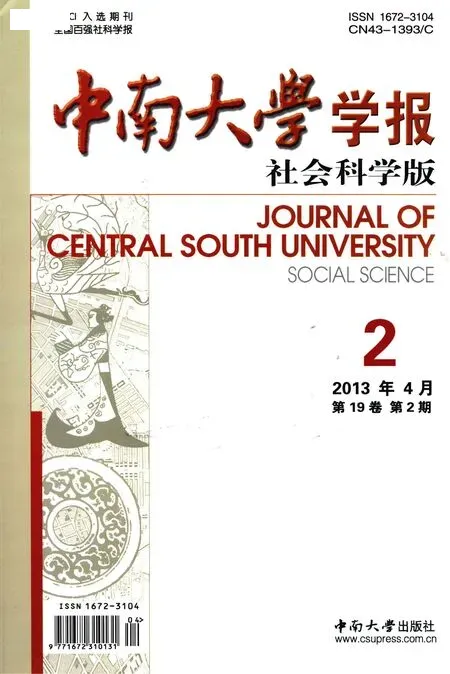目的论的康德历史哲学
李永刚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历史理性批判”能否构成康德的“第四批判”,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康德的确非常关注“历史”,并形成了较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长期以来,康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是被认为在与赫尔德的争论中作为失败的一方而失去了立足之地;或者是被看作黑格尔的先驱而被笼罩在其阴影之下。但从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线索来看,康德正处在思辨历史哲学的独立化过程之中:一方面,他撇开历史现实而完全从哲学上来思考历史,为思辨历史哲学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他对历史的思考服务于他力图沟通自然与自由、知识与道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或者说,他是从道德主体的视角来考察历史的,由此,历史哲学成为了道德形而上学的一部分。正是这种中间地位使得我们要重视康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因为“它们提供的却是康德早已发展了的有关国家与历史本质新概念的全部基础,它们对于德国观念主义的内在发展而言,丝毫也不次于《纯粹理性批判》在其自身领域的至关重要性”。[1]
一、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的普遍史
“历史”对于康德来说就意味着人的历史,即便“自然史”(Naturgeschichte)也是人根据自身的有限理性而对自然起源的追溯,是一门人的学科,而非神的学科。正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为了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能够追溯其起源,就必须引入目的论原则,而对于上帝的无限来说,目的论原则是不必要的。同样,为了理解人类的历史,康德也将目的论原则引入其中,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就是以“终极目的”为依归的人类自身的历史。
自然史以整个自然界为其对象,那么,人类历史的对象是什么呢?康德说:“无论人们在形而上学观点上关于意志自由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意志的显象(Erscheinung,常译作‘现象’,作者注。),即人的行动,毕竟与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都是按照普遍的自然法则被规定的。无论这些显象的原因隐藏有多深,以叙述这些显象为己任的历史仍然可以使人希望:当它宏观地考察人的意志之自由的活动时,它能够揭示这种自由的一种合规则的进程;而且以这种方式,在个别的主体那里杂乱地、没有规则地落入眼底的东西,在整个类那里毕竟将能够被认做其原初禀赋的一种虽然缓慢,但却不断前进的发展。”[2](24)在此,康德把人类历史的研究对象限定为自由意志的现象,即人的行动。这种自由意志的现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与任何自然现象一样服从于普遍的自然法则,因而具有自然科学的合规律性;另一方面,它作为自由意志的现象是“人的意志之自由的活动”,就不仅仅服从自然法则,也要服从自由意志的法则,因而具有道德形而上学的合目的性。正是这种双重性凸显了人类历史的特殊地位,即处于合规律性的自然科学与合目的性的道德形而上学之间,既具有合规律性又具有合目的性,或者说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但这一意义上的“历史”是普遍的人类史,而非个体的人的历史,因为只有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历史才体现了一种“不断前进的发展”,而对于个体来说,历史总是杂乱无章的,充满着偶然性和随意性。
那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人类史呢?康德的人类史并不是以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人类为对象的,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属于自然史,而是关于人类未来的一部预言的历史。关于“预言的人类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预言完全以自然法则为依据,所形成的就是自然的人类史;如果预言并非以已知自然法则(如日食、月食)为依据,就形成了“预卜的但却是自然的”人类史;如果预言以超自然的启示为依据,就构成了“先知的”人类史。但康德认为,预言的人类史并不是以上三种意义上人类史,因为任何观测都需要有恰当的观测点,“但不幸恰恰在于,在涉及对自由行动的预言时,我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置于这个观测点上。因为这会是神意的观测点,它超越了人类的一切智慧,人类智慧也延伸到人的自由行动,但人虽然能够观看它们,却不能准确无疑地预见它们(对神的眼睛来说,这里没有任何差别),因为为了能够预见,人就需要依照自然法则的联系,但就未来的自由行动而言,人却必然缺少这种引导或者指示。”[3](80)这是在历史领域中实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不是从人类的观点,而是从超越于人类之上的“神意”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史,但这种“神意”仅仅是人类观察历史的“引导或者指示”,而非历史本身,如此所形成的“预言的人类史”就既不是自然史也不是神的历史,而就是人类整体自由活动的历史,这就突破了历史决定论,而为了理解这样一种非决定论的人类历史,就必须发挥目的论的作用。
二、目的论视域下的人类普遍史
目的论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目的论原则作为从属于上帝理念的一个“预设”:“这个惟一地基于理性概念之上的最高形式的统一性就是诸物的合乎目的的统一性,而理性的思辨利益使得我们必须把世界的一切安排都视为好像它们是出自一个最高理性的意图似的。就是说,一个这样的原则向我们应用于经验领域的理性展示了按照目的论法则连结世上事物、并由此达到其最大的系统统一性的崭新的前景。”[4](A686−687,B714−715)这就是说,目的论原则是我们理解世界万物的一个原则,它能够把自然万物联接为一个“看似”有着统一目的的整体,以便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但作为一个“调节性原则”,其作用也仅止于此,而无关乎人类的经验性认识。假如把目的论原则作为“构成性原则”而应用于知识领域,就是理性的迷乱。
目的论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有机体,而且整个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论系统,而人类“作为地球上惟一的具有知性、因而具有自己给自己建立任意目的的能力的存在者,……按照其使命来说是自然的最后目的”。[5](286)这里所说的“按照其使命来说”,就是指人类“应当”是自然的“最后目的”,自然的“最后目的”就是指人类的文化和幸福。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充分运用其理性的禀赋,从动物般的野蛮状态向理性指导的文明的进步历程,由此,人类整体始终是在向着善而进步的。虽然这种目的论原则作为一种调节性原则,无助于增加对人类历史的知识,但却是我们从哲学上理解历史的“导线”。
在康德看来,人类历史既不像伏尔泰等乐观的启蒙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帆风顺的进步,也不像卢梭所设想的那样是倒退的堕落,而是在对抗、斗争中的前进历程。康德认为,大自然并没有为我们人类配备强大的动物本能,其使人类的全部理性禀赋得以发展的手段就是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人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偏好,因为他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说,感到自己的自然禀赋的发展。但是,他也有一种使自己个别化(孤立化)的强烈倾向,因为他在自身中也发现了非社会的属性,亦即想仅仅按照自己的心意处置一切,并且因此而到处遇到对抗,就像他从自身得知,他在自己这方面喜欢对抗别人一样。”[2](27−28)人类的这种“非社会的社会性”产生了双重性:一方面,人类通过对抗,唤醒了人的力量,使得人类在荣誉欲、统治欲和占有欲的推动下,迈出了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一步;另一方面,人类本身的社会性又使得人们能够团结成为整体,从而形成民族、国家,以便战胜各种灾祸,延续人类的生存。
大自然是全善的上帝的作品,在其中没有自由,有的只是对自然法则的服从,因而自然的历史是从善开始的;而人类历史则是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作品,人的本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正是这一自由,使得人能够把违背道德法则作为自己的准则,把自爱等动机看作是遵从道德法则的条件,这就造成了人类本性的“根本恶”。因而,人类的历史是从恶开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就永远是恶的,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使得人类不断地由恶向善,因而人类历史是向着善而不断进步的:“有一个命题,不仅用心善良、在实践方面值得推荐,而且不管有多少无信仰者,即便是对于最严格的理论,也是站得住脚的,这就是:人类曾经始终处在向着更善的进步中,今后亦将继续前进。”[3](85−86)
人类历史作为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就是要使人类的理性禀赋充分实现出来,这就需要达成一个“普遍管理法权的公民社会”,它分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两个层次:首先,在国家内部,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种合法的公民宪政”。在这一社会中,由于拥有最大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达到普遍化,同时,公民宪政又能够对个人的自由进行限制,从而避免人类社会成为狼与狼那样的野蛮状态,正是在这种既对立又协作的关系中,社会成员充分地发展自身禀赋,从而促进了人类整体的完善。就像在一片森林中,每一株树都为了争夺更多的空气和阳光而努力向上生长,就迫使其他树木也向努力向上生长,从而导致了整片森林长势良好。社会中,每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的目的而努力发展自己的禀赋,就会迫使其他人也这样做,在这种相互竞争中,整个社会处于良性发展之中。与此相反,在没有竞争的社会中,每个人完全按照其自由发展,就无从改善其根本性的恶,所造成的就是人类整体的堕落,因而“一切装扮人的文化和艺术及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非社会性的果实,非社会性被自身所逼迫而管束自己,并这样通过被迫采用的艺术,来完全地发展自然的胚芽”。[2](29)这是向“世界公民状态”迈进的第一步。
其次,这样一种理想社会有赖于合法的国际关系,即“国际联盟”的建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如同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同样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一方面,由于资源的有限,各国为争夺资源而长期处于竞争、战备,甚至是战争状态;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各国也有相互协作,并且即使是国家间的战争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其目的并不是使人类消亡。各国正是在这种对立与协作中建立起一种国际联盟,建立一部类似于“公民宪法”的“联合起来的意志的法律”,从而使各国取得自身的安全与法权。
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在于人性的根本恶,就在于人类的自爱本性,就在于人类本性的“非社会性”。正是在个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性,充分实现自身的荣誉欲、占有欲和统治欲,在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中,人类的理性禀赋才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使其不至于在一种美满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亚式的田园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从而使得大自然能够实现其隐蔽计划——人类的幸福。
康德强调了战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不管其性质如何,带来的都是灾难与破坏,但也正是战争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如果不是那种总是令人害怕的战争本身迫使国家元首们有这种对人性的尊重,那么会看到这种文化吗?会看到共同体的各阶层为了相互促进他们的富裕而紧密结合起来吗?会看到聚居吗?甚至,会看到尽管在极度限制性的法律之下却依然余留下来的自由程度吗?”[2](124)这就是说,战争,更准确地说,对战争的恐惧,保留了对人性的尊重,保留了人的自由,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所以,在人类目前尚处的文化阶段上,战争是使文化继续进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惟有在一种文化完成(谁知道什么时候)之后,一种持久的和平才会对我们有益,而且也惟有通过那种文化才有可能。”[2](124)同时,战争也建立起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建立起了新的国际组织,经过若干次的推倒和重建之后,一种类似于公民共同体的国际联盟最终会永久性地建立起来,也就是实现“永久和平”。
战争看似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但却是深深隐藏着的、也许是无上智慧有意的尝试,即借助于各个国家的自由,即使不是造成了、但毕竟是准备了各国的一个建立在道德之上的系统的合法性、因而准备了它的统一性,……但战争更多的却是一种动机(尽管离对人民幸福的安居乐业的希望越来越远),要把服务于文化的一切才能发展到最高的程度。”[5](288−289)可见战争只是实现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即人类历史发展最后目的的手段而已,尽管这个手段对个人而言可能是残酷的,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也许是灾难性的,但对人类整体的进步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
康德目的论视域下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考察,是思辨历史哲学的一种形式,它虽然无法取代历史学家的职责,但却是我们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的有效的“导线”。对此,康德也有明确的意识:“认为我想以一部世界历史的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一条先天导线的理念,来排斥对真正的、纯然经验性地撰写的历史的探讨,会是对我的意图的误解;这只是关于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此外,他必须很精通历史)还能够从另一种观点出发来尝试的事情的一种想法罢了。”[2](38)
三、以道德本体为依归的思辨历史哲学
康德的思辨历史哲学立足于道德形而上学之上,乃是为了克服自由与自然、道德与知识之间的鸿沟,正如沃尔什所说:“就他(即康德)来说,至少历史哲学乃是道德哲学的一种派生品;假如不是因为历史似乎提出了道德问题的话,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能提示他会去论及历史的。”[6](121)因此,康德的历史哲学虽说也是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它是立足于道德形而上学之上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是一种在黑格尔等人的思辨历史哲学体系的类比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康德把人类的幸福和文化作为自然的“最后目的”,但这一意义上的人类仍是有条件的,或者说,仍可能是实现其它目的的手段,因而对于“最后目的”,我们仍需追问作为其目的的无条件的“终极目的”,这一“终极目的”就是“作为本体看的人”,或者说“道德的人”:“人对于创造来说就是终极目的;因为没有这个终极目的,相互从属的目的链条就不会完整地建立起来;而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仅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部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5](291−292)在此,康德把人区分为作为物自体的人,即道德的人,和作为现象的人,即作为自然界的最后目的的人,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可能性条件和目的,“自然目的论”(以“最后目的”为最高目的的目的链条)必须以“道德目的论”(以“终极目的”为最高目的的目的链条)为依归,因而“在康德底哲学系统中,‘道德’是非历史的,或者说,超历史的”。[7](XXV)
康德并不关心纷繁杂乱的历史现象,历史之所以能够引起康德的兴趣就在于其中隐含着大自然的计划和目的,即人类的完善和幸福,“因为如果在最高智慧的大舞台上这个包含着所有这一切的目的的部分——即人类的历史——据说一直在与最高智慧唱反调,眼见这种情形使我们不得不嫌恶地把我们的眼光从它那里移开,而且由于我们对有朝一日在其中发现一个理性意图得以完成感到失望,而使得我们只是在另一个世界中期望它,那么,赞美无理性的自然界中创造的壮丽和智慧,并且劝人加以考察,又有什么用呢?”[2](37−38)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作为具有意志自由的人的作品,虽然是从恶开始的,虽然充满着斗争与苦难,但却是以“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为其最后目的的,是向着善不断进步的。假如历史中没有理性,没有最后的目的和价值,那么我们探讨纯粹偶然的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
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史是一部“道德史”,即人类向着善不断进步的历史,它体现了大自然的善意,即便大自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如此之多的灾祸,“但毕竟也又促使人重新鼓足干劲,从而促使人更多地发展自然禀赋的非社会性和普遍对抗的源泉,也许显露出一位睿智的创造者的安排;而且绝不是一只在其美好部署中搅局或者嫉妒地败坏它的恶意精灵的手。”[2](28−29)如果仅仅按照理性来安排人类历史的话,“恶意精灵”也是可以做到的,但康德强调说,它出自“一位睿智的创造者的安排”,这就说明,人类历史是向着善而进步的道德史。但这种进步史并不需要每个人在道德上成为一个好人,只要他遵守公民宪法,成为一个好公民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它并不意味着“意念的道德性的一种日益增长的量,而是意念在合乎义务的行动中的合法性之产物的增多,不管这种增多是由什么样的动机引起的;也就是说,人类向着更善的努力的收益(结果)只能被置于人们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好的善良行为之中,因而被置于人类的道德性状的现象之中”。[3](88)这样的一部道德史的最后目的——永久和平,是值得期待的,因为它可以在实践中经过漫长世代的努力而实现出来,因而它具有较少的乌托邦色彩。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一种以道德哲学为依归的思辨体系,它无关乎人类历史现象本身,而仅仅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将其看作一部通向人类永久和平的道德史,正是在这一历史进步的历程中,自由与自然、道德与知识的分裂得以沟通。
四、康德历史哲学的“类比性”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一种目的论体系,它引自然目的论概念入人类历史领域,以便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加以认识,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知识,而仅仅是类比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因而康德强调说,它仅仅是历史理解的“导线”。而且,目的论意义上的“进步”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真正进步,因为这种进步是从作为本体的人或道德的人的角度做出的观察,并不是生存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的观察,因而,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历史的形而上学,我们无法用经验的历史事实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
康德的历史哲学开启了完全从哲学上考察历史本身的思辨历史哲学的新方向,其许多论点也为后来者所继承,如历史的进步性、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但与黑格尔从人类历史的事实进展中看出逻辑上的进展,并用这种逻辑上的进展来规范事实进展的思辨历史哲学不同,康德的历史哲学无关乎人类历史本身,而是属于道德哲学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道德哲学得以可能的一个例证。因此,严格来说,康德的历史哲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而仅仅是类比于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1]卡西尔.康德历史哲学的基础[J].世界哲学, 2006(3): 73−76.
[2]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七卷(学科之争、实用人类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康德.判断力批判[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6]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7]康德.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导论[M].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