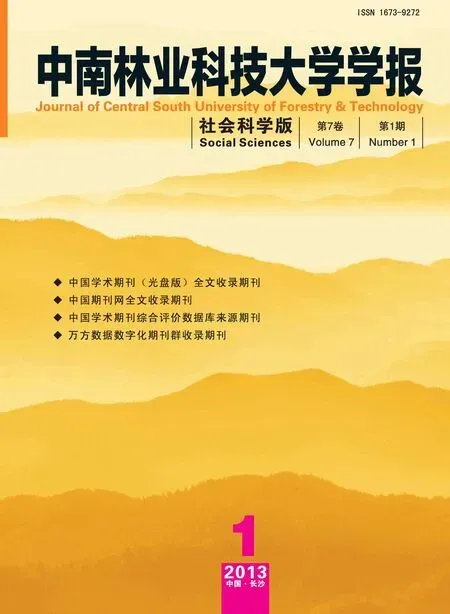洋泾浜语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刘文慧,阳志清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a.语言与教育技术研究所;b.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洋泾浜语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刘文慧a,b,阳志清a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a.语言与教育技术研究所;b.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语言是社会变迁的忠实见证者。中国洋泾浜语最早出现于16世纪中叶的澳门,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蔓延到内地,它经历了澳门葡语、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语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和正规英语教育的普及宣告了中国泾浜语的消亡。但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的洋泾浜现象以特定的贸易用语等形式存在于当代社会。洋泾浜语和洋泾浜语现象的形成、发展和消失反映出自明末清初以来,中西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层面的交流与冲突,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澳门葡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语;历史变迁
沿着西方殖民者在近代中国的侵略步伐和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中国洋泾浜语经历了从澳门葡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语再到现代洋泾浜现象四个历史阶段。英国语言学家帕默曾经指出,“语言的历史和文化和历史是同步发展的,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启发。[1]”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洋泾浜语和洋泾浜现象的出现与消亡折射出近四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一、洋泾浜语
当一种语言作为没有共同语的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时,这种语言称为中介语(lingua franca);如果这种中介语是不属于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第三种语言,并且在语法和词汇上大幅度简化,这种语言被称为洋泾浜语(pidgin,也称皮钦语);如果整个语话团体放弃了它原来的语言而将洋泾浜语作为其母语,这时洋泾浜语言就转化为克里奥语(creoles)。世界各地的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语大约有200多种,中国洋泾浜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洋泾浜语之一,也是太平洋地区最古老的洋泾浜语。[2]
中国的洋泾浜语是明末清初帝国主义殖民列强逐步侵略的附属产物。洋泾浜原是旧上海一条小河的名称,位置在今天的延安东路。1843年上海开埠后,来上海的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想在上海占有辟设租界,于是威逼当时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签订了卖国的《土地章程》,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的土地批租给英国商人;1849年4月,上海道台麟桂又屈服于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的淫威,将洋泾浜以南、护城河以北的土地划为法租界。于是洋泾浜成了英、法租界的分界线,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易往来集中于洋泾浜附近,他们交流中使用的是一种混合了中文和英文特征的皮钦语,这种混合语被称为洋泾浜语。“洋泾浜”是Pidgin 一词的汉语翻译。由于中国洋泾浜语由于历史原因在上海发展到鼎盛,所以学术界通常将历史上出现的此类混合语统称为洋泾浜语。对于Pidgin一词的来源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17世纪英国人发现美洲新大陆时最早曾经与一个位于Orinoco河口的名叫Pidgins的印第安部落打交道,当时出现的简化英语被人们称为Pidgin;另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商务往来和奴隶贸易的原因,多种多样的洋泾浜英语大多出现在中国和非洲,所以Pidgin一词来源于中国广东人发business这个词的讹音。[3]
外国人把中国洋泾浜语称为破碎的语言,认为它怪诞可笑,是一种严重扭曲的语言。但是,正这种滑稽的语言在当时中西双方沟通中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洋泾浜语的出现与17世纪后资产阶级国家不断殖民扩张侵略紧密相连。在上海洋泾浜英语正式出现以前,中国洋泾浜英语经历了澳门葡语和广州英语两种雏形阶段。
二、葡萄牙殖民者与澳门葡语
根据历史记载,葡萄牙人是最早到东方从事殖民活动的西方人,也是第一批来华的西方人,因而葡萄牙语是最早与东方语言接触的西洋语。[4]
葡萄牙殖民者一直垂涎于广袤富饶的中国,从16世纪初期开始就不断生事借以侵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企图打开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门。1514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抵达觊觎已久的广东海岸。1517年,安刺德率领由四艘武装葡船和四艘马来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闯入广州港开炮示威。此后,葡萄牙舰船更加频繁地进出广州口岸,袭击广东沿海地区。明嘉靖二年(1523),明朝军民在广东新会海面击败葡萄牙的入侵船队。葡萄牙人在广东被逐后,又在浙江、福建沿海与倭寇勾结,不断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海域,强占并盘踞一些岛屿,后被中国军民驱逐。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者改变强攻的策略,私下买通明朝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登陆澳门。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潜入澳门建小货栈,更以租借为名,用欺骗贿赂的手段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并宣布正式开埠,长期霸占澳门。[5]
借助澳门,葡萄牙成为英美以前中西贸易的主角,16世纪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商人基本都来自葡萄牙。出于生活与交际需要,葡萄人必须与当地的中国人进行交际往来,葡萄牙语逐渐成为中国沿海贸易的通用语言。中国最早的洋泾浜语,即澳门葡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其适用范围主要限于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地区,并于清初广州开关以后至乾隆初年流行与整个广州口岸。[6]美国商人马士记载道:“对中国贸易的英国船上大班,首先需要具备葡萄牙文的知识。从1517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以上,到中国去的欧洲商船都是葡萄牙人,而他们的语言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沿海的通用语。[7]”这是一种由葡萄牙语、英语、印度语、马来语和中国粤语混合组成的杂交体,是澳门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交往的唯一语言。澳门葡语的产生和使用区域都基本都集中在澳门、广州一带。澳门葡语的发音都是用汉字纪录,主要以粤方言为基础标注发音,也有个别用闽方言拼写。由于澳门葡语都用汉字注音,直接导致澳门葡语的发音与真正的葡萄牙语存在着巨大差别,例如“孟加拉”,汉字注音为“自明呀喇”,葡文对应为“Bangla”;“里斯本”,汉字注音为“预济窝亚”,葡文对应为“Lisboa”等等。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S. Williams)博士根据自己的体验总结到:“尤其在仆人和店主那里讲的这种方言,是葡语和汉语的大杂烩,它的用法和发音与真正的葡萄牙语相差太大,以至于刚从里斯本来的葡萄牙人几乎连一句都听不懂。[8]”
葡萄牙人对澳门的侵占拉开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序幕,也开始了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从19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英国在中国贸易地位的不断提高,英国殖民者逐渐取代了葡萄牙殖民者取得在华贸易的垄断地位,一种新的洋泾浜语应运而生,即广州英语。澳门葡语由于失去其滋生的土壤,大约在19世纪中期退出历史的舞台。
三、鸦片战争前的广州英语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在统一台湾后在严格的限制下在东南沿海开放海禁,允许外国商人到广州十三行等地区自由进行通商贸易,早在那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就已经超越葡萄牙。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置商馆,这标志着英国对华贸易已经超过葡萄牙占据首位,成为在华的主要外国势力。
英国人早在于17世纪中叶开始对华贸易,但当时中英语言尚未接触,英国人要靠懂得澳门葡语的通事才能与中国人沟通。随着英国对华贸易地位的提高,17世纪末18世纪初,一种中国人与洋人之间用于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在广州逐渐形成,即广州英语。广州英语是一种以广州话为基础,词汇以英语为主,夹杂着广东话、葡萄牙语、马来语以及印第语的混合语言。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大批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人。在现实利益的趋势下,这些人很快掌握了这种广州英语并将其传播到内地等周边地区。19世纪30年代后,在中西交往持续发展背景下,广州英语的应用范围在原有基础上扩大,民间出现了若干种用作教材和词典的广州英语词汇书的刻本。[9]大约到了1750年前后,英语来源部分已经成为广州英语中的主体,而葡萄牙语来源部分则大多都被英语所替代。关于澳门葡语是广州英语的前身的立论是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因此,不少澳门葡语的词汇进入到后来的广州英语中。从18世纪初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100多年间,这种没有句法、逻辑不清、词汇有限、读音不准的广州英语是中西交往的主要语言媒介。广东洋泾浜最常用的词汇在400个左右,大都来自英语。广州洋泾浜主要是一种口头交际语,带有浓重的粤方言特点,在语法方面以汉语语法为基础。[7]向西方读者详细介绍了这种语言的卫三畏以近乎谴责的态度说:“由于汉语习惯在其中的存在,在英美人士的听觉上引起的混乱,再加上糟糕的发音,使这种粗俗土语成为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交流工具。”但他不得不承认,它是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9]”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开始了屈辱的条约时期,并逐渐沦落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洋泾浜的传播迅速开始,传播的路线主要有三条:向香港传播;向太平洋地区传播;向中国内地传播。[8]鸦片战争后英国在华势力不断扩张,英国占领香港之后,许多外国人和华人迁居到香港,他们将洋泾浜语带到香港作为中西方和操不同方言的中国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语言,香港的洋泾浜语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洋泾浜的第二条主要传播路线是向太平洋地区传播。许多华人在鸦片战争后移居到太平洋诸岛和北美、澳洲等国家地区,这些华人带去的中国洋泾浜语在华人聚集地区使用到近20世纪初才大体结束。第三条线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通商口岸相继开放,随着外国势力入侵,广州英语向中国内地发展。19世纪60年代后,广州在中西关系中的地位下降,上海成为新的贸易中心,随后出现的上海洋泾浜语逐渐取代了广州英语的地位。
四、鸦片战争后的上海洋泾浜语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辟上海为商埠,1928年设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为上海市。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后,上海的对外贸易地位很快超过了广州成为中西贸易的中心,广州英语也随着贸易延伸蔓延到吴越一带。
对外交往的增多使江浙一带急需外语人才,能讲广州英语的广东人成为江浙一带广为招徕的人才。正如冯泽夫在《英语注释》自序中所称:“在开埠之初的上海等通商口岸,能操一口‘夷语’的通事倍受青睐,而通事者仍系广东籍居多。[10]”在英法租界之间的洋泾浜是中外居民聚集之地,一批露天通事、华商和无业游民操着蹩脚的英语牵合从事沟通中外商人,促成商业交易等事情。起初从事翻译活动人大多来自于广州,后来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也加其中,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洋泾浜语。这种在广州英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英语是一种以英语和上海话为基础的特殊的混合语言,其中夹杂一些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澳门语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上海洋泾浜语。广州英语可以说起源于澳门葡语,上海洋泾浜则起源于广广州英语。从下面这段沪语和粤语混合汉字注音的歌诀中,我们可以管窥当年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原貌:
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
廿四铜钿“吞的福”(twenty-four);
是叫“也司”(yes)勿叫诺(no),
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真崭实货“佛立谷”(very good),
鞋叫“靴”(shoe),洋行买办“江摆渡”(comprador)。
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boat),
“翘梯翘梯”(chowtea)请吃茶;
“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侬坐,
烘洋山芋“扑铁秃”(potato)。
东洋车子“力克靴”(rickshaw),
打屁股叫“班蒲曲”(bamboo chop);
混帐王八“蛋风炉”(damn fool),
“麦克麦克”(mark)钞票多。
“毕的生司”(petty cents)当票多,
红头阿三(I say)“开波度”(keep door);
爹要“发茶”(father)娘卖茶(mother),
丈人阿伯“发音落”(father-in-law)。[11]
19世纪末,当学习外语在北京等地还被士大夫普遍嗤之以鼻的时候,上海各种各样外语培训班已经多得来可以与当铺相比,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出现进外语学校要送钱开后门的状况。[12]从中我们足以推断清末时期,上海洋泾浜语的繁盛程度。这种中英混合洋泾浜在中国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30、40年代,约有200余年的历史。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结束以及解放后正规英语教育的普及,上海洋泾浜英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殖民地土壤而逐渐消亡。
五、当今社会的洋泾浜现象
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结束和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洋泾浜语的消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普及正规外语教育。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改革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日益与全球经济接轨。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开展经贸活动。于是,在一些贸易和服务等行业,一种新的洋泾浜现象悄然出现。
文化的“异”使在表达同一概念时,在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必然给予词汇不同的意义和大量的文化信息。[13]这种类似洋泾浜的英语语言变体是是一种以贸易和服务等为目的的语言变体,是中国从业人员与外国人进行交流的主要语言。这种语言变体的出现与新形势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上海原襄阳路服饰礼品市场为例。上海襄阳路市场是上海地区外国人密度最大的地区,平均每天接待外国游客超过千人,外国人之所以青睐襄阳路市场,除了因为商品物美价廉,还因为外国游客可以与商贩直接用英语进行交流。尽管襄阳路出现的洋泾浜语现象与近代的洋泾浜英语在使用目的、使用范围和语言本身有很多相同点,但是它不是洋泾浜语的再现。首先,近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必须首先学习这样那样的洋泾浜英语才能与本地人打交道,洋泾浜英语对中外双方来讲都是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历史上的洋泾浜语使用范围更广,是中外客商、主仆等之间的交流用语,而襄阳路市场上出现的洋泾浜语现象的目的只是为了买卖双方交易的完成,而且外国人也不必像他们的祖辈那样事先学习这种交流用语。造成这种类似于洋泾浜语的语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从业人员语言水平较低,句子中语法错误太多。根据朱宁和赵宝国的调查,襄阳路市场内的从业人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他们大都经过正规的英语教育,但是没有得很学好,他们认为自己的外语是在以往英语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学来的。[14]
此外,20世纪中叶以后,香港出现的洋化粤语现象是是中国洋泾浜长期在香港存在导致的一种语言借用现象,这种现象与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语言西化现象一样,但都不是洋泾浜语的再现。由于人类语言和思维的统一性[15],当今社会的洋泾浜语现象和历史上出现的几种洋泾浜语都是中西贸易交往的产物,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式的语言和思维特点,但这种类似洋泾浜的语言现象与当年真正的洋泾浜语有本质区别。
六、小结
语言的变迁映的是社会历史的变迁。洋泾浜语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文化的产物,是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混合语体。它的形成过程是单向的,即在土著学习欧洲语言的过程中形成,其底层是土著语言,没有以欧洲语言为底层的洋泾浜语。16世纪中叶的澳门葡语、18世纪初的广州英语和19世纪中叶的上海洋泾浜,三种洋泾浜语印证了近代中国一步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新中国成立宣告了存在于中国社会近400年的洋泾浜语的消亡,但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洋泾浜现象因其存在的必要流行于当今的中国社会,这些以交际功能为主目的语言变体与当年的洋泾浜英语有着本质差异,反映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环境下对外经贸的发展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
[1]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31.
[2] Richard Hall. Hands off Pidgin English [M]. Sydney: Pacific Publications Pty, 1955: 28-29.
[3] 刘文慧. 中国历史上的洋泾浜英语[J]. 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4):42-43.
[4]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 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563.
[5] 冯克诚,田晓娜. 中国通史全编(中) [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929.
[6] 周 毅. 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历史渊源之探讨[J].中国文化研究,2005,(4):110-122.
[7] 亨 特. 旧中国杂记[M]. 沈正帮,译校.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170
[8] 张振江. 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述评与探索[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2):28-38.
[9] 吴义雄. “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J]. 近代史研究,2001,(3):186-190.
[10] 周振鹤. 随无涯之旅[M]. 北京:三联书店,1996:200.
[11] 汪仲贤. 上海俗语图说[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
[12] 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J]. 学术月刊,2002,(5):57-58.
[13] 刘胡英. 从英汉习语翻译看中西文化差异[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13-15.
[14] 朱 宁,赵宝国. 当代“洋泾浜”产生的可能性—上海襄阳路服饰礼品市场从业人员英语使用状况调查[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4):49-53.
[15] 蒋丽平. 文化差异视角下的英汉颜色词的联想[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3):92-94.
Pidgin and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Chinese Society
LIU Wen-huia,b, YANG Zhi-qinga
(Language and Teach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Hunan, China)
Language is the authentic witness of the social change. Chinese pidgin fi rst appeared in Macao in the middle of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n spread into the inner land with the western colonial invasion. It consists of Macao Portuguese,Canton English and Shanghai pidgin. Chinese pidgin has disappear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and formal English education,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pening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ew pidgin atmosphere appears in modern society.Pidgin and Pidgin atmosphere ref l ex the exchange and conf l ic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t the level of economy, culture and even politics, which shows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Chinese society.
Macao Portuguese; Canton English; Shanghai pidgin; historical change
H059
A
1673-9272(2013)01-0104-04
2012-11-12
湖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项目:“基于认知学习理论的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设计”(编号:湘教通[2012]401-20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认知理论下的二语习得图文理解整合研究”(编号:12YBA348);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语言习得的图文理解整合研究”(项目号:2012ZD08)。
刘文慧(1978-),女,辽宁锦州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二语习得。
阳志清(1962-),男,湖北京山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语言与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
[本文编校:杨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