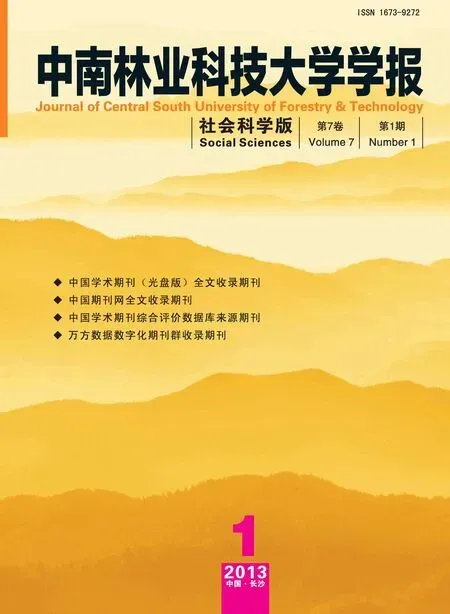论破产公司环境侵权债权的优先受偿性
李丹萍
(云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论破产公司环境侵权债权的优先受偿性
李丹萍
(云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公司作为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往往是许多大规模环境侵权行为的制造者。在公司破产状况下,环境侵权债权只能作为普通破产债权参与破产财产分配,获得清偿的比例较低甚至可能完全无法受偿。应在维护债务人利益平衡的前提下,在破产法中赋予环境侵权债权一定的优先受偿性,以体现“污染者负担”原则,防止公司以破产制度逃避环境侵权责任。
破产;公司;环境侵权债权;优先受偿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根据国家环保部《2006中国环境状况公告》,我国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其中45%为重大风险源,相应的防范机制却存在缺陷,导致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1]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在巨大的赔偿和污染治理费用面前,事故企业往往只得被迫破产,而2006年《企业破产法》对公司环境侵权责任引起的债权没有做特殊规定,只能作为普通破产债权参与破产财产分配,其受偿顺位处于最后,获得清偿的比例较低甚至可能完全无法受偿。我国至今还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破产公司的环境侵权责任进行有效调整和规制,导致受害者得不到及时的补偿救济,造成的环境破坏只能由政府花巨资来治理。受害者个人、企业、政府三方都将承受巨大损失。因此,落实破产企业的环境侵权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实践对破产法和环境法的新要求。
一、强调破产公司环境侵权债权的意义
《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侵权责任可以具体表述为“污染者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依法不问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法律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2]”因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所引发的债权即为环境侵权债权,破产公司的环境侵权债权与其他普通债权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环境侵权债权具有公益性。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环境恶化,日益脆弱的环境问题成为和谐社会构建当中的不和谐因素,环境污染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环境的破坏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严重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最终会给全人类带来环境危机。环境侵权债权不仅关乎受害人个人损失的救济,更加具有公益性质,每个人都必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保证环境侵权债权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在保障人类的生存权利。
其次,环境侵权债权影响的广泛性和严重性。2011年震惊世界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露事故,为防止核辐射对周边居民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20公里“警戒区”内居民必须全部撤离,在警戒区内的77000名居民在未来几年无法回家。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我国多个省市也监测到轻微放射性元素,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其后果具有严重性,波及范围具有广泛性。
再次,环境侵权债权影响的长远性。由于环境侵害往往是经过广大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经过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后,才逐渐形成和扩大的,其造成的侵害结果也是持续不断的,如福岛核电站泄露出的各种放射性元素,要在一百年之后才会完全衰变,环境污染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将持续很长时间,甚至需要花费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弥补其带来的损失。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理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要求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绿色政治制度、环境文化价值观、绿色科技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素和实现途径。而环境和资源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和资源领域的各种社会冲突说到底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结果,是人类追求片面的社会目标的产物。[3]公司作为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在经营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产生各种污染和破坏,是导致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基于破产环境侵权债权具有的公益性、广泛性和长期性的特征,环境侵权债权数额往往十分巨大,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及容易导致企业陷入破产倒闭的状态,如果将环境侵权债权归为一般债权,环境侵权责任根本无法实现,长此以往,容易引发某些公司通过申请破产以逃避环境责任,因此,破产法中必须对环境侵权债权进行不同于一般债权的处理。保证公司承担环境侵权责任,采取环保措施是解决环境问题,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公司为了减少日后承担责任的风险,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会自觉地控制污染源,减少排污。
二、影响破产法规定环境侵权债权优先受偿性的可能因素
对于环境债权在多数国家破产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其优先受偿性,影响破产法中规定环境债权优先受偿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可能因素。
1.破产法中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因素
破产是一种涉及多方当事人的特殊的执行程序,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和破产清算程序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与债权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利益冲突,按照利益法学派的观点,“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法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利益的平衡。“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抗衡来实现,换言之,法律对社会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利益的调整控制而实现的。法律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4]”庞德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工程,法的目的是尽可能合理的建筑社会结构,以有效的控制由于人的本性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中人类的利益。为此,作为社会控制最有效的工具的法的任务就在于使人的合作本能与利己本能之间保持平衡。[5]”破产法中必须实现多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如果在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中过多的赋予某些债权优先性,造成的后果是一般的无担保债权人难以受偿。特别是环境债权数额往往较大,赋予其优先受偿的地位无疑会对企业融资带来潜在影响,造成交易相对人的逃逸,企业经营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2.环境侵权债权的社会化承担方式因素
影响破产法中规定环境侵权债权优先受偿性的另外一个可能因素,是立法者也许考虑到环境侵权债权可以通过多种社会化的责任承担方式予以实现,“法律对环境污染损害的调整,已由过去的单一机制即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转变为复合机制,即在环境民事责任制度以外,又设立了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等。这些制度的设立,将加害人的全部或部分赔偿责任转移给了社会,故称之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社会化。[6]”其中最常用到的社会化承担方式: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和环境侵权公共补偿基金,是否能够彻底保证实现环境侵权责任呢?
“环境责任保险是环境侵权行为人(即投保人)因从事保险合同约定的业务活动造成环境损害而应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形式。其性质是基于民事责任的一种分散和防范侵权损害风险的法律技术。[7]”通过将投保人对第三人承担的环境民事责任转嫁给保险人,再依照保险的损失分担机制,最终实现环境民事责任的社会化分担机制。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单纯依靠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目前无法保证环境侵权责任的实现。首先,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在我国并非强制保险,在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强制责任保险主要是《海洋环境保护法》、《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规定的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并且,在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中,海上或内河运输的污染等强制险是可以通过财务担保替代的。尽管许多地方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和推进环境责任保险,如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实施意见》,要求滇池流域2920平方公里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都应当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和交强险、旅游人身意外险由国家来推动、有相关法规可依,必须强制购买不同,地方政府的实施意见其法律依据基本上是一些政策性文件规定,据此来支撑整个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仍存在一定难度。因此,推行强制环境责任保险还存在各种制度障碍,目前仅靠企业自觉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有相当难度,环境责任保险难以覆盖所有企业,还未充分发挥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其次,即使购买了环境责任保险的企业,也并非能够确定的实现责任的分摊,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巨大,承保风险非常高,保险公司出于营利和控制风险的考虑对保险责任范围具有一定的限制。“在美国的公众责任保单和欧洲的第三人责任保单中,都含有突然和意外发生的污染,均属于除外责任。譬如由于废液、废气、废渣等的排放和处理,空气、水、土壤等的污染所致的人身或财产损害,都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8]”承保范围的限制导致保险赔付率较低,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的积极性。另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属于限额赔偿,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和保险人所约定的保险金额为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因此,仅依靠环境责任保险并不能完全保证环境侵权债权的实现。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指“为了受害人得到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由排污者付费、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等多个渠道组成的主要用于污染损害赔偿,发展环境科技等多个方面,并且具有完善的运作机制的专项基金。[9]”它是为弥补传统环境侵权民事赔偿责任对受害人救济的不足而实施的一种社会化救济制度,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分担机制。我国目前还未建立完善的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仅有国务院于1988年发布的《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且该法第5条规定基金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为:重点污染源治理项目;“三废”综合利用项目;污染源治理示范工程以及为解决污染,实行并、转、迁企业的污染源治理设施。我国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立法和实践。从环境侵权公共补偿基金在国外的发展轨迹来看,即使建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环境污染造成的侵权债权数额十分巨大,各国都面临着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入不敷出的窘迫状态,以美国为例,“迄今,EPA(美国环保局)已判定了1245处需要进行紧急净化的地区,美国技术评价局判定有1万处必须净化的地区,会计检查院判定有40多万处需要净化的有害废物堆积地……EPA已判定的1245处需要进行紧急净化的地区就需要498亿美元,1万处则需四千亿美元。[10]”虽然1996年美国国会修改超级基金法时,将基金总数扩大到85亿美元,缺口仍然很大,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
笔者认为,在设计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方面,各国破产法,特别是许多破产制度相对发达国家也许就是考虑到上述几方面的因素,因而在破产法中回避了环境侵权债权的优先受偿性,而要完全的确保实现环境侵权债权,仅通过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和环境侵权公共补偿基金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
三、在破产法中规定环境侵权债权优先受偿性的思考
当我们再次审视破产法中的环境侵权债权时,必须摆脱传统破产法的思维路径,跳脱商法对“营利”的关注,更新现代破产法的理念,认识到现代社会中不同种类债权呈现出的新特点,不仅要关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各种自愿债权人,更加要看到侵权债权所造成的深远社会影响,并在破产法中做出相应的调整。基于破产公司环境侵权债权的特殊性,许多学者提出,应赋予其优先于普通债权得到清偿的效力,笔者赞成这种观点。考虑到环境侵权债权对环境本身造成的巨大破坏,环境污染的长期性甚至是不可逆性,以及环境污染所导致的受害人的财产、生命、健康和精神造成的损失,由破产公司承担环境侵权责任体现了“污染者负担”原则——应由污染者来承担治理污染和防治污染的责任,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如果允许破产企业以破产免责来逃避环境侵权责任,则有违社会公平和正义。但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因素,笔者认为以下两种途径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环境侵权债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利益平衡。
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有限额的环境侵权赔偿制。如1959年《匈牙利民法典》,1973年瑞典的《油污损害赔偿责任法》1960年《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公约》的规定,我国《海商法》第210条的规定等。其理论基础在于,传统的全部赔偿原则有利于受害者得到与损害相称的赔偿,但是却可能使一些无过错的致害企业陷入经济困境甚至破产的边沿。全部赔偿原则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从促进社会发展和稳定、充分就业的角度出发应实行限额赔偿制,至于限额赔偿与实际损失之间的缺口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等方式解决。因此,破产法中赋予环境侵权债权优先性,并不意味着环境侵权债权完全挤占了一般债权获得清偿的空间,虽然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较大,但限额赔偿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二者之间的冲突。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环境侵权债权都应该不加区别的获得优先受偿的效力。从国外的立法来看,美国是当今环境立法最全面和完善的国家,美国《破产法》和《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CERCLA)对破产公司的环境债权清偿顺序没有直接做出规定,法院在具体破产案件一般也不直接讨论环境债权是否有优先受偿性,而往往是考虑各种因素,间接的赋予破产环境债权优先性,比如环境债权是破产案件申请前产生的,则作为一般债权对待,如果是在破产案件申请后产生的,则有可能作为破产管理费用获得优先清偿,但各州法院对此并不能达成共识。“瑞典对不同性质的环境债权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1969年环境保护法所规定的环境清理债权在公司破产程序中享有优先受偿权,而1986年环境民事责任法所规定的环境债权则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如果原告是个人而非商业实体时,他可以通过环境民事责任基金得到赔偿。[11]”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尽可能保证普通破产债权人受偿的可能性,我国破产法可以考虑对破产公司环境侵权债权进行区分,比如受害人是自然人的情况下,为保证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能够充分获得救济,可以赋予其在破产财产分配有享有一定的优先性。
至于环境侵权债权具体的优先顺位,比较合适的做法是规定在“破产人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之后,“普通破产债权”之前。首先,“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是保障职工维持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为了职工能够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处于第一的受偿顺位是不能动摇的。而“破产人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中,社会保险费用是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要求,对保障职工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税收具有财政、经济、监督等职能,通过税收筹集财政收入以保证国家能履职职能;利用税收体现其有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对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的调节;约束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使之符合国家的政治要求。环境保护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让人类更好的生存,因此,环境侵权债权首先应让位于职工的生存权。国家是环境保护的主体之一,如果国家无法正常履行其职能,则各种环境污染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处罚,所以,环境侵权债权应该在保证国家债权受偿的基础上再获得清偿。
结语
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是一个内容众多、纷繁复杂的体系,涉及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公司破产状况下如何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就赋予其优先受偿地位,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在破产状态下,涉及环境侵权责任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如破产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环境侵权责任与环境责任保险的关系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希望通过这些有益的探索,可以就破产公司环境责任的承担构建一个合理运行的制度,以更好的落实环境侵权责任。
[1] 姜素红,陈彩霞. 论政府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6-49.
[2] 杨立新. 侵权责任法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 廖小平. 可持续发展的两个伦理论证维度——兼论生态伦理与代际伦理的关系[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36 - 42.
[4] 赵震江. 法律社会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汪世虎. 商法管见[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6] 蔡守秋主编. 环境资源法学教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7] 周 珂,杨子蛟. 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 法学评论,2003,(6):113 - 123.
[8] 刘 维. 构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模式的理性思考[J]. 环境科学与技术,2006,(7):55 - 58.
[9] 孟春阳,弓永健. 构建我国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若干思考[J].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2):95 - 98.
[10] 蒋 莉. 美国环保超级基金制度及其实施 [J]. 油气田环境保护,2005,(1):1 - 3.
[11] 兰国红.公司破产情况下环境侵权责任问题研究[EB/OL]. 丰台法院网,http://ftq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582 .2012-5-13.
On the Priority for Repayment of the Bankrupt Company Environmental Tort Claims
LI Dan-ping
(Law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Yunnan, China)
A company, as the main market main body, is often the maker of lots of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torts. When the company goes under, environmental tort claims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general ordinary claims being involv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ankruptcy property, and the proportion of getting settlement is relatively low and it is even completely unable to be repaid.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of the debtor, the environmental tort claims should have certain preferred payments in the bankruptcy law, in order to ref l ect the “polluter burden” principle, to prevent the company from bankruptcy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tort liability.
bankruptcy; company; environment infringement claims; priority claim
DF969
A
1673-9272(2013)01-0079-04
2012-09-26
2011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环境友好型社会视野下破产公司的环境侵权责任问题”(编号:2011Y035)。
李丹萍(1979-),女,云南昭通人,彝族,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行政法学。
[本文编校:杨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