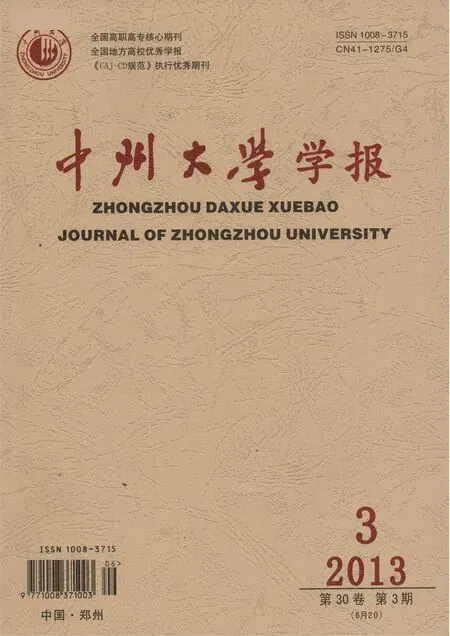近代中国人口和妇女问题略论
李春霞
(中州大学德育教学部,郑州450044)
自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以来,战乱频繁,国弱民贫,人口问题以及作为生育主体的妇女问题再次引起众多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关注。五四时期以来,在“科学”“民主”两大理念感召下,中国人为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谋求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努力引进西方近代思想观念,寻求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法。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美国桑格尔夫人的母性自由论被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改造中国社会,解决中国人口和妇女问题的有效方法引进国内。本文探讨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人口和妇女问题的思考,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桑格尔夫人的母性自由论对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努力寻求解决人口和妇女问题的重要启示。
一、近代人口问题和妇女问题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将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国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传统自然经济日益解体,以家庭手工生产为主的手工业失去了市场,小农及手工业者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已不符合时代需要,为机器生产所取代。在机器生产方式下,“一切物品的制造,不用人工,都用机械,其结果劳力过剩,人类无处谋生”[1]。大量无以为生的破产农民被迫或逃亡他乡,或涌入城市沦为贫民,造成大量社会问题,如非正常死亡、饥饿、疾病和溺婴卖女等悲惨社会现象。根据陈望道的记载,浙江义乌“乡间有许多把女儿出卖,只要三块钱便可买一个,真如卖小猪一样。”[2]浙江义乌为陈望道的家乡,其记载大致可信。在城市,大量贫民失业,往往沦为乞丐、盗匪和无赖,严重影响社会安宁。
在这种形势下,人口问题日益突出,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甚至有人把中国国弱民贫等种种社会问题都归因于人满之患。他们认为,人口过多不仅影响社会安定,还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人口过多会导致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失调,大量的闲置人口无法安置,使主要采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化改革无法进行,从而影响社会进步。因此,中国推行产业机械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人口问题,“近代化的主要条件,便是用机器的生产方法,来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无论在什么生产事业中,我们一谈到机械化,便遇到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采用机器之后,排挤出来的人口如何安排?”人口过多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提倡节育。由此他们大声呼吁:“我们愿意中国近代化,所以我们主张节制人口。”[3]
中国近代化进程是否缓慢是一个不必讨论的问题,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缓慢是否应该全部归因于人口过多还可以再讨论,不过人口的增加与减少确实会影响社会结构、社会协调、社会稳定,也是不争的事实。合理的人口结构、人口数量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反之,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人口数量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人口问题的凸显促使人们对传统生育观念进行反思和质疑,努力探索建立科学文明的生育观念。
与人口问题相伴而行的是妇女问题。旧式家庭中的女子只是生儿育女的机器,是“家庭的劳役,家长的财产,男子的玩具,生育的工具”[4]。新思潮的倡导者极力抨击这种不合理现象,认为要建设现代文明社会,占一半人口的妇女必须取得人格上的平等自由,否则我们的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女子既是人,一定应该具有人格……一个人不依靠他人,而能独立的生活,具有身体上,精神上,意志上种种自由,社会上地位也是和他人平等,待遇也平等,这样才可以说是具有人格。”
人格独立需要经济独立作为基础,这也符合中国自古以来衣食足而知礼节的古训。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女子只是家庭中的生育工具,是两性生活中被动的一方,既然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与基础,自然也没有争人格、争自由的权利乃至想法。在中国传统社会,很多女子十五六岁就出嫁,从此就被无休止的生育拘囿于家庭中——“女子当怀胎后五六个月,在这个时期内,女子不适宜劳动;产出以后,襁褓三年;由三岁以至六岁时,儿童虽离母亦可,但是仍然常常依恋母膝。这样合算起来,女子如果遇着生产,简直是要白费六七年光阴,因为在这时期内不能工作。”[5]如此的生命历程怎能使妇女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与机会,所以中国妇女要走出家庭,走进社会,首要的问题是节制生育,轻装上阵。
随着西方近代新思想的传入,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摆脱旧伦理、旧道德的束缚,追求个性和自由。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对传统的婚姻、家庭及两性道德标准提出质疑,竭力抨击束缚人性、摧残妇女的旧伦理、旧道德,开始意识到恋爱是婚姻的基础,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的本质或因子,只有恋爱。婚姻的结果,或有生育。生育是婚姻下可能有的现象,然而不是婚姻的因子。”[6]
从这种立场或判断出发,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即性与婚姻特别是与生育的关联逐渐减弱,基于恋爱而结合的男女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平等的。生育是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结果,也可能通过人工辅助不发生,即性是婚姻状态的必然成分,而生育不应该是婚姻状态的必然因子。
为此,稍有觉悟的妇女和那些思想先进者,竭力反对压抑人性的传统大家庭制度,积极推崇西方小家庭组织形式,认为西方社会中男女双方基于恋爱而组成家庭,不仅家庭结构简单,便于家庭成员和谐相处,并且为谋求自立,实行晚婚和依据自身经济能力生育子女,对于自身和社会都有很大益处。反观中国传统婚姻与家庭制度,男女结合的主要目的只不过是为公婆娶媳妇,为家族传宗接代,往往男子十八九岁娶妇,女子十六七岁嫁夫,两个人不但没有足够时间接受完备的教育,甚至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由此而导致的必然后果是:“不完全的父母,岂能生得完全的子女吗?今日中国人种这样的孱弱,岂不是受早婚之害不少吗?社会上盗贼如此之多,亦岂不是吃家庭所需的多子多孙的亏吗?”[7]显而易见的结论是:要解放妇女,首先就要打破旧的家庭制度,建立新的家庭形态,使人人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使女性可以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与责任。
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示与桑格尔夫人母性自由论的引入
把近代中国人口与妇女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何在不影响、改变人类社会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前提下,采用人为的方法对人口增长进行适当的调节,以保障社会经济人口的协调发展,同时又能把妇女从毫无节制的生育压力下解放出来,打破旧的传统的家庭伦理婚姻道德的枷锁,从而有利于妇女走进社会,促进妇女自身乃至国家民族的解放,成为当时众多先进知识分子思索的一个有待迫切解决的课题。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论被介绍到中国,成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一部分知识分子进一步肯定中国国弱民贫和种族衰弱的原因就是人口过多和素质低劣,以为“一国人口之稠密,孳生之繁众,恒与人民个人之发达成反比例。一国个人贵发达,然后国家有一人得一人之用;否则民数虽多,而强半皆陋劣昏庸,能力薄弱,无教育,无知识,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日往月来,忽生忽灭,人民虽众,国家莫能得其用,虽多亦奚以为?”逻辑的结论必然是:“今欲发达个人,增多人才,减少生育实为必要之一举。”[8]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恒速于食品的增加,最终会引起人类食品的不足。他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天然之限制,即由饥馑、灾荒、战争、祸乱、疾病、瘟疫等引起的自然界自我调节;二是人为之限制,即迟婚减育。天然的限制过于残酷,且属不可抗力。人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力实行人为限制,实行迟婚节育。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参照遗传学和经济学的原则,人为限制生育和迟婚节育至少有这样一些足够的理由:“凡有危险遗传疾病者,不应结婚,除男女个人宜慎选择外,国家尤宜严加取缔”;“夫妇养子不宜太多,必审家计之盈虚,与子女未来之教育。为夫者宜体恤其妻养育子女之莫大牺牲,故养子期间,不宜过密。”[9]以遗传学和经济学的原则对人口数量增长进行控制,以期达到提高人口素质、减少社会压力的目的。
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启示下,一些中国社会学学者和女权主义者开始将婚姻、家庭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赋予节育以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他们认为,必须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经济生活和人口生殖三者之间的关系:结婚就要生育,生育子女,就必须为其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然而在这谁都知道的接连三个事项中,就是婚姻→生殖→生活资料中,却存着纠结的葛藤。其原因就在最末一项——生活资料——难得,换句话说,就是贫穷。为什么贫穷呢?就在人口比生活品过多。为什么人口过多呢?就是因为婚姻,生殖不曾节制的缘故。”[10]
既然人口增长带来如此多的社会问题,那么节制生育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避妊这件事,实在是现代的一种顶好的现象:他能用科学的能力,在性欲生活上面,支配从来不可抗的出生;又用科学的能力,改善人类的实质;更能发挥科学的社会改造精神,去确立世界永久平和的基础;为人口和生产力的调和;使人类的生活,易于维持;一方更能造成健康有为的人物,谋人类幸福的增加;不能不认他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特质,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赞扬他。”[1]
早期节制生育提倡者虽然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理论依据,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控制方法可能还存在某些弊端,认为如果一味实行晚婚与节育,“事实上不能实行其主义,且引起社会风化之大弊(如通奸、堕胎及卖淫者、花柳病者之增加)”[11],为防止这些弊端在中国发生,他们又引入新马尔萨斯主义作为补充。
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西方节育主义者对马尔萨斯主义的发展,在限制人口增加这一点上与马尔萨斯主义相同,但主张采用的方法有差别。马尔萨斯主义主张用晚婚或独身等节欲方法限制人口,即“婚姻的限制”;而新马尔萨斯主义则与之相反,主张在适当年龄结婚,但婚后要依据自己的具体条件限制生殖,即“生育的限制”。显然,新马尔萨斯主义较马尔萨斯人口论遏止正常情欲的思想倾向,更具有一种人道精神,人本情怀。
在马尔萨斯主义传入中国后,1922年,美国妇女活动家桑格尔夫人访华,传入了比较系统的现代西方节育理论和方法。桑格尔夫人的节育理论虽然从新马尔萨斯主义出发,但更注重对母婴的保护和妇女自身权利的维护。她使女性问题和妇女问题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与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念截然不同的母性自由论。
桑格尔夫人认为,“母性不得自由,是妇女之隶属的基础,而妇女之隶属,又由人口过剩而起的一切祸害的基础。生产是妇女的问题,所以妇女不可不立足于自己能够解决这问题的地位。她必须有对于她自己身体的权利,所以她必须有选择什么时候生产小孩的权利。如果把这种权利绝对的给予妇人,那么,世界上决不会再有无生存余地无生存机会的小孩,也不会再有病弱或不完全的小孩。”[12]简而言之,所谓母性自由论,就是女性对自身生育与否的自由选择权。
妇女之所以在社会婚姻家庭中毫无地位,沦为男人社会的附属品,就在于妇女对自身生育权利的无可选择,生育被看作妇女唯一的天职。一生拘于家中进行无休止的生育活动的妇女,再无余力和时间从事社会生产,从而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进而丧失了作为人的全部权利。所以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桑格尔夫人认为,生育与否、选择什么时候生育是妇女自身的权利,不是妇女必须要尽的义务。只有把生育权完全交给妇女,让她们拥有自己身体的权利,才能促进妇女的解放,解决人口过剩问题。
母性自由论的引入,获得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妇女解放主义者的欢迎和拥护。他们高呼自由的母性“是不受捕捉的母性,是不受束缚的母性,而能防止可以毁灭母亲精神和肉体的过剩的子女的产生。并且自己可以决定有小孩的时期,自己可以严密地规定产儿的数量,这是母性的权利和义务!这样的产儿,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盲目的,是由于母性(两性)深切的要求。婴孩富有生命力,自然是合理的事,无形中吻合优生学。”[13]母体身心健康才能生育出富有生命力的孩子,从优生学的角度考虑妇女生育自由,无疑赋予母性自由论更为科学、深刻的社会意义。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介绍与桑格尔夫人母性自由论的引入,给努力寻求解决人口和妇女问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重要启示。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桑格尔夫人的母性自由论为理论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近代中国生育节制思想,被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视为解决中国社会人口和妇女问题的有效方法,并且进行了积极宣传和实践。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妇女的解放,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但是无论人口问题还是妇女问题,都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们的解决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直至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并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
[1]三无.避妊我观[J].妇女杂志,1920,6(12).
[2]陈望道.妇女问题[M]//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09.
[3]吴景超.中国人口问题[C]//人口问题资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205.
[4]黄石.家族中的妇女[J].妇女杂志,1923,9(4).
[5]郑容,孟齐.妇女经济独立问题[J].妇女杂志,1920,6(4).
[6]陈德徵.婚姻和生育[J].妇女杂志,1922,8(6).
[7]吴弱男.论中国家庭应该改组[J].少年中国,1919,1(4).
[8]陈长蘅.中国人口论[C]//人口问题资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0.
[9]陈长蘅.进化之真象[J].东方杂志,1919,16(1).
[10]陈望道.婚姻问题与人口问题[M]//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99.
[11]邵飘萍.避妊问题之研究[J].妇女杂志,1920,6(5).
[12][美]玛莱忒·珊格尔夫人.妇人之力与产儿制限[J].健孟,译.妇女杂志,1922,8(6).
[13]陈伯吹.《婚姻问题》的六个断片[J].妇女杂志,192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