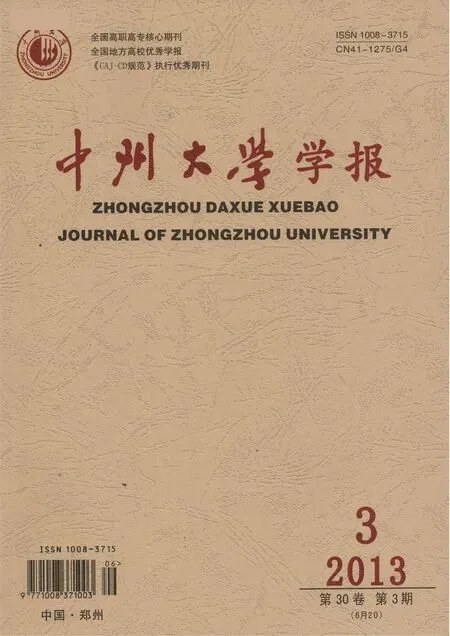从“气韵神境”论墨白与卡夫卡
孙青瑜
(河南省文学院,郑州450008)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总是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东西,归于“气韵神境”的范围。东方文论和鉴赏心理不同于西方,东方人倡“虚”,西方人讲“实”。“实”好讲,“虚”难论,宋代的郭若虚在论“气韵”时曾说过“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也就是说,“气韵”不好论,因为它是属于鉴赏心理学,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这也是笔者研究墨白小说多年,一直无法落笔成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气韵神境”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精髓,却一直在绘画的领域里转悠,或者说,只有绘画艺术将古老的“气韵神境”说发展到了最高境界。尤其是到了王维、梁楷之后,“气韵神境”更成了国画的根本,画不在“命根子”的“线”上,而是求神境于“线”外。
中国文学的“神”和“境”多是以“实”求“虚”的,而非是以“虚”求“实”的。以小说为例,一般小说引发的文外妙思,多是利用故事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当然这里并不否定故事的价值,而是在说除故事之外,语言同样有能力达到这种文外妙思。
在我们的阅读视野里,能布控这种高层气韵的作家,少之又少,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就是卡夫卡和墨白。
卡夫卡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就是他的叙事,他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梦语,他在展示人类生存状态的时候,依赖的不全是故事,还有他梦幻般的叙事构置出来那个的虚境。他的《城堡》,每每读来,总是让人跟着K陷入他梦幻般的生存境域。
可是从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标准来说,卡夫卡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还不成熟的小说家。从他的整体小说创作来看,靠故事力量说话的小说很少(最成功的大概就是《变形记》)。作为一个写作者,迷失了故事走向,小说自然无法再写完,也很难再靠故事的选材和走向来完成形而上的思考。或者说,作为一个作家,连最其码的故事关都没过,那卡夫卡靠什么风靡世界文坛的呢?又靠什么力量将一个又一个写不动的“半截头”变成了世界经典的呢?答案就是他依靠的是“气韵”。卡夫卡靠引发读者对生存状态思考的气韵,完成了他一个又一个“半截头”小说的精神建构。
小说中的故事犹如以线为命的国画一样,属于小说艺术的命根子。缺失了虚构故事能力,写作者就缺失了“技”。笔者认为,卡夫卡是幸运的,在众人没有能力窥出他小说中真正艺术价值的时候,恰逢了一股弥漫世界文坛的“现代派”,解构或抛弃故事的呼声让很多被“故事关”卡得半死不活的写作者奉为神旨,卡夫卡的小说便在这种时潮下风靡全球,被奉为经典。尤其是《城堡》,单从他的细节选择来看,如果还用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眼光来看,卡夫卡还有一关没过,那就是将生活变成艺术的关卡。通篇读来,《城堡》大有“流水账”的嫌疑。但是从现代派小说的审美视野来说、从他的那篇让人拍案叫绝的《变形记》一文的构思来看,他绝对不是没过“从生活到艺术”的关卡,而是思维的大反叛。他选择的细节不是生活的,而是梦境的,他不是戴着放大镜在看生活,而是戴着放大镜在看“梦”遇,这就与现实主义小说精编故事、深挖细节的老传统彻底决裂了,形成了故事的陌生化。
除了《城堡》,卡夫卡的其他小说里的思维、眼界和笔触仍是属于生活的,他在那些小说里一直着力想把他心中变异的世界和噩梦般的生活表达得淋漓尽致,一直想穷极这一主题思考,可他却一直力不从心。因为那时候,他依然没有突破靠生活和故事说话的现实主义的路子。再加上,卡夫卡的确不是一个故事天才,除去《变形记》之外,在其他小说中编出的故事和细节总是无法和他眼中那个变异的世界、那个“噩梦”的主题思考“浑然天成”。因为那时候,他受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依然是比较大的,除去《城堡》之外,卡夫卡的小说,包括《变形记》,描写的仍属于生活的细节,而不是梦幻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样写这一噩梦主题的《审判》,就是失败的,或者说,是他实验过程中的习作。
世界上一生都在写同一主题的作家不少,卡夫卡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之所以揪着一个母体思考不丢,是因为他们觉得写出来的小说还没有达到他们心中所想的高度,还无法穷极或“绝笔”他们心中的母体思考。直到卡夫卡去世,他可能还在这种自我怀疑和苦闷中徘徊。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城堡》已经把他思考了一辈子的文学母体推到了极至,或者说用故事之外的东西闭合了他思考了一辈子的文学母体和中国那句“人生如梦”的古老谛悟。
“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境,凝视了好一会儿。”用中国传统的“比兴”手法来看,《城堡》的开篇其实已经在告诉读者他在“虚”取梦境,而不是现实生活,或者说不是艺术化后的生活。整个《城堡》的描述从始至终都飘散着一种梦域感,随着目光的游动,读到的不是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卡夫卡制造的梦境。比如:“他走呀走的……皑皑的白雪,没有一个人影儿——可是最后他到底挣脱了这条迷宫似的大街,逃进了一条巷……”以及后面,他误入一户人家,又被人家赶出来。这些细节,若是现实主义小说家肯定会弃之不要的,滞缓故事行进的一切,可有可无的内容,都会被现实主义小说家视为累赘。但是,对于《城堡》,对于卡夫卡,对于“人生如梦”的古老格言,这些细节却具有血液意义!再比如:“在大路转弯的地方,K认出来他们已经离客栈很近了,看到暮色已经降临,他感到非常惊奇。难道他跑了一整天了吗?照他的估计,那至多不过一两个钟头……”“他们往前走着,可是K不知道是往哪儿去,他什么都辩认不出来,甚至连他们已经走过了那所教堂都不知道……他们不是在朝着目的地走,而是漫无目的地跑。……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了?这儿就是路的尽头了吗?”
这些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看似多余的累赘和朦胧的细节,直应开篇“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境”,是属于梦幻的,而是非生活的。这些朦胧的细节,带着梦的特征,被卡夫卡直接搬入了小说。这对于卡夫卡头脑里涌动的世界观太重要了,在一切形而下的生活细节描述和故事选材都无力穷极他所想的时候,在写《城堡》时,他于极度苦闷中另劈出的一条故事之外的道路:用“梦”表达“梦”,来直抵那个悠远的、噩梦般的深境。很多人读《城堡》都会有一种深陷梦幻的感觉,原因就是卡夫卡不只是在用文字单纯地描述梦境,他还在着力引领读者的身心进入一场由他构置的梦境,这就是他“统文”、“统道”的大气韵。这股子引发形而上学思考的大气韵从头弥漫到尾,和他笔下散漫的梦境融为一体,达到了让读者陷入一场“生存梦域”的旅行和反思的效果,盖为神品!
可是,卡夫卡小说里那团能引发形而上学思考(生存梦境)的气韵,并不能排除翻译所至。当然,我并不是在否定卡夫卡小说里的“以梦穷梦”的小说新技法和他噩梦般的母体思考的浑然天成,着实是因为中国流行着“美文不可译”一说。译者的语言功力千差万别,千本译文中,让人拍案叫好的译本也难见一二。也就是说,如果译者的文字功力不深厚,反而会造成一种生涩、拙笨和梦境般的现象,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卡夫卡小说语言上飘漫的上层气韵真因翻译所至,或者说纯属无心插柳所为,在他选择梦幻细节的时候,于无意识间造成了阅读重构的梦幻感。那么从艺术系毕业的墨白作为老子的乡党,便成了当今文坛气韵派的开山作家,他将中国古老的“诗画一律”,引进了小说创作。
墨白曾说过:“真正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比如我们能称为作家的人很多,能称为语言大师的作家就很少。”因为除去故事,文字本身也有一个很大的“投机”空间,这就是阅读重构。在理性无力穿透的部分,作家应该和画家一样学会利用空白的力量,学会留白,用空白给读者构建出一片“此地无声胜有声”的妙境。说白了,就是要有老子的那股子“玄”劲儿!说一半,留一半,说出来的一半好达到,留下的这一半就要见功夫了。再说白一步,留白处就是艺术要学会跟着老子一块卖“玄”,将无法穷尽之处,散布出一团“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玄气”,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跟着一块品味“文外之妙”和“线外之妙”。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牵引“境”的问题了。
古典文学理论中的“神、气、韵、境”是相互联系的,相互滋生的,形成一个空间,形成一个象外,形成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虚境,展示着对宇宙、对人生的某种形而上学的生命体悟,从而达到悟“道”的妙境,说白了就是以虚求实、以空求实,这才是“气、韵、神、境”的最高境界。它们看似在象中、意中、言中,实则又在象外、意外、言外,属于阅读重构和鉴赏心理学的范畴,同时也是文字给作家们留下的伸延空间。
清代诗人冯舒说过:“大抵诗言志,志者,心所之也,未可直陈,则托为虚无惝恍之词,以寄幽忧骚之意。”可以说每一个小说家和诗人想达到他心中涌动的思想,都需采用九曲十八弯的迂回之策,这在文学创作中属于最根本的“技”法问题。心中有“道”不一定得了“技”,有了“技”也不一定能得了“道”。艺术难就难在这里,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大美不能言”的审美高标,不能直接概念化地推理道论,也不能直接“写生”,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得想法把“妙”寄于文外,将“技”浑然天成地进乎于“道”,才能直抵“巧夺天工”的高境。
墨白曾经说过:“能不能用文字之外的空间与读者说话,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优秀的基本标准。”在我看来,墨白所说的这个“文字之外的空间”与“道”一样是没有外延的,它能形成一股子不可抵制的力量把读者拉向一个看不见的高度,用“虚”和“空”构建出一片形而上学的天地。卡夫卡之所以能为世界文学开辟一片文学天地,就在于他反判了故事的力量、反判了以实求实的叙事传统,用“虚”“空”搭建一片体悟生存现状的场域。他不是在用文字说话,而是在用文字之外的“空白”说话。他的小说看似写的很“满”、很梦幻,将许多现实主义小说根本无法入眼的琐碎细节统统搬了进去,其实他是留了白的,他的留白处不是在文字内部,而是在文字的外部,形成一个象外之象,牵引着读者进入一场又一场生存状态的大反思。当然,这是不是因为他在构置梦幻细节时于无意间打造出了这一上层气韵?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墨白自觉的语言实验,也和卡夫卡噩梦的主题实验一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他的代表作《讨债者》、《风车》、《光荣院》等一系列佳作来看,那时候的墨白与卡夫卡一样,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现实主义小说的大网,仍然是在用故事的力量直抵着“虚境”,而不是文字本身。像《讨债者》,作者在时代大背景下对讨债者的悲惨命运沉痛揭示,靠的依然是故事的走向。那时候,他的文字气韵,仍然还是“小气”。虽然那时候,墨白就有意识追寻语言的陌生化,却还没有“陌生化”成功,小说里的叙事语言依然带着音乐般的节奏起伏,润化着读者的心胸和眼目,在顺滑行进。就连那个一度让我拍案叫绝的《风车》,也和《讨债者》一样,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尴尬,依然和现实主义的铁网处在似分未分状,依然运用着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因子。在面对民族的痛苦和荒谬,面对我们曾经的疯狂和残酷时,《风车》却运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带着音乐般的节奏起伏的语流,让我们看得心胸激荡,一气读完。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墨白在向我们再现戏剧性和荒谬存在的时候,靠的依然是艺术化了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塑造等诸多传统手法。比如,在强大的“集体合作化”的面前,老穆以死来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理论家这个疯狂年代普遍存在的滑稽小丑的唐·吉诃德式的行为,他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和丧失的人性所构成的矛盾对立,在对畜牲和人的情感处理上出现的偏差,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本质,成为那个到处充斥着悖谬社会的象征,当那场大火把一切都烧毁之后,理论家“看到那霞光把眼前的一切都弄得迷迷茫茫”……小说中这个“迷迷茫茫”的虚境,其实是非常明晰的,因为现实主义的故事力量、人性深层的真实以及细节的设置在这部小说里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因为现实主义的力量还在,小说并没有在更高的意义上完成理论家“迷迷茫茫”的生存反思,也没有从更高的意义上穷极“痛苦”、“疯狂”、“残酷”的人性反思。但是,从现实主义小说的角度来看,我们又不能否定《风车》是一部携有很多经典因子的小说。但是,对于行走在语言自觉实验大道上的墨白,他是很不满意的,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自己,所以他的语言实验行进的步伐一刻也不敢怠慢。
墨白在《事实真相》的小说集自序中说过:“我们使用语言和文字是为了让记忆和幻想变成某种画面或情绪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需要独立的人格和诗性的叙事。在技术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叙事。我所说的叙事当然不是单单去讲述一个故事,绝对不是。故事只是使读者进入回忆内部的一种手段,叙事的灵魂应该是一座巨大的宫殿,一座迷失在时间和历史之中的宫殿……”后来他又在《墨白作品精选》一书的后序上说:“语言来自思想,来自灵魂深处,那是生命里所经历的东西,是一种真诚。”
从墨白一次又一次有关语言的自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要捕捉的是什么?就是他绘画老本行上的“墨外之境”!这么多年,曾经的美术老师墨白先生,一直在他的小说里彰显着种种“画境”,一直在用他小说的语言努力捕捉着“墨”外之妙的效果。他一直在着力而自觉地将绘画艺术的精华理念移入于小说创作中,用单纯的“墨”或者说文字建构着别乎于任何人的“巨大宫殿”,一座让读者随同“迷失在时间和历史之中的宫殿……”从而穷极他心中之所思,以此来闭合种种文学母体。
墨白的不少小说都是写“在路上”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包括“寻找”与“逃离”,像《重访锦城》、《寻找旧书的主人》、《雨中的墓园》、《错误之境》、《月光的墓园》……寻找的过程是痛苦而迷茫的,正如墨白曾在他的长篇小说《映在镜子里的时光》的开场白中所说:“我们世间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受了死神的旨意,踏行在时间的迷途之上。”也许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像墨白一样,在有意或无意地追寻着自己的生命价值。人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存在有没有价值?这是我们人类一再探寻的哲学命题。从个人的寻找和逃离,到对普遍生存状态的关怀,墨白在《重访锦城》的自序中如是说:“我用我的亲历和感受来剖析我所看到的一切,这种剖析是真诚的,我把刀子首先对准自己的胸膛。”其实,这种直接性的哲学追思并不是墨白的小说最大价值所在,或者说,墨白笔下一个又一个迷茫寻找的故事,只是他借用气韵说话的载体。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意取“文外之妙”,来完成他的哲学追问。
也正是这些“寻找”主题的小说,迎来了墨白文字建构史上的一次大换血。这时候他的小说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故事和细节的传统技法,但作者已经有意识开始加大文字的阅读阻力。比如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的片断性细节、大量自言自语的内心独白,以及闪跳的意识流的运用……出现在他小说里的这些叙事手段,造成了一种叙事和阅读的混沌、生涩,混沌的叙事继而又造成了焦躁、烦闷、隔膜,以及茫然的阅读情绪。这种阅读重组的情绪,就是墨白故意在文字中设置的阅读障碍,或者说他故意在文字之外散布的“迷魂药”,让你不得不在阅读中一次又一次停顿下来反思。
墨白21世纪前后的作品像《街道》、《欲望与恐惧》、《映在镜子里的时光》、《光荣院》、《尖叫的碎片》、《隔壁的声音》等更是明显。在这些小说里,他一反《讨债者》和《风车》用故事说话的传统写作手法,几乎完全颠覆了让故事和细节说话的传统,有意用放大镜将“寻找路上”的茫然、无聊、焦躁、无病呻吟、痛苦的细节放大扩展,语言上更是背离了润滑的因子,在看似很“满”的文字之外,留下一个“象外之象”,引领读者一次又一次进入寻找的程途,刺激着读者对当下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和追问。
如果说在“实”文化下浸淫下的卡夫卡,他作品中的“象外之象”属于无心插柳之作的话,那么被中国传统文化“熏”出来的墨白,则是从一开始便是有意而为之的。
深谙绘画艺术理论的墨白像简笔画大师梁楷戏墨一般,一直在建筑着他的语言大厦,一直在用文字之外“空白”来表现着“在路上”的茫然、烦躁、孤独、隔膜、痛苦……用西方的理论来说,就是“文学不仅仅是由语言构成;它还是进行比喻的意志,是对尼采曾经定义‘渴望与众不同’的隐喻追求。从墨白中后期的大量作品里,我们随处都可见到那些意象丛生的“自由意识”、随处可见到那些象征着人类为了生存所产生的疯狂与病态行为的隐喻,不可遏制的动物的本能和原始性的人性像潮水一样汹涌而出……“我们要对这种困境有所认识,我们首先应该理解和认识我们的生活,然后才是文学。”正是持以对苦难的深刻体验,使墨白认识到现实主义小说中无论多么绝妙的故事和细节,都无法淋漓尽致地展示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当现实主义小说的一切技法都无法穷尽他这一社会学思考时,墨白开始逃离了翻译语言——就是那种在中国文坛曾一度风行起的所谓的“陌生化”文字。
在《寻找旧书的主人》里,寻找昔日情人的过程和墨白的其他小说里的寻找一样,充满了焦虑、痛苦、烦闷、迷茫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不是人的生存实在,而是一种生存情绪。这种生存情绪很难用传统技法的故事和细节淋漓尽致地表达,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捕捉的心绪,是虚的,属于心理学的,却又是社会学的。换句话说,就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当很难再用传统的生活细节闭合那个“噩梦”母体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来个以毒攻毒,以梦解梦。同理,墨白在一切形而下的手段无法穷极他众多生存情绪的思考时,也来了个以毒攻毒,在具有阅读重构功能的文字上展开实验,开始在他的许多小说中大量涉及“自由联想”这一主题,当然,这只是他阻碍阅读顺畅的其中一招。除此之外,墨白还运用极度理念化的语言与口语化的小说叙事决裂;用一个个有头无尾或者有尾无头的片断化细节与线性前进的传统小说决裂,用闪跳的意识流或者说“混乱”的“自由联想”与明晰的现实主义小说决裂;用不再压韵的句子与讲究韵律美的中国小说决裂……从而给顺滑的阅读铺设成堆的障碍物,无形中让阅读陷入了一种烦躁、茫然不知所云的状态或情绪里,从而达到引发读者进入焦躁、烦闷、隔膜乃至痛苦的生存反思。尤其到他后期的作品,比如《街道》、《欲望与恐惧》、《映在镜子里的时光》,这种能引发哲思的上层气韵,已被墨白运用得十分娴熟,可以说随意点染即成。以短篇小说《街道》为例,这篇小说完全是主人公在重会昔日情人路上的所看所思,细节琐碎,“自由联想”随处都是,几乎没有故事。也就是说,作者意不在故事载道,也不在刻画人物,而在极力用文字之外的空白载道,用无法捕捉的气韵搭建一片体悟同样难以捕捉的生存情绪的大场域。因为这篇小说里几乎没有故事(如果说有故事,也都被作者推到了结尾处,大概只占整篇小说的五分之一),只是在文字之上建构了一个象外之象。用“文字之外的空间”形成一种不可抵制的力量。
这种用“大气韵”说话的成功的例子,在墨白后期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可以说篇篇都穷尽了他小说中的母体思考,冠绝了有关“生存情绪”的这一大文学母体,它比故事的力量更大,比细节引发的妙思更无穷。墨白将中国古老的气韵学说从诗画一体引伸进了小说创作。
让我们不由反思:原来在故事和细节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片广阔的文学天地。
[1]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卡夫卡.卡夫卡全集[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刘小逡,墨白.小说是叙事和语言的艺术——墨白访谈录[J].文学界,2008(7).
[4]雷霆,墨白.对文本的探索——墨白访谈[J].山花,2003(6).
[5]墨白.墨白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6]墨白.欲望与恐惧[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 《印象:我所认识的墨白》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