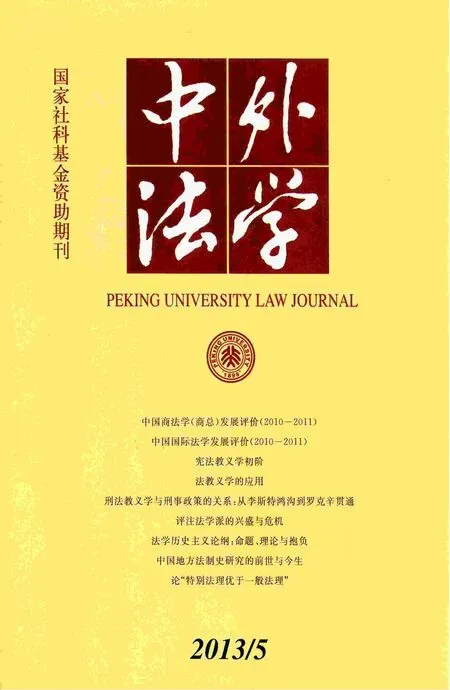宪法教义学初阶
张 翔
过去十余年间,中国的宪法学者试图摆脱政治话语的纠缠,并在法教义学的总体方向上确立宪法学的学科属性(“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但在当下,中国宪法学却又在经历政治话语的强势回潮(“政治宪法学”等)。〔1〕对林来梵、韩大元、陈端洪、高全喜等讨论的主要参与者的观点梳理与评析,可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研究进路的反复与不同学说之间的争论,是学术史的常态。在反复辩难中,争论问题自身会更加明确,而不同学术主张也会从散漫无意识走向自觉的体系化。在此,笔者尝试对宪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路径作一梗概式的整理,〔2〕就笔者的观察所见,近年来各部门法研究中都出现了法教义学的方法论自觉,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中心”,《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蔡桂生:“学术与实务之间——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司法考试(刑法篇)”,《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第1辑(2009年)。法理学层面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武秀英、焦宝乾:“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林来梵、郑磊:“基于法教义学概念的质疑——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并回应若干重要的争议。论文的基本安排是:①对法教义学的一般性描述;②对宪法教义学历史与现状的梳理与介绍;③分析“宪法作为政治法”这一宪法教义学的特殊问题;④回应对中国宪法教义学的两个前提性诘问。
一、法教义学:概念、任务、功能与方法
(一)法教义学的概念
“法教义学”是对德文术语“juristische Dogmatik”或者“Rechtsdogmatik”术语的翻译,其他的译法还包括“法释义学”、“法解释学”、“法律信条学(论)”等。“法教义学”这一中文译名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法学流派,但实际上,在德国人的观念中,法教义学乃是法学的本义,或者说“法学=法教义学”,其他诸如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史学,只是基于其他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而对法律的研究。〔3〕参见Karl 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Aufl.1991,S.189.(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113-114。在德国的法学文献中,“法教义学”这一术语的用法有多个不同的层次:可以在学科整体意义上使用,如“民法教义学”、“刑法教义学”;可以在某个领域层次上使用,如“基本权利教义学”、“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教义学”;也可以在非常具体的层次上使用,如“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教义学”、“平等原则的教义学”,甚至 “某判决的教义学”。围绕整个法律文本或者个别法律条文的解释和适用而形成的规则和理论,就是法教义学。
法教义学,简单而言,就是“对于法律素材的科学体系化的预备”,〔4〕Uwe Volkmann,Veränderung der Grundrechtsdogmatik,JZ 2005,S.261(262).或者“对给定的法律素材的体系性建(重)构”。〔5〕Wolfram Cremer,Freiheitsgrundrechte:Funktionen und Strukturen,2003,S.17f.按照魏德士的概括,法教义学提供对实定法的论证,给出法律问题的解决模式,包括一切可以在法律中找到的以及法学与法律实践为法律增加的理论规则、基本规则和原则。〔6〕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137。阿列克西将法教义学概括为三个不同层面的工作:①对现行的有效法律的描述;②对贯穿于现行法律中的概念和体系的研究;③给出解决法律争议问题的建议。〔7〕Robert Alexy,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1991,S.308f.通过对实定法的解释,将复杂的规范进行类型化,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设定分析案件的典范论证步骤,教义学为法规范的适用、为实践问题的解决预先作出准备。
(二)法教义学的任务与功能
为什么需要法教义学?法教义学是不是法律人的一种生存策略,只是法律人为了确立法学的学科地位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饭碗而故弄玄虚?事实上,如果我们需要法治,我们就需要法教义学。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依据法律规范裁判争议。然而,法律是一般性的规则,无法自己对具体争议作出判断,因此“法律人必须把待裁判的具体的个案,与组成实定法秩序的、或多或少存在抽象性的规则联系起来”〔8〕Helmut Coing,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5.Aufl,1993,S.243.以作出判断。在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和具体的案件之间,还需要进一步的裁判规则。准备这种法律规则就是法教义学的任务。〔9〕参见(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教义学在德国法文化中的意义”,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5。法学是一门指向争议解决的实践学科,因此,为法律人解释法律和处理案件提供框架性规则指引的法教义学就是法学的核心工作。〔10〕同时,即使是建议修改或者创制法规范的“法律政治”活动,法教义学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创制新的法律规范也需要对现有法秩序的充分了解,以使得新的规范能与既有的法秩序在概念、逻辑和体系上相互融洽。即使此种“法律政治”活动本质上决定于政治判断,只要仍然希望新的规范能够被解释和适用,就必须用合乎固有法律思维的方式去表达。Alexy,a.a.O,309.Larenz,a.a.O,S.195.
基于此,法教义学首先的功能是简化法律工作,减轻法律人负担,也就是所谓减负功能。“通过预先准备依据规范处理案件的标准流程和标准论证步骤,法教义学使得法律实践者的工作变得容易。”〔11〕Cremer,a.a.O,S.18已经建构好的、并且被普遍接受的教义学方案可以让法律人不必在任何案件中都重新去讨论问题。“法教义学可以把已有的对于法律问题的论证与学说整合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使得法律人在面对新问题时,可以从这个体系中提取所需要的知识,所以法教义学可以降低法官审判时在对同一法律条文的不同理解中做出选择所遇到的困难。”〔12〕卜元石:“法教义学:建立司法、学术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的途径”,载田士永、王洪亮、张双根主编:《中德私法研究》总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8。除此以外,法教义学的功能还在于:①总结过去和启发新知。教义学体系是对个别问题研究中所获得的认识状态的概括总结,同时,通过整理既有的问题解决模式,教义学可以提供新的观察和新的联结的出发点,从而启发新的知识,以处理新的争议。②控制法律人的恣意、维护法的安定性。法学总是希望通过一套可靠的法律技术来落实社会的稳定性预期,〔13〕鲁曼认为,法律系统的功能就在于为社会提供规范性期待的稳定感,参见(德)尼可拉斯·鲁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页184。从而落实法治目标。通过建构具有一致性的、可供长期使用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教义学体系,庞大、杂乱而且存在内在矛盾的法律规范体系得以增强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这同时还使法官的恣意得到控制,因为论证上的负担会促使法官尽可能地从既有体系出发去解决问题,而非寻求新方案,这能保证法秩序不会受到经常的激烈的冲击。〔14〕魏德士,见前注〔6〕,页140。法教义学具有维护法秩序的一致性、安定性,简化法律工作,保证法律知识和技艺的可传承,以及为实践中争议的解决提供指引的功能。〔15〕关于法教义学的功能,阿列克西进行了详细概括。Alexy,a.a.O,S.326ff.因此,以法治为目标的法学,就必然是教义性的。
(三)法教义学的方法及其实证主义倾向
服务于法的适用和法律判断活动的法教义学,其基本方法是解释和体系化。所谓解释,就是通过对法律文本的理解来把握其规范性含义,而体系化则是将解释获得的概念与规则等进行整合而形成逻辑一致、内在和谐的整体。前者以萨维尼所概括的四种解释方法为基础,而后者以“统一”(Einheit)和“秩序”(Ordnung)为基本特征。〔16〕Claus-Wilhelm Canaris,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2.Aufl.,1983,S.13.关于宪法教义学中的法律解释方法以及体系化思维,可参见本人的两篇论文:“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
教义学方法是法学区分于其他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重要方面。〔17〕Larenz,a.a.O,S.189ff.法教义学的任务和方法也决定了其与法哲学和法社会学在关注焦点上的差别。法教义学是关于现行有效法律的规范科学,是在现有法秩序内的研究。与此相对应,法哲学所关注的则是“应然法”,也就是法的正当性问题。“法哲学是关于正义的学说。”〔18〕Arthur Kaufmann,Rechtsphilosophie,2.Aufl.,1997,S.7.在此意义上,“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19〕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3。因为要评价法的正当性,所以法哲学经常要超越现有法秩序。法教义学所关注的问题是现行实定法的规范性,或者说法律的“效力”(Geltung),也就是依据法律规范,人们应该怎样去行为、享有怎样的请求权、承担怎样的义务。而法律的“实效”(Wirksamkeit),也就是法律是否真正得到了贯彻,以及法律的贯彻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法律在事实上怎样影响着社会生活,则是法社会学所主要关心的问题。
法教义学的工作是探究实定法的规范效力,而非探讨和评价现行法是否符合正义,是否在社会生活中真实发生着影响。法教义学在此体现出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实证主义的理想就是保护实在法理论不受任何政治倾向,或者说,不受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它的知识在政治上冷淡这一意义上的纯洁性,就是它的突出的目的。这仅仅是指它接受既定法律秩序而不对它本身加以评价,并且力求在提出和解释法律材料时最大公无私。”〔20〕(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79。基于这一倾向,法学也就在各种与法有关的学科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这意味着法学在知识上和方法上并非漫无边际,而是有着应当遵守的界限,正如拉伦茨所言:“假使法学不想转变成一种或者以自然法,或者以历史哲学,或者以社会哲学为根据的社会理论,而想维持其法学的角色,他就必须假定现行法秩序大体看来是合理的。”而否定现行法秩序、忽略针对现行法的教义性工作的人,根本就“不该与法学打交道”。〔21〕Larenz,a.a.O,S.195.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学是否“价值中立”、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是怎样的关系。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相关研究,可参见许德风,见前注〔2〕。
二、宪法教义学:历史与现状
诚如有学者所做的概括,德国宪法学(国家法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教义化”的过程,“如何通过方法论努力科学地进行国家法和宪法的体系建构或者解释,一直是问题的重心。”〔22〕李忠夏:“宪法学的教义化——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法学家》2009年第5期,页35。实际上,宪法学的这种教义学取向并非只存在于使用“法教义学”这一术语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学之所以成立为一个独立学科,教义化乃是其基本的特征。
(一)德国宪法学的教义化
在德国的三月革命前,宪法学的话语与政治话语、宪法学的争论与政治争斗是完全纠缠在一起的。“这段时期典型的是,激烈的政治问题发展成了宪法问题,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法讨论的政治化。政治理性和法律理性之间的界限常常不明显。……公法学家必须进行政治思考,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宪法政治和德意志同盟的政治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以自己的利益明确表示,自己要在讲台上主张什么。”〔23〕(德)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1800-1914)》,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96。宪法学的讨论就变成了“政治内容的词义拼斗”,“所有的国家法文献资料等同于政治文献资料,”宪法基本概念的讨论成为不同政治阵营斗争的工具。〔24〕同上注,页97、101。在这种学术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局面下,宪法学根本不足以成为一种冷静客观的学术力量,充满价值判断和政治恣意的国家法学也根本不能提供宪法秩序的稳定和安全感。尽管这一时期也不乏运用实证主义的教义学方法进行德国国家法学建构的学者,但由于德国尚处于分裂状态,并没有实际生效的宪法,而整个社会处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氛围中,建构宪法教义学体系的基础并不存在。
德国国家法学的教义化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前后,真正成为了宪法学的主流,并由此形成了宪法学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传统。这种转变的背景是德国的国家统一和1871年帝国宪法的产生。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法体系的产生,使得解释和体系建构性的法学工作有了规范文本上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格贝尔和拉班德。当时,民法学的发展已经使得实证主义的教义学方法非常成熟,格贝尔和拉班德则将此种方法引入了国家法的领域,最终建立起了国家法的教义学体系。格贝尔的基本思路是:将“建构的法学方法”传播到国家法中去,相应地排除掉政治、哲学和历史观点,通过对教义的基本概念的更详细具体地阐明,创立一个具有统一性的科学体系。〔25〕同上注,页439。法学的、概念体系化的方法是其进行此项工作的基本方法。在这一意义上,格贝尔是在对过去的国家法学进行清算,在他看来,以往的那些用历史的、统计学的、哲学的、政治的方法建立德国一般国家法学的工作都是徒劳的。〔26〕同上注,页441。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颁布以后,拉班德以此规范文本为基础,运用实证主义的教义学方法建立起了影响深远的德意志帝国国家法学的体系。〔27〕关于拉班德的国家法学的介绍,参见林来梵:“法律实证主义方法的故事——以拉班德的国法学为焦点”,《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拉班德在其巨著《德意志帝国国法学》的导言中这样写道:
在一个特定的实证法体系下的教义学的任务在于:……在法律制度的架构内,将各个法律条款追溯到一般概念,另一方面又从这些概念推导出给定的结论。对实证法条款的考察——对被分析材料的全面认知和掌握——这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活动。为完成这一任务,舍逻辑之外别无他法。……所有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因素,对于以具体法律素材为基础的教义学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因素经常只是被用来掩盖其无力进行建构性工作。〔28〕Vgl.Paul Laband,Das Staat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BD.Ⅰ,S.Ⅸ(Vorwort zur 2.Aufl.)
拉班德主张仅仅将成文法本身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他希望通过排除所有“外部”因素,通过价值中立和逻辑周延的方法去型塑法律规范、阐释法律的真实内涵。拉班德在建构德国国法学中毕生的努力目标就是把那些反复无常的政治偏见、缺乏专业性的业余研究、新闻评论式的通俗话语从法律科学中排除出去。〔29〕See Peter C.Caldwell,Popular Sovereignty and the Crisis of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The Theory &Practice of Weimar Constitution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16.拉班德的工作使得国家法学摆脱了当时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哲学和社会理论,使得那些貌似深刻却完全无法形成共识的玄思不再成为决定国家法学的因素,使得国家法学通过展现自身的逻辑自足和科学体系性而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学科。
在理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拉班德还以其实证主义方法妥当处理了现实中的宪法争议,使宪法争议得以摆脱政治立场上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在宪法文本的解释之下得到令众人信服和接受的解决。最著名的例子是预算法的冲突问题。按照普鲁士1850年宪法第62条的规定,国王和联邦议会共同享有制定法律的权力,而按照第99条,关于收入和支出的预算必须每年以法律的方式规定。然而在议会和国王无法就预算达成一致因而没有通过新的预算案的情况下,国王依然继续收入和支出,这就产生了违宪与否的问题。帝国首相俾斯麦提出“空隙理论”(Lückentheorie),认为在君主权力的恢复时期可以没有预算。尽管这一维护君主权力的主张在政治上获得了胜利,但显然与宪法第99条相抵触而遭到批评。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议会则认为,预算法是授权国家支出的基础,必须经过议会批准。预算法冲突是一个政治问题(君主与议会的权力斗争),也是一个宪法争议,但拉班德并不是以政治立场或者价值判断(民主vs.君主)去评价,而是运用法教义学的方法,通过概念的阐释解决了这一争议。拉班德通过区分“形式法律”和“实质法律”,指出预算并非实质法律,只是政府和议会在支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上达成的一致。构成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实质性法律基础不是预算,而是其他的法律,比如税法和薪俸法。依据这些法律,政府就可以做出支出的决定,而预算只是政府对下一年的支出的一个估计。因此,虽然其形式上是法律,但实质上只是一个行政法令(Verordnung),其制定权限属于享有行政权的国王,而议会只对此行使同意权而没有否决的权力。在新的预算法未被通过的情况下,国王依然可以依据其他原来已经通过的、对国王实质性授权的法律进行支出,没有预算法的支出并不违宪。〔30〕Walter Pauly,Der Methodenwandel des deutschen Spätkonstitutionalismus,1993,188ff.拉班德的结论在政治上是对国王有利的,但他拒绝了俾斯麦完全抵触宪法规范的理论,拒绝了基于政治立场的粗鲁判断,而是通过对宪法规范的精妙阐释而得出结论。这种方法上的客观性和政治上的不偏不倚为拉班德的实证主义的国家法学说赢得了声誉。
“格贝尔—拉班德”实证主义的、教义化的法学,作为宪法学的主流一直被延续和继承,其中的重要人物包括安许茨(Gerhatd Anschütz)、托马(Richard Thoma)、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等在发展中也产生了有着极高概念体系化水平的法教义学成果。〔31〕例如耶利内克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地位理论,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87及以下。有学者曾说,拉班德的学说“完全统治了不止一代的德意志公法学者”,〔32〕H.Tripel,Staatsrencht und Politik,1927.S.8f.尽管一直存在批评和质疑,但直到宪法学歧路并出、异彩纷呈的魏玛时代,作为法律实证主义伟大人物之一的凯尔森,仍然宣称自格贝尔、拉班德以来的德国国家法学已经被赋予了严格的法学的、而非政治的色彩,并且认为应该坚守这一学术立场。〔33〕Hans Kelsen,Allgemeine Staatslehre,1993,S.Ⅶ.魏玛时期关于国家法实证主义的部分争论,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在经历了魏玛宪法的失败之后,联邦德国进入基本法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对于宪法学意义重大的新因素:一个是德国接受了历史上曾经遭排斥的司法审查理念,建立了宪法法院制度(宪法法院制度最早是由凯尔森所倡导的),这为宪法学的教义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德国战后自然法的复兴。基于对纳粹暴政的反思,拉德布鲁赫等实证主义的主张者开始转而承认法学不可能是全然价值无涉的,实证法体系必须建立在正义的价值基础上。但这一转变很快就被重新纳入到传统的法教义学方法之下。杜里希教授在1956年发表了《人的尊严的基本权利条款》一文,通过解释指出,宪法的制定者是将“人性尊严”这一“客观的价值”确定在宪法之中(基本法第1条第1款),是将道德价值移植到实证法中,同时就使得这一道德价值成为法价值,从而也就成为实证法上的命令。〔34〕Günter Dürig,Der Grundrechtssa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AöR1956,S.118f.由此,整个基本法下的法秩序就是建立在人性尊严的价值基础上的,对于实证法的解释必须经常回溯到这一价值基础。尽管法学不再是价值无涉的,但这个价值就存在于实证法当中(基本法第1条第1款),法学的价值判断并不应该舍此他求。杜里希教授的这一教义学方案迅速为德国宪法法院所接受,通过确立“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整个实证法体系在趋向“正义的法”的同时又保持了相对的封闭性,在法学引入价值判断的同时又使得这种价值判断成为在法律规范下的教义学工作。此外,在协调法的正义性和安定性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拉德布鲁赫公式”。按照这一公式,实证法应该被优先适用,即使存在缺陷和争议,也应该被适用下去,“有法总还是好于无法,因为它起码还实现了法的安定性。”但是,如果实证法与正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不正当的法”必须向正义让步,“极端不正义的法不是法。”〔35〕Gustav Radbruch,Gesetzliches Unrecht undübergesetzliches Recht.SJZ 1946,105(107).在德国基本法时代的法哲学中,判断实证法的正义性的最高标准就是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人性尊严”,而联邦宪法法院对这一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使得一切价值判断都可以在宪法教义学的运作下完成。或许拉伦茨的一句话可以概括这种状况:“作为法律人不可以再质疑宪法的规范性效力。”〔36〕Larenz,a.a.O,S.196.
基于宪法法院的建立以及对宪法价值基础的阐释,德国的宪法学从魏玛时代的多样性又回归到了教义化的方向上(当然,已经不再是古典的完全封闭的法律实证主义),而其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裁判之间的良好互动更加展现了法教义学的基本功能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当代德国宪法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裁判的“解释科学”(Auslegungswissenschaft)。〔37Thomas Oppermann,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die Staatsrechtslehre,FS.50J.BverfG,BⅠS.460.〕
(二)英美宪法学的“类教义学”取向
以上简要介绍了在德国这个法教义学的母国,宪法学是如何法教义学化的。实际上,在英美法系,虽然并不常使用法教义学的术语,但其基本的工作方向与德国的宪法学却有相通之处。
在英国,戴雪的宪法学无疑是一个影响久远的学术主流。按照洛克林的分析,戴雪的《宪法研究导论》所试图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努力区分法律人研究宪法的视角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宪法的视角。戴雪指出,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主要关注宪法发展的历程或者政治共识,而并不直接关注当前的宪法规则,这种研究方法之下的宪法“仅仅是一个历史与习惯之间的交叉路口,而完全不配被称为法律”。要让宪法法律化,宪法学的方法就必须实证主义化。因此,戴雪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主张是:“英国法学教授……的职责在于阐明哪些法律是宪法的组成部分,安排这些法律之间的等级秩序,解释它们的涵义,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展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38〕(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27。这种方法的路径是解释性的,或者说是教义学属性的。这种方法的特殊性在于,不再把某种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社会理论作为理解宪法的基础,不对宪法作政治上的评头论足,而只是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和描述宪法。在洛克林看来,戴雪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转变根源于这样一种需求:建立一种独特的法律科学,将实证法从边缘地带引入研究的核心,通过定义和体系化来获得对宪法的科学理解。〔39〕同上注,页31。戴雪的宪法学方法一直是英国宪法学的主流,尽管一直遭受着各种批评,但这些批评“几乎没有触动戴雪在法律规则与政治道德或惯例之间所做区分的根基”。〔40〕(英)杰弗里·马歇尔:《宪法理论》,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11。
在美国,宪法学所围绕的主要要是宪法解释问题,也就是理解和适用宪法规范的问题。由此而形成的原旨主义和非原旨主义两个大的流派,只是在宪法文本的约束性和解释者的自由度上有着主张上的差异。尽管有时候显得更加自由和能动,也并不像德国宪法学那样有着很高的概念体系化的外在表现,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宪法学所围绕的正是宪法的解释与适用问题。在这一点上,称其大体上也是一种教义学的法学并非不正确。在共和主义兴起后,伍德、阿克曼、桑斯坦等人开始更多地将政治和历史的因素引入宪法学的研究,但却遭到了批评。美国学者却伯对那些在宪法解释中滥用政治理论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宪法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被限定了的讨论领域,不仅是为宪法文本所限定,而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文本解释的基本规则所限定。尽管某些宪法条款可能更富于弹性,但没有哪个条款可以被过分歪曲到自我破坏的程度。”〔41〕Laurence H.Tribe,Taking Text and Structure Seriously:Reflections on Free-Form Method i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108Harv.L.Rev.1224(1995).宪法并不是一些人们可以任意加个人好恶于其上的语言,相反的,法律人本身受到宪法文本的约束。任何理论、价值和原则,如果没有宪法文本与结构的基础,都不应当被看作宪法的规范。而将宪法解释的主题从宪法文本转向政治理论是背离宪法解释的本意的。〔42〕id,at1301-1302.
通过以上的简单概述,我们可以看出,宪法学之所以独立而成为一个学科,其基本的思路就是将宪法真正当作法律,将实定宪法作为研究的对象并与价值的、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进行切割,主要运用规范解释的、概念的、逻辑的和体系化的思维去建构实施宪法的规则体系。可以说,教义化乃是宪法学之所以成为宪法学的基本特征。何以如此?这又可以追溯到宪政国家的基本目标:法治。因为只有这种教义化的宪法学才能保证宪法成为一国公法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边界,使得公权力真正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从而有效消除政治恣意所带来的危险。正如施托莱斯所概括的:“把自然法和形而上学的法律理由排除掉……其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坚信,通过坚定不移地清除法学思想中的非法学因素,就能够达到建造一个由定义组成的没有漏洞的概念金字塔的目的。这种主张看上去不仅能保护反对政治强制的抵抗力量,保障法律安全,而且还能保证法学的科学性及其相应的社会地位。”〔43〕施托莱斯,见前注〔23〕,页436。出于对法的安定性的法治主义追求,宪法的法教义学化使其可以约束和对抗各种法律外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为社会带来和平与秩序。
(三)宪法教义学的现状:以宪法案件的“审查框架”为例
如前所述,法教义学是为法律人处理案件争议所做的科学体系化的预备,是为法律人解释法律和处理案件提供的框架性指引。为了避免对一门充满实践理性的技艺之学仅仅作理论性描述,这里尝试介绍宪法教义学的具体样态:通过对宪法教学中训练学生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审查框架”的介绍,展示宪法教义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帮助了法律人判断现实的宪法争议。
如同民法学要教给学生用“请求权基础”的思维去解析案例,刑法学要教给学生用“三阶层”的框架去解析案例一样,德国的宪法学也要教给学生审查公权力行为是否违反宪法的教义学框架。这种“框架”(Schemata)思维乃是法教义学的重要体现,也是法学教学要反复对学生进行训练的。通过这种模式化甚至可以说是格式化“框架”的反复训练,可以让法律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大体上有类似的思维路径。据此,法律裁判中的恣意得到大大控制,而法律解释和适用的一致性、稳定性则大大加强。可以说,这种框架式思维的训练,是法治得以落实于司法实务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技术因素。
在这里,以审查限制基本权利的公权力行为的“三阶段框架”作简单例示。当基本权利作为防御权或者说自由权时,也就是当国家公权力限制了基本权利,而基本权利主体要求排除侵害时,对该项公权力的合宪性审查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步骤:①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②基本权利的限制;③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论证。概括言之,第一步要审查:在这个案件中,谁得主张哪项基本权利?也就是自然人或者法人在其所主张的行为或利益上,是否存在基于某项基本权利的请求权。如果有,则第一步审查结束,进入第二步。第二步所要审查的是,公权力行为是否确实限制了该项基本权利。依传统的“限制”(干预)的标准看,该行为必须具备“目的性”、“直接性”、“法效性”、“强制性”、“高权性”方属于对该项基本权利的限制。如果公权力行为经审查确实对基本权利构成了限制,则进入第三步,审查该公权力行为是否具备阻却违宪的要素,主要包括:①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则;②是否合乎比例原则。如果通过了审查,则公权力会被认定合宪,如果未能通过审查,则会被认定违宪。
在以上这个总体的教义学框架中,每一步都还有非常具体的分析步骤。例如,在法律保留原则的分析中,首先要去看该项基本权利是属于“单纯法律保留”事项,还是“加重法律保留”抑或“无法律保留”事项。不同种类的法律保留有着不同的审查规则(此种区分并非法学家的臆造,而是依据德国基本法不同条款规定的差异)。又如,在比例原则的审查中,要逐项进行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的审查。〔44〕关于德国基本权利的教义学框架,参见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法学家》2011年第2期。此外,针对不同的基本权利,这一框架又会在各具体宪法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别形成各单项基本权利的审查框架。〔45〕Lothar Michael,Martin Morlok,Grundrechte,1.Aufl.,2008.S.457ff.通过这种细化的审查步骤,各种可能出现而应予考虑的因素都被体系化地预先纳入,宪法审查从而变得具有更强的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
除了基本权利作为防御权的审查框架,宪法教义学还归纳出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各项功能的审查框架、平等权的审查框架,以及关于国家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审查框架。这种教义学框架的得出,是学术与司法实务良好互动的产物。比如,关于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一般行为自由”的教义学,前述杜里希教授的论文和联邦宪法法院的艾尔弗斯判决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公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公共利益”的界定则是在药店判决中由宪法法院给出了最初的类型化方案。〔46〕BverfGE 7,377.上述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则是在大量的宪法裁判基础上,由学者最终完成归纳总结并成为通说的。可以说,这些框架是在解释适用宪法规范的基础上、在反复探索和辩难过程中得出的人类理性的体系性固化。
这种体系化的教义学训练一方面使得法律人在面对宪法实施中的争议时,不至于手足无措,而是有分析和讨论的出发点与思考方向,不必在每个问题上都重新回到抽象的价值起点和纯粹生活事实去思考,而是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体系,在以往的法律人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推演。另一方面,这种追求体系性和一致性的法律思维训练,又保证了宪法实施的前后一致以及国家秩序的合宪性。仅仅有宪法而没有这样一套教义学体系,稳定而和谐的宪政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从现实情况看,德国也正是通过完善发达的宪法教义学,得以应对诸如联邦架构、政党违宪、堕胎、国家统一、反恐与人权、欧盟一体化等充满价值和政治争议性并且极易引发社会纷争的宪法问题,为德国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三、“宪法作为政治法”:宪法教义学的特殊问题
如前所述,法教义学化是宪法学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并区分于其他学科对宪法的研究的基本要素,而当代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更强化了宪法学的教义学取向。然而,相关的批评却从未止歇过,其中最重要的批评在于认为宪法乃是政治法,排除政治因素而对宪法进行纯粹的教义学式的概念阐释和体系建构是错误的,也可能是徒劳的。
无人否认,宪法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诚如德国学者博肯福德所言,宪法是具有特殊的政治关联性的法,宪法规定国家政治性决定的路径,规定政治权力的运作程序与边界,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起着建构性和秩序性的作用。〔47〕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Die Eigenart des Staatsrechts und der Staatsrechtswissenschaft,in:ders.,Staat,Verfassung,Demokratie,2.Aufl.,1992,S.15.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民法、刑法等法学科的教义化或许是可能的,因为其与政治距离较远,而宪法学则是不能彻底教义化的。例如,有学者在批评前述杜里希教授的观点时,认为其追求教义学的封闭体系的思维是19世纪德国民法典编纂时期的方法,而宪法产生于此之后,传统法学思维根本不能涵盖。〔48〕Ulrich Scheuner,Pressfreiheit,in:VVDStRL.22,1965,S.44.而鲁曼也认为,不能试图去建构唯一的教义学公式,而是要对宪法作政治社会学的研究。〔49〕Niklas Luhmann,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Soziologie,1965.对于奠定宪法教义学基础的拉班德,斯门德毫不客气地批判他“对德意志民族宪法政治的良知问题和生活问题缺乏严肃态度”,甚至直指拉班德的犹太人身份而斥责其宪法学是“无根基的”、“空洞的形式主义”、“机械的”甚至 “变态的”。〔50〕施托莱斯,见前注〔23〕,页462-463。可以说,如何对待宪法的政治性,如何看待宪法判断中的政治考量,是任何试图将宪法学教义化的努力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笔者尝试在四个方面探讨:①宪法是否应该由司法来保障;②宪法学的教义化是否会取消政治;③宪法解释如何处理政治因素;④宪法学术与政治权力的角逐。
(一)宪法是否应该由司法来保障?
宪法是政治法,只有认为应当将宪法当作法律去解释和适用以判断政治活动合宪与否,宪法学的教义化才是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主张宪法学的教义化和主张宪法的可司法性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宪法是否应通过司法来适用,是否应该由法院或者类似法院的机构来保障实施,从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尽管迄今为止建立司法性的宪法保障是一个大的趋势,〔51〕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新发展包括,英国在议会主权的原则下建立的“弱型违宪审查”以及法国宪法委员会向着更强的司法性的变革。参见李蕊佚:“议会主权下的英国弱型违宪审查”,《法学家》2013年第2期;李晓兵:“法国宪法委员会n°2009-595号裁决述评——兼论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审查提请主体的扩展“,未刊稿。但反对的意见也一直存在。美国是司法审查制度的母国,但在美国建国初期,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就坚决反对最高法院的“篡权”,主张应当由总统来解释宪法。〔52〕参见(美)乔伊斯·亚普雷拜.:《美国民主的先驱:托马斯·杰斐逊传》,彭小娟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页52。而在司法审查制度早已根基稳固的当代,图什内特还在主张将宪法从法院拿开。〔53〕Mark Tushnet,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反对意见主要针对的是司法审查的政治正当性问题,也就是所谓反民主、反多数的难题。尽管也有学者(如却伯)认为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本质上只是个政治学的问题,而非宪法学问题,〔54〕Referred to Laurence H.Tribe,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Vol.1,New York:Foundation Press(2000)(3),p.302.但事实上大量宪法学者在认真地用各种理论去证成司法审查的政治正当性。对于美国学界的相关讨论介绍甚多,此处不赘。而在德国,同样有过是否应该将宪法司法化的争论,这就是魏玛时期著名的“宪法守护者”之争。这场争论的主要参与者是施密特和凯尔森,二人基于对政治和司法是否应该区分的判断,分别主张由“帝国总统”或者“宪法法院”来充当“宪法的守护者”。
施密特认为,司法有其功能边界,这决定了其不应该对政治问题进行裁判。在他看来,司法活动就是进行涵摄(Subsumtion),也就是将案件事实归属于某一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因此,“无论如何,司法审查权及裁判的基础都必须是能够进行确定及可测度之涵摄的规范。”〔55〕(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页23。可以用来实施涵摄的规范必须是构成要件明确的,而宪法并非这种要件明确的规范。宪法中充满了形态各异的原则、计划性和方针性的条款,以及各种妥协,宪法条文自身既不明确,又充满矛盾,因此无法作为涵摄的规范基础。〔56〕同上注,页45。如果非要让司法处理法律合宪与否的问题,就是让司法对未竟的政治问题进行判断。在施密特看来,“政治上的关键决定应该留在立法者手上。”〔57〕同上注,页22-23。如果由司法对法律的内容予以厘清,就是在“行使立法者的权力。而如果厘清的是宪法法律的内容,那么所行使的就是制宪者的权力”。〔58〕同上注,页47。让司法适用宪法以判断法律的合宪性,不仅错误地导致政治的司法化,也把司法权扩张到了不同于司法本质的领域,让司法权也受到了损害。〔59〕同上注,页25。在施密特看来,进一步明确宪法的内容是一项政治性的活动,本质上应由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来决定,而不能由司法来决定。严格区分政治与司法是施密特理论的重要出发点。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反对由司法来适用宪法,进而认为在政治上具有中立性,并具有全民选举的政治正当性的帝国总统才是合格的宪法守护者。
凯尔森逐点批驳了施密特。凯尔森认为,施密特的论证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认为司法的职能和‘政治性’职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60〕(奥)汉斯·凯尔森:“谁应该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张龑译,载许章润主编:《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251。按照施密特的界定,政治是关涉权力运用、利益冲突的,乃是立法之事;而司法仅仅是法的产物,并不涉及权力运行与利益冲突,只是在运用立法者创设的秩序。然而,凯尔森针锋相对地指出,司法同样关涉政治,同样关涉权力运用,同样关涉利益冲突。
在法官的每个判决中,都或多或少地隐藏着决断的要素,一个权力运用的要素。司法的政治特征越强,自由裁量的范围越宽,这一裁量究其本质必然允许司法的普遍性立法。认为只有立法,而非真正的“司法”才是政治性的主张,就如同认为只有立法是生产性的法律创设活动,而诉讼则是再生产性的法律运用活动一样,都是错误的。〔61〕同上注,页252。
也就是说,司法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试图区分政治与司法并使之对立的做法是错误的,“立法的政治特征和司法的政治特征之间,所存在的只是量上的差别,而非质的差别。”〔62〕同上注。在这种意义上,宪法的政治性根本不是司法适用宪法的障碍。
针对施密特关于司法只能基于构成要件明确的规范进行涵摄的主张,凯尔森指出,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规范就其内容带有疑问和争议的时候,通常大部分司法的大门才会开启,否则就只存在事实争议,而非实际上的‘法律’争议,”〔63〕同上注,页254。具有更多原则内容的宪法并非不可作为司法依据的规范,施密特所持的不过是早已被抛弃的认为司法不过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的陈腐主张。在凯尔森看来,“宪法的政治功能就在于:为权力的运用施以法律上的限制。宪法保障意味着,为实现此功能提供安全机制,即法律限制不能被超越。”〔64〕同上注,页243。当议会和政府的公权力行为违反宪法时,由一个法院对其进行审查,是实现宪法政治功能的唯一选择。针对施密特关于宪法守护者的主张,凯尔森认为,且不说国家元首根本就不可能如施密特所言是中立的,让帝国总统作为宪法守护者,无异于让他重新拥有类似君主的绝对权力。而从历史来看,君主才是宪法最主要的侵犯者,因而施密特学说的目的其实是:避免有效的宪法保障。〔65〕同上注,页243-244。
也就是说,如果不将宪法的保障交给司法,而是交给某个政治机关,那么宪法控制公权力的功能将彻底丧失。在现代社会,政治已经不再等同于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宏大概念,而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相对于法律系统并没有超越性。在现代的法治国和立宪主义原则下,不允许有任何法外空间的存在。〔66〕参见鲁曼,见前注〔13〕,页465。“需要对政治施加限制以确保政治热情在正确的行为框架之内活动。于是,法律就成为一套为政治实施提供根本性框架的事物了。政治必须得到驯服并置于边界之内,从而使其能力真正得以控制与利用。”〔67〕(英)马丁·洛克林:《剑与天平——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省察》,高秦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249。由司法来保障宪法的实施、对政治行为的合宪性进行法律判断是必要的,而对于政治的法律控制自然必须运用法学的逻辑。
(二)宪法学的教义化是否会取消政治?
在宪法走向司法保障之后,宪法学就成为为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提供规则和知识预备的法律科学,走向实证主义的技术化,真正成为法教义学。然而,一个自然的担心就是,如果政治问题最终都可以由司法来裁判,而裁判的依据又是教义学规则,那么这是否会导致政治被取消?在施密特看来,凯尔森等实证主义者是在支持政治的消亡而用技术取而代之,“政治意味着恒在的冲突可能性,而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假定的中立力量,则要取消这种政治。”〔68〕(美)约翰·麦考米克:《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徐志跃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页5。洛克林也设问:“如今的法律发展到了更高的理性与原则状态,在此巅峰之时,法律是否有可能产生对政治的胜利呢”,是否因此会出现所谓“政治的终结”?〔69〕洛克林,见前注〔67〕,页249。无论是将政治看作社会共同体意志的形成,还是看作对权力的追逐,无人能够否定政治在社会运作中的功能,无人能够否定政治活动和政治决断对于一个国家的必要性。因此,在宪法司法化、宪法学教义化的背景下,政治被取消的担心就是难免的。
然而这种担心却是不必要的,因为宪法的司法化和宪法学的教义化并不会取消政治的功能空间。正如洛克林所言,“法官虽然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但是他们不会在解释与适用实定法时试图占领政治的领域。”〔70〕洛克林,见前注〔67〕,页239。尽管在当代的法治和立宪主义原则下,政治活动必须被纳入宪法的控制,但是宪法对于政治而言只是一种“框架秩序”,其在为政治设定边界的同时,依然为政治保留了广阔的功能空间。德国学者史塔克对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规范与政治实务中的作用方式进行了概括,他指出,尽管宪法法院的宪法解释在维护宪法的最高性以及审查立法者的形成空间上具有决定性的地位,但是宪法法院的裁判必须为政治上负责任的机关(议会和政府)保留自我决定的空间。基于对社会事实的评估,立法机关有权决定制定怎样的规范,而行政机关在执行这些规范时也有裁量空间,“与此同时存在的政治的形成自由,不得经由宪法法院的法规违宪审查而破灭。”〔71〕Christian Starck,Das Bundesverffassungsgericht in der Verfassungsordnung und Politischen Prozeβ,in:Badura/Dreier(hrsg.),Festschrift 50Jahre Bundesverfassungsfgericht,BdⅡ,2001,S.7f.这意味着,对于宪法自身,宪法法院不能够“积极地”给出具体化方案,而是要让政治机关享有其形成自由。
宪法作为“框架秩序”而保留政治“形成自由”的思路,经常表现为宪法法院这样的裁判方式:一方面认定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违宪,但又指出,针对该领域应该做出怎样的新的规制,仍然由立法机关来裁量。比如,关于堕胎规制这一具有高度政治争议性的问题,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认定立法机关没有尽到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相关刑法条文违宪。但同时又明确指出,“确定具体的保护的方式和范围是立法者的任务,宪法将保护义务视为目的,却不提供具体的保护方案,但立法者需要注意‘保护不足之禁止’的原则,受到宪法司法审查”。〔72〕参见陈征:“第二次堕胎判决”,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 第一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页167。同样,在关于大学组织的判决中,宪法法院指出相关法律所规定的大学组织模式未能充分保障学术自由的同时,又强调大学组织可以有多种模式,在决定采用何种模式上,立法机关有充分的形成自由。〔73〕参见张翔:“大学判决”,同上注,页119。所谓“宪法不提供具体的保护方案”、“立法机关享有充分的形成自由”,都意味着宪法只是给出了政治活动不可逾越的规范边界,在此边界内政治依然存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妥协、游说、联合以及最终政治意志的法律表达都依然在发挥着作用。自始至终,宪法法院不会替代立法机关去规定法律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宪法裁判只对政治活动超越宪法秩序的边界进行约束。此外,在宪法审判中发展出来的“合宪性推定”以及法律解释中发展的“合宪性解释”的原则,实际上都是司法尊重立法在具体化宪法上的优先权的表现。这种避免权力僭越的谨慎与对政治的功能空间的尊重是原理相通的。
另一方面,即使对政治问题作出法律判断,也只能以法律系统所能容纳的路径进行。正如鲁曼所观察到的,在美国,司法审查所能够处理的只是“案件与争讼”(cases and controversies),也就是诉讼两造之间的具体争议,并不处理抽象宏大的判断。而在德国,个人只能基于“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害”才可以提起宪法诉愿并被受理。〔74〕鲁曼,见前注〔13〕,页462。换言之,法律系统所处理的只是适宜由其处理的事务,而应该由政治决定的领域依然留给政治。按照鲁曼的系统理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必须保持相对的封闭性,而不能任由其他系统的逻辑取代其自身逻辑而造成该系统崩坏,不同系统之间只会发生相互的“扰动”(例如法律系统对于具有案件性的政治争议的裁判),而各个系统的功能依然必须保留。〔75〕张嘉尹:“法的社会学观察:《社会中的法》导论”,见前注〔13〕,页16。
(三)宪法解释如何对待政治因素
上述关于政治是否会被取消的担心,应该说是来自教义学外部的质疑。这里还有一个来自教义学内部的质疑:宪法教义学如何保证其所承诺的法的安定性?如何避免宪法因其政治性而丧失规范性?这是因为,无论怎样为政治保留功能空间,宪法解释(宪法裁判)最终还是要对其是否逾越宪法边界进行判断,因而宪法教义学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政治因素。如果所谓基于教义学规则的判断背后不过都是来自实定宪法之外的政治判断,宪法解释的结果基于解释者政治倾向的差异而有根本性分歧,那么法教义学指向的目标——法秩序的安定性——还是否可能,宪法的规范性还是否存在?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分别分析:一个是政治理论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另一个是具体情境中的政治因素、政治后果的考量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
宪法的一般性、原则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宪法解释不可能仅仅依靠宪法条款的文字及其相互关联,而是经常需要政治理论的填充。博肯福德曾经指出,对于基本权利条款的解释经常需要借助特定的“基本权利理论”。所谓“基本权利理论”是一个关于基本权利的一般特征、规范目标以及内涵射程的导向性观点,〔76〕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Grundrechtstheorie und Grundrechtsinterpratation,NJW35,1529B(1529).总是以一定的国家观或者宪法理论为基础。在基本权利解释中利用某种“基本权利理论”(其背后是某种政治理论)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意识形态的补充(ideologische Zutat)”。按照博肯福德的概括,流行于联邦德国的基本权利理论有“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基本权利的制度理论”、“基本权利的价值理论”、“基本权利的民主功能理论”、“基本权利的社会国理论”等。如果不同的宪法解释者都依据自己所持有的政治观念去解释宪法,在法学方法上就无法控制宪法解释结果的巨大差异,宪法之下统一稳定的法秩序也就绝无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因素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判也曾被质疑并非法律判断,而是一种“基本权利政治”。〔77〕Klaus Stern,Idee und Elemente eines Systems der Grundrechte,HStR,Bd.Ⅴ,Rn.16。由于社会中的政治观念千差万别,如果在法学上不加以控制,就会出现如博肯福德所说的“宪法被降低为一个形式上的外壳,通过宪法解释这扇大门,各种异质的主张都得到了入口”。〔78〕Böckenförde,a.a.O.S.S.1537被政治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绑架的宪法判断是无法实现应有的法的安定性的。
为了克服这种颠覆法治的危险,博肯福德给出了被奉为经典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不能轻易地把来自法秩序外的各种政治理论引入宪法解释,而是要回到宪法文本自身,从文本中寻找宪法内在的政治理论。博肯福德认为,德国基本法的文本所内在包含的政治理论包含三个核心的观念:自由、社会国、民主法治国。〔79〕ebenda.如果需要对基本权利条款进行价值补充,也只能以“被设定”的政治理论为指引。这一理论建构的有力之处在于,它用宪法文本限定了可以被援引来解释宪法规范的政治理论的范围,使得超越实证法的、没有宪法基础的政治理论被宪法解释所拒绝。这使得一种外部因素的颠覆性影响最终被内化为宪法解释的内部问题,法学的基本立场得以维护,价值与政治判断的滥用得以避免。
而对于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具体情境(个案)中政治因素、政治后果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在德国被归入“结果取向的宪法解释”来讨论。极端的观点会认为,宪法解释的结果根本上决定于法官对结果取向的认识,而解释规则只是解释结论的论证工具而已。〔80〕参见刘飞:“宪法解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中心的宪法解释方法考察”,《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但同时,也没有人会主张解释结论可以超出解释规则的可能空间。对于此解释方法上的争议,此处无法充分展开。〔81〕上述刘飞教授的相关梳理详尽而富于创见,值得参考。但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案件裁处中,不难发现固有的法律解释规则对于政治因素考量的控制。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裁判的“社会主义帝国党违宪案”和“吕特案”中〔82〕分别参见张翔:“社会主义帝国党违宪案”,载张翔主编,见前注〔72〕。,都有着非常敏感的“反纳粹”问题,清算纳粹和重新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可无疑是影响案件结果的重要政治因素。但是,这种影响绝非直接以政治判断取代法律判断。相反,考察宪法法院的判断,是严格以宪法条款的阐释和固有的解释规则为论证边界的。换言之,这种政治判断受到了法律方法的严格控制,之所以解释结果有反纳粹的政治效果,根本上是因为宪法规范本身包含的反纳粹内涵,而对相关个人和政党的规制也是基于严格的规范阐释和论证的。而任何解释结论如果超越宪法文本和解释规则的客观可能性,最终都是无法被接受的。诚如论者所言:“并不因宪法的规范对象是‘政治’,就使宪法丧失规范特质。单纯的国家整合、取向于(不知由何而得之)个案适当解答的国家理性,乃至政治后果的考量,都不足以要求曲解宪法规范,以顺服政治的需求。”〔83〕陈爱娥:“宪法作为政治之法与宪法解释——以德国宪法学方法论相关论述为检讨中心”,载翁岳生教授祝寿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当代公法新论(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页736。
(四)宪法学术与政治权力的角逐
如何对待宪法的政治性问题,还涉及宪法学者对于自身所处情境的反思。宪法高度关涉政治,宪法学者的理论会对实际政治产生影响,各种政治力量也必然会寻求不同宪法学理的支持。在此,宪法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自己的理论何以仍然是客观中立的学术,而非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或者甚至沦为政治的工具?〔84〕同上注,页713-714。在前述的宪法守护者之争中,凯尔森就批评施密特不过是在用学术来掩盖其政治主张,是为“党派政治”的目的服务,在他看来,这种混淆既损害了学术,又因为非常容易被对手看穿而根本达不到政治上的目的。出于维护学术科学性的必要,必须“拒绝这种与政治之间具有诱惑力的纠缠”。〔85〕凯尔森,见前注〔60〕,页290。
如果宪法学因其政治性而向政治现实毫无保留地开放,那么在政治的洪流中,学术的中立与客观就根本无法保持。在这种意义上,法教义学的进路不仅指向法秩序的安定性,也指向宪法学术自身的中立性与科学性。将宪法这一所有政治力量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文本奉为中心,通过法学方法的严谨运用去解释和适用规范,甚至于排除那些自己在政治上同情但在宪法规范上无法支持的判断,宪法学术就不会成为政治的玩偶而保持高贵的精神力量。托克维尔曾把法律人称作司法贵族。这种贵族精神的核心就是“唯法是尊”的客观中立性,“法律与政治之间的紧张,经常会因法律人无偏见地继续坚持贵族统治的信念,使民主政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无知的或者过于雄心勃勃的行为得到缓和”。〔86〕洛克林,见前注〔67〕,页243。因此,“宪法学者应该与历史及政治理论家一样,对法律和政治都有所涉猎,同时却不混淆二者”。〔87〕马歇尔,见前注〔40〕,页15。
四、中国的宪法教义学:两个前提问题
前文对法教义学的一般特征、任务与方法、宪法教义学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宪法教义学如何处理宪法的政治性进行了讨论。但是,要在中国主张宪法教义学,还须回答两个特殊问题:
(一)宪法教义学是否以违宪审查制度为前提?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法教义学在实践层面主要指向法律的司法适用,也就是依据现行法对法律争议的裁判。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并没有司法审查制度或者宪法法院制度,依据《立法法》而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也一直未见有效运作。那么,既然在中国并没有依据宪法裁判宪法争议的制度,为宪法的解释和适用服务的宪法教义学是否就是不必要的,或者说,即使有也只是屠龙术?
在笔者看来,宪法教义学并不以违宪审查制度为前提。事实上,只要有依据宪法判断争议的需要,宪法教义学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法治发展到今天,许多法律问题都已指向宪法,需要依据宪法进行法律的而非政治的、价值的论证。笔者经常以物权法草案的违宪争议说明这个问题。物权法草案的违宪争议所涉及的当然也是价值问题和政治问题,但是既已被设定为一个法律争议,就不允许再以“保守—改革”、“左—右”之类的政治判断去做出回答,而是必须基于对宪法第12条、第14条、第15条等规定的体系性解释,给出宪法判断的规范前提。又如,在“副教授聚众淫乱案”的争议中,在法院已经依据刑法给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被告人仍然主张自己“有宪法上的自由”。此时,法律人必须能够依据宪法给出判断,包括被告人主张的自由究竟属于宪法上哪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以刑罚方式对其进行处罚是否违反比例原则。最终我们的结论应该是,刑法聚众淫乱罪条款或者法院对其的适用是否违宪,而不是被告人是否违反社会道德。类似需要在宪法教义学上进行分析论证的争议在当前是大量出现的,这里还可以举两个近期的争议。“天价乌木案”虽然在实践中是以民事争议的方式出现,但对这一争议的完整法律判断依赖于对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属于国家所有”中的“矿藏”和“所有”的概念的解释,甚至还依赖于对宪法第6条规定的分配制度内涵的理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引发了诸多争议,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决定”是否是《立法法》第8条所要求的法律。处理这个问题所要依赖的只能是基于现行宪法相关规范而建构起来的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教义学框架。这些例子说明,虽然我们没有有效运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但却存在依据宪法判断争议问题的现实需求。〔88〕我国台湾学者苏永钦观察指出,中国大陆的宪法学已经在走向“议题化”,并将此种变化与宪法落实其规范性的宪政要素联系起来,参见苏永钦:“走向规范宪法——从台湾的经验看大陆的选择”,载吴庚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政治思潮与国家法学》,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页246。
对于以上的这些争议,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政治立场甚至个人利益轻易地做出判断。但只要我们的目标是法治,是宪法第5条所宣告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立公权力受约束的法治国家,那么依据现行宪法而建构的、指向中国宪法问题解决的教义学体系就是必要的。
(二)现行宪法是否足以作为宪法教义学的文本基础?
1.正当性问题
如前所述,法教义学是以现行有效的法律为研究对象的工作,其目标在于实现实证法下的安定秩序。但是,法学又不可以完全无视实证法的正当性,现代法治也无法接受“恶法亦法”的极端实证主义主张。正如前文述及的拉德布鲁赫公式的内容:极端不正义的法不是法。如果实证法是极端不正义的,就不应该以之为基础进行法教义学建构。那么,在此意义上,我国现行的宪法是否具备足够的正义性,而足以成为宪法教义学的基础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存在已久的争议:“八二宪法”是不是一部好的宪法?
认为现行法律存在正当性问题或者至少是重大瑕疵,是我国许多部门法学科的教义学工作不能充分展开的一个重要主观原因。法律人习惯于把问题归结于法律文本的缺陷,进而不断主张修法。在宪法学中,也存在着各种修宪乃至毁宪另立的主张。然而,这种主张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由于实证法本身不断被质疑,从而基于实证法的稳定秩序难以形成,最终也损害了正义的实现。在笔者看来,仅就宪法文本来看,这部宪法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民主原则与代议制、法治原则、公权力受限原则(一切国家机关、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工等现代宪政的基本要素。尽管无人能够否定其中仍然存在正当性不足的内容,但如果将这部宪法看作“极端不正义的法”却无疑是过苛的。按照拉德布鲁赫的观点,即使成文法存在缺陷和争议,也应该被适用下去,那种站在极高的道德立场对存在不正确内容的法做根本性否定的主张,是缺乏合理性的。法律总有缺陷,不加区别地、简单粗暴地概括否定,只会导致法治秩序无法建构。相反,对于有缺陷的法,只要认真地适用,在落实法的安定性的同时,也可以满足正义的需要。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宪政都是从被公认为不完美的宪法开始的。例如,美国宪法在制定之初就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由于出任当时极端重要的驻法大使一职而没有参加制宪会议。在看到宪法草案后,他致信亚当斯、麦迪逊等人,指出“其中有很好的条款,也有很坏的条款”,并为宪法没有包含一个人权法案,也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限制而感到愤怒,甚至于认为当初赞成召开制宪会议是一个错误。〔89〕参见梅利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集》(下),刘祚昌、邓红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页1022-1030。尽管这部宪法最终获得批准,并在1791年补充了权利法案,但批评并未消除。又如,德国1949年基本法在制定之初也未获好评。基本法只是被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宪法,在德国统一后就会制定新的宪法。并且,在1969年德国联邦议会就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去研究“基本法的全面修订”。可以说,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宪政的典范国家,其宪法最初也是饱受批评的。然而,后世的美国人却会将自己的宪法视为是完美的,而德国人也会认为“基本法是一个值得我们充满自豪的文本”,并将其作为爱国热情的寄托,提出“宪法爱国主义”的口号。〔90〕参见(德)冯·多尔夫·斯登贝格:“宪法爱国主义”,陈克勋、赖骏楠译,《清华法治论衡》2009年第2期。何以如此?在笔者看来,违宪审查(宪法解释)和依据宪法文本进行的法学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法谚有之:“法律比立法者更聪明。”通过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法律自身的很多缺陷可以被排除,正义得以体系化、制度化地实现于社会之中。历史上的法家曾经批评强调法的道德性的儒家是“坐候尧舜”,〔91〕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309以下。如果我们总是批评宪法中存在的缺陷,而无视其中好的内容并以法律技术的手段使其得到落实,我们所期待的法治、宪政永远不会到来。
2.技术性问题
对于中国宪法学教义化的另一个怀疑在于:宪法文本中如此众多的政治性话语,如何教义化?例如,有人会质疑:教义学进路的宪法学如何处理宪法第一条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处理“党的领导”?
实际上,没有哪部宪法不是充满政治性话语的,而大量的法律术语原本就是政治语言。如果我们以一种教义学的思维对这些政治话语作去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这些话语完全有可能被确定规范内涵而转化为法律概念。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条款”作法律规范化而非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就会发现其在一个层面不过是要求实现“社会正义”,要求实现社会经济生活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衡。这一原则性的规范内涵在与其他条款结合后就会进一步具体化。比如,在将“社会主义条款”与“私有财产权条款”结合后,就有可能证成“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也就是私人财产权为了社会平衡的目标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限缩。这一规范要求落实到具体法律制度中,可能意味着:在公司法的领域,私营企业主不能仅仅出于个人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而经营企业,而是要顾及依赖企业生存的劳工的权益,在最低工资、劳动保障等层次上遵守国家的法律,并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让劳工共同参与企业的决策;在房屋租赁法的领域,出租人解约的权利以及调整租金的幅度和频率受到限制;在知识产权法的领域,著作权人必须接受某些出于公益目的而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并不能要求支付费用等。而所有的这些限制又要与财产权保障私人经济自主和个人生存的物质基础这一核心内容进行衡量,接受技术化的比例原则的合宪性审查。两个在价值层面根本冲突、在意识形态上根本对立的东西,完全可能被包括在同一部宪法之下。
当然,这种教义学工作无疑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极高的法律技巧。笔者对于前述的政治语词也并非有现成的解释方案。这里尝试对另外两个政治术语的法学解读提出一点思路:①对于“党的领导”的解读,似乎不宜将视野限定于宪法序言,而应该看到宪法总纲第5条第4款第1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以此种教义学的体系解释方法观察,则视党为超越宪法的主权者的解读似乎过于顺服于现实政治。同时,如果以历史解释的方法关注到第5条在1999年修宪时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不难对宪法约束政党活动的规范内涵得到认识;②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解释,如果结合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9条,也就是将“爱国统一战线”扩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则其区分敌我的斗争性几乎就已不复存在。魏源有言:“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这种源自道家思想的技道合一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正可用来类比法教义学的技术理性。
五、结 语
史家蒋廷黻先生有言:“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92〕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页323。讲求自由的学术居然尚有“纪律”?这种纪律其实无关乎学术自由,也无关乎学者的个人志业,而是与学科的任务关联。一个学科的任务决定了其基本进路,失此“纪律”,则无异于自我否定。另一位史家汪荣祖说:“历史是既往之事的记录,如何把往事真实无讹地记录下来,原是史家天字第一号的要义”,“若根本尽失,则史家尚存几何?”〔93〕汪荣祖:“重申历史学的本质”,载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245、239。固然,任何学科都可能在基本进路的充分发展之后走向僵化境地;然而如果根本无视此基本进路,则该学科就会崩坏无遗。
万物同理,即使追求怡情任性的艺术也要讲“法度”和“基本功”。闻一多曾言:“法度是书法存在的基本条件,”针对书家要“学诗”、要具备“书外修养”的主张,李叔同却断言:“须知书家不懂得书法的基本功,只是学诗,那是可耻的。”〔94〕转引自沈尹默:《书法论》,徐建融导读,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页2、导言。
于法学而言,教义学就是其“纪律”、“根本”、“法度”、“基本功”、“第一要义”、“基本进路”。何以如此,正是法学的任务——落实法治——所决定的。教义学的主张无意排斥其他的法学研究进路,正如拉班德所自我辩白的那样,他并不否认历史、经济、政治乃至哲学对于法律认识具有的价值,更无意压制这些方向上的研究,但如果法学不去探究实证法律素材,不去做逻辑的、体系的建构,也就不成为法学了。〔95〕参见陈爱娥,见前注〔83〕,页714-715;施托莱斯,见前注〔23〕,页460。马丁·路德也有过这样的当头棒喝:“一个脱离法律文本而夸夸其谈的法律人是可耻的,但更为可耻的是作为一名神学家却绝口不提圣经经文。”〔96〕拉德布鲁赫,见前注〔3〕,页118。引文参考了白斌博士的未刊译稿,特此致谢。言虽刺耳,但却引人深思。在笔者看来,在既有的成文宪法之下,将各种利益纷争和意识形态对立限定于规范的场域,将各种价值争议尽可能技术化为法律的规范性争议,是构筑社会的重叠共识并最终走向宪法政治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