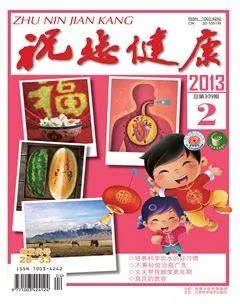莫言的宽容
“他是中国文坛超重量级的作家,他的文学才华、创造力、艺术能量在中国文坛上应该说是举足轻重、首屈一指的,因此我个人斗胆地说,莫言的高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对莫言的评价。57岁的莫言真的没让大家失望,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上世纪80年代初,莫言在河北的《莲池》发表了处女作,当时在《花山》当编辑的铁凝还从自然来稿中编发了他的第一篇散文。1984年莫言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老师的指导和文学热潮的刺激下,他悟到很多东西。《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使莫言名声大震,走向世界。
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除了极高的文学造诣和这种并非伪装的谦虚,莫言的身上还有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宽容。他提出,对新生代作家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他认为,年轻作家往往积累不够,没有相对可以上升到哲学的思想,但是他们确实非常认真严肃地进行着文学探讨,而且恰恰是他们追求了更多的非世俗的东西。他认为,再过20年,“80后作家”会成为创作主角,更年轻的作家也会发展起来。
这番宽容的话语无疑是给中国文坛的年轻力量注入了兴奋剂。在读书时,莫言同样有很宽容的心态。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彻底的。我们在读前人的作品时,往往能看到历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对前人的局限性,我们大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这种宽容里边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惋惜。我们潜意识里想:如果没有这种局限性,他们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现在我想,我们这种对人的局限的否定态度,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没有局限的人,也许不该从事文学;作者的局限,也许是文学的幸事。”
莫言出生在山东一个很荒凉的农村,因为贫困,他辍学回家劳动,正式学历只有小学五年级。虽然不能上学,但是莫言特别迷恋读书。没想到这样的爱好竟遭到父母的反对,家长反对他看“闲书”,是怕他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也怕他因看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有一次,莫言借到一本《青春之歌》,钻到草垛里,一下午就把整本书读完了。他从草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傍晚。由于耽误了放羊,他心里很恐惧,推测一定会遭到家长的责骂,可没有想到,母亲看看他忐忑的样子,只是宽容地叹息一声,那一刻,莫言心情好得要命。他也因此对宽容感触尤深。
莫言的宽容,还表现在出版社欠他稿费,他顾着朋友面子不愿去要。一次,他找人装修房子,钱花了,家里装修的效果一点不好,他也不抱怨,再找个人来重新弄。莫言都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追求,在他看来吃饱穿暖有地儿住,挺好。
创作至今,莫言的文字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前的尖锐、反抗渐渐在隐退或是藏在了幕后,而浮出水面的反而是一份平静下的波涛汹涌、沉思后的人生剖析。面对这样的变化,莫言自坦言:“年龄越大,我对他人的理解也更宽容了。”
《蛙》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曾获我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姑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她是乡村医生,几十年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而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则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
在台湾版《蛙》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对此莫言解释说,我们过去都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放大镜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人只要认识到灵魂深处的阴暗面,才能达到对别人的宽容。作为作家,应该对他人抱有同情。哪怕他是十恶不赦的恶棍,哪怕他无中生有地造我的谣言,哪怕他将唾沫啐到我的脸上。因为他本来可以成为好人的,成为恶棍,是他的最大不幸。如果能达到这一高度,才是真正的宽容,才能达到真正的悲悯。”
由此观之,宽容实为莫言成功的一种智慧。一直以来,我们对中国作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抱以宽容,在这种宽容的等待下,宽容的莫言终于走上了领奖台。(编辑汤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