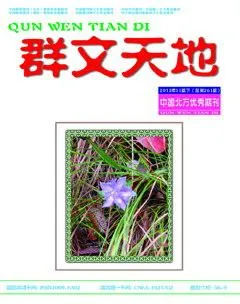东汉私学与豪强世族化
摘要:私学教育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教育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私学更是空前繁荣,并一度超越官学,成为重要的人才培养模式。私学的繁盛对东汉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豪强地主通过私学不断接受经学并最终完成世族化。文章拟从东汉私学繁荣与豪强热衷经学的原因,私学繁荣情况,豪强世族化过程三个部分来探讨东汉私学与豪强世族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私学;经学;豪强地主;世家大族
一、东汉私学繁荣及豪强世族化的原因
东汉时期,私学达到了一个繁盛期,而且在它的影响下,豪强地主逐渐向世族化过度。文章拟从以下几个原因来对这一现象做一个说明。
(一)经学复兴和以经致仕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前提
东汉时,刘秀为培养忠君人才,限制军功豪强,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 [1]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2]东汉一朝读经成为风气,使经学但得极大的发展。同时自汉武以后,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以明经为主,儒生只要通经,便可以入仕做官,甚至封侯拜相。“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经学不明,不如归耕。”[3]两汉时期,如要进入仕途,不管采用哪种形式,经学始终是最核心的选官标准。正是经学的复兴和以经致仕,才为东汉私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二)今古文之争,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学术需要
自西汉末年刘歆提出设立古文经学博士开始,今古文由于在经义上和治学上的风格和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今古文之争变得日益公开化和激烈化。到了东汉时期,今文经学独占了官方教育,但古文经学并未因此而退出。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而获得官方的认可,便坚持在私学中传授,从而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在今古文两派长期的论争过程中,两派除了希望通过官学途径发展外,“而更多地是借助私家传播的形式,聚众授徒,以至使得东汉私学的发展规模极大,盛况空前。”[4]
(三)东汉经学发展与官学不足的矛盾为私学发展提供了社会需求
东汉时期,由于经学的发展和选官的更加注重经学标准,使社会上读经蔚然成风,然而东汉当时的官学仍然承袭西汉的官学系统,主要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而且“东汉时期中央太学时兴时废,而地方虽有官学之名却无官学之实,许多郡县学校都久废不修”。[5]即使官学最为繁盛时,其规be6f841fe9971bac7ec5153e143e7fbf模数量,入学名额也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相对于官学的弊端,私学以其灵活性、广泛性,特别是儒学大师的加入而得以空前发展。因而,传经的重任慢慢向私学转移,私学教育成为传经的中流砥柱。
(四)东汉对豪强地主的压制与笼络使其寻求新的出路
东汉政权本身就是在南阳豪强地主力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东汉建立后,豪强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豪强实力的增加,势必会影响到东汉社会的稳定,故而东汉政府对豪强地主即利用笼络又压制其发展。豪强地主为了维持其家族利益的发展,不得不寻找一条更加稳定的道路进入东汉政权。东汉入仕以通晓经义为主要标准,故而当时豪强地主纷纷“通过演习儒术来改变家族的生存境遇,从明经入仕的途径以一种更被皇权接受的方式进入皇朝政治”。[6]
二、东汉私学繁荣的突出表现
东汉时期,私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盛极一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私学的数量多,规模大
东汉时私学繁荣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庞大。“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7]而且,“据学者统计,《后汉书·儒林列传》及其他传记所记载较大规模的私学共38家,受业弟子千人以上者15家,万人以上者两家,尚未计官僚士大夫之私学及家学。”[8]
(二)形成较为完善的结构体系
东汉私学自下到上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办学体系,该体系主要有书馆、乡塾和精庐或精舍构成。书馆是东汉启蒙教育的场所,王国维考证:“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书名曰书师。”并指出书馆“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9]之后,便可以进入乡塾,进行基本的经书学习。这一阶段仅要求学生掌握经书的大意,不求精深理解。最后就是精庐或精舍,要求专经研习。精塾与精舍的开设主要是通经大儒或著名学者。如“(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10]又如“(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11]
(三)经学大师与私学的关系密切
经学大师与东汉私学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汉的经学大师投身于私学教育。他们开设精庐精舍,广收学徒,宣扬学术思想,使私学成为传经研经的最重要的阵地。例如“(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12]而其他经学大师如楼望,蔡玄,魏应等皆开馆授徒,弟子少则千人,多着万人;二是私学中名家辈出,成绩斐然。《后汉书·儒林列传》所列名儒42人,有39人出自私学或直接兴办私学。
(四)私学类型多样和形式灵活
东汉时期,对兴办私学者并没有明确的身份限制,凡“通晓经义”者皆可设馆收徒。因而使东汉私学类型多样,大体来说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私学:一类是官僚士大夫私学,如楼望“建初五年,坐事左转太中大夫,后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13]一类是民间人士办学,如周泽“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14]还有一类就是家学。东汉私学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对地点和场合并没有特殊的要求。如桓荣既可“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也可“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15]私学的类型多样、办学灵活,大大的扩宽了私学的发展途径。同时入学者也无身份、地域、年龄的限制。正是这样,东汉私学才能繁盛一时,显现出无限生机。
三、豪强世族化的过程
东汉经学的发展和私学的繁荣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结果就是豪强世族化,本文大体把豪强地主的世族化分为两步:一是豪强的文化化,二是垄断文化传播,完成文化的家族化,成为世家大族。
(一)豪强的文化化
东汉时期私学繁盛,多名家大儒,官学所不能及。东汉豪强地主虽可以通过其社会地位进入官学,但是当时豪强研习经文,掌握经学多选择私学。豪强的文化化与私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豪强子孙游学各地,拜访名师在东汉几乎成为其掌握文化的通常道路。如南阳乡里著姓樊宏,其子儵“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16]又如南阳豪族阴氏,在阴子方时“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而到阴识时“识时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刘)伯升。”[17]再如当时的军功豪族马援一族,其兄马余之子马严“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18]河南豪族侯霸“家累千金,不事产业。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谷梁春秋》”。[19]
(二)垄断文化传播,形成世家大族
豪强地主通过私学方式掌握经学,完成家族的文化化后,为了家族长久利益,讲求家学,垄断文化的传播,形成世代相传的累世经学,即所谓的“传父业”、“修父业”等。陈寅恪曾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优美,不同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术之因袭。”[20]如东汉世家望族杨氏一族,在杨震时“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杨震受业于私学,而到了其子杨秉时“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其孙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曾孙杨彪“彪字文先,少传家学。”[21]再如当时大族袁氏一族,在袁安时“安少传(袁)良学。”其子袁彭“(袁安)子彭,字伯楚。少传父业”。[22]
东汉以经取士,豪强地主不断学经,进而由文化垄断变成仕途垄断,由世代传经变成世代为官,最终完成向世家大族的转化。同样以东汉的杨氏一族为例,杨震“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杨秉“代刘矩为太尉”杨赐“代刘郃为司徒,”“复代张温为司空”。杨彪“中平六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冬,代黄琬为司徒。”[23]再如被誉为四世五公的汝南豪族袁氏一族,“袁安官司空,又官司徒,其子敞及京皆为司空,京子汤亦为司空,历太尉,封安国亭侯,汤子逢亦官司空,逢弟隗先逢为三公,官至太傅”。[24]杨袁二族正是因为世代传经而成为东汉极为显赫的世代公卿家族。
四、结论
东汉时期的私学空前繁荣,并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豪强的世族化正是得益于东汉私学的发展。当豪强地主转化成世家大族后,对东汉文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上使东汉繁荣的私学逐渐转化成家学。政治上,世家大族依靠其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上影响力,垄断仕途。成为东汉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到魏晋南北朝时,皇权与世家大族相互妥协,形成当时特有的门阀政治。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2][7][13][14]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3]班固.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6).
[4]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3).
[5]蒋华.汉代私学以经学传授为主的原因[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5).
[6]吴桂美.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J].海南大学学报,2007(3).
[8]杨振梅.东汉经学世家述论[J].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4).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4(6).
[10]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11]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三·姜肱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12]范晔.后汉书·卷六十·马融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15]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16]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17]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二·阴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18]范晔.后汉书·马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19]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六·侯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2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
[21][23]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2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5).
[24]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