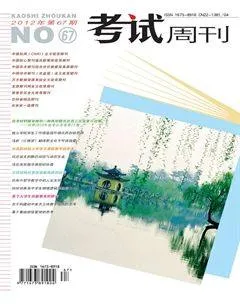试论语文的静态阅读与动态生成
语文教学应当是训练学生对一切文明符号理解力和创新力的活动。语文的理解力,即读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标准去体悟、涵泳、读解文字背后的丰富意蕴,去体悟作者之所以为文的真意,去揣摩作者表达、概括和思考的内涵,从而形成认识、理解、阅读、初步鉴赏的能力。
作家用文字编织的生命密码,能够穿越时空,感动读者的心灵,引起情感的共鸣。他们的笔下或嬉笑怒骂直刺贪佞,或婉曲含情直抒胸臆,尤其是那些人人心中有却是口中无的体悟,读来会倍感亲切,引起漫远悠思,像墨滴入水般慢慢扩散开去,读者的生活经验诠释、补充着作品,作家的作品濡化、熏陶着读者。读者通过与作者的穿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获得了丰富的审美享受,升华了感情,提高了认识。
作家的创作总是充满着激情的,没有哪位作者是社会的一个冷严的解剖者、观察者和描述者,社会生活在作家睿智的思考中总是融入了他们对生命的审视,对命运的拷问。据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创作时,常会和书中的人物吵起来;明朝剧作家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也曾痛哭流涕以至于昏倒在书房内。所以借朱光潜先生在转述尼采的话说,所有有价值的诗歌无不是和着血泪写成的。朱光潜先生倍加推崇李煜的诗歌,就是因为南唐后主的诗歌里流淌着的是对生命的拷问与真切的血泪。
但是,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因为对作家文学作品的诞生情境缺乏了解,再加上阅读者经验的匮乏,知识背景、鉴赏能力不足的各种原因,常常使阅读的过程呈现静态阅读形式。没有唤起生命体验的阅读作家的文字只是“文明的符号”。苏轼评价说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不哭是不忠,读李密的《陈情表》不哭是不孝,读韩愈《祭十二郎文》不哭是不友。读过此三文者的人很多,但是能眼含热泪的恐怕很少。苏轼一生备尝艰辛,坎坷不幸使得他对生命的体悟要超越别人,读这类文章更容易激起他的共鸣,而高中学生读这样的文章,因为缺乏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他们的感动可能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阅读的认识价值在中学生学习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他们的见识、阅历、心理的不完备,知识结构的不完善,需要他们去接受、去接纳,大脑甚至要暂时作为一个知识的容器去存储,去内化,去积累。因为思想和精神的存在不是空洞的,而是依托于语言的,语言的丰富性能够帮助成长中的学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阅读中接受某种思想,甚至这种精神成为自己的信仰,反过来又促进语言的学习。精神的形成和语言的学习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语文的静态阅读形式,也是由于教师对教材的处理方式。语文教材是专家编选,专家作注,教师引导解读,凝聚众多智慧的语文教材如同一位面目冷严的长者,很难唤起阅读者的亲切感、认同感,语文教材给人的感觉总是像板起面孔把所有的情感体验都变成了简单的说教,学生跟着教师亦步亦趋地拷贝着教师的传授留待考试时的复制和粘贴,很难在书中读出自己来。语文教育对文明符号的理解力偏执地被接受力过分地强调了,而创新力却被挤占甚至淹没了。教师把对教材的权威解释及自己的灌输给学生,学生在情感隔膜中进行着语文学习,只能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语文能力训练没有落脚点,理解力、思维能力训练也就没有着落。语文鉴赏审美能力、创造力的培养也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中成了镜中月,水中花。
但是,语文学习最终的目的不是接受,不是要把学生打造为知识的容器,而是要发挥语文的育人功能。语文的育人功能不能止于认识,而要通过语文教材来教,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能力。
作品的语言、立意、结构、思想、情感、精神总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由于阅读者的知识、经验、阅读、学养参差不齐,对作品的阅读更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更应采取民主而灵活的原则,撷取一点,生发开去,作为语文阅读动态生成有效尝试,在语文学习中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阅读文章之后,不会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一句话,一个词语,都会引起我们内心的波动,勾起我们模糊的零散的思绪,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着这思路,定下我们的思考,记下我们的探索,理清我们的思路,用线索将那些生命成长中的片断串起,如珍珠项链般光彩夺目。这样,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才能真正提高,灵魂才能真正被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