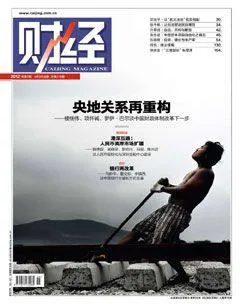蝗虫如何长出翅膀
2012-12-31 00:00:00马杰伟
财经 2012年9期

部分香港网民,称来港的大陆人为“蝗虫”。一位北大教授,称香港人为“狗”。“蝗虫”与“狗”,表面是意气之争,背后有着几十年的文化沉积。愈往深处探视,愈能看出曲折的香港身世。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中年,更是百般滋味在心头。“蝗虫论”在这场风波之中,作为标签、作为意象,有一个复杂的孵化和蜕变的过程。
我第一次知悉此说,是在年前。“蝗虫”是香港学生的暗语,矛头指向宿舍里的内地同窗。由共用冰箱中食物不翼而飞,到浴室厕格的不卫生行为,突然间“蝗虫”在私语乍现,流传于小范围的学生社群间,不满情绪都投射到这个无端冒出的恶虫身上。其实,在香港网络世界,多年来早已蝗虫横飞:流量极高的香港网上讨论区“高登”,年轻网民口无遮拦,批评大陆涌港生子的孕妇是蝗虫,反对大陆人来港消耗资源。但由于此说难登大雅之堂,亦惹族群仇恨,主流媒体避谈,直到两个月前民间矛盾白热化,“高登”社群捐钱集资,在报章刊登反内地孕妇广告,蝗虫隐喻这才公开化,引起新一轮的热烈讨论。记得事发之初,一位资深教授一头雾水,追问何为蝗虫?当他知道蝗虫系同学暗语后,愕然说,这明显是歧视行为,怎可能出自大学宿舍?广告刊出,八方争鸣;到如今蝗虫所指为何,人尽皆知,不再是只属于大学宿舍的次文化语言。此害虫在生物学上的流行印象,加上香港政策失误所引起的汹涌民情,促成“蝗虫”一词成为流行比喻。
一
隐喻变成明喻,蝗虫起飞,拍翼腾空闯入香港舞台。这种转变,有近因也有远因。其中一个触发点,是香港名店街的D&G风波。香港尖沙咀广东道名店林立,其中有意大利时装名店D&G,该店保安允许大陆游客拍照,却禁止港人按快门,并出言不善,对话及过程被摄录上载网络,引起极大回响。港人为表抗议,周末到D&G店外自由拍照,有人穿学士袍拍毕业照,有人推婴儿车来拍全家福,咔嚓之声不绝,人多得水泄不通。小风波赫然演变成城市奇观。此事件耐人寻味,背后有深层的文化暗涌。尖沙咀广东道为港人宝地,多年来华洋杂处,是雅致生活的场所;商场名店云集,展示华衣美服与钻戒名表;酒店餐馆棋布,活现小资的富裕生活。过去十年间,广东道在急剧变化。由于内地豪客一掷千金,在各店门外大排长龙,或站或蹲,甚至坐在路边高声笑闹,改变了整个名店街生态。街道变脸,打碎了优雅的形象。港人路过,看见满身名牌的内地游客,有一点酸苦妒忌,不足为奇。以前港人自视过高,不把内地同胞看在眼内,是不对的。今天内地富人三五年就富起来,部分港人不容易调节集体心理。但更多港人关心的不单是财富,而是公平、自由、文明、法治等普世价值。名店的不公平,被港人狠批,实为市井港民的小胜利。
港人流传,说广东话的本地客,常遭名店售货员冷待,因为港人“小家子气”,买得少,左挑右拣,半天不做决定。内地客呢,“噢,本季新款吗?给我十件!”然后拿出一叠一叠的现钞付款。售货员与保安员,渐尊外宾而轻港人。这几年,在港人心目中,广东道名店街已成为大陆豪客的天地,自家宝地失落之感油然而生。不少人觉得这儿本来是绮丽殿堂,今天已变成庸俗又媚俗的高消费旅游区。这次D&G拍照事件,与这种多年累积的文化暗涌不无关系。“高登”宅男,甚至现身广东道示威,弄出赶蝗虫的闹剧。
“蝗虫论”的另一个触发点,是近年内地孕妇纷纷来香港产子,孩子出生就领身份证。私家医院为内地孕妇接生,财源滚滚,只顾私利而妄顾公益。婴孩有严重健康问题,就送政府医院由公费承担。跨境产子热潮,已到了香港难以承担的地步。护士医生疲于奔命,连香港的孕妇也几乎照顾不来。更甚者,有孕妇在没有登记又得不到名额的情况下冲关,在婴儿快要降生的关头闯进急症室,医生基于人道主义不得不接生。近年香港医院产房婴满为患,新生婴孩的哭喊、港妇得不到照顾的怨懑、两地习惯不同而引起的磨擦,凡此种种的情绪火花,可说是蝗虫言论的温床。大陆孕妇的大量涌入,被很多港人视为对本地优质医疗服务的霸占。本地家庭真实体验到牛奶供应吃紧、产科病房床位短缺。
跨境出生的婴孩,领了香港身份证,其父母均非港人。近年来这一群体激增至一二十万人,不知会否来港久居,令人忧心长远的社会代价。香港实行中小学免费教育,不少学校英语教学、与国际接轨、部分中小学有英国殖民遗风、大学在国际上名列前茅,都会吸引此类孩童,跨境来香港读书者为数不少。这些“内地港孩”也许就寄居在香港的寻常百姓家,从此展开一页奇特人生。有些内地母亲用旅游的身份来港照顾孩子,也有一些在香港边界的深圳聚居,孩子每天过关到香港上学。早上7时到8时,深圳罗湖的一个景观,就是一群一群小学生像鸭子一样,背着书包、踩着球鞋,吵吵闹闹地跨境上学去。此趋势正反效应兼有。香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多了不同背境的孩童来港成长,有助于促进文化多元创生。但跨境上课也引起家教问题,教育体系增加了不明因素,香港家长亦有社会资源被争夺的负面情绪。港人和陆客之间的对立,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二
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香港媒体中的大陆人形象,并进行了十多年的港人身份认同调查,到2010年完成最后一次报告便终止了此项目。本以为香港回归中国十多年,身份问题已趋稳定,不必再一次研究考察。想不到最近又出现蝗虫论这个新发展,这挑起我多年从未有过的反思。一直以来,我都是从香港的视点回望中国内地。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出于对家乡、对中国那深入骨血的好奇。我在香港出生,家乡在广州花县。由于殖民教育,我对中国历史只有碎片式的认知。我成长于香港起飞的上世纪70年代,回乡探亲不觉得是回乡,反觉是异域探奇;深感香港优越、家乡落后贫穷。就算是亲戚,也当作外人。我这种个人经验,其实也是那个年代的写照。上溯半个多世纪,港人大都与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然而,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两地社会经济文化差距加深,这些亲密的血亲关系受到了压抑。从南中国移民香港的亲友被视作“外乡人”。于是,“我们”和“他们”对立,竟压倒了对于血缘关系的重视。
上世纪80年代,港人面对九七回归,心理既焦虑亦难以调适。我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去研究香港媒体上的大陆人形象。我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章,就是分析1979年播出的一部港剧《网中人》。此剧对香港普及文化的发展极为重要,它讲述了内地与香港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剧集里,一个典型的香港家庭,长子由港星周润发扮演,其弟阿灿突然从大陆偷渡来港,阿灿其貌不扬、不学无术、好食懒做,只会拖累家庭。剧中的这个弟弟“阿灿”,与父母兄姊,本是一家人,却被单独拉出来,成为一个土头土脸的大陆人。奇怪的是,此电视人物“阿灿”,竟化作污名,成了港人对大陆人的统一称呼。“阿灿”一词,一叫20多年,可说是“蝗虫”形象的“母体”。当年南下的大陆人,有文人雅士、有阔少大亨,当然也有劳苦大众,但由于内地与香港的生活差距,“阿灿”这个脸谱人物,被拿来代表所有大陆人,是沿用整整几十年的巩固形象。“阿灿”这一称呼的流行,说到骨子里,就是压抑血缘关系,扩大“他/我”对立,甚至掩人耳目,视亲人于不顾,把兄弟看作陌路人。
我研究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互动多年,万想不到,我的家庭就是现实中的《网中人》,我在分析大陆人的形象,却仍被巨大的文化积习迷糊了耳目,对自己家事也视而不见。我一家六口,家庭合照却只有五人——父、母、姊、妹与我,经常把第六个家人——我的哥哥,排除在外。他国内出生,长年企图来港而不得,活像电视剧中的那个阿灿,而学者如我,竟然多年来不自觉地把他视作外人。我就是我所撰写论文的主角。个人就是难以逃脱时代的定见。
三
1979年“阿灿”以丑角出现。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回归问题触动香港人的焦虑,加上一些跨境匪徒来港持械行劫,造就了“省港旗兵”一词,不时在日常用语中出现,反映出当时的恐惧心理。大陆匪徒在一系列“旗兵”电影中,手持强大军火,直攻香港闹市大开杀戒,既把港人的焦虑情绪戏剧化,亦加深港人对新移民的歧视。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回归前夕,则出现一系列“表姐”电影,“表姐”“表叔”等新称号流行坊间,泛指大陆特权人士,穿凉鞋、着丝袜,尽管外表仍然俗气、仍随地吐痰,不过却有权力有才干,与香港人有血缘关系,可以做好朋友、好拍档。
到九七后,大陆人的形象在香港媒介中转趋多元。1999年至2002年,导演陈果拍摄了《细路祥》(1999)、《榴莲飘飘》(2000)和《香港有个荷里活》(2001)等一系列与身份认同相关的电影。故事中香港人与大陆人的互动比以前更为复杂,香港人走到内地,内地人来到香港,各式各样的爱情、友谊、婚姻和背叛,成了电影的主轴。
除了电影,电视剧中的大陆人角色,亦不再被贬低为丑角或反派。90年代,较突出的例子是无线电视的长篇处境剧《真情》,连续五年以上,于黄金时间每周播放五晚。2005年和2008年,《真情》也曾在每周日间回放。该电视剧成功塑造了由薜家燕出演的“好姨”,这个来自内地的角色,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最受爱戴的电视人物之一。像“阿灿”一样,好姨自内地来港与家人团聚。她刻薄、计算、与在香港生活已久的母亲常生冲突。好姨带着女儿来港,为求生活无忧,强迫女儿嫁给一个香港有钱人。从上述情节看来,好姨好像与阿灿一样急功近利。但随着故事发展,她渐渐变得硬朗、聪明、又有同情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好”姨,香港观众开始接受她。自此,演绎此角色的薛家燕,一直被称为好姨。这部长寿处境喜剧,正好点明了内地人形像的明显改变。与早期电视剧中的内地人物不同,好姨的广府话不带内地口音,谈吐和衣着也与香港人无异。事实上,香港人大都忘记她刚从内地来港,而倾向认同她属于香港成功故事的一部分。
自2000年后至今,电视剧中已再无突出的内地角色可与阿灿或好姨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大多看来已如普通香港人一样,不再引起社会注意,亦没有给观众留出内地与香港差异的想象空间。
四
也许出于身份好奇,在九七回归大陆之后,我己不满足于分析香港电视与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十多年来,我一步一步走入陌生的国内城市,深圳、东莞、广州、上海、北京,努力做田野调查,表面是学术研究,心底也许是追寻自我的文化根源。我才发现,那些阿灿、表姐、好姨的角色,只不过是适用一时的幻象。当我逐步深入国内的社会现场,我对中国的种种定见,如洋葱白衣,一层一层脱落:中国有愚民、有暴发户、有朴实民工、有修养比香港教授高雅十倍百倍的文人学者、有新兴的中产阶层我在学术生涯中梳理自己的矛盾,完成最后一个国内的研究项目之后,本以为解开心结,却突然出现了蝗虫新论。
这篇随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只想指出,内地人与港人的文化磨擦,复杂多变,而且深深触动了多年积习。比如说,蝗虫论近月己经淡化,影子犹在,新的插曲又突然响起。网上传说,港人俗称“拐子佬”的骗子出没香江,躲在暗角拐带小孩,港孩危矣!他们是跨境集团、是自由行犯罪分子、是讲普通话的内地怪客。传闻是传闻,但也成新闻:小学生真的报案去,指校门外有可疑人物!坐在电视机旁的香港小市民,马上想起深圳的种种可怕故事:孩子不见了,被卖给富人,更惨的是沦为小乞儿,在路边讨钱讨吃。港人以为“拐子佬”十面埋伏,却原来,警方澄清了,没有小童失踪,不少案例是误传,也有的是误会。例如国内游客,见小学生站在街边,上前以普通话慰问,仅此而已。唉!虚惊一场。有趣的是,误传与误会,为什么迅即流传大小媒体,而不少公众信以为真?更甚者,警方澄清不到几天,网上又疯传耸人听闻的新故事——警方发现被挖空内脏的童尸,器官被卖往内地。此无稽之说,竟甚嚣尘上。
人类学家有所谓“城市传说”(Urban Legend)的说法:某些故事,市民特别上心,可说是击中社会要害,轻易成为热门话题。拐子传说,配合蝗虫论的流行印象,社会情绪是会感染的,港人对跨境威胁特别敏感,风吹草动,容易轻信流言。九七之前,香港有一个更加无稽的城市传说。当年港人忌怕回归,想起重投祖国怀抱,就焦心莫明。当年有个电视广告,宣传铁路接通港穗。广告中有小孩子搭胳膊玩“火车开行/火车开行”的小儿游戏,很纯真的画面啊,却有说小孩口角滴血,都是鬼魂。如此脱离情理的花边故事,当年竟成大新闻,广播电台以此编撰鬼故事,《壹周刊》做了封面专题。还有传闻指出,记者到内地去找广告中的小演员,发现各人均已不得好死。地道港人就是觉得,接通香港与内地的轨道上,总是重重魅影。可见香港这几十年来,对“内地”总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阿灿如是、鬼火车如是、蝗虫也如是。此其中,多年累积,虚虚实实,千头万绪!
五
近年来香港各大学愈来愈多国内学生,一些是以资优成绩考进香港的高材生,一些是自费来港的富家子弟。这些学生都冲击着港生的自我形象,论财富与才能,港生往往不如内地生。当然,香港学生对自由、廉洁、法治、人权方面的耳濡目染,也有一种特殊的本土气质与尊严。但今天内地与香港的高调交流互动,已难概括出稳定的文化形象与边界。
港生与内地生的隔阂与矛盾,不会蔓延到我这个老师身上吧。我是这样想。但蝗虫论辐射力强劲,老师亦被波及。让我谈一下两次个人经历。春节期间,我到香港机场附近的东荟城走了一圈,惊觉整个商场变成“陆客城”,人头汹涌,几乎所有人都在讲普通话。售货员都先是自动用普通话的,见顾客中有港男港女开腔,才转用广东话。商场是“香港地”,但已“人面全非”,按人数计,绝对是内地同胞的购物乐园,普通话是第一语言。从港人角度,真有香港商场“沦陷”之感。我就听到身旁的港女们窃窃私语地抛出一声“蝗虫”。
但我学生的另一个经历令我再三思量。这学期我带一个研究生小班,其中一个女生就写来一份东荟城实地考察。她本身是内地学生,在港读本科,今年已是第五年在港。她曾带国内父母到东荟城购物,她坐在商场长椅上,大包小包放在地上。一个港女走过,有意无意踢她的购物包。再过一会,同一港女又走过来,再次“踢场”,并不屑呢喃——“暴发户!”内地学生回想起来,虽事隔多日,在我们面前,也是气愤难平:“我在港五年,不插队,乖乖的,你这个港女,凭什么?!”尤其是国内父母到香港探望宝贝女儿,竟目睹这难堪一幕。我从这位内地学生的眼睛去看,的确为她难过,也为文化矛盾而神伤。她是半个香港人了,还是被骂被“踢”。但反过来看,港人自己的地方,改变市容以迎合大陆来客,不满之情亦可以理解。
第二次难忘经历是一个简单的访问。内地学生以记者身份访问我,不好拒绝。但15分钟的对话,情绪有如打乒乓球。开口第一问:“你是否同意香港只是中国其中一个普通的城市?”看似平常的提问,背后多少心生不忿与强烈质疑。几十年的歧视,压在这提问的刀锋。我冲口而出,说,“到目前为止,香港还是一个独特城市!它的法治与自由,仍能感召人心。”显然,言词背后,也背负了多年的文化期许!第二问:“由阿灿、省港旗兵,到今天的蝗虫论,港人是否歧视大陆人?”第三问:“国人富起来,香港人是不是看不过眼?20年后,香港是否最终会被边缘化而成一个普通城市?”一连串追问,一个香港老师,一个大陆学生,有如两只草蜢,被置于蝗虫辩论的背景下,草蜢本是良善,却不能独善其身,蝗群拍翼,我们都逃不过它所引起的情绪漩涡。我收拾心情,好好回答——“港人多年来歧视大陆人,是不对的!20年后,我希望香港仍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我希望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各有特色,都不普通,各自有本土的独特性格。”
“蝗虫论”伤害感情,我不能置身事外。在了解与访谈之间,我渐渐发现,我研究内地与香港文化角力这么多年,仍然难以掌握这个诡异多变的现象。香港学生都玩Facebook,里面充斥“蝗虫”及其变种,大量批评、讽刺、咒骂内地人在香港的种种不文明行径:插队、炫耀、吐痰、在路边大小便然而,由国内用户主导的微博世界里,其主流意识却是,香港只不过是中国一个城市,受中央照顾,柴米油盐,皆来自周边,因殖民多年不认祖,反视大陆同胞为次等人正如那位被骂的内地学生所说,你们凭什么! Facebook与微博,两个世界,两种香港形像,两种家国认同,彼此可否搭一道沟通的桥梁?
时代变了,香港、内地,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若我们以过去的视野看今天的对方,擦枪走火,爆出来的偏颇言论,如香港人是殖民文化孕育出来的应声狗、大陆移民与孕妇是“袭港”、“祸港”的蝗虫,这些愚昧低俗的指控,不仅基于当下矛盾,亦有积累多年的形象倾斜。香港特区政府实属不智,其人口政策失误,令闯关产子的孕妇加深香港与内地文化矛盾;其城市规划失误,让一个一个香港黄金地段化为游客特卖场。内地与香港交往日深,整合有利,亦有磨擦。今天我们怎能不反思积习?须知道,昧于文化身世,不解社会变迁,最终忘记了进步必先有自省。整合与分化、国族与本土交杂在一起,“他”和“我”搏弈,在香港的日常生活中若隐若现。如何相处相依,让暗涌化活泉,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考验。
马杰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著有《影视香港——身份认同的时代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