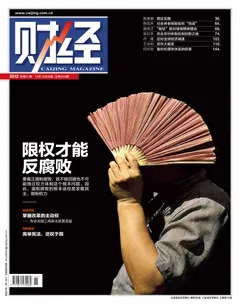大众伦理中的“幸福”
2011年9月,全国开学的主题是“守望幸福”,中小学生共上幸福课,纷纷在学校里谈幸福体会。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前期,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走基层的记者们分赴各地采访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在内的几千名各行各业的人员,向他们询问“你幸福吗?”
“幸福”随即也成为媒体的热门词汇。向普通人敞开“幸福大家谈”和“幸福随便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虽然哲学家、伦理学家经常讨论幸福问题,但幸福一直就是一个似乎大家都有话可说的大众伦理话题。
“幸福”为何成为大众伦理
18世纪-19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幸福观,他对幸福和快乐的关注全面地影响了好几代普通民众,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大众伦理。
这首先是因为功利主义本身相当简朴而易于理解,说的是大多数人都自以为已经懂得的道理。功利主义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幸福,而幸福是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的。每个人都想要快乐和幸福,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出发,功利主义思想家推导出一整套关于“好”的、可以用“幸福”来表述的道德理念。如边沁所说,“功利,或者说最大幸福原则,认为行为的正确性与其增进的幸福成正比,错误性则与其增进的幸福反面成正比。幸福意味着快乐与没有痛苦;不幸福则意味着痛苦与缺乏快乐。”
功利主义能成为一种大众伦理,第二个原因是它给人以“科学性”的印象,让人们觉得幸福具有可度量的确实性和精确性。边沁提出,幸福和它的反面痛苦在其主要方面都是可以核定的:强度、持久度、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是否由某种行为或政策所产生)、近或远、产生(是否有可能造成其他快乐或痛苦)、纯粹性(快乐不会引起痛苦,痛苦不会引起快乐)、范围(可能影响到多少他人)等。
功利主义出现在一个人们向往科学,对科学抱有一种几乎是无条件信任的时代。在功利主义之前,伦理学往往把“善”归因为上帝的诫命、人的理智推导、人性的实现或是服从某种绝对道德命令等,而这些给人带来的却常常是关于什么是诫命、理智、人性或道德命令等的疑惑。只有功利主义似乎可以用一种人人都能懂的标准来测量每一种行为或政策。这个标准便是,一种行为或政策是否能让人觉得快乐。
在边沁那里,功利主义的伦理思考是与18世纪-19世纪英国的许多现实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是为当时的社会改革实践提供哲学和伦理支持。这是它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又一个原因。怀特(Nicholas White)在《幸福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Happiness)中指出,幸福哲学,也就是量化享乐主义(quantitative hedonism)“不仅将伦理与科学结合起来,而且还将伦理与我们今天所泛称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结合了起来”,“主张量化享乐主义,为的是用测定不同政策所能产生的快乐的不同的量来解决一直存在争议的伦理问题”。用科学方法来为快乐或幸福计量,并以此来为解决社会问题制定政策,可以让广大国民对政策的正当性、透明度、民主价值和公益性质口服心服。
因此,功利主义思想家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怀抱社会改革之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怀特所说,“他们都希望,也都相信,(功利主义的幸福学说)可以让他们影响社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那就是,增加幸福的量”。边沁是一个社会改革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如《政府片论》(1776)、《为高利贷一辩》(1787)、《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1789)、《争取宪法》(1803)、《议会改革问答》(1809)。边沁不仅写下这些著作,他还亲身介入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辩论,一直是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
作为“本质之善”的幸福
把快乐确定为最终的善,把痛苦确定为最终的恶,这样的哲学观使得普通民众觉得明白、实在、亲切而可以接受,其中还包含着一种他们能够理解并接受的“本质之善”(intrinsic good)的观念。什么是“本质之善”呢?为了评估一个行为或政策,我们需要分辨什么结果是好的(善),什么结果是坏的(恶)。这里的善和恶不应该是个人的好恶印象,而应该具有公共标准。善和恶都可以分为“工具性”和“本质性”两种。工具性的善只是手段,例如,刷牙这种行为是一种工具性的善,刷牙有利于清除牙垢,清除牙垢有利于避免牙疼,那么避免牙疼又是为什么呢?人们一般不问这个问题,因为“不牙疼”不需要再对什么“有利”,避免痛苦本身就是最终的利、好、善。这就是功利主义所认为的“不痛苦就是本质之善”,而痛苦就是“本质之恶”。
功利主义者的行为规则以一些关于人性的假定为基础(与霍布斯和洛克所持观点类似)。他们认为,所有人的本性都是相当一致的,他们都在进行着理性的计算。理性的个人首先是由人的自我利益,或者说自利心所推动。功利主义哲学所面向的就是这种个人,他们试图通过运用自利心来寻求自我实现。功利主义者认为,快乐是好的,所有人都是追求快乐的动物。
因此,人的行动就以个人寻求快乐、避免痛苦的欲望为基础。他们认为社会不过是各个多样化、各自独立的部分(也就是构成社会的、原子式的个人)的总和。
把快乐视为本质之善,把痛苦视为本质之恶,这并非肇始于边沁。
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驳斥过这种看法,可见这种看法在当时就已经广有影响。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270)是最早从“本质之善”(最高的善)来看待快乐的。他认为,人的生活应该是善的,而“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幸福和快乐是不再有其他目的的善,是人生的目的和伦理的最终目标。
人不能在不知道痛苦或不在乎痛苦的情况下了解什么是快乐和追求快乐,因此,伊壁鸠鲁把快乐首先确定为避免痛苦。他说:“所谓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快乐包括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
一是要排除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以及其他使灵魂不安静的因素,以实现心灵的宁静;二是快乐又必须是实际的感性的,必须满足身体必要的物质欲望,这种满足以身体无痛苦为限,而不是恣性纵欲。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快乐理解为一种无痛苦状态,既不求锦衣纨绔,也不贪饫甘餍肥,只要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便不再是不快乐和不幸福了。这种低要求的快乐与幸福已经很难为今天的大多数现代人所接受,他们不会因不受冻馁之苦便知足常乐,而是要追求他们心目中的更高快乐和幸福。
幸福的标准与测度
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虽然主张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幸福的,而幸福便是获得快乐和免除痛苦,但他同时也说:“当一个不满足的人要比当一只满足的猪要好,当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比当满足的傻子要好。”满足带来幸福,那么猪或傻子的满足给他们带来幸福吗?对此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感觉的(又称主观论),另一种是理智的(又称客观论)。
感觉论的回答是,幸福不是哲学推理,“幸福”只是表达一种关于快乐和满足的主观感受,因此,谁感觉到自己的需要或欲望得到满足,谁就可以说是幸福。
理智论的回答是,只有按照客观的“好生活”的标准和价值所确定的那种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需要有自我意识,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否则便不能算是幸福。
感觉论的幸福不都等于猪或傻子的幸福,因为对幸福的感受也可以是包含价值的,当一个人觉得他所认为是有价值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或者他的欲望合理地接近于某种价值时,即使不能用客观的“好”来衡量,他仍然可以自称幸福。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哲学教授琳·麦克弗尔(Lynne McFall)在《幸福》一书中举了五种感觉幸福者的特殊例子。第一种是“幸福的白痴”,他不动大脑,也没有动大脑的需要,整天乐呵呵,吃饱喝足倒头就睡,无忧无虑无烦恼。
第二种是“幸福的瓶盖收集者”,他的愿望和生活目的就是成为世界上收集瓶盖最多的人,这是他经过思考后确立的人生目标。当他认为自己已经收集了非常多的瓶盖(是否确实如此则另当别论)时,他因此觉得非常满足而幸福。这种人包括其他“一门心思”从事专一爱好的人。
第三种是“幸福的受骗傻子”,设想一个女子爱上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其实是个坏蛋,而且根本是在玩弄这名女子。她非但不知道上当受骗,而且觉得非常幸福。希特勒时代的许多被洗脑的德国人就是如此。
第四种是“幸福的不道德成功者”,他们或是像希特勒、卡扎菲、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独裁者,或是飞黄腾达的贪官污吏。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作恶,也没有罪恶感,他们在信众的拥戴或自己的成功中感觉到幸福。
第五种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怀有某种高尚、美妙的理想,为了某种完美的正义事业、全人类的幸福、实现某某主义,即使为之付出痛苦的代价,乃至饱受牢狱之灾,甚至丢掉性命,也还是觉得幸福。
麦克弗尔指出,我们对这些人所感觉到的“幸福”往往会有颇为矛盾的直觉反应。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并不“真正幸福”;但另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又不能说他们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是相当程度的满足。如果我们同意,“幸福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此而已,它最重要的特征是相信自己得到了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并且得到了与这种相信一致的快乐”,那么我们便没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五种人不幸福。
在理智论者看来,上述五种人的幸福都不符合“好生活”的标准,“好生活”要求人的全面自我实现,包括身体、心智、价值判断、成熟理性。人在肉体的本能需求之外还有精神和心灵的需要,因此浑浑噩噩是一种脑死状态,玩物丧志是一种心灵锁闭,上当受骗是一种变相奴役,不道德的成功是腐败之恶,不切实际的理想是非理性的虚妄。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人在自我实现道路上的障碍,那种主观感觉的幸福其实不过是幻觉和自我欺骗的结果。
理智论者的幸福观虽然能对感觉论的幸福观提出价值质疑,并对极端的感受主义有所制衡,但这种价值观却也很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绑架,成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革”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便是一个例子。正是因为思想统治用权力武断规定和强行灌输的价值来代替本该在公共社会中通过人们理性思考来形成的价值共识,与人的全面自我实现有关的幸福观念变得难以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以提升幸福感为目标的施政方针就更需要从建立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开始,而不是绕开价值观来急急忙忙地做实证的幸福评估。幸福不是一种个人陈述(你觉得幸福吗),幸福应该是一种评价(你真的幸福吗?你的好生活标准又是什么?你期待怎样的幸福)。
绕开价值观的幸福评估总是把幸福设定为一些满足物质欲望的数字指标,如20平方米的人均住房、每户一辆汽车、1万元的人均月收入、70岁的平均寿命等。这些数字可能是幸福的测度,但并不是幸福的标准。这就好比我们用温度计只能测得温度有多高,而不能用它来提供关于温度的标准。水烫并不是因为温度计的读数是40℃,40℃只是测出水有多热,但不是“烫”的标准,如果“烫”的标准是70℃,那么40℃便是“不烫”。
同样,满足物质欲望的数字指标不是幸福的标准,而顶多不过是某种“幸福”的测度,如果幸福的标准需要在物质之外添加公民权利、道德修养、心灵自由的话,那么纯物质性测度显示的便不是幸福,而是不够幸福或根本就不幸福。
作者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