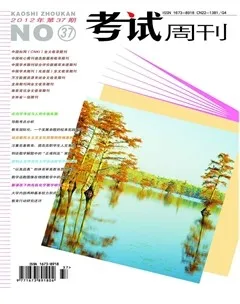扑火的飞蛾
摘 要: 《欲望号街车》是美国戏剧大师田纳西·威廉斯的一部力作。该剧女主人公白兰琪,作为南方女性的代表,向来是评论家关注和争议的焦点。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原理,结合细致的文本分析,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入手,对造成白兰琪悲剧命运的成因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 戏剧《欲望号街车》 白兰琪 男权社会 南方妇道观
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称得上是二战后美国最杰出的剧作家,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四次获得纽约剧评奖和道诺森奖,代表作有《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作为迄今为止唯一获得美国戏剧三大奖项的作品,《欲望号街车》以其精细巧妙的构思、委婉细腻的文笔、生动饱满的人物和丰富深刻的思想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誉。该剧女主人公白兰琪,作为南方女性的代表,向来引起关注和争议。对导致白兰琪悲剧命运的根源,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本文旨在运用女性批评的基本原理,结合细致的文本分析,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入手,对造成白兰琪悲剧命运的成因进行深入剖析。
一、悲剧的外因:无所不在的男权社会
女性主义者之所以要争取妇女的平等、独立、自由,就是因为父权制社会中不平等的性别等级制度。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文艺批评家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被公认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批评的一部成熟之作。米利特认为:“‘政治’……是指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1](P32)“政治的本质是权力。”[1](P34)“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是一个群体(男性)对另一个群体(女性)的全面控制。”[1](P33)所谓“性政治”,即用来描述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压迫和歧视,在两性之间确立男权制的等级关系的状况——这与政治关系中的统治、压迫和歧视并无二致。“性政治”中的不平等,造成了长期以来女性无可逃脱的悲剧命运。
《欲望号街车》中处处可见男权占统治地位的表现,而剧中的白兰琪就是一位被压迫的女性。白兰琪原本是南方贵族的后裔,但由于接连遭受丈夫自杀、亲人辞世和家道中落等一系列精神重创,从此变得一蹶不振。她选择了放荡的生活以麻痹神经、排解孤独、满足欲望,最终声名狼藉的她不得不投奔住在新奥尔良的妹妹斯黛拉,以开始新的生活,但与妹夫斯坦利愈演愈烈的矛盾最终将她对新生的憧憬化为泡影。
妹夫斯坦利是战后美国社会的典型人物,他意志坚定、性格粗野,是权力的载体,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欲望号街车》中,威廉斯对他的描述是:“自他成年以来,生活的中心就是沉溺于女色。无论是给予是获得,不是被动的依赖性的纵欲,而是像一只羽毛丰茂的雄鸟,威武自傲地傲立在一群母鸡之中!”[2](P29—30)他周围的女人——斯黛拉和白兰琪毫无疑问是他的臣民;而家就是他的“王国”,他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他多次在餐桌上咆哮着告诉斯黛拉:“别用命令的语气跟我讲话!”[2](P155)暗示着发号施令是男性的特权;当妻子请他帮忙收拾餐具时,他把一只盆子扔到地上,说:“这就是我收拾桌子的办法!再也不许这样跟我说话!猪猡——波兰佬——恶心——粗野——邋遢!等等字眼一直挂在你嘴边,这类话你姐姐在这里也说得太多了!你们俩以为自己是什么人?一对皇后吗?记得胡夷·朗说过,每个男人都是国王!我就是这里的国王,可别忘了这一点!”[2](P155—156)接着又愤怒地将盘子打碎,用这种粗野的方式界定“女人应该做的事”。受过良好教育、举止温文尔雅的白兰琪却从骨子里瞧不起平民出身、语言粗俗、举止无礼的斯坦利,把他说成是“石器时代的遗存者”、“猿人”,说他身上有种“低于人类,还没有进化到人类阶段的习性”,[2](P98)并力劝斯黛拉离开他。斯坦利感到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财产都受到了严重威胁,而白兰琪正是这个“王国”的侵入者。为了保卫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下定决心要把白兰琪从他的地盘上清除出去。为此,他开始暗中调查白兰琪,并将她不光彩的过去向米奇和斯黛拉和盘托出。斯坦利不仅以男权社会的道德观为利器无情地摧残了米奇和白兰琪的爱情,还试图挤掉她最后的一点生存空间,给她买了一张返回劳雷尔镇的单程汽车票。在斯坦利的步步紧逼下,白兰琪无处逃遁,精神濒临崩溃。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就在斯黛拉住院待产的那个夜晚,斯坦利肆无忌惮地强奸了白兰琪,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摧毁了她。
法国女作家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分析指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的文化中,男性总是被理解为积极的一方,代表着常态和普遍的人性;而女性则具有第二等的形式,是常态之外的“他者”,不拥有明确的意义,而只能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来获得定义。女性总被认为是被动的,只该消极等待男人的选择,在两性关系中是被统治、被支配者。[3](P57)白兰琪正是在这个男权文化的左右夹击中挣扎求生的“他者”,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从表面看,是残忍的斯坦利强暴了她,是虚伪的米奇侮辱并遗弃了她;但真正摧毁白兰琪的力量却是“现代社会里各种野蛮残忍的势力”,[4](P62)是男权社会中僵化的传统道德观念活埋了她。这只“白飞蛾”被男权社会恣意侵犯、凌辱,在男权社会的不断挤压下逐渐失掉了生存空间,最后被剥夺了活下去的权利,不得不遁入疯人院了此残生。
二、悲剧的内因:如影随形的南方妇道观
《欲望号街车》一剧中,男女主人公斯坦利和白兰琪的矛盾贯穿始终、不断升级,据此不少评论家把斯坦利看成白兰琪的毁灭者,而没有深究其悲剧的真正根源。其实,白兰琪的悲剧早在她和斯坦利见面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尽管斯坦利——这个被父权文化熏陶和造就的“男子汉”——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与白兰琪冲突不断,但他充其量只是加速了白兰琪被边缘化的过程。该剧的著名导演卡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她(白兰琪)的问题在于传统——她自认为妇女应该怎样。她沉溺于这种‘理想’,这就是她,她的本我。她只能这样,否则她就无法生存。”[5](P212)所以说,真正的原因出在她自身。她屈从了南方妇道观强加于其身的社会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这才是酿成她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
白兰琪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南方种植园家庭,在密西西比州拥有一座有白色柱子的大房子——“美梦庄园”,生活无忧,接受的是南方淑女式教育。纵然“美梦庄园”在父辈和叔伯兄弟的纵欲中就这么从她的“手指缝里流走了”,[2](P27)它却是白兰琪生活的原点,是她所有戏剧行动的发端。在分析白兰琪的悲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她生长的那块失落的南方土地。
虽然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但种植园文化并未随着黑奴制度的废除而迅速消亡,它的阴影一直笼罩到了威廉姆斯笔下这位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的南方女性白兰琪上。在她成长的那片南方土地上,庄园主尽情享受奴隶们的劳动成果,即使那些自耕农,也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独立不羁的生活,这样就养成了一种自由放任习气和享乐主义人生观。但与此同时,南方的居民,尤其是妇女,在内心深处却又受着严格道德准则的约束,是某种程度上的清教主义者。“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地位都直接反映社会的本质”。[6](P301)种植园的经济结构使妇女对男子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她们长期脱离实际劳动和种植园的管理活动,成了依附于男人或供男人享乐的玩物。南方妇道观将这些白人妇女都调教成所谓的“大家闺秀”。她们必须举止风雅、谈吐得体,具有仪态万方的大家风范;南方妇女分内的职责之一就是要让男士觉得赏心悦目,所以即使是大家闺秀也要学会适当地在男士面前卖弄风情以博欢心。因此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到清教徒主义与享乐主义的奇特混合。《欲望号街车》中的白兰琪,不仅体现了清教徒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混合,而且体现了其冲突。
作为一个深受南方价值观念熏陶的女性,白兰琪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南方淑女的标准。直至她的同性恋丈夫艾伦自杀前,她一直是个守“规矩”、守“妇道”的女人。她画地为牢,界定女性生存价值就在于“取悦她的绅士”[2](P120)、在于“可以无限地丰富男人的生活”[2](P185)。她不仅自觉遵守这条男权主导社会的自然法则,而且乐此不疲。为取得男人的欢心,她对自己的形象在意到几乎病态的地步,对他人的评价十分介意。就连最了解她的妹妹斯黛拉也承认这是“她的小弱点”,[2](P37)并请求斯坦利多迁就她。白兰琪来到新奥尔良刚见到妹妹时,就抱怨妹妹没有就她的“外貌发表过意见”,[2](P18)并以“十年以来没长胖一盎司”[2](P19)而自夸;她从不愿意和米奇白天出去约会,即使在夜晚也只喜欢昏暗的灯光,因为借此可以掩饰脸上的皱纹;她对服饰和香水的搭配十分讲究,出现在别人面前时也一定要补补妆,擦擦粉。白兰琪之所以刻意追求青春和美丽的外表,是因为她渴望被男性欣赏,从内心深处认同并迎合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要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是这样描述女性地位的:“她们是男人的镜子,有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她们唯一的作用便是满足男性的需求。”[3](P67)像白兰琪这样的传统妇女,由于受南方妇道观毒害太深,为造就淑女形象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束缚扭曲自己,而事实上,她们已经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沦落为供男人欣赏、享乐的精美而易碎的玩偶。
白兰琪不仅视“取悦男性”为南方淑女对男士应尽的义务,而且在精神上、物质上依附男性,缺乏独立性,这正是铸成她悲剧的直接原因。自从丈夫死后,白兰琪过起了放荡的生活,艾伦的死标志着她堕落的开端。那么,对视贞洁为生命的白兰琪来说,是什么导致了她的堕落呢?白兰琪曾对米奇真诚地忏悔道:“我觉得恐惧,是恐惧驱使我不断换人,到处寻求保护,一个接一个……东找西找。”[2](P174)丈夫死后,她不顾一切地依附于各种各样的陌生男人,以寻求保护以获得安全感。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既不坚强,又不能自立。软弱的人,弱者只好乞求于强者,希望得到一点点光和热……我为得到保护而奔波。”[2](P108)她以这样的方式“填补心灵的空虚,”[2](P174)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些男人只是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在劳雷尔镇上她“像美国总统一样闻名,只是任何人都不尊敬她”。[2](P142)她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更是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斯坦利正是据此将白兰琪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席,彻底摧毁了她对新生的希望。“堕落的女人”白兰琪最终被撵出了劳雷尔,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来到新奥尔良投奔妹妹,可她依然没有停止向男性寻求荫庇。她将米奇视为自己“停靠的港湾”,希望借助他摆脱压抑窒息的环境。甚至在她深陷绝境、最为无助的时刻,她仍将求助的双手伸向男性:为了避免被斯坦利奸污的噩运,她拼命地给旧日情人谢普·亨特利打电话求救。让人遗憾的是,白兰琪把投入某个男人的怀抱以摆脱另一个男人的威胁看成是她寻求安全的手段。她追求光明的途径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父权制社会里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思维模式,因而注定了其最后悲惨的命运。精神上柔弱的白兰琪在经济上也依赖男性。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地位是女性丧失社会地位、遭受压迫的主要根源。白兰琪与逆来顺受、消极适应男权社会的妹妹斯黛拉不同,她不甘于屈从男性权威,多次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与男权抗争,甚至鼓励妹妹离开粗野的斯坦利,和她一起创造新的生活。可是,经济上的拮据令她在现实世界里寸步难行,她只好自欺欺人地幻想起那位百万富翁——谢普·亨特利——也许可以助她一臂之力,给予她经济上的援助。幻想终归是幻想。失去了“美梦庄园”,失去了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白兰琪只能寄人篱下,忍受妹夫对自己种种无礼的举动甚至蹂躏。
不难看出,白兰琪是个依赖性很强、离开男性就无法生存下去的女性。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揭露性别压迫的真相时指出:“妇女对男性的依赖,不是出于生理差别,而是男性文化强制行为的结果。”[7] (P367)白兰琪之所以“总是依赖陌生人的善心”,[2](P210)正是由于南方传统文化中鼓励妇女依赖性的一面造成的。布兰奇有意遵循男权社会设定的女性价值标准,认同男性主导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努力使自己在体格上柔弱、精神上依赖和在性欲上的单纯。然而,也正是她所认同的所谓女性特征——柔弱、依赖性,使得她在失去丈夫后在性问题上堕落,不断寻求陌生男人的关心,最终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迷失自我而被无情淘汰。
四、结语
南方那温馨宜人的气候、悠闲富裕的生活造就了许多像白兰琪这样的南方女性:她们崇尚浪漫,但软弱孤独、缺乏独立进取的精神。在男权文化的凝视下她们艰难挣扎,绝望斗争,但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无法对抗父权制社会对人性的亵渎,只能最终隐退到梦幻的世界里,寻求解脱。威廉斯借白兰琪这个悲剧人物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通过《欲望号街车》这部作品,威廉斯旨在向世人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相爱、理解和宽容,再次说明平等的两性关系对于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凯利·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田纳西·威廉斯著.冯涛译.欲望号街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4]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4)[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Kazan,Elia,John Orr.Tragic Drama and Modern Society.London:Macmillan,1985.
[6]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7]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