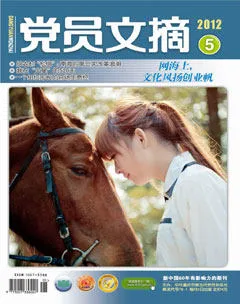王跃:我在“火星”的520天
“……爸,我要关机了,一年半后再打给您。保重,照顾好妈妈……”
2010年6月3日清晨,俄罗斯,一个小伙子在给家人拨了这通电话后,便进入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闷罐子”里,从此“人间蒸发”520天。
莫斯科时间2011年11月4日下午2时,全世界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个“闷罐子”——“火星500”试验舱。在那里,六名来自四个国家的年轻勇士,终于结束了人类首次全程520天封闭模拟的火星之旅,“重返”地球。
那个一年半前打电话的小伙子,就是参与这项国际航天试验的唯一一位中国人——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教员王跃。
想吃“螃蟹”的“80后”
1982年出生的王跃是标准的“80后”。2010年1月30日,踏上俄罗斯土地的王跃,没想到自己最初“上火星”的兴趣,将日益演化成“鸭梨山大”。
王跃是代表中国为参选“火星500”项目而来。“火星500”是由俄罗斯组织、多国参与的一项探索火星的国际试验,是人类首次在地面上模拟飞往火星、环绕火星、登陆火星和返回地球的全过程。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着迷?
因为在地球的“近邻”中,火星的自然条件最接近地球。这让各国科学家认为,人类有望在若干年后,将火星改造成“第二栖息地”。火星,也理所当然成为人类继月球之后的下一个着陆点。为此,美俄等大国已开始“发力”。2009年,美国放弃以月球为中心的“星座计划”,把深空探索的中心转移到火星上。
但是,人类要像阿姆斯特朗登月一样,在火星上“留下第一个脚印”,又何其艰难:火星距地球至少是地月距离的145倍,往返需要一两年时间。如此漫长的深空探索,对人类的航天技术、生命保障技术,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能做到吗?
这次俄罗斯组织的“火星500”项目,就是要在全球选出六名“先驱者”,为人类全程模拟探索火星“吃第一只螃蟹”。
而当时27岁的王跃,就特想做吃这只“螃蟹”的人。
“报名时是凭兴趣,当层层淘汰到只剩我一个中国人时,入选就成了责任”
回忆起自己的报名动机,王跃笑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航天梦。”
但光有梦想不够,王跃要想成为“火星六勇士”之一,必须跟全球4000名同样怀抱梦想的志愿者进行残酷的“淘汰赛”。
经过过五关、斩六将,2010年1月底,王跃从国内70名参选者里脱颖而出,站到了莫斯科进一步甄选的舞台上。
强中自有强中手。按俄方“魔鬼要求”筛选出来的各国志愿者,虽说都不是职业航天员,但脑力、体力个个不俗。在选训时,每隔几天就会有几名志愿者“消失”。2月,王跃发现自己成了11个“仅存硕果”里唯一的中国人,“压力瞬间达到峰值”。
“在国内,选不选上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在俄罗斯,只要有中国人在,也无所谓。但当只剩下我一个中国人时,被选上就是一种责任。”这个在父母眼中“不声不响、但关键时刻特有主意”的“80后”坦言。
对“火星500”,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陈善广曾评价说:“这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重要国际试验,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跟上!”作为航天大国,中国不能缺席这场“盛宴”。王跃心里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
于是,在被野外生存训练、特殊技能培训、实验项目训练、语言训练“轮番轰炸”的最后两个月选训期里,王跃“发飙”了——
尽管被俄方饮食折磨得口腔发生溃疡,但为了配合完成“盐分摄入”试验,硬吃;尽管俄语里的弹音怎么卷舌也发不出来,但为了团队交流,硬学;尽管唾液采集、睡眠监测等实验“黏糊糊又难闻”,但为了尽快掌握,硬做……
其实,相比11进6淘汰赛中最残酷的部分,也就是在零下20摄氏度的森林里进行野外生存训练,这些都不算“玩命”的。
试验前83天,王跃所在的六人小组接到任务:在雪地里呆至少24小时,次日中午11点到达指定地点。食物、水自己解决,每组只带两把斧子、一把刀和一盒火柴。
俄罗斯的冬天,曾让拿破仑的军队望而生畏。但最后,王跃他们胜利了。“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多好,但我绝对没给咱们中国人丢脸。我有好几次摔倒在雪地里真不想爬起来,可还是咬着牙告诉自己:中国男人,不能倒下!”王跃在日记里写道。
最终,在入选“火星六勇士”的一排名字中间,出现了一个简短的名字:王跃,来自中国。
“我一定会坚持到底,万一出现不测,必须在我清醒的时候,征得我个人同意,才能安排我出舱”
在模拟舱内的520天,根本不像想象中那样美好。
没有离地升空的刺激,没有穿越太空的激动,“长途跋涉”后也无法看到一个新世界。一旦进入这个550立方米的“闷罐子”里,就只有横亘一年半不辨昼夜的密闭空间、日渐“延迟”的天地通讯、仅能维持基本生命的食物和睡眠。此外,还有高负荷的实验任务和体能训练。里面除了每人3.4平方米的私人空间和洗手间,随时都有摄像头在捕捉他们精神崩溃的蛛丝马迹……
王跃入舱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领导们叮嘱他说:“小伙子,实在顶不住了,就出来。”王跃点点头。
但中心驻俄试验队发现,王跃留给他们的是另一个承诺:“我一定会坚持到底,万一出现不测,必须在我清醒的时候,征得我个人同意,才能安排我出舱。”
“其实,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觉得自己本来就比较‘宅’,好挨。后来发现,这跟‘宅’根本不一样。”王跃回忆起在“闷罐子”里的时光说,“那是只有我们六个人才能理解的压力与孤独。”
压力首先来自繁重的实验。模拟舱内,“火星六勇士”的首要任务是“随时测试自己”。
王跃在日记里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从早8点到晚10点,每隔2小时采集一次唾液,并完成4份测试,耗时30~40分钟;在另外不到1.5小时的时间里,要做体育锻炼、尿样采集和心理测试;晚6点开始,要佩戴红色眼镜,一直戴到第二天上午11点;睡觉时也没闲着,要测呼吸和进行睡眠检测……”
更无形的压力,是来自身心上的:在往返“火星”的520天里,饮食每阶段依次是土豆、罐头和粉末食品,这对习惯喝热水、吃炒菜的王跃而言,堪称“一天比一天折磨人”;为了防止心血管失调和肌肉萎缩,六人必须在舱内完成魔鬼式身体训练;碰到最“销魂”的负重跑步,“汗水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到处飞溅”……
最难熬的是孤独。尽管有五个同伴,但“与地球隔绝”的孤独感是刻骨铭心的。没有电视、互联网,每天从局域网传来的两封邮件,是来自“地球人”的全部信息。由于试验全程模拟“太空延时”,到第350天时,通讯已延迟了20分钟,一来一去两句话要40多分钟,怎能没有“流落到茫茫宇宙”中的怆然?
想象这样的生活持续一年半,你会怎么样呢?至少,王跃不是超人。第46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压抑、烦躁”;第118天,“越来越有一种空洞的感觉”;第154天,已经“麻木了,像机器人一样,前方似乎是个黑洞”;第304天,“灵魂好像被抽走了”……
但王跃从没想过要“提前退场”。
“往小了说,入舱时我们六人有约定:‘同进,同出’;往大了说,我已经向国家承诺了。承诺作出了,就要兑现。”
王跃兑现承诺的方式,就是尽量快乐地“死扛”着。
俄方规定,志愿者在舱内可以无理由地拒绝参加任何实验,但时常睡不好、掉头发、“体重快降成仙了”的王跃,一样没落下;舱内电脑是俄文系统的,“文盲”王跃就从零学起,硬是没影响一项实验进度;舱内体能训练,是按“吃肉长大的”欧美大块头的标准设计的,比如,负重跑步的定额是4000米,但最瘦的东方“大瓣蒜”,没比别人少做。
凭责任感“死扛”之余,抚平焦躁也需要快乐的支点。六人中,队长的支点是睡觉,意大利人迭戈的支点是用自编软件更新Twitter,王跃的支点最特别——写书法、看专业书、期待“洗澡日”。“我不去想520天有多漫长,我只以十天为一个单位。每坚持到十天后的洗澡时间,对我就是一个新开始。”他说,“这样化整为零地接近终点。”
王跃的表现征服了摄像机后的眼睛。这些挑剔的眼睛负责在“抵达火星”前一个月,从“火星六勇士”中确定三名佼佼者,模拟登上“火星”。
最终,王跃成为这1/3。2011年2月18日,他穿过连接登陆模拟器与“火星”的过闸段,首次代表中国,把足迹拓展到了“火星”表面上。
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出舱时,身高从175厘米缩到了172厘米,体重掉了十公斤,头发基本接近“荒漠”。
“当不起‘了不起’这三个字,但我们做了件‘很棒很特殊的事’”
直到现在,王跃也不认为自己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
“相比真正的航天员,我们的艰苦,其实随时有退路,而他们的每次升空都是生死考验。在他们面前,我们当不起‘了不起’这三个字。”王跃认为。
但这位“80后”也不妄自菲薄,提起“火星500”试验,他的评价是“这是件很棒很特殊的事”。
“火星500”试验的成功,证实了人类可以在模拟太空环境中经受一年半的隔离,不同文化与民族的人可以和谐共处、通力合作,而且工作状态、身体健康可以保持在一个好的水平,舱里的硬件设备也经受了考验。“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前景论证。”王跃表示。此外,六人在520天内完成的105项科学实验,其医学设备和诊察方法,有的对未来、有的在现阶段就可能得到应用。“从这个角度说,‘火星500’至少是目前为止,我经历的最棒的一个试验!”
如今,在王跃的柜子中,珍藏着他在“火星500”试验舱里身着的蓝色航天服。它正等着被若干年后的王跃再次穿起,把鲜花与接力棒交给后面的人。
(王景义、冯兴方荐自2012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图:廖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