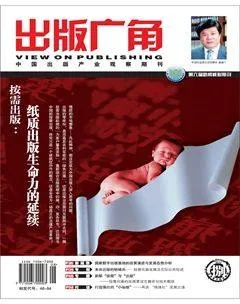饥饿与餍足时代的阅读
作为人,其实真应该好好享受这种人较之非人更其为人的享受,而不必非要等到物质短缺的饥饿时代才肯想到它。
在“高级老头”北岛老师“充满了可感性细节”却不免被视为怀旧的《城门开》里,有篇《读书》,读来不免令人心有戚戚焉。
北老师说,“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今天的少年,甚至上推十年二十年的孩子们,似乎并不把阅读作为生活的需要,而至多是消遣。今天孩子们好奇心的淡薄,或许正可以与阅读的缺失互为对应乃至表里。因此,他们的生活中少有惊喜,于是也就少有淘宝的快乐。
北老师的阅读入禁,可以看做是他开蒙的真正起点。这样的起点,如此“始于十岁,一直持续到十七岁”的“秘密阅读”,该说不愧成就他后来写诗的成色,或者说不愧让赵振开成为北老师。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许多少年,并没有亲睹乃至“私有”他那般奢侈书单的机会。
与北老师年纪相仿的张木生先生,是在杜润生身边工作过的“红二代”。在一篇访谈中,他也提到:“只有在‘文革’这种状态下,读书的范围可以大大超过学校教育,而且都是兴趣读书,无聊读书。天下第一快事就是雪夜无人读禁书,也就只有那时候的农村能做到,黄泥小屋,油灯一盏,思维能力、记忆能力都达到最强。”
当然,北老师的禁书阅读,实际上发祥于城市,与张木生先生所云略有不同。不过两人的阅读,都十分富有那个时代的元素或曰印记,这应当也是令如我辈之心有戚戚焉的原因所在。这就涉及了一个有些吊诡的问题:当文化产品处于短缺状态时,往往刺激大众的文化饥渴,说白了就是,越是找不到书看的时候,大家的求知或者阅读欲望反而越强烈;反之,当文化产品处于滞涨的餍足状态时,物质的堆砌却遏制了大众对文化的饥渴,也就是说,当身边堆满了书的时候,阅读欲望偏偏退化消解乃至丧失。
这样的对比是鲜明的:北老师、木生先生的时代,满面菜色的青年,舍弃半个月乃至几个月的菜钱买下自己心仪却难以买到的书,私下传看的书,不论是文艺的还是政治的,不论是灰皮、黄皮还是白皮的,都会用近乎疯狂的热情去读。而今天书店里的书,不能说真正的丰富,但得到书的难度几乎没有。然而,月入几千元的白领,也未必有什么买书的预算,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在喝酒抽烟泡妞之外,并不会打入买书的开销,阅读或许正因为物质的堆砌而远离人们的生活。生活的优裕的确抚平了今天的人口腹乃至肉体的饥饿,但同时也抹杀了他们消化系统及其他什么系统的饥饿,尤其是和肉体若即若离的精神饥饿。
这其中自然有时代营造的因素,毕竟,相对处于静态的阅读,与完全属于饱和动态的奔跑,是不大容易搭界的两种生存样貌。痴迷于竞速的人们,无暇或者并不屑于沉下心来从容阅读。又或者,物质的堆砌,足以开列出种种诱人的消遣品种,这些品种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愉悦,起码从刺激烈度层面来看,远在阅读之上,因而令人弃阅读于不顾。相比短缺时代,物欲的选择,的确是一个让人纠结或者来不及纠结的问题。
不过,更深层次地观察,不难发现,这之间,根本的还是在于,社会的氛围缔造出的对于阅读之于生活的价值判断。也就是,阅读在人的生活中究竟担任什么角色。
阅读作为一种自发的行为,当然有取与舍的不同选择,不读书毋宁死,即便在短缺时代也不方便作为一种口号流行。不过,即便在物质堆砌的当下,人作为一种生物体,不可能始终处于奔竞的状态,疲劳实在是身体的一种警示,提醒停下来休息是维持继续奔竞乃至延续生命的必需选择。而那些足够外化的诱人消遣,沉浸久了,厌倦也一样会笼罩心头。如同吃多了油水过大的肉食之后,清淡的白菜豆腐不失为调整肠胃的荣养,对满身疲惫和镇日厌倦的人们来说,阅读也许是一副不错的调理品——这自然是十分功利的劝诱,富有浓郁的当下色彩。
实在说,阅读之于人的生活,其实是救心的,是人之所以区别于非人的所在,起码是十分重要的所在之一。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包括高级动物,尚未闻有能够阅读的个例发生,正像北老师说的,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作为人,其实真应该好好享受这种人较之非人更其为人的享受,而不必非要等到物质短缺的饥饿时代才肯想到